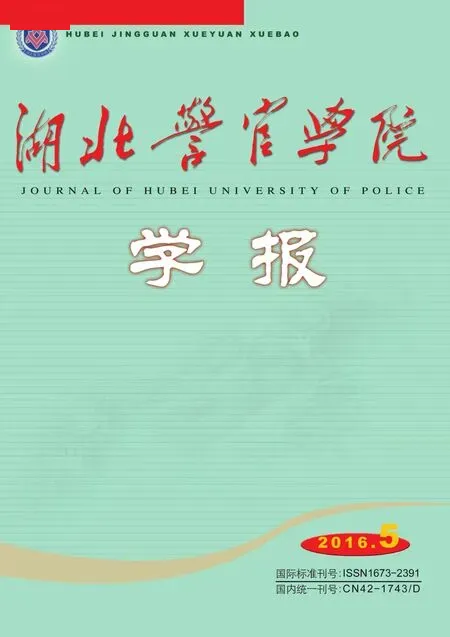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研究
陈世伟,石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研究
陈世伟,石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联名信作为民意表达方式之一,在刑事案件中并不少见。但何为联名信,联名信的地位究竟如何,联名信能否影响刑事司法裁判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联名信具有朴实性、非专业性、易受影响性等与一般民意相同的特点,应被审慎对待。但联名信又具有案件结果与联名者的密切相关性、客观性、全面性的特征,并且联名信的部分内容能够反映与案件及当事人相关的信息,从而可以影响量刑。司法裁判者负有嫁接起朴素道德观念与法治价值的重任,因而既不能对联名信视而不见,也不应对其曲意逢迎,而应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与信任度。
联名信;民意;刑事司法;量刑
对普通大众而言,联名信并不是陌生事物,而屡见于新闻及报刊杂志之中。据学者调查,基层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中有5%的案件会出现联名信等相关材料。[1]联名信是民意表达的方式之一。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在学界讨论已久,但论者的视角往往集中于网络舆论、媒体舆论等大众舆论与司法的关系,鲜有人着重研究联名信对司法的影响。随着权利意识的高涨,民意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凸显,公民的表达意识愈发强烈,联名信就是民众表达对审判的建议的方式之一。若法院视而不见,置民意于不顾,就会削弱公民对司法的信任感和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度;若全盘接受,则会损害司法的独立性,牺牲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尽量避免模糊。只有确立明晰的标准,才能获得信服与尊重。本文通过分析与研究上述关于联名信的问题,探讨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
一、刑事司法视角下联名信的解构
(一)联名信的基本含义及内容
联名信又被称为请愿书或请求书,最早可追溯到古时的“万民书”或“民间上书”。“上书”现象起源于战国,兴盛于汉代,是指官僚队伍以外的其他人员以“布衣”身份向皇帝直接上书[2],目的主要是言事、求官和诉冤。在现代社会,联名信的含义则更加宽泛,指多人参与签名的、对同一件事情发表共同一致的主张的信件。收信的主体不限于政府或国家机关,甚至可以是学校、商家和个人。而在刑事司法领域,联名信则是指以多人的名义联合发出的,表达所有签名者对某一案件共同的主张或意愿的信件。
经过学者的调查统计及分析,联名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陈述部分和请求部分。陈述部分分为两类:一是当事人个人情况,包括案件当事人的个人品德、日常表现、家庭环境等;二是与案情相关的情况,主要包括案件起因、犯罪动机、危害后果、被害人过错以及其他关乎定罪量刑的情况。请求部分则分为四类:一是反对指控,即对定罪和量刑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人无罪。此类情况占收集案例总数的22%。二是程序要求,即对定罪和量刑均不表态,而提出一些程序要求,如公开开庭等。此类情况占收集案例总数的8%。三是宽大处理,即认可定罪,但在量刑上要求从轻处罚被告人。此类情况占收集案例总数的64%。四是严厉惩处,即认可定罪,且在量刑上要求从重处罚被告人。此类情况占收集案例总数的10%。[3]可以看出,联名信的内容主要是当事人的个人情况、联名者所知的案件相关情况以及联名者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建议。
(二)联名信的特征
民意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4]联名信作为民意表达的方式之一,天然具有与普通民意共同的特征,但又因其群体范围的大小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具有区别于普通民意的特性。
1.与普通民意相同的特征
(1)朴实性。古语有云:天理、人情、国法。人情就是公众的情理。民意离不开人情,亦可说是民众情理的表达。本质上,情理是道德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道德观念的体现。正如学者所言:“情理反映事理和常情。它源于并体现民众道德情感,反映社会的道德观念。”[5]社会的道德观念往往是一种“朴素的正义”。人们心底的正义观质朴而感性,往往也缺乏理性。例如,“恶有恶报”“一命抵一命”等观念在民众的道德观念中早已根深蒂固,他们也习惯于将自己代入受害人的角色,从而对被害方产生同情,对加害方产生憎恶。但是,法律并不是只站在受害人一方,而必须保护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法律应当具有宏观的思维,进行全局的考量。例如,对于最近被热议的“贩卖儿童一律死刑”的话题,在数十万网友的网络投票中,80.6%的网友表示支持。[6]在这场论辩中,许多法律学者都对“贩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弊端进行了论证与说理,但换来的回应往往是民众的不理解。他们质疑法律学者置百姓利益于不顾,与他们心中的正义背道而驰。实际上,正因为民众习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思考,对于犯罪行为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憎恶,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组成国家、政府,建立法制,就是为了设立一个比我们个人更高的存在,而不是任由个人的正义和复仇心泛滥”。而在联名信中,联名信的书写主体多为被告人的亲朋好友或亲近的同学、同事。他们因为与被告人存在交情,往往容易代入被告人的立场,或者对被告人产生同情。所以,联名信中的内容往往也带着人们朴素的情感,使联名信中的民意难以保持中立和客观。因此,有时朴素的正义感与法治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着隔阂与鸿沟。当然,质朴的正义观、道德观往往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心理基础,但一个真正公正的裁判却并不只考虑这一个因素。
(2)非专业性。纵观大多数案件,不论是民众舆论还是媒体报道,他们的判断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或法律精神,往往也没有对案件进行严密的法律论证,更不会像公安机关那样通过调查取证获得案件信息。他们对于某一案件的判断和看法多依据自身对案件粗浅的了解,而且一般社会公众缺少法律专业知识,也很难了解法律规定所考量的各方因素,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尽管民意反映了公众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但往往失之于简单化、偏执化、情绪化,[7]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冲突由此显现。
(3)易受影响性。普通民众对案件的认识往往源于媒体或周围人的信息转述。夸大的、歪曲的或者带有信息报道者个人情感和主观态度的信息易影响人们对案件的看法。如在复旦投毒案案发几天之内,在犯罪嫌疑人未被锁定的情况下,众多报纸和网络等媒体就对案件进行了各类主观性报道,让民众对案件结果预先作出了结论。由于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较为激烈,人们“仇富、仇官”的心态也较为强烈,许多媒体抓住这类心理,在报道中特意将报道方向引向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仇视、对滥用权力的官员们的痛恨等,使人们把对案件的理性关注演变成不理性的情绪发泄。另外,民意有时也会被利用。2015年7月,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了一个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调查,自2012年7月以来,该律师事务所先后组织、策划、炒作包括黑龙江“庆安事件”、郑州十人被拘事件等40余起敏感案事件。根据嫌疑人供述,他们就是利用制造事端、在网络上炒作的方式煽动舆论,以达到打赢官司的目的。这些手段十分隐蔽,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被利用的一方。
同样,写联名信的群众也很容易受到他人言论的影响,尤其是与当事人较为疏远的人,很难对消息的真假进行自我判断。在大部分人意见“一边倒”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此外,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也可能会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收买民众。这时的民意已经被扭曲。它包含了特定主体的利益需求,易对量刑结果造成恶劣影响。
2.区别于普通民意的特征
(1)案件结果与联名人具有密切相关性。据统计,在递交联名信的案件中,发生在乡村社会的占70%。[8]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约有6亿的人居住在农村。大多数农民聚村而居,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9]大多数人认为,民意对于司法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某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但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亲密度远高于城镇居民。刑事案件发生之后,经过村民的口耳相传,便能传遍全村。所以,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也能如投入池中的石子一般,迅速在一定区域内激起人们关注的涟漪。这也是联名信大多发生在乡村社会的根本原因。普通民众关注案件的热度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消减,但绝大多数联名信的签名者与当事人具有一定的亲缘、地缘或业缘关系,从案件发生至审判结束,他们的关注都不会停止。对于法制宣传力度薄弱的乡村而言,人们对法律最直观的感受来自案件的审判结果,案件的结果也将直接影响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服。由此,裁判者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审理案件将比在其他情况下背负更大的压力。
另外,联名者关注案件结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密切,更是因为案件结果与他们直接相关。刑罚裁量所考量的不仅仅是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而联名者与被告人的关系密切,生活区域相近,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如在“黄某生故意杀人案”中,黄某生因为长期遭受儿子黄某军的打骂和虐待,而用水果刀刺伤了儿子。最终,被害人黄某军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案件发生后,当地村民200余人集体签名为黄某生求情。联名信提及黄某生日常为人和善,与街坊邻居关系较好,其杀人行为是长期忍受儿子虐待的无奈之举,因而请求法院轻判。实际上,联名信的内容是在表明,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很低,村民们对此表示谅解,并认为黄某军被轻判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低。相反,联名要求严惩,则多是因为被告人平日里经常为非作恶,损害村民的利益。村民们认为若不严惩此人,被告人在刑满释放后可能仍不知悔改,甚至继续欺负周围居民,侵害村民的生活秩序和人身安全。由此,案件的结果会影响联名者的日常生活,联名者往往有与案件结果较为密切的相关性。
(2)信息的全面性。相较一般公众舆论,联名信的内容较为全面。在媒体舆论中,媒体材料的筛选多以新闻的价值性为标准。他们不会长篇累牍将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当事人的背景一一细说,而只着重报道能吸引人眼球的部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他们的关注点往往只集中于某些方面,所以一般公众舆论具有片面性。如在许霆案中,人们的关注点在于ATM机出错,而少有人关注许霆取钱的次数、经过及逃跑的过程。在药家鑫杀人案中,人们热议的是药家鑫杀人手段的残忍性,而鲜有人关注药家鑫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品德。相较之下,在多产生于熟人社会的联名信中,联名者与当事人的关系较为密切。他们见证了被告人的成长过程,对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案件的各个细节了解得较为充分,对行为人的日常表现和品性也有着直观、全面的认识。[10]因此,联名信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充实。
(3)相对客观性。上文提到,联名信与一般民意都具有易受影响性的特征,但与一般公众舆论相比,联名信具有相对客观性。一般公众舆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网络和媒体,信息来源的间接性使公众舆论更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联名者多与案件当事人具有关系上的密切性和地域上的相近性,他们的信息通常来自自身感受,不会轻易被他人所干扰或煽动。所以,他们提供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稳定性。而案件的结果与联名者自身利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他们所提出的请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联名信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法治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并通过积极表达自己意愿和想法的方式参与、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司法领域,民意的渗透也越发广泛,群众提交联名信就是民意参与量刑的形式之一。然而,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的复杂样态,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量刑中合理吸纳联名信的关键所在。
(一)联名信对量刑的积极影响
第一,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肆意横行”。[11]民众的声音往往表达的是他们对利益的看法和需求。若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与民意相悖,司法裁判者总是一味回避民意,就会降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因此,将联名信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之一,让法官了解民意、倾听民意,可以架起法官与民众沟通的桥梁。第二,法律并不是超脱外物而独立存在的,在法律中也能看到伦理道德的痕迹。将联名信引入量刑过程,可以让法官更好地判断当前的价值共识和利益共识,使量刑结果更好地体现时代的精神价值,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第三,联名信所具有的与联名者密切相关性、全面性和相对客观性可以将更多法庭外的事实传达给法官,使其更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整体过程及影响程度,弥补案卷材料的局限性。
(二)联名信对量刑的消极影响
第一,联名信的朴实性与法律的客观理性存在冲突,容易使刑罚裁量成为“道德审判”。正如西原春夫所言:“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基本上可以肯定,而且必须肯定国民的欲求中含有直观的正确成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构成国民欲求基础的国民个人的欲求之中也沉淀着一些非正确的成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片面的观点乃至情绪的反应。”[12]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标准看待问题,并要求法律作出回应。[13]但是,法律不是朴素的道德思维,刑罚裁量必须站在一个客观、理性的位置,从宏观的角度在各种社会价值中进行选择,协调被告人、被害人及国家和社会的各方利益。法官迫于联名信的压力而屈从于民众的朴素道德观,将使司法审判变成一场道德审判。
第二,联名信的非专业性与法律的专业性的冲突容易导致量刑不均。法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法律工作者均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其职业理性思维也必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14]量刑的过程正是法律职业者运用理性思维进行裁量的过程,但联名者不可能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和素养。特别是在法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众的法律意识更大程度上与传统相连,因而一部分量刑结果与民众心中的期待值差距较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量刑的基本原则。只有运用司法的自身逻辑与思维才能均衡各项因素,使作出的裁判达到罪责刑相适应。不加筛选地采纳联名信的建议将破坏罪刑的均衡。
第三,联名信的易受影响性与司法独立性的冲突容易导致司法误判。如前文所述,联名信具有易受影响性的特征。联名信者掌握信息的不对称会影响其评价的质量,更有甚者会根据这种特性利用和煽动民意。在这种情况下,联名信可能就变成了裹挟着部分人的私利而伪装成“群体真理”的“民意病毒”,对司法独立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导致司法误判。
(三)联名信影响量刑的基本原则
既然量刑吸纳联名信同时存在正负两面效果。那么联名信是否应当影响量刑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法官在拥有了自由裁量权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民意(当然也包括联名信)的影响。例如,一项加拿大法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2/3的受访法官认为,当他们在作出判决时,公众的意见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15]2008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到珠海法院视察时曾提出“是否判处死刑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之一”的观点。[16]不难看出,在司法审判当中,司法工作者很难回避民意。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联名信的内容往往更加具体,判决结果对联名者的影响也更大,法官将更难以回避联名信。因此,与其要求法官消极回避,不如构建完善的吸纳联名信的规范机制,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判决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1.坚守司法独立的底线
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要求审判人员拥有独立性和自由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之外,不受外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司法独立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是出于防止权力滥用而保障公民自由的需要。所以,联名信绝对不能影响司法独立性。司法工作者必须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理念,依据法律的逻辑思维进行推理和判断,遵循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方法论。不能动辄以民众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任意吸纳联名信。否则,不仅司法独立会荡然无存,法治和人权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与破坏。因此,司法裁判者在量刑时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与司法独立的底线。
2.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吸纳联名信的合理部分
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法律条文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使法律必然会赋予裁判者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就是法官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法官自身的经验有着高度的依赖。霍姆斯曾说,“法官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经验可以帮助法官洞察各种案件涉及的人情世故,对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进行衡量与选择。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他的经验也是从自身经历及社会中其他人的经历中总结而来的,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大众价值取向的影响。而在我国当前特殊的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处于变动状态,立法难以及时和具体回应社会变化。为了增加法律的适应性和大众对法律的信服力,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需要将社会价值观念纳入考虑范围,从而解决法律滞后性的问题。因此,不论是普通的大众舆论还是联名信中特定人群的民意表达,都有群体理性的存在。笔者认为,法官应当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吸纳联名信的合理部分。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吸纳联名信不是以联名信为裁判依据,而是通过对联名信内容的合理化论证来实现的,即法官对联名信中的意见表达、伦理、道德标准等非确定性因素所进行的考量与判断都是在内心完成的,它们只能作为隐性的裁决理由而存在。如果这些内在因素外显,则必须寓于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法律价值的衡量、立法意图、公共政策之中,接受法律规则、程序性步骤以及逻辑推导等确定性因素的推敲与检验,并依托某一项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定外化出来。[17]这一过程对法官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在短时间内也许难以使每一个司法裁判者都能合理进行民意的筛选和剪裁。因此,现阶段司法裁判者应当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但至少应让民众的声音被关注和重视,让联名信与司法在碰撞中找到平衡。
三、联名信影响量刑的具体路径剖析
(一)联名信对犯罪相关事实的具体化
联名信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因为联名者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较为密切,对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案件的各项细节了较为解,且联名者的信息通常来自自己的所见所闻,因而联名信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笔者认为,联名信中涉及案件事实相关情节的内容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明材料。《刑法》第61条规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量刑承载着社会正义对犯罪行为报应性的要求,量刑结果要实现犯罪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建立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法官在量刑时,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各项情节,才能对犯罪人和犯罪行为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判断。实践中,法官往往通过阅览案卷及庭审了解案件事实,联名信则可以将更多法庭外的事实传达给法官。如联名信中经常提到的犯罪动机、犯罪造成的损害和影响、犯罪分子和被害人恩怨等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信息可以为法官提供更为直观、具体的材料,帮助法官全面评判案情,衡量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有反对者认为,刑事法律的证明标准十分严格,而联名信的证明力较弱,不应当作为证据影响量刑。但笔者认为,酌定量刑情节本身就具有内容抽象的特点,出于保护被告人权益的需求,可以适当降低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就根据不同的证明事实而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重要的、将导致大幅度提升量刑的事实,需要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标准,甚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对于一般的量刑事实和情节,只需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如在英国,控诉方必须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证明犯罪事实,而在辩护方提出减轻量刑情节时,只要满足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就可以被法官接受。这些都表明在量刑环节对证明标准要求的降低和放宽。[18]所以,司法裁判者可以将联名信中对被告人有利的酌定量刑情节的相关信息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在采纳这方面证据时适当放低证明标准。
(二)联名信对犯罪人个人情况的细化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影响定罪量刑的唯一因素就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但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人身危险性对量刑的影响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理论。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8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所以,对人身危险性的判定成为量刑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身危险性是对犯罪人主体人格的揭示,如何探索深潜于行为人主观之中的危险人格,是司法面临的难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科学的评估机构与测评方法,主要依靠司法人员凭借主观经验与个人直觉的模糊性判断手法。[19]但是,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不能一蹴而就。欲准确把握人身危险性的现实内容,就要及时跟进并予以全面评估。笔者认为,在联名信中,联名者与当事人的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大多见证了被告人的成长过程,对被告人的日常表现和品行也具有直观、全面的认识。司法裁判者对一个十分陌生的行为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时,在自己的主观经验和感性判断之上,参考这些与被告人有直观、亲密接触的人的评价,将使判断结果更具有客观性。
实际上,对被告人的人格调查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有体现。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情节轻重及犯罪后的情况,认为没有必要予以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其中就规定了被告人自身要素的调查,主要包括行为人的品行、癖性、习惯、健康状态、家庭环境、职业、人际关系等。日本法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从而更加客观地衡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又如在美国建立的量刑前社会调査报告的制度中,缓刑官员会与犯罪嫌疑人就其个人背景情况进行面谈,了解罪犯的特殊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婚姻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精神及心理健康状况等,并通过査阅记录、约谈家庭成员等方式向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调査核实。该项报告将作为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加以考虑。[20]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说明我国也注意到行为人的社会调查对于判断行为人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联名信与社会调查报告有异曲同工之效,即通过行为人的家庭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对行为人个人品格、社会关系和个人背景等内容的描述,帮助法官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出更合理的评估。因此,法官在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判断时,可以吸纳联名信中对行为人人格的判断建议。
(三)司法裁判者对联名信中的伦理参考
《庄子·说剑》中提到:“中和民意以安四乡。”这句话在当时体现了执政与民意的关系,放于现在也可说明,欲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考虑民众的伦理道德观念。尤其在乡土社会之中,建立民众对法律的信仰还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法官必须以公平正义的案件处理结果构建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威信。联名信的第二部分表达了联名者对定罪量刑的态度和建议,也正是民众向司法机关表达其伦理观和正义观。伦理是法律生长的根基,法律永远流淌着伦理的血液。法官应当倾听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让自身经验与观念和民众的声音进行交流与碰撞,去感受和体察民众的伦理道德观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让司法裁判者可以在不同的声音中保持司法独立,将社会效果、社会道德观念、公共政策等内化为自己的法律思维与逻辑推理,在法律原则和规定的大框架下吸纳联名信中的伦理观念,由此才能让普通公民在质朴的正义感、道德观、伦理情的基础上生长出合乎法治精神的理性与自治。
(四)联名信中应当排除的内容
裁判者可以参考民意,吸纳民意,但民意对量刑绝不是无原则、无限度地影响,而是有限制地影响。由于联名信中的民意表达具有朴实性、非专业性、易受影响性的特点,司法裁判者在阅读联名信时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
第一,要审慎对待联名信中联名者基于同情或愤怒等情感作出的情绪性意见抒发,剔除盲目的、非理性的民众意见,从中剥离出理性的、客观的描述。
第二,要辨识联名信背后有无特定利益主体操作甚至收买联名者,或刻意煽情、传播错误的信息影响联名者的判断,防止相关利益主体扭曲民意。
第三,司法裁判者必须始终保持理性和冷静。不论联名者的意愿多么强烈,裁判者都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断是非曲直。即使是倡导常识、常情、常理的陈忠林教授都郑重声明,他提出三常理论,并不是认为法官要根据常识、常情、常理来判案。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该遵守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不是任何一种抽象的常理。一个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常理来审判案件。他强调的只是我们理解法律必须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但这些只能内化为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却永远不能替代法律。
第四,民意的可采纳程度与表达民意的人数不具有正相关性,不能因为联名者的数量多而认为有道理,从而认定其合理性。面对来势汹汹的民意,应保持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屈从。
(五)联名信的审查程序
量刑中裁判者可以有选择性地吸纳联名信中的内容,所以联名信中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材料。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据材料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联名信的内容也应当参照证据的审查流程操作。但是,联名者人数众多,联名信性质介于书证和证人证言之间,而其证明力也低于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对联名信的质证应当区别于其他证据。联名信陈述部分具有一定的证据性质,请求部分可以作为法官量刑的考量因素。因此,这些内容既可以在庭前审查,也可以在庭中审查。庭前审查由工作人员到联名信所涉区域随机调查核实,也可以对联名者进行电话询问。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3条,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且可以互相辩论。因此,笔者认为,在庭中审查和质证时,应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展示联名信。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联名信的内容发表意见,并可以互相辩论。在特殊情况下,对联名信可以参照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如人民法院认为联名者有必要出庭作出说明的,可以随机抽取部分联名者出庭,或者通过视频等便捷、灵活的方式对联名信内容作出说明。
四、结语
相较常态社会或者成熟社会,转型社会的司法裁判在严格依法与获得公众认同、保持法律权威之间存在着更加紧张的张力。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并不乐观,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偏低,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就需要法官以高超的司法智慧和高度的司法理性,在影响司法公信的多元力量中综合权衡,审慎决断,努力凝聚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联名信作为民意表达的方式之一,多出现于法制宣传较为薄弱的乡村熟人社会当中。为了缓解司法与民意冲突,对于联名信中民意的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曲意逢迎。司法裁判者应当重视联名信中的民意表达,排除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对联名者予以回应,才能形成司法正确回应和引导民意的长效机制,建立民众朴素道德观念与现代法治的桥梁,提高法律的权威性,让人们真正尊重并信仰法律。
[1]杜健荣.民意影响司法的机制与效果——基于中美差异的比较分析[J].河北法学,2014(6):4.
[2]赵光怀.民间上书于汉代政治[J].求索,2005(11):1.
[3][8]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院报社联合课题组.个案处理中的民意与司法——以50个联名信刑事案例为考察样本[J].人民司法,2012(1):2.
[4]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
[5]崔鹏,晓琼.情理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J].山东省青年管理十部学院学报,2009(3):22.
[6]关于拐卖儿童判刑,大家都在争什么[EB/OL].http://news.sina. com.cn/c/2015-6-18/164531965856.shtml,2016-04-16.
[7]李润华.认真对待量刑中的民意[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2013(3):4.
[9]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A].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7.
[10]徐双桂.论乡村社会中民意在量刑中的合理导入[J].法律适用,2014(4):1.
[11][德]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1.
[12][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荣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0.
[13]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1998(1):34.
[14]陈金钊.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9.
[15]徐光华.转型期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91.
[16]王淑静.论民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与协调[D].兰州:兰州大学,2010:8.
[17]李润华.认真对待量刑中的民意[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2013(3):6.
[18]许美.酌定量刑情节规范适用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4:127.
[19]陈伟.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J].比较法研究,2014(5):10.
[20]殷健康.论量刑前的社会调查制度[J].刑事法评论,2013(6):12.
【责任编校:王欢】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Joint Letter on Sentencing
Chen Shiwei,Shi Lu(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s one of the expression ways of public opinion,the joint letter is common in criminal cases.But as to what is a joint letter,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joint letter,and whether the joint letter can influence the criminal judicial decision,there has been no specific answers.The joint letter is simple,non-professional and susceptible,which 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opinion.Therefore,the joint letter should be treated carefully.But the joint letter also has oth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se result and joint signatories,obje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andthepartialcontentofthejointlettercanreflecttheinformationrelatedtothecaseandlitigants,thusinfluencing the sentencing.The judicial judg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linking the simple moral ideas and value of rule-of-law.Therefore,the judicial judge should neither ignore the joint letter nor flatter it,but should absorb the reasonable parts to enhance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trust towards the judiciary.
Joint Letter;Public Opinion;Criminal Justice;Sentencing
D924
A
1673―2391(2016)05―0037―07
2016-04-20
陈世伟(1975—),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石璐(1991—),女,广西南宁人,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律。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FXY201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