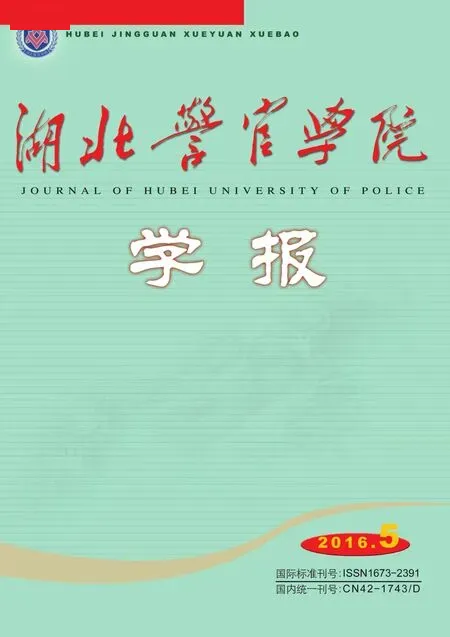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占善刚,张博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占善刚,张博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新的证据;攻击防御方法;诉讼迟滞;可归责性
从1982年出台《民事诉讼法(试行)》时起,“新的证据”这一用语便存在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之中,且在现行民事诉讼规范中多有出现。那么,“新的证据”之内涵为何?以历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观之,不难发现,“新的证据”不仅出现在第一审程序以及第二审程序的开庭审理阶段,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开启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在再审程序中多有体现。不过,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范抑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皆未能正确界定“新的证据”之内涵,诸多条款甚至导致越解释越混乱的局面。因此,如何解释“新的证据”之内涵即成为亟待明确的问题。
纵观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之修订历程,笔者滋生下述疑惑:(1)在制定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初,“新的证据”之功能为何?在三十多年的法律完善过程之中,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新的证据”之功能何在?两种功能是否相同?(2)“新的证据”源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为何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时,“新的证据”之内涵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及实务界的广泛讨论?(3)从诸多法律规定来看,“新的证据”在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之中的内涵并不相同,为何目前学术界探讨之“新的证据”多局限于审判监督程序?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以为,对于“新的证据”之理解不能仅仅拘泥于目前的若干法律规定,还应当从“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的关系着眼。本文拟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之失权之间的关系反思目前我国“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之关系,从而力求更加合理地分析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以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制度下的“新的证据”之内涵。
一、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适时提出主义”
通常认为,大陆法系理论上存在“随时提出主义”“法定顺序主义”以及“适时提出主义”。“随时提出主义”又被称为自由顺序主义,即当事人自起诉至辩论终结,可以随时提出诉讼之攻击防御方法,在时间条件上不受限制之立法主义。虽然“随时提出主义”能够尽可能查清案件事实,具有保障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之优势,但易造成当事人故意利用攻击防御方法的突袭而拖延诉讼的情形。为了避免此项制度之流弊,以便法官及当事人能及早整理案情争点,促进诉讼之进程,“法定顺序主义”应运而生。依“法定顺序主义”,当事人必须同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或严格限定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时间前后顺序,违者会遭至提出权利之丧失。然“法定顺序主义”易造成当事人害怕遭受失权处罚的恐惧心理,两造当事人会尽量提出各种事实及证据,包括不重要甚至毫不相关的事实与证据。如此一来导致法院承受不必要之负担,不但不能促进诉讼程序的迅速进行,反而造成诉讼迟延现象的频繁发生。综合以上两种立法主义之优劣而衍生出的“适时提出主义”除别有规定外,以要求当事人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的适当时期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为原则。“适时提出主义”一方面科以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要求当事人在适当时期提出证据以尽早确立争点,另一方面通过例外规定来免除当事人遭受证据失权之可能,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益。[1]在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所存在之价值截然不同。“随时提出主义”强调攻击防御方法提出时间的随意性,每一个攻击防御方法的提出相对于前一个方法在时间上都是新的。在此种制度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实乃以提出之时间先后顺序来界定,从字面含义理解即可,立法上对于攻击防御方法之提出并无太多限制。换言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出现于立法中能够更好地揭示“随时提出主义”。而“法定顺序主义”对于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时间顺序有严格限定,不允许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新的攻击防御方法”在此种立法主义下不免失去意义,实无存在之必要。作为“随时提出主义”和“法定顺序主义”的折衷做法,“适时提出主义”既需要以诉讼经济原则为考量因素,亦需要以当事人实体权益为关注对象。“适时提出主义”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促进义务,使违反诉讼促进义务者受证据失权制裁,从而节约了司法资源,但失权难免会和发现案件真实之要求相抵触。为了缓和二者之矛盾,兼顾保障程序与实体之利益,在一般情形下,当事人逾期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会遭受失权之制裁,但在特殊情形下,当事人逾期提出需要免遭失权之风险。此时,“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是指逾期提出却可以免遭失权制裁的攻击防御方法,其具有了特殊的含义。换言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之内涵应当是对“特殊情形”的解释说明。在三种立法主义中,“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适时提出主义”之关系最为密切。总之,探求“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之内涵不能脱离“适时提出主义”这一制度背景。
二、“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失权制度
目前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皆采取了“适时提出主义”,不仅督促当事人于适当时期提出攻击防御方法,而且提醒当事人逾适当时期提出会遭受失权之制裁。此种失权效果试图间接强制当事人适时进行攻防,从而满足促进诉讼程序之要求。在此种意义上,客观真实已非优位价值,毋宁系兼顾客观真实及诉讼促进两项价值追求。然二者从学理上说颇具矛盾:失权处罚既然已经赋予促进诉讼之效果,则需以“新的攻击防御方法”发现客观真实以补正程序上瑕疵。质言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是对于已经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错误地遭受失权后的一次补救。那么,“新的攻击防御方法”必然不满足适时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遭受失权所需之条件。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对于违反适时提出义务之当事人,法院欲驳回其所提出之证据,除了满足逾时提出之要求外,尚需具备以下两项要件:
第一,当事人逾适当时期提出与诉讼延滞具有因果联系。判断有无诉讼延滞,在德、日有两种理论,即绝对理论与相对理论。不论采取绝对理论还是相对理论,均必须以当事人的逾时提出造成诉讼迟滞为前提,始可制裁该当事人,亦即在当事人之迟延提出行为并非诉讼延滞之唯一原因时,不能认为逾时提出之行为当然遭受失权之效力。倘若诉讼迟滞另由法院之失误行为(违反法院阐明义务)或者其他第三者之行为(例如证人不到庭)所致,则不得驳回当事人逾时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因为基于程序不利禁止原则,不应将法院之责任或者其他第三者之责任归诸于当事人,使其负担程序上的不利。[2]另须注意的是,纵使当事人在法院规定的适当期间内提出,亦可导致诉讼迟滞。例如,对于多数人皆知之事实证据,当事人放弃其中就近可出庭之人,却偏以现已远行之人为证人;又如,当事人早已知晓某一事实证据,却于多次言词辩论期日皆不主张,迨最后言词辩论期日已至始行提出。因此,多有学者称所谓“逾适当时期”应当指客观上已逾适当时机而言。[3]
第二,当事人逾时提出具有可归责性。通常所说可归责性即指当事人逾时提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判断逾时提出有无重大过失,在我国实践中乃是选择一般人作为参照物。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一般人能发现这一证据,但是案件当事人却未能发现,就足以推测当事人未能审慎收集证据,表明当事人存在重大过失。[4]而台湾学者则认为,对于可归责性,还应该结合当事人本人及诉讼代理人之法律知识来考量,应当关注各个当事人之期待可能性及其能力,如在法官善尽阐明义务、指明适时提出之必要性后,若当事人本人或代理人依旧怠于适时提出,则并不必然被认定具有可归责性,因为当事人并未认识到适时提出之可能性及必要性。只有当事人认识到适时提出之可能性及必要性,才能认定其逾时提出具有重大过失。[5]
综合上述,逾时提出之当事人遭受失权之制裁,不仅需要满足逾时提出之条件,还须具备当事人逾时提出与诉讼迟滞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以及当事人逾时提出具有可归责性。易言之,倘若当事人逾时提出却未遭受失权之拘束,那么当事人逾时提出必然与诉讼迟滞缺乏因果关系或者当事人逾时提出必然不具有可归责性,而此种情形也正是“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之真谛。
三、我国“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
相较大陆法系之失权制度,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失权范围仅涵盖逾期提供的证据方法,不及于当事人逾期对诉讼请求赋予理由和逾期主张、争执、证据抗辩等攻击防御方法。应当说,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属于有限的失权制度。同大陆法系的失权制度变革如出一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沿革进程中,举证时限规定也经历了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转向证据“法定顺序主义”,并最终走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过程。首先,立法者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08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从而确立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新的证据”中的“新”是相对于此前未提出的证据而言的。当事人可以随时在法庭上提出之前并未主张的证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证据规定》中作出举证时限的规定,各地人民法院由于缺乏实践操作经验,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证据规定》施行,适用严格的证据失权制裁措施。此时,可以说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转向证据“法定顺序主义”。凡是违反举证时限要求而提出的证据被一律采用失权制裁。虽“新的证据”可以突破举证时限规定,但法官不正当地强调程序的效率致使严格失权较为泛滥。由于严格失权带来的法院放弃当事人实体权益、忽略实体公正的负面效应过于严重,法院不得不放弃此前严格失权之做法,转而宽松地允许“新的证据”介入法院审理程序,证据随时提出出现了“复辟”的迹象。[6]截至目前,立法者为了避免旧法中举证时限与“新的证据”之弊端,采纳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并将之写进2012年《民事诉讼法》之中。“新的证据”从表面上看可以不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其更深层次的作用应当是协调举证时限制度适用证据失权制裁措施所造成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价值矛盾。虽然我国关于“新的证据”之立法体例至今未曾改变,始终沿用“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表述,但显而易见的是,类似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失权制度的联系,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思想的转变使得“新的证据”在新旧民事诉讼法中扮演了迥然不同的角色。
“新的证据”之功能之所以发生改变,且直到2001年《证据规定》出台才激起关于“新的证据”的大讨论,皆是因为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关于举证时限制度之理念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过渡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但由于立法者及司法者未能正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中的效率与公正之问题,导致“新的证据”之讨论忽略了第一审程序及第二审程序,而多集中于审判监督程序。笔者以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5条正式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但是立法者对于“新的证据”之内涵依旧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阐释。显而易见,欲正确理解何为“新的证据”,须以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为前提,通过检讨当前法律体制下之一审、二审以及再审中的“新的证据”,以发现更加契合我国现行举证时限制度之“新的证据”。
四、我国现行体制下之“新的证据”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之“新的证据”
从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规范来看,关于第一审普通程序之“新的证据”的内涵规定于2002年的《证据规定》第41条第1款和第43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10条以及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31条。自《证据规定》出台,我国理论上始终以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为前提。如同大陆法系的“适时提出主义”,证据失权的适用理应具备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具有因果联系且当事人逾时举证具有可归责性两个要素。反之,“新的证据”作为突破举证时限的特殊情形,也理应强调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缺乏因果联系、当事人逾时举证不具有可归责性。
依《证据规定》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一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1)一审举证时限届满后,当事人始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且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第一种“新的证据”是指当事人新发现的证据。所谓“新发现的证据”应当囊括于原本存在的证据,而原本存在的证据能否被认定为“新发现”,显然不能依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否则,当事人会任意将举证期限届满后所提的证据认定为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应结合主客观标准进行衡量。客观上看,诉讼迟滞并非逾期举证导致,如法庭对当事人适时提出的证据不予采纳导致当事人无法适时提出,或者法庭未事先告知当事人举证时限,致使当事人不知必须适时提出证据;主观上看,当事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如当事人故意不提出证据,希望将案件的事实审理拖延至第二审程序,或当庭提出证据使对造当事人猝不及防。第二种“新的证据”强调“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与上述客观标准相同,皆应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的因果联系出发进行判断。依第43条之规定,“新的证据”是指:(1)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2)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延长的期限内提出的证据,若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可将其视为新的证据。质言之,“新的证据”应当满足举证期限届满之要素。倘若证据未逾期,即为适时提供之证据,何来“新的证据”一说,第43条第1款显然前后矛盾。第2款亦强调“因客观原因”,与前文所要表达之文义并无太大差别,在此不予以赘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10条第2项则是从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进行判断的。
从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31条看,最高人民法院似已意识到“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之关联性,其要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款处理,即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的理由,根据不同情形作出是否采纳该证据的判断。换言之,倘若当事人说明的理由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诉讼拖延,客观上诉讼拖延并非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后果,那么此时逾期提出之证据便会被采纳,被称作“新的证据”;反之,倘若当事人说明的理由从主观上或者客观上会导致诉讼程序的迟滞,该则证据会因逾期提出而遭受证据失权之制裁。
总之,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旧有的规定还是新出台之解释,皆是围绕当事人逾期举证的可归责性及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联系而认定逾时提出之证据是否为“新的证据”。
(二)第二审程序之“新的证据”
欲对二审中的新证据的内涵予以界定,需要先理解第二审程序的性质。从一般学理来说,第二审程序是为纠正第一审未确定裁判的错误而设,具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分别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所谓“复审主义”是指第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受第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的拘束,对案件作全面的审理。实质上,第二审法院重复第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不仅可以重新全面地搜集第一审中存在的诉讼资料,当事人还可以任意主张第一审程序中未主张的事实。就民事诉讼制度之机能而言,复审主义虽然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却有违诉讼经济原则。事后审主义则指第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只能以第一审程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为限进行事后审查。实质上此主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审理程序,虽然具有诉讼经济之优势,却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第三种续审主义为前两种主义之折衷做法,第二审法院在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的诉讼状态下,继续进行第一审的言词辩论。[7]
就我国而言,在审级制度上采取的是两审终审制,故第二审程序不仅是上诉审程序,亦为终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作为司法救济途径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注重对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因而第二审程序将努力实现案件真实发现之目标。然我国人口众多,民事纠纷频发,且全国司法资源有限,第二审程序亦会兼顾对诉讼经济原则之考量。加上对比德国、日本等大多数国家民事诉讼法皆采取续审主义之做法,我国对于第二审程序之定性采取兼顾诉讼经济原则与实现案件真实发现目标的续审主义。[8]续审主义下之当事人于第一审程序中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亦为有效力之行为。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于第65条明确贯彻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加重一般性诉讼促进义务,使当事人负有须在适当时期主张证据之义务。倘若当事人未在法律或法官所规定之期间内提出证据,则会遭受证据失权之后果。那么在续审主义的前提下,第二审法院得以第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基础,第一审程序中法官裁定的当事人逾时提供的证据所遭受的证据失权之不利后果会当然地延续至第二审程序的审理过程中。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于“新的证据”之内涵界定依旧停留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证据规定》第41条第2款规定之中。“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依据该规定,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存在两种情形:其一为“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在续审主义的前提下便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未能在一审举证时限的规定下提出的证据。换言之,二审法院审查的是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已经逾期提供的证据是否应遭受证据失权之不利后果,以实现诉讼经济原则和发现案件真实二者之间的平衡。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1条第2款“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的前半句,可以看出,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所提交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若符合客观原因,即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缺乏因果联系,则被视为第一审程序中未逾时提供之证据;而从后半句来看,则不免滋生歧义。应当明确,由于举证时限规定系为达到节省或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之目的,具有强行性、公益维护性,绝对禁止任由当事人予以处分,故证据逾时可否提出、是否适用失权制裁属于法院职权所及之事项,应适用职权探知为审理。[9]因此,是否逾期不能以对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为判断标准。《证据规定》中的另一种“新的证据”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从该规定不难看出,二审法院审查的对象是一审中已经适时提出的证据,只是因为该证据未被一审法院所采纳才会续行审理于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在一审程序适时提出证据并不会拖延程序,也不具有相应的主观过错。事实上,对于适时提出的证据不采纳本为法院之判断,并不能责令当事人承担一审法院由此产生之过错。相对于一审中已被采纳的证据而言,“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实乃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来判断是否为“新的证据”。[10]
总之,对于二审中的“新的证据”之理解应当从二审程序的性质出发,在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续审主义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证据规定》中对于第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的界定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对于“新的证据”之认定应当从当事人之可归责性以及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关系两方面进行。
(三)审判监督程序之“新的证据”
作为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情形,审判监督程序之“新的证据”最早见于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后在修订进程中沿用此项规定,现行《民事诉讼法》依旧如此,仅将条文排序更改为第200条。至于该规定中“新的证据”之具体含义,最初源于《证据规定》第44条,仅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之证据。随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第10条将“新的证据”规定细分为:(1)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3)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4)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目前,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88条在《审监解释》的基础上将其修改为:(1)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发现;(2)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提供的;(3)原审庭审结束后始形成,无法据此另行起诉的;(4)原审已提供但未予质证的,视为新的证据。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之规定保持了既有的思路,但概括言之,当前“新的证据”的认定其实只存在两种:其一为因客观原因导致举证期限届满而未提出的证据;另一为原审中本已存在,因特殊情形而认定为新的证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认定规则依旧遵循当事人之可归责性以及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关系。
虽然上述诸多司法解释对“新的证据”之认定表面上看具有合理性,因为皆遵循了上述适用失权之条件,但实质上对审判监督程序中“新的证据”之考量仍然忽视了既判力之作用。从一般法理来讲,为了维持判决所确认权利关系之安定及对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院之终局判决确定后,无论该判决结果有无误判,法院及当事人均应受到判决结果之拘束,不得就该判决内容进行争执,此即既判力之作用。而既判力之作用仅在于确定事实审法院最后言词辩论终结时所存在或不存在之权利义务关系,言词辩论终结以后所发生之事实或权利义务关系之变动事实均不应受到既判力之拘束。易言之,于既判力基准时以前所存在之事实资料,无论其为应主张或抗辩之事实,当事人如不适时于诉讼中提出,则于另外之后诉不得再提出此类事实为主张或抗辩,而就前诉已有既判力之诉讼标的权利再为争执。[11]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之“新的证据”而言,《证据规定》中“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之证据”应当包括原审庭审结束后才形成之证据。《民诉法司法解释》中“原审庭审结束后始形成,无法据此另行起诉的”涉及的“新的证据”显然应为事实审法院最后言辞辩论终结后才产生之证据,根据既判力原理,应当被排除在“新的证据”之外。
综上所述,从2001年出台《证据规定》起,“新的证据”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随着立法的多次修订以及新司法解释的颁布,“新的证据”规定依旧存在。从大陆法系“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与失权制度的角度来看,是否构成“新的证据”本质上应当以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是否具有因果联系、当事人逾时举证是否具有可归责性两个标准进行判断。
五、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于“新的证据”向来缺乏系统、全面、正确的认知。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采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大前提下,“新的证据”之功能在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上之真实,从而弥补举证时限适用失权制裁措施之缺陷。而辨别何者为“新的证据”,何者为应当适用失权之证据,则应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和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两个角度进行界定。
[1]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上)[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56.
[2]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419.
[3]王甲乙,杨建华,郑建才.民事诉讼法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178.
[4][6]李浩.民事诉讼法典修改后的“新证据”——《审监解释》对“新证据”界定的可能意义[J].中国法学,2009(3):160.
[5]许士宦.新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6.
[7]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360.
[8]赵钢,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345.
[9][10]许士宦.新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0-321.
[11]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中)[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267-269.
【责任编校:王欢】
Thinking of"New Evidence"in Civil Procedure Law
Zhan Shangang,Zhang Bo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new evidence"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evidence systemof the civil procedure,and itis also a concep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 limit system of evidence.When the circl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vidence,the connotation is often divorced from the system for adducing evidence in limited time.That itjustcomplywiththelegalrulesbyrote,anditfailedtoclearthelegislativereasons,leadstonewevidenceindiscriminately.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of the new methods of attack and defense,the function of the new evidence is actually in contradiction tobalance theentity andthe procedure of the loss ofrights system.The connotation ofthe new evidence should be classified from causal relationship of overdue burden and litigation retardation,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ies overdue burden of proof.
New Evidence;Measures of Defense and Offence;Delaying the Litigation;Responsibility
D925.1
A
1673―2391(2016)05―0012―06
2016-07-03
占善刚(1971—),男,安徽安庆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张博(199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研究”(13YJA8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