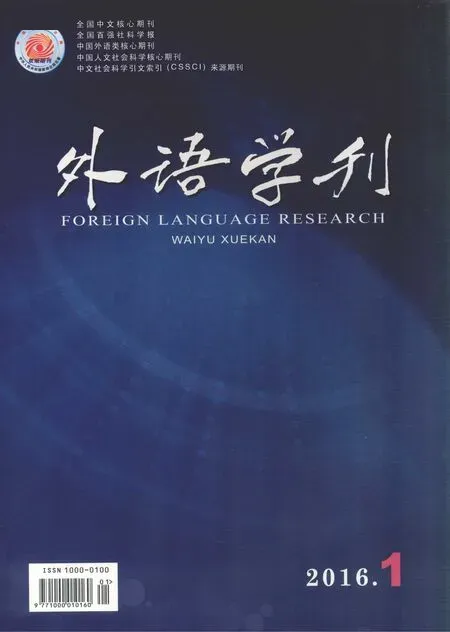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学意义*
文兰芳
(湖南商学院,长沙 410205)
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学意义*
文兰芳
(湖南商学院,长沙 410205)
人类语言具有多样性特点,这种特点是维持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基础。语言的多样性具有多维多层级,既是现存状态,也是演变过程;既是一种事实叙事,也是一种价值叙事。维护语言多样性,其价值显现于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与人类自己的健康发展。
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濒危语言;生态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根本、最深刻的基础,它与人类的一切活动相伴。没有语言,我们不能回顾和联系过去;没有语言,我们无法展望和规划未来;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些都由语言的人类学意义昭示。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世界上人类语言的总量在不断减少。语言的多样性正如自然生态系统的丰富性一样,是世界和谐发展的前提与重要标志。语言的消亡与濒危对于全球语言生态、人类文化与人类未来具有消极与否定意义。维护语言多样性,其价值显现于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与人类自己的健康发展。
2 语言多样性图景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描述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Wilson 1988),现在多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它是地球得以美好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存在环境、相互关系、变异和发展过程中,人类语言和文化也像生物系统一样,具有多样性特点,而这种多样性是维持人类社会这种生态系统的基础(杜茜 2011)。世界上的语言众多,虽然人们尝试确定世界语言的数量,但不同调查表明可能有3,000-10,000种,而绝大多数文献则认为是5,000-6,000种(David 2002:286)。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现在的语言约六千九百种。各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各不相同,差异很大。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有汉语、英语、印地语、俄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和日语8种,它们的使用人数均超过一亿。它们仅占语言总数的0.13%,其使用人数却占世界总人口的40%。另有199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2人。全世界约96%的语言,其使用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3%左右。
语言的多样性不仅是数量级上的一个指标,也表现在地域分布与语言系属的多样性和语言结构的复杂性上。地球上使用语言种类最多的国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那里有八百多种语言。使用语言最少的地区有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毛里求斯等非洲单一语种国家。语言的地域分布差异非常大,其特点有:一是语言种类从南北两级向赤道地区不断增加,二是干旱环境中的语言类型较少。语言多样性丰富的地带有两条:一条贯穿东西非洲,另一条覆盖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世界上绝大部分语言都在这两个区域使用。现有语言根据亲缘关系可以分为十多个传统语系,比较大的语系有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闪含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澳泰语系和澳亚语系等。汉藏语系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系;印欧语系的语族最多,影响力最大。此外,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其结构类型具有多样性。语言类型学把人类语言大致分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和综合语。从内部结构看,语言还可分成4大子系统:语音系统、语义系统、语汇系统和语法系统。语言的多样性是多维多层级的,不仅表现在其外在使用与分布上,也在其自身的复杂性上。
语言的多样性既是一种事实叙事,也是一种价值叙事。每种语言都记载自己民族的发展历史,记录自己民族的生存智慧,记录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产品。每种语言的消亡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与生态知识的消失。“每一种语言都独特地表达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每消亡一种语言, 我们对人类语言结构和功能的理解方式、人类史前史以及保持世界多样性生态系统等方面的证据都会有所减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2006:87) 语言多样性蕴含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是时间上的事实描述,也是空间上的人类组织结构表现。语言多样性蕴含生态学意义。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杜茜 2011)。Oviedo和Maffi 研究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在欧亚大陆上,语言多样性的两条丰富地带刚好与赤道森林自然带吻合,这一地带孕育大部分物种。这两条丰富地带一是从非洲象牙海岸穿越西非到扎伊尔,另一是从南印度及东南亚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到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群岛(Daniel 1998)。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相关性。正因为多样性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人类社会的健康生存与良性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如果语言多样性衰退,会引起生物与文化生态的衰变(范俊军2005)。
3 语言活力与濒危评估
语言多样性既是现存的状态,也是演变的过程。语言学家估计,公元前全世界大约有十五万种语言,中世纪仍然有七、八万种;到20世纪,只剩下现在的不足七千种。现在世界上使用语言中至少有3/4(也有人说是90%甚至更多)将会在2100年时停止使用。语言数量不断减少已是客观事实,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语言都面临着消亡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目前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亡,语言消亡的速度超过很多动物的灭绝速度。如果某种语言的交际场合越来越少,或者不再使用,或者不再代代相传,那么这种语言就面临濒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发布第三版世界濒危语言图谱,对全球濒危语言按不安全、危险、濒危、垂危和灭绝5个标准分类。其中,一些数据着实令人担忧:目前存世的六千九百多种语言中,607种不安全,632种危险,502种非常危险,538种情况危急,另有二百多种语言已在最近3代人的时段内灭绝(定义为不再存在讲这种语言的人)。全球濒危语言图谱举例说,有18种语言是“极度濒危语言”;之所以为“极度濒危语言”,是因为该语言有据可查的使用者不足10人,有的甚至只有一个人使用(罗伯特·迪克森 2010:97)。
正如生物多样性破坏、大量物种消失会造成生物链缺失,进而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会造成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破坏。这种破坏直接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无法延续(杜茜2011)。当下,语言正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其主要表现有:(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濒危与消失;(4)方言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使用者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主动抛弃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7)语言岛和方言岛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难产或势微(梅德明 2014)。可以说,语言生态危机的最直接后果是语言濒危与消亡。语言濒危与消亡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也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内部因素是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化。语言濒危与消亡的外部原因主要有:(1)残杀或疾病造成的人口丧失;(2)被强势族群禁止使用而造成的强制性的语言丧失;(3)双语使用中自愿与非自愿的语言转换;(4)自然环境尤其是传统栖息地的退化引发的语言多样性流失(罗伯特·迪克森 2010: 89-91)。
鉴于语言濒危的严重性,同时更好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颁布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评价的9大准则(世界教科文组织语言网站语言濒危栏目)。其中,1-5准则是语言活力的主要评估指标,7和8准则关涉语言态度与政策,6和9准则关于语言教育与记录。评估语言活力最常用或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是语言代际传承指标与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指标。前者指某种语言是否仍然代代相传:一种语言的使用场合、使用对象以及谈论的话题范围直接影响该语言能否世代相传。后者强调,使用人数少的语言群体容易被强势语言族群吞并,少数语言族群从而丧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9个评估准则在客观、全面界定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时也亮出黄牌,警示语言消亡与濒危对语言生态的危害。
4 濒危语言扶持
语言濒危是语言多样性的致命威胁。根据世界濒危语言图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濒危语言扶持战略,采取积极有效的濒危语言扶持行动。该组织当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维护语言权利,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它针对语言权利、语言教育、语言活力、语言濒危、语言多样性和语言遗产等问题制定规约,大部分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制定语言政策、开展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活动的基础(郑梦娟 2008)。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介入保护、抢救和传承濒危语言的工作,主要举措包括:确定语言的特性,宣传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濒危语言的基本情况,定义语言活力的标准与确定语言濒危状况的等级,确定母语使用权利和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基本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从197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生效以来,联合国做出一系列努力,扶持濒危语言,比如设定“国际母语日”(每年的2月21日,纪念东巴人民为争取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而作出的牺牲),2003年发布《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并制定《行动计划建议书》,2009年编绘“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2013年召开“第十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濒危语言的挽救和保护呈多方位多举措态势。
相比联合国的宏观战略与行动,不少国家、政府及组织采取可称为中观的语言政策与语言保护行动。国家、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及语言政策(包括语言官方地位和使用)很大程度上影响语言的推广与使用,其对母语特别是对少数族群语种的保护是维护语言多样性的最重要举措。作为超国家治理性质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欧盟颁布《欧洲区域性或少数民族语言宣言》,其宗旨是致力于保护区域性和少数民族语言,促使各成员国政府采取适合各自具体国情的积极措施,支持和促进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促进语言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平等,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为非歧视性原则的实施做出贡献(王静 2013)。美国以社区为单位,在儿童早期就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与双语教学项目联合起来推进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借此实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田有兰 2013)。不少非洲国家意识到语言问题触及其发展核心,因此在语言政策上普遍开始重视本土语言,鼓励民众更多地使用本土语言(罗美娜 2011)。澳大利亚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方面开展很多工作,支持《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并制定《反种族歧视法》。中国也正在积极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以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目前,组织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旨在规范化、科学化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无论在欧美大陆还是在亚洲、澳洲或非洲,那些发达、较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濒危语言的保护与扶持非常主动与积极(哈正利 杨佳琦 2012)。
语言族群对语言濒危状况的不同态度可以成为促进语言发展或加速语言灭亡的强大力量,正面的语言意识形态无疑会激发语言族群保持母语的积极性。新西兰毛利语言文化由于受到欧洲殖民者长期的同化、融合政策而面临灭绝的危险。毛利人为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有争取母语官方地位、教育主导权和创立民族语母语环境等,其成效是新西兰政府通过《毛利语言法案》(Maori Language Act of 1987),毛利语被确定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之一(何丽 2014)。北美印第安人通过多种努力与争取,到1988年已有超过50%的人学习本民族语。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最初只以书写形式存在,后被复兴为日常生活语言,已成为新一代以色列儿童的母语(白瑞思 2009)。日本两万多阿依努人原本只有三百余人会说本族语。为保护本民族语言,他们建立协会、文化博物馆、资料馆、文化振兴研究促进组织和“同胞恳谈会”等组织与机构,开展多种活动,使自己的语言得到保存与传承。濒危语言保护的中坚力量始终是那些濒危语言使用的族群,濒危语言保护的成效最终也体现在这些语言的使用上。
扶持濒危语言、保护语言多样性,不只是一种生态伦理,在当今国际政治背景下更是一种政治伦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成为发展中国家自我辩护、自我肯定的一种理论(单世联 2005)。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族群语言的基础,也是少数族群保护本族文化和语言的强有力理论武器,是少数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根据这一政治伦理,扶持濒危语言和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反对语言霸权。对于全球来说,反对语言霸权就是反对英语霸权。目前,在所有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自卑心理、实用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强力下,从个人到社会都被淹没在英语洪流中。大卫·克里斯托(D. Crystal)在《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EnglishasaGlobalLanguage)中指出, 英语霸权加剧世界语言的濒危和消失(曹杰旺 2005)。如果全球化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由此带来的语言霸权就是对语言多样性的巨大挑战;如果语言霸权现象不能改变,语言濒危趋势得不到控制,语言生态体系将受到严重破坏,世界的多样性平衡将被打破。弗思曼(J. Fishman)说,“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朱风云 2003)。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存在之源,语言不能随意地剥夺。语言“多样性”是不同民族国家与少数族群“走自己的路”的一个基本理由(单世联 2005),其政治意义也在于它从文化角度反抗各种形式的国际强权政治,内在地要求代表不同文化的国家承担尊重其他民族国家与少数族群语言文化的政治责任。
5 结束语
多样性创造世界和生活的丰富性。维护语言多样性就是维护世界和生活的多样性。抢救和保护语言是21世纪的重大挑战之一。在语言不断减少的大趋势下,维护语言多样性需要上至联合国、下至语言族群及语言使用个体的积极自觉的实践活动。
白瑞思. 世界濒危语言的抢救和复兴[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3).
曹杰旺. 关于英语霸权时代民族语言文化保护的思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8).
杜 茜. 从生物多样性到语言多样性[J].北方语言论丛, 2011(11).
范俊军. 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 2005(11).
哈正利 杨佳琦.国外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经验及其启示[J]. 广西民族研究, 2012(2).
何 丽. 濒危语言保护与语言复兴[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民族语文,2006(3).
罗伯特·迪克森.语言兴衰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罗美娜. 非洲国家的多元语言使用问题[J].世界民族, 2011(2).
梅德明. 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4(1).
单世联.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J].天津社会科学, 2005(2).
田有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理论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实践[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王 静. 多语言的欧盟及其少数民族语言政策[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郑梦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问题规约情况[J]. 世界民族, 2008(5).
朱风云. 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外语研究, 2003(6).
Crystal, D.TheCambridgeEncyclopediaofLanguag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Daniel, N. Explaining Global Patterns of Language Diversity[J].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 1998(17).
Wilson, E.O.Biodiversity[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EcologicalSignificanceofLanguageDiversity
Wen Lan-fang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Human language features diversity, which functions as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Languages diversity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ayered. It is the stat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It is value narrative as well as factual narrative. The value of maintaining the language diversity is embodied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cological system as well as human being.
language diversity;biodiversity; endangered language;ecology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外语课程融合研究——一种和谐课程观”(12WLH34)和湖南省十二五教科规划课题“外语课程价值取向与价值实现研究”(XJK12YYB002)的阶段性成果。
H0-05
A
1000-0100(2016)01-0028-4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1.005
定稿日期:2015-09-13
【责任编辑谢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