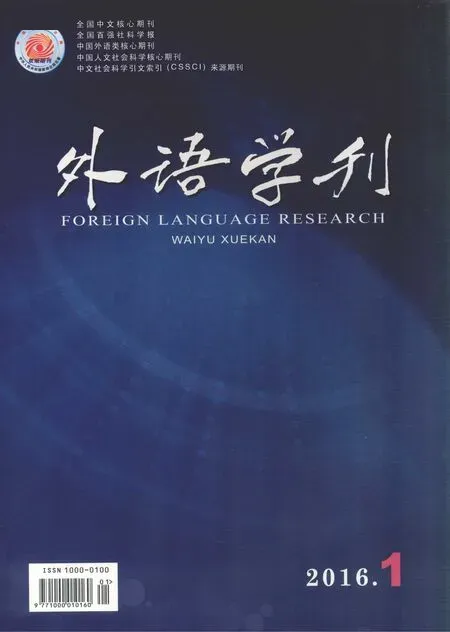意义整体论与话语理解疑难*
王爱华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611731)
意义整体论与话语理解疑难*
王爱华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611731)
意义整体论主张,一个表达式(语言或心智表征)的意义由它与其所在系统内的所有其它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一些哲学家认为,意义整体论必然导致种种语言学上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意义整体论正确,人们之间的交流将变成不可能,因为意义整体论必然产生“全局效应”,造成意义变化不定,话语理解难以实现。本文认为,哲学家们提出话语理解疑难时,犯了3个重要错误:一是片面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变化关系;二是混淆了存在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三是对理解(包括话语理解)的错误领会。就前者而言,所谓意义整体论所带来的“变化全局效应”问题,没有区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把所有变化都看成质变。第三个错误将语言的整体属性看为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并将理解看成是一个被动机械的行为。本文认为,话语理解涉及的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间的互动,才是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语词意义的整体性,不是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也不是话语理解的障碍。
意义整体论;话语理解疑难
1 意义整体论
虽然Saussure的结构主义和Frege 的语境主义早已经体现意义整体论的思想,但最早将该论题引入语言哲学的是Quine(1951)。一般认为,Quine的理论整体论的提出基于Duhem-论题,以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即意义证实论。意义证实论有两个基本特性:证实性(verificationist)和原子属性(atomic)。证实性是指句子的意义由证实它的经验构成。原子属性是指每个句子有其特有的证实经验,只要掌握这些证实经验,每个句子可以独立于其他句子而被理解。但是,Quine和其他逻辑实证主义者(如Neurath和Carnap)发现,几乎没有句子具有单个证实经验。很多句子能够被正确地断言,不是因为发生某些经验,而是它们与其他为真的句子有归纳或演绎的推理关系。Quine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指出,意义证实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关于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 (Quine 1951:42)。
Quine之后,意义整体论在Wittgenstein(1953)和Davidson(1967,2001)等哲学家的语言观,以及Brandom(1994)、Block(1986)、Bilgrami(1986, 1998)和王爱华( 2013)等的推理作用语义学(inferential semantics)中得到发展。这些哲学家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基本主张,即一个表达式(语言或心智表征)的意义由它与其所在系统内的所有其它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全局整体论(global holism),或理论整体论(theory holism)(Young 1992)。这里的全局或理论是语言系统。例如,Wittgenstein说,“理解一个句子,就是理解一种语言”(Wittgenstein 1953:PI §199);Davidson在“Truth and Meaning”中说,“只有在语言的语境中,句子(由此,语词)才有意义” (Davidson 1967)。正如心脏只有在整个机体中才是心脏;财政部只有在机构的整个系统中才是财政机构(Fodor, Lepore 1992:ix)一样,语词和句子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有意义。
2 对意义整体论的反驳:话语理解疑难
对意义整体论的反驳起始于Dummett(1991:chapter 10)。他认为,意义整体论必然导致种种语言学上的难题,其中之一是,如果意义整体论正确,说话人的交流将不可能。基本理由有两个:第一,一个句子不可能被理解,除非所有的句子都被理解。比如,对“这是草莓”这个句子的理解,依赖于对所有其他汉语句子的理解,包括对“四川发生了大地震”这个句子的理解。第二,整体论必然是唯我论的(solipsistic)。每个人拥有不同的整体理论(total theory)(即对整个语言系统的掌握是不同的),没有两个人会有完全相同的语言知识集。这会导致如下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关于其他说话人具有的语言知识,就没有办法获得他们的某个句子的意义。Dummett相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人相信的一切,除非我们能知道他们所有话语的意义。
Dummett的反驳起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如果整体论正确,句子的意义会随着整个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语言系统中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导致整体系统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任何差异所带来的全局效应(global effects of any difference)”。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整体网络有任何一点不相同,两个网络涉及的所有表达式的意义必须不同,因为意义是构成性的,由整体网络来识别(Fodor,Lepore 1992,1999)。由于表达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整体网络,如推理关系,在两个人之间肯定不同,意义整体论使语言交流成为不可能:任何两个人会给语音相同的语词分配不同的意义,因而彼此不可能相互理解,因为交流可能的唯一情形是:两交流者的意义构成网络完全一致。Weir(1985)甚至警告说,整体论引起一个幽灵——激进的不可通约。
为解决上述疑难,哲学家们采用两种进路。一是放弃全局整体论,寻求一种所谓可行的意义原子论(Fodor, Lepore 1992)或意义分子论 (molecularism)(Dummett 1973)。原子论认为,单个表达式可以不依赖系统内其它表达式而具有意义,就是指称意义。原子论因其过于简单和解释力极差,至少不能解答Frege困惑(1952)和Kripke困惑(1980)(两个困惑都表明,意义研究不应仅仅是指称的研究,还应包括对sense, narrow content等的研究),而为多数哲学家弃绝。分子论又叫温和整体论(moderate holism),其主张是,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只依赖于整个系统中部分表达式,而非所有表达式。这个主张的困难是无法确定系统中哪些部分可依赖,哪些部分不可依赖。二是保留全局整体论,寻求话语理解的合理解释。比如,Jackman(1999)、Margolis和Laurence(1998)、 Lormand(1996)、Becker(1998)、Jorgensen(2009)、Penco(2002)和Podlaskowski(2010)等分别从多重意义观、意义相似性、全局与局部整体论的划分、经济学的类比分析、意义倾向论(semantic dispositionalism)与意义整体论的相容性等多种角度解答意义不稳定性导致的交流和翻译等问题。这些解决方案都不成功,因为它们仍面临很多困难。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讨论这些困难。
3 对话语理解疑难的反驳
本文将不遵循上述两种进路,也不评论两种进路,而要说明这两种进路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Dummett等哲学家所谓的由意义整体导致的话语理解疑难,隐含3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片面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变化关系;二是混淆存在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三是对理解(包括话语理解)的错误领会。
3.1 整体与部分的变化关系
我们先讨论Dummett反驳意义整体论所基于的前提,即“任何差异带来的全局效应”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全局效应问题,没有区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把所有变化都看成质变。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具有质和量两个属性。量是指衡量事物某种状态的数量或具体形式;质是指事物的性质或本质。量变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变化,是连续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的变化,是一种飞跃,往往表现为突变,通常是当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原来的部分本质被扬弃,而产生新质。但是,在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之前,由于超距作用,整体以自己特定方式统一规范所有部分之间的变化与相互作用,使千变万化的系统仍然是同一个整体,不至于瓦解,而是继续存在(吴石山 2013:37-38)。
就语言系统而言,其变化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单个语词意义的改变,语义的增减,语词的消失与增添,句法规则的微调,都属于量变性质;单个人的词汇数量不同,或掌握的意义有差异,也应归属于量变范畴。在量变过程中,语言系统的超距作用统一规范着每一个变化,使其保持同一的整体。语言系统的这种统一规范作用,常见于外来词在语形、语义、或语音上为了适应语言系统的特征而有的变化。例如,英语中有很多外来词,已本土化而失去外来词的特征。如commence原是法语词,如今在英语中从语音、语形上都看不到法语的特征,完全英语化。这样的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还没有使人们使用的语言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在我们看来,语言中的变化基本上都是量变,任一语词的改变,都不会使整个语言系统发生质变,以致无法辨认和理解。以此类推,个人之间的语词理解差异或语词掌握的数量大小,也都是量变,都不会使个人的整个语言系统发生质变,而成为不被理解或识别的语言。
所谓的“任何差异带来的全局效应”问题,错误地把所有变化都当成质变,否定或忽略量变。由此,我们认为,如果Dummett反驳意义整体论的这个“全局效应”前提是错的,那么他对意义整体论的所有反驳都站不住脚。
3.2 意义整体论与话语理解分属不同的范畴
即使我们假定“全局效应”成立,意义整体论也不会导致话语理解疑难。因为意义整体论与话语理解分属于不同的范畴。意义整体论属于存在论问题,话语理解属于认识论问题。一事物的存在与否,属于存在论问题,不依赖于我们的理解与认识。深林中,一棵树倒下,从存在论上看肯定产生声音,但从认识论上看,如果树倒下时,旁边有听力正常的人,就感知到这声音,对于远离深林的城市人来说,这声音因没有被感知到,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理解与认识,但是理解与认识需要条件,比如,某人是否感知到树倒下时发出的声音,有距离与听力等条件限制,这些条件显然与事物存在的特性无关。当然,事物的特性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其认识的方式,但不会导致认识与理解成为不可能。例如,如果一个物体如此高大,以至于我仰头也看不到它的顶部,但我可以退后一点,或用望远镜,或用梯子等方式,终究能看到顶部。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用某一方式无法看到顶部,就宣告说我无法认识这一物体。
如果认为意义整体论会导致话语理解成为不可能,那只能是因为这种主张有一个错误的预设,即被理解对象的特性是理解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即事物存在方式和特性决定我们认识论上的理解。如果理解对象是单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能理解,如果理解对象具有整体性,因其整体的模糊性和整体效应,而无法被理解。这样的错误预设把理解看成只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被动接收的、无发展变化的过程。然而,人类的理解远不是这样的过程。理解或认识是人的心智特性或能力,是人之成为人的本性,有其自身活动的规律。现代认知语言学揭示,人类心智对外在世界的识解,是一个相当能动与复杂的过程。真实的情形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成功的话语理解。那么话语理解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我们这里循着Davidson对话语理解的讨论,借用现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3.3 话语理解的条件
根据Davidson(1973;2001;2002b;2005a,b),理解的必须条件是自我、他者和客观世界构成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自我、他者和客观世界三者缺一不可。它们既相互影响和制约,又有各自独特的作用。自我与他者作为理性存在构成社会关系,这两个理性存在又分别与世界构成因果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和因果关系的相互关联,确定话语的意义,使理解成为可能。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自我、他者和客观世界各自在话语理解中的独特作用,它们如何互动达成话语理解。目的是想说明语词意义的整体性,不是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也不是话语理解的障碍。
3.31 话语理解的条件之一:客观世界与真概念
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是话语理解的必要条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话语理解离不开物质世界;第二,我们的语言里包含世界的道理或逻辑。外部世界是我们赖以生计的环境,为了生计,人类从一开始就学会或掌握观察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推理活动。这种对万物关系的把握能力以及大脑的推理能力可以使我们理解各类话语,甚至完全不懂的话语。
哲学中的两个思想实验,即Quine的“最原初的翻译”和Davidson的“最原初的解释”,正是利用人类的这两种能力。Quine(1960:chapter2)设想一个田野语言学家遇到一种完全陌生的土著语言时,他理解该土著语言所依赖的,除了他自己的语言、他有关世界的信念,赞成和否定、真与假,以及与此相关的逻辑性质和各种可能性假设外,就只有他和土著人所共享的环境和刺激。那么这个语言学家在翻译土著语言时,他能利用的认识论资源就由3个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1)土著人说的话语(U);(2)包括说话这个行为本身在内的土著人相关的可观察行为(B);(3)土著人与语言学家共享的外界环境和环境变化(C)。这3个认识论资源构成语言学家的全部外来信息,Quine称其为感觉刺激(S),如此形成一个由此3类要素构成的三元组世界:S=
Davidson(1973)在Quine的基础上提出“最原初的解释”观。他赞同Quine的观点,认为可观察行为是语言学家解释土著语最初的基本材料之一,我们能从相应场景中发现土著人对观察句的同意和不同意的态度也有很强的经验上的保证。但Davidson的更进一步是把经验事实与Tarski的真理论框架结合起来。他认为,无论你对真之本性如何看待,赞同与否这件事是同真联系在一起的。对于Dummett(1978)赞同或断定先于真,而对于Davidson真是原初的,用它可以解释同意和断定的态度。Davidson(2002:210-211)直接把持定一个句子为真(holding a sentence true)当作对土著语解释的基本证据,因为一个解释者不能直接观察另一个人的命题态度;信念、意愿、意向,包括那些部分地决定话语意义的意向,都是肉眼不可察知的。但是解释者可以直接观察非个体化态度,如“持定一个句子为真”这个态度是非个体化的,因为说话人与话语之间的持真态度是外延关系,是在不知句子表达的意义时能被确知其成立的关系。持真态度的好处在于,有这种态度和周围的场景便能发现说出句子的真值条件,并从而揭示出意义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持真态度使我们对话语的理解具有一个切入点,即在意义和信念都不知道也不能假设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持真态度这个切入口进入到意义和信念的领地,以达到对语句的理解和解释。由于持真态度本身没有给出意义,它必须与能更直接地给出意义的要素联系起来。在Davidson看来,实现这一联系的框架就是Tarski关于真的理论模式,即T约定。所谓T约定,是能由真定义中推出所有那些T-句子,即S is true if and only if P. 那么证明的基础框架就可以从这些T-句子上着手。于是田野语言学家对土著语的理解所需要的证据,在Quine的基础上增加了说话人认为句子真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S=< U, B, C, T>。
Davidson的T-句子设定,隐含一个基本的假定,即语言能大致正确地描述这个世界。语言并没有严重歪曲或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看到的世界大致是语言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尽管存在大量模糊不清的概念,但不可否认,通过语言大致上能触及到世界的真理(Davidson 2005a:129)。
Quine的“最原初的翻译”与Davidson的“最原初的解释”假设,涉及很多哲学问题,也存在很多争议,但这两个假设至少说明,具体的语境和客观世界是话语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我们的语言里包含世界的道理或逻辑,语言与真这个概念分不开。我们共享一个客观世界,即使我们不共享一种语言,但由于语言大致真实地描述我们共享的世界,话语理解还是可能的。“意义整体论导致的话语理解疑难”这个论断忽略世界和环境在话语理解的作用。
3.32 话语理解的条件之二:自我与他者的理性维度
上文提及的人们对世界万物关系的把握能力以及大脑的推理能力,已经表明人具有理性。在这一节,我们将专门讨论人的理性维度,集中考察在话语理解中人的心智如何运作,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将证明:对于理性存在来说,理解是一种最为基本的能力,理解无处不在。
3.321 理解对整体敏感,从局部开始
理解是人类心智的能力,也是一种认知活动。哲学家所谓意义整体论造成的理解疑难,涉及的不是心智能力问题,而是认知活动或过程问题。任何一种认知活动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发生。对于这种认知过程,目前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McClamrock 1989:258):(1)理解过程具有整体性(holistic)、全局性(global)或非分解性(non-decomposable)。也就是说,心智不是部分达到的(mind doesn’t come in parts);(2)分解(decomposability)是理解的先决条件。如果通过信息处理的方法来解释这两个对立阵营,前者认为理解在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top-down),即我们关于世界的总体知识渗透于我们的感知加工处理,知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种关联和影响没有原则上的限制。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对政治的了解,会影响我们对草莓的感知理解。而分解观认为,感知理解在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bottom-up),这就是认知上的不可进入性(cognitively impenetable)(Pylyshyn 1984:130-145),或Fodor(1983)所说的“信息上的封闭性”(informationally encapsulated),即我们的感知理解对背景知识的获取非常有限。我们对政治的了解不会影响我们对草莓的理解。
感知理解的整体性和分解性,看似相互对立,其实是相容的(McClamrock 1989:268)。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解既具有整体性也具有分解性。从理解过程来看,人们从实际具体的清楚表征开始,这个过程是局部的、封闭的、模块性的。但是用什么类型的表征启动我们的理解,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携带两种信息:(1)对具体模块直接敏感的信息,涉及对模块的内在运作;(2)对整体系统间接敏感的信息,这种信息限制理解的范围,但在对模块处理的内在运作中不起作用。也就是说,一旦理解的整体范围被给出,剩下的所有事项便是局部性的或模块性的加工处理。这说明理解的整体性与局部性是相容的。
理解的这种整体性与分解性的相容特性也可以用来解释话语理解。Heidegger认为,“语言的本性当然只能在那个发生的维度中获得理解”(转引张祥龙2003:251)。也就是说,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理解只能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问题是,语言的本体性和现实性如何相容呢?显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语言本体性,同展现在具体时空中的语言现实性之间存在矛盾。对此,海德格尔给出的办法是“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海德格尔 2004:239)。海德格尔这句话中的3个“语言”既相同又不同。第一个“语言”强调语言的本体性;第二个“语言”强调语言的现实性;而第三个“语言”强调语言的统一性。他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把作为本体语言的现实语言带向(统一的)语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方式就是使用。通过使用,本体的语言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使用,本体的语言展现在现实之中,并获得自身的统一。
由此可见,语言在本性上是整体性的,而语言的现实性(语言的使用与理解)是分解性的。语言的整体性和分解性统一于语言使用。而话语理解显然是对现实使用中的语言的理解,而不是对本体性语言的理解。同理,语言学习也应该是对使用中的语言的学习,而非对本体性语言的学习。
现在我们回到话语理解的疑难问题。如果我们担心一个句子不可能被理解,除非语言系统的所有句子被理解,这个担忧在本质上没有看到理解的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相容特性。如果理解具有分解性,那么单个句子可以被理解,并且随着理解的推进,语言系统的所有句子将被近似地分解,而最终被理解。而每一次的理解总会受到个体掌握的知识集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常有误解发生。
3.322 善意原则
如果我们的话语理解对语言整体敏感,但总是从局部开始,那么这个局部理解是如何开始的(或实现的)?也就是说,Davidson和Quine所设想那个田野语言学家在理解或解释土著语时,认为真与T-句子的真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设想和达到这一点需要借助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Davidson(1973)所谓的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善意原则的大致内容是:在理解他人话语时,首先要假定对方不是在骗自己,对方说的都是真话。的确,理解者无法事先知道说话人是否故意在隐瞒什么,是不是在说真话,说话者也的确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也就是说,有太多的不定因素会使“别人不是在骗自己”这一点得不到保证。然而如果要使交流成功的话,设定这一条却是必要的。只有认为别人在说真话,才能进一步根据说话者的话语的真值条件来解释说话人的话语意义,进而达到交流的目的。由此看来,善意是强加于会话双方的,无论交际双方是否喜欢它,如果他们想要相互理解,就必须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对方看作正确的,是在说真话。假定说话人的语句为真之后,便是对语句为真的条件进行解释。接下来的问题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真理论如何才能相互沟通呢?理解者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根据说话人说话的时间、地点以及其他语境因素,也就是,我们的话语理解都依托于Searle(1983,1992)所说的background,用自己的真理论推及说话人的真理论,为说话人说出的语句提供一个成真条件。
理解者在理解他人的话语时,必须要依据自己的真理论,这一过程近似于Gadamer(1989)的前理解。理解者在进入理解前,必然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前有、关系态度和前见。前有是理解者具有的知识与能力背景,关系态度是理解者具有的价值观念、目的、欲求、情态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各种事物的态度。前见,即前判断、前把握,或筹划,是基于前有和关系态度,在进一步寻找证据之前所做的判断,或给理解话语划定的视角与意义期待,这就是所谓的“谁在理解,谁就一直在进行筹划”。
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前理解或真理论,理解就似乎完全是主观的,没有正确标准。但Davidson强调的真这个概念以及Gadamer(1989)的特定历史的合理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就真这个概念而言,一个人的大多数信念必定是真的,“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对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一般图景是错的;因为真实这幅图景向我们报告其他信念,并且使它们可以被理解,无论它们是真还是假”(Davidson 2001b:146)。Gadamer认为,理解受历史传统的限制。我们被抛入特定的历史处境,其中包含有特定的合理性标准,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合理性标准而任意理解。真这个概念与特定历史的合理性标准,使我们的理解具有公共客观的基础。
3.323 人的合理性
话语理解之所以可能,还因为人具有寻求合理性的内在本能。那么什么叫合理性?根据Davidson(1967)的因果理论,如果一个人一致地将自己的信念作为根据来行动,或者有根据地持有信念,那么他就是理性的,即他的行动或信念具有合理性。信念和意向等的心智状态可以是行动的原因。但是,要解释一个行为,且使一个行为合乎理性,必须为这个行为提供理由(reasons)。理由又必须在逻辑上支持这个行为及其相关的命题态度,才能使其成为理性的。故此,理由作为行动的解释,使行动具有理性,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行动必须有理由。第二,理由必须与关于行为结果的相应信念有逻辑关系,认可一个信念的理由应该是逻辑上支持它的其他信念。比如,解释某人每天跳操的行为,可能需要假定他认为健康是幸福的,跳操有益于健康。当问他为什么每天都跳操时,他回答说,因为跳操会导致幸福的结果,这是一种合理性的解释。
我们在理解他人话语时,出于善意原则,会假定说话人的行为和信念具有合理性,他所说的话语也具有合理性。其实Davidson甚至认为,合理性是语言和思维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一切具有命题态度的生物共同享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基本原则,比如一致性的要求和基本的逻辑原则。在这些要求和原则面前,行为者或行为的评价者或批评者的合理性标准趋于重合(Davidson 2004:346, 351)。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确定一个基本标准或原则的集,并使它永远固定下来,也不可能事先决定一个与合理性标准值偏离的可允许的程度(Davidson 1993: 297)。但重要的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划出理性原则与非理性偏差之间的明确界限,而是非理性之发生及对它的理解如何依赖于理解理性和在基本方面的理性存在。
3.33 话语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他者-世界3者的关系维度
我、他者和世界3者的关系在前面两节已隐性地谈到,在这里我们将直接地讨论3者如何互动,使话语理解能成功达成。
话语理解发生于至少两个生物之间,即我和他者之间。他者如何分辨出我的一串声音具有什么意义?确定一串声音的意义需要3个必要条件(Davidson 2002a: 120):(1) 说话人使自己能被解释,(2)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意欲自己的话能被解释(Grice的心理主义),(3)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与外在世界的因果关系。这就是Davidson所说的因果-社会三角测量模式(王静 2005:106)。在这个三角测量模式中,两个生物从不同的方向对来自某一方向的感觉刺激进行反应,他们的视线在共享原因那里相交。这时,如果这两个生物注意到彼此的反应(如言语反应),两人都能将观察到的反应与自己来自世界的刺激联系起来,于是共享原因得以确定,三角形得以形成,思想和语言的内容得以赋予,但必须两个人同时进行三角测量来完成(Davidson 2002:213)。
在三角测量过程中,人的理性发挥着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作为理性存在者,我和他者各自对共享世界进行能动观察与理性把握,与世界发生因果关系,同时运用善意原则将自己的合理性与世界的因果关系赋予对方,与对方发生社会关系。意义在因果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被确定与理解。
Cornejo(2008:175)把通过上述因果关系和社会关系获得的意义称为“具有生机的现象学经验”(a lively 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Cornejo所说的意义现象维度与Searle(1994)的所谓“存在上的主观性”(ontologically subjective)在概念上大致相似。意义是经验,是基本的由第一人称感知的经验,但同时也是与他者在一起的经验。将意义看成经验,就会将意义安顿在一个在世之在的有机体里(anchor meaning to a certain organismic being-in-the-world)(Cornejor 2008:176)。于是,意义总是一个情景现象,离不开语境和互动环境。我与他者共享一个充足的复杂的非语言背景知识,这允许合作指称行为(collaborative referring)的发生。 当我们住在同一世界,我们趋向于与他者一同感受,像他者一样去感受。共同经历(co-experiencing)同时能从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被注意到。意义的现象维度总是隐含在任一主体间的相遇,而主体间的可观察的共时同感是语言理解的现象学基础。由此观之,语言意义和理解同时体现出社会的、现象的和生物的维度。
3.4 话语理解不需要的条件:语言的约定性和整体性
上文对话语理解的必要条件讨论表明,语言的特性不是话语理解的必要条件。首先,我和他者的社会关系,关键在于观察他人对同一对象的相似性反应,这个相似性的反应反过来作用于我们对外在对象的观察和对比。两个生物之间的这个社会因素,并不在于言语或社会的约定,因为即使我和他者所处的文化知识背景不同、所用的语言不同,甚至所持的思想也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对同一对象进行交流。即使在同一语言共同体中,表达式的意义也不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的约定,关键在于我们认为是真的语句与语句对应的对象在世界中的状况是否符合。例如,日常语言使用中有很多反常规现象,如隐喻(Davidson 2001a)和用词错误(nalaprop)(Davidson 2005)。二者之所以反常规,是因为仅仅就语句的字面意义而言是无法被理解的。大多数隐喻语句,就其字面严格的意思而言,显然是假的,如“世界是舞台”, “基督是一座天文钟”等诸如此类的隐喻。尽管一个隐喻语句从字面上看似荒谬和矛盾,但它仍然能被理解,就在于这种荒谬和矛盾恰好保证我们不会从其字面意思上相信它,并且使我们(在一些恰当场合)以隐喻的方式理解这个语句。
用词错误也是一种普存现象,但同样能被解释者毫无费力地理解,显然不是因为有共享的约定和规则,因为所说的话照其字面意思无法理解。有趣的是,只要说话人本意想让对方听懂,听者不难按照说话人意向的方式准确理解说话人带有简单用词错误的话语。为了解释这一言语行为现象,Davidson(2005)提出两个新概念:先有理论(prior theory)和即兴理论(passing theory)。对于解释者来说,先有理论表达他在事前准备如何解释说话者的话语,即兴理论表达他实际上如何解释这个话语。对于说话人,先有理论是他相信解释者的先有理论是什么,即兴理论是他想让解释者使用的理论。显然,先有理论和即兴理论都不是共享的语言。就先有理论而言,交流双方完全可以不相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阅历、所受教育肯定不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技工对“阀门”的理解与非技工对其理解,肯定有差别。当这两人提到“阀门”时,他们的先有理论并没有对上号,但是仍可以达到正确的理解。在整个交流过程中,先有理论有助于即兴理论的形成,但不能决定即兴理论。与先有理论相比,即兴理论更不是共享语言,因为即兴理论不但对每一个人可以不同,且对每一个人的每一具体交流场景都可以不同。然而,Davidson认为,即兴理论是交流成功必须共享的,“因为即兴理论是解释者实际上用来解释话语的理论,它也是说话者倾向于解释者使用的理论。仅当它们重合,理解才能完成”(Davidson 2005:442)。因此,交流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到达即兴理论的一致,是解释成功的标志。他还认为,语言能力是不时地会聚于即兴理论的能力,因为不存在到达即兴理论的规则,所以无法对这个过程进行规范化(Davidson 2005:45-446)。即兴理论的达到,近似于科学发现的过程,即没有一般的方法,原则上永远面对新的情况。但即兴理论的达到与科学发现有实质上的不同:科学发现的结果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而即兴理论只能是一些一个个特定交流场合下即时得出的“意义”的堆积(叶闯 2006:391)。
总而言之,对隐喻与用词错误的理解超出语言的约定性,语言不是我们理解的必要条件。那么什么保证这种正确的理解?按照Davidson的术语,成功的交流中什么导致即兴理论的获取与共享?根据Davidson的观点,一个人学会一种语言,就掌握一种能够获得正确即兴理论的能力。交际能够成功,或交际双方能达到一个共享的即兴理论,虽然有侥幸的成分,但是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能借助机智、从个人词汇和语法中获得智慧、使自己被理解的方法知识、推出什么偏离词典最有可能的拇指规则(或经验法则)(Davidson 2005:107)等理性活动,能获得交流的成功,即获得一致的即兴理论。
其次,既然语言不是话语理解的必要条件,语言的整体性质也不会成为语言理解的障碍,更不会使语言理解成为不可能。中国的禅宗机缘性会话(Zen’s encounter dialogue)甚至表明,理解不需要语词,语义甚至成为在会话中被破坏的对象。如《五灯会元》中的“你有柱子,我与你柱子。你无柱子,我夺你柱子”。如何理解这样的禅宗语言?语词与意义在这里没有多大帮助。据说僧人要理解这样的禅宗语言,靠的是当下的禅悟。我们认为,这个当下的作用就是Davidson的三角测量中我、他者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作用。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王爱华. Brandom的意义整体论和交流观[J]. 外语学刊, 2013(2).
王 静. 基于先验论证的戴维森纲领研究[D].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吴石山. 整体及其认识方法[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叶 闯. 理解的条件——戴维森的解释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张祥龙. 现象学导论[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3.
Becker, K. On the Perfectly General Nature of Instability in Meaning Holism[J].JournalofPhilosophy, 1998 (12).
Bilgrami, A. Meaning, Holism and Use[A]. In: LePore, E.(Ed.),TruthandInterpretation:PerspectivesonthePhilosophyofDonaldDavidson[C]. Oxford:Blackwell, 1986.
Bilgrami, A. Why Holism Is Harmless and Necessary[J].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Mind,LanguageandOntology, 1998(12).
Block, N. Advertisement for a Semantics for Psychology [J].MidwestStudiesinPhilosophy, 1986(10).
Brandom, R.MakingIt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DiscursiveCommit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vidson, D. Truth and Meaning[J].Synthese, 1967(3).
Davidson, D. Radical Interpretation[J].Dialectica, 1973(3-4).
Davidson, D. Paradoxes of Irrationality[A]. In: Davidson, D.(Ed.),ProblemsofRationality[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Davidson, D.LocatingLiteraryLanguage,LiteraryTheoryafterDavidson[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l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dson, D. What Metaphors Mean[C]. In: Davidson, D.(Ed.),InquiriesintoTruthandInterpreta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a.
Davidson, D.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A]. In: Davidson, D.(Ed.),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
Davidson, D. The Emergence of Thought[A]. In:Davidson, D.(Ed.),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c.
Davidson, D. The Second Person[A]. In: Davidson, D.(Ed.),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a.
Davidson, D. Three Varieties of Knowledge[A]. In: Davidson, D.(Ed.),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andObjectiv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b.
Davidson, D. Incoherence and Irrationality[A]. In: Davidson, D.(Ed.),ProblemsofRationalit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son, D. Seeing Through Language[A]. In: Davidson, D.(Ed.),Truth,LanguageandHistor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a.
Davidson, D.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A]. In: Davidosn, D.(Ed.),Truth,Language,andHistor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b.
Dummett, M.TheLogicalBasisofMetaphysic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A]. In: Geach, P., Black, M.(Eds.),Translationsfrom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GottlobFrege[C]. Oxford: Backwell, 1952.
Fodor, J.A.TheModularityofMind[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3.
Fodor, J., Lepore, E.Holism:AShopper’sGuid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Fodor, J., Lepore, E. All at Sea in Semantic Space: Churchland on Meaning Similarity[J].JournalofPhilosophy,1999(96).
Gadamer, H.-G.TruthandMethod[M].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89.
Gregory, R. L.EyeandBrain[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Jackman, H. Moderate Holism and the Instability Thesis[J].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 1999(4).
Jorgensen, A. K. Holism, Communi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Meaning: Lessons from an Economic Analogy[J].Philosophia, 2009 (1).
Lormand, E. How to Be a Meaning Holist[J].TheJournalofPhilosophy, 1996 (2).
Margolis, E., Laurence, S. Multiple Meanings and Stability of Content[J].JournalofPhilosophy, 1998 (5).
Marr, D.Vision:AComputationalApproach[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Co., 1982.
McClarmrock, R. Holism without Tears: Local and Global Effects in Cognitive Process[J].PhilosophyofScience, 1989 (56).
Penco, C. Holism, Strawberries, and Hair Dryers[J].Topoi, 2002 (1)
Podlaskowski, A.C. Reconciling Semantic Dispositionalism with Semantic Holism[J].Philosophia, 2010 (1).
Pylyshyn, Z.ComputationandCogni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Quine, W.V.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J].PhilosophicalReview, 1951(60).
Quine, W.V.WordandObject[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Searle, J.Intentionality:AnEssayinthePhilosophyofMi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earle, J.TheRediscoveryoftheMind[M].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2.
Searle, J.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A]. In: Casati, R., Smith, B., White, G.(Eds.),PhilosophyandtheCognitiveSciences[C]. Vienna: Holder-Pichler-Tempsky, 1994.
Weir, A. Against Holism[J].PhilosophicalQuarterly,1985(35).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Young, J.O. Holism and Meaning[J].Erkenntnis, 1992 (3).
MeaningHolismandthePuzzleofUtteranceUnderstanding
Wang Ai-hua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Meaning holism holds that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linguistic or mental) is determined by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expressions in the same system. Some philosophers argue that meaning holism would necessarily lead to various problems, one of which is that it will make understanding of utterance and thus communication impossible because it necessarily leads to a so-called “global effect of any difference”. This paper holds that such a claim makes two important mistakes: (1)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hole and part; (2) confusing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3)mis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of utterance). The first mistake lies in its treatment of all changes as qualitative changes with ignorance of quantitative ones. The third mistake regards the holistic property of language as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utterance-understanding and treats understanding as a passive mechanic behavior. We hold that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utterance understanding is not holistic feature of meaning b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others and the world.
meaning holism;the puzzle of utterance understanding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三维意义整体论: 先验、构成与生成”(11YJA740086)和四川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项目“三维意义整体论: 先验、构成与生成”(SC11WY020)的阶段性成果。
B089
A
1000-0100(2016)01-0007-8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1.002
定稿日期:2015-05-13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