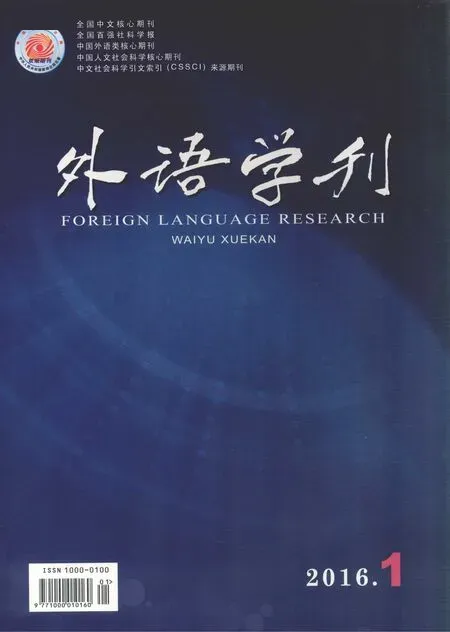巴赫金学派的语言意识形态观和批评话语分析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97)
●语言学
○引进与诠释
巴赫金学派的语言意识形态观和批评话语分析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97)
意识形态批评始终是任何社会批评理论,包括批评话语分析的基本组成部分。目前,大多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传统,同时也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目前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审视巴赫金学派的意识形态观,提出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理解和阐释意识形态的一些建议。
意识形态;巴赫金学派;话语批评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旨在通过语言和语篇分析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其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传统,同时也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正如Williams指出的,鉴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曲折历史和其所要阐明的社会过程的复杂性,“要想无争议地确立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定义是不可能的”(Williams 1977:56)。本文通过对巴赫金学派(the Bakhtin School)语言意识形态观的介绍和讨论来帮助理解意识形态的性质,澄清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表明对话性意识形态批评的必要性。
1 巴赫金学派的意识形态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里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理想主义,是对现实的一种虚假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对劳动大众的剥削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它往往把自己伪装成客观普世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始终是核心概念,但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经常带有贬义。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从“虚假意识”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认为全部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巩固和强化现存秩序服务。Marcuse在批评人们被工业社会中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外观所迷惑、看不到其极权主义的实质时指出:“这种多元的实在成为意识形态的、骗人的东西”(Marcuse 1964:51)。Althusser肯定意识形态为人们理解和解释自己的经验和生存状况提供框架,但同时指出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人们“与其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虚构关系的(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统一体。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为虚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达一种意愿(如保守的、尊奉的、改良的或者是革命的),一种希望或一种怀旧,而不是描述一种现实”(Althusser 1969:233-4)。
虽然意识形态经常被用于否定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趋势,即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列宁在分析本世纪初俄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形势时号召详细系统地阐述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Lenin 1969: 41)。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Gramsci(1971)在总结西欧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他既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经济基础的附带现象,也不同意把意识形态当成一堆错误的观念,而是主张将其视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世界观。他认为马克思只是在论战的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些虚幻颠倒的错误观念。马克思实际上也看到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是一个战斗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活动着,斗争着,并获得关于他们自己地位的意识”(同上:377)。Gramsci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人们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在观念上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人正是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中成长并获得世界观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已获得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行动。意识形态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世界观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arbitrary ideologies),即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意味着它既可用于否定意义又可用于肯定意义。
Gardiner认为,巴赫金学派学者的主要兴趣和思想基本上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太关注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聚焦于上层建筑现象,例如工业化对人类价值观的破坏和商品形式对现代社会文化和民生各领域的不断侵入(Gardiner 1992:5-6)。他们都谴责资本主义把人异化为生产工具,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reify)。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批判性的,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其目的是理解和反思那些压制性的社会结构和贫乏枯竭的思维方式。巴赫金学派把意识形态当作一个中性的甚至积极的概念,指各种社会意识的总合,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被Volosinov等巴赫金学派成员用来指任何表意活动”(同上:71)。
巴赫金学派坚持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和物质性,因为它涉及社会和历史中的具体符号交际:“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具有意义,它表征、刻画或代表外在于其自身的事物。换言之,它是一种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Volosinov 1973:9)。Volosinov如此定义意识形态:“说到意识形态,我们想到的是人们大脑中对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反映和折射的总和;人们通过词语、绘画、图表或者其它形式的符号来表达意识形态”(同上:9)。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以其符号性为前提。一切人类行为和认知都体现在某种符号中,这样的符号会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每一词语都会透露其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因此每一说话者都是意识形态的,每一话语都代表一种意识形态。在选择说什么的时候,说者首先考虑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不是仅仅作为语言表达的话语的局部意义。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植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中,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一种附带现象,而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意识形态反映和折射外在现实,它或者忠实于现实,或者通过另一视角来看现实,它具有歪曲其表征的潜力。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领域都以不同的方式折射现实,但所有领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使用共同的物质符号,因此“每一个意识形态符号都不仅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一个影子,它本身就是现实的物质成分”(同上:11)。
巴赫金与Volosinov一样反对把意识形态视为抽象意识的产物,认为意识形态自身就构成一种物质力量。他同样试图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源于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表征实践,一再强调意识形态符号和意指过程与广阔的社会斗争密切相连,它们自身就构成斗争的领域或者冲突的场所:“思想是活生生的事件,产生和作用于两个或数个意识之间相遇和对话的那一刻”(Bakhtin 1984:88),“个人的言语既反映又生产其在阶级社会中的立场,并由此进入阶级关系的对话中”(Bakhtin 1986:52)。当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受到主流话语或机构话语的渗透之后便会在维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Gardiner将巴赫金学派的意识形态观总结为以下几点:(a)意识形态并非对现实的被动(歪曲性)反映,而是其本身就构成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b)任何人类活动和主体性本身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的符号表征,意识形态参与构成这种表征;(c)意识形态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是表义过程蕴含的核心成分;(d)如果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符号现象,是话语或语篇的产品,那么要抓住意识形态的本质就要去理解和分析其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的具体表达。(Gardiner 1992:66-67)
2 语言和意识形态
巴赫金学派的意识形态观表明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代意识形态批评一直试图探索意义或观念如何影响现实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探索的角度、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但似乎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即在这种探索中语言和话语分析必须占据优先地位。Volosinov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与语言哲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Volosinov 1983:113)。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语言和意识一样古老,语言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实践性意识,它因此也为自我存在;语言跟意识一样产生于与人交往的需求和需要”(Marx, Engels 1978:158)。
20世纪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真思考始自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正是结构主义几乎垄断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打造联系的尝试,至少在发现Bakhtin, Volosinov和Medvedev之前是如此”(Gardiner 1992:143)。Lévi-Strauss在其结构主义的文化分析中将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联系起来,指出文化分析的目标应该是那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的基础结构或深层结构,表层现象正是由它们产生的。Lévi-Strauss尤其感兴趣的是部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神话体系,认为必须通过重构产生具体神话的那些深层转化规则才能认识神话的重要性。神话思想并非前工业化社会所特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神话思想的滋生地(Lévi-Strauss 1968:209-210)。Lévi-Strauss关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对Barthes产生巨大影响,后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主要以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Barthes指出,神话属于二级意指系统(second-order signifying systems),被资产阶级用于强化具体的内涵或意指联想网络,以表达和强化处于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神话其实属于一种一般科学的领域,它与符号学中的语言学具有同样的涵盖范围”(Barthes 1973:111)。
巴赫金学派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源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知识界对语言在文化和政治中作用的争论。当时的形式主义强调语篇结构的重要性,认为语篇中的思想内容或意识形态只是服务于语篇的形式结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语言与社会和意识形态割裂,把语言形式独立于思想内容。不过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他们基本上将语言或语篇仅仅视为传递思想内容的媒介。正是巴赫金学派试图克服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二元论,强调话语的形式结构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结构,语言表达方式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一样影响意识形态信息的生成和接受。意识形态不仅“反映”(reflect)现实,也可能通过语言表征来“折射”(refract)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都因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切而以不同的方式反映或折射现实世界。因此,意识形态符号不仅是表征现实的外壳,而且是社会斗争的赌注和场所:“话语从来都不仅反映或表达已知和确定的存在之物,它总是创造此前从未有过的绝对新鲜的不可重复的事物,它尤其总是与价值(真假、好坏、美丑等)相关”(Bakhtin 1986:119-120)。人类生产和使用的任何东西,包括工具和食物等,都可以转化为超越物体本身的具有意义的符号,因而符号具有歪曲其所表征的现实的潜力,或者忠实于现实,或者通过另一视角来看现实。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领域都以不同的方式折射现实,但其共同点是它们都使用共同的物质符号:“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重叠,它们相互等同。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Volosinov 1973:10)。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并产生社会效果必须依赖物质符号。
人类任何形式的认知和实践活动都是符号过程,意识和文化必须通过具体的媒介形式来传播,媒介难免影响传播的内容及其接受:“意识形态符号对存在的这种折射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同一符号共同体中具有不同倾向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交织重叠,即取决于阶级斗争”(同上:23)。巴赫金一再强调没有中性的符号:“每一话语都有关于正义、美好和真理等的主张”(Bakhtin 1986:123)。而Volosinov精辟地道出符号或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和起作用方式:“不同的阶级会使用同一语言,从而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变成阶级斗争的舞台。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多重音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统治阶级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以超越阶级的永恒特点,扑灭或内化其内部各种价值观之间的斗争,使之成为重音单一的符号。其实,每一个意识形态符号都像雅努斯(Janus)一样具有两面性。任何当下的咒语都可能变成赞美之词,任何当下的真理在许多其他人听上去都会不可避免地像是最大的谎言。符号的这种内在辩证性只有在发生社会危机或变革时才会彻底展示出来。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各种意识形态符号所包含的矛盾并不会充分显露,因为在已经确立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意识形态符号总是有一些反动的性质,似乎总是试图稳定社会生成过程这一辩证潮流中的以往因素,也因此总是强调昨天的真理,使之看上去像今天的真理。这导致占支配地位意识形态里的意识形态符号的折射和歪曲特性”(Volosinov 1973:23-24)。可见,思想不会发生于构成它的符号体系之外,意指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意义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词语总是各种意义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意义也是各种社会冲突的反映。思想不仅反映被观察的客体,也反映观察主体自身及其社会存在:“思想是一双面的镜子,两面都可以并应该明亮清楚。”(Volosinov 1976:26) 这种观点把我们引向作为意识形态符号的语言或话语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Althusser运用弗洛伊德的“下意识”(subconscious)和拉康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提出通过“招呼”(hailing)或者“意识形态质问”(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来解释主体性的建构。巴赫金学派则另辟蹊径,认为主体性或心理并非自主先在的东西,而是通过不同声音或话语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斗争形成。巴赫金认为全部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本质上都具有深刻的主体间性或对话性,这种与他者、与自我(内部话语)或与外部世界之间不断的对话建构人的主体性,并成为任何创造性思维或行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巴赫金看来,自我并非统一意义的最终保证者。巴赫金笔下的自我从来不是完整的,因为它只存在于对话关系中。它本身并非一种物质或本质,而是存在于与所有其他事物尤其是与他者自我的弹性关系中”(Clarke, Holquist 1984:65)。因此,主体性是一种由社会决定的内部复合体,主体之间总是处于对话关系中,它们具有不可预知性和不可量化性:“主体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概念(他自己说话并回应)”(Bakhtin 1986:169)。在巴赫金学派看来,个人意识必定是异体语言性质的,因为一个人掌握的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不可避免地相对于总是存在于那里的所有其他语言。不同体裁、不同职业、不同时代的话语,甚至是不同个人的话语,以及官方语言、文学和政治运动语言都是不同的语言,都是纷繁世界中的“异体语言”(heteroglossia):“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合言语同在的;这是现今和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之间各种社会意义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巴赫金 1998:71)。其结果,“异体语言中的所有语言,无论其背后的原则和独特之处为何,都有其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表达世界的特殊形式和特殊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对象、意义和价值观”(Bakhtin 1981:291-292)。巴赫金这里所说的视角和世界观对每个主体而言显然是一种潜意识中的、背景化了的意识形态。
3 意识形态的语境性和对话性
既然语言和意识形态如此相互依赖,那么意识形态研究就必须包括对表达它们的符号系统的分析。Volosinov指出,意义和形式、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不是自然的,这种联系可能比较稳定,但“语言形式和价值观判断之间的联系是出于理所当然的教条信念,这种信念不容讨论”(Volosinov 1976:101)。Volosinov的观点既在某种意义上修正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说,又应和沃尔夫关于意识形态内在于语言并构成人们言语交际的背景化常识的观点(Whorf 1956:220)。巴赫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Medvedev(1985)在谈论言语体裁时也指出,“每一体裁都有明确的选择原则、明确的观察与认识现实的方式和明确的探究范围和深度”(Gardiner 1992:22)。这种体裁构成某种意识形态框架或者文化“格栅”(grid),在此框架内话语形成各自具体的语义和形式特征。如果语言和意识形态如此相互胶着,那么任何话语里都存在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而当代话语批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这一事实及其含义,例如“批评话语分析是关于事物如何被自然接受的理论。经常提到的观点是我们的许多信念和表征可能看上去很自然,但它们是被自然化了”(Stubbs 2002:208)。意识形态意义在不被察觉时才最有效,它作为背景知识一方面引导语篇生成者以特定方式来描绘世界,另一方面引导读者以特定方式来理解语篇:“语篇通常并不是向外‘喷发’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提供线索引导读者将意识形态带入对语篇的理解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对其再生产”(Fairclough 1989:85)。
意识形态意义有自然化、固定化的一面,但也有相对的、随语境变化的一面。巴赫金学派充分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语境特性,即其功能不仅是其形式结构问题,也与在什么语境条件下说什么和如何解读具体语篇密切相关。因此,意指机制和语篇的语境对于意识形态批评同等重要:“一种语言中的词语在词典里的中性意义表明其一般特征并确保某一语言的所有使用者能相互理解,但在实际言语交际中使用的词语总是带有个人和具体语境的性质”(Bakhtin 1993:88)。词不属于任何人,它们本身并不评价任何事情,但它们可以服务于任何说话者,被用于表达说话者各种有时明显矛盾的评价意义:“感情、评价和情态是语言之词所没有的,它们只是在词语实际用于具体表述的过程中才能产生”(Bakhtin 1986:85 )。
巴赫金认为意义由词语的所指功能、说者意识以及相关话语与他者“陌生话语”(alien utterances)之间的对话关系3方面构成,缺一不可:“当我们试图理解话语时,重要的不是词语赋予物体和情感的直接意义——这是词语的假面具,而是该意义的实际使用以及说者表达意义的方式,这种使用取决于说者的立场(职业、社会阶级等)和具体的情景。由谁说和在什么条件下说才是词语实际意义的决定因素。所有直接意义和直接表达都是虚假的,情感意义的表达尤其如此”(Bakhtin 1981:401)。巴赫金指出,任何一个词对于说话人而言,都存在于3个层面上:“一是中态的不属任何人的语言之词;二是他者之词,充满他者表述的回声;三是我的词,因为既然我同他者在一定情景中打交道,并有特定的言语意图,它就已经渗透着我的情态”(巴赫金 1998:174)。没有“语言之词”在词典里的中态意义,语言就失去其至关重要的共同性,也就无法保证所有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如果把词在第一层次上的存在叫作“语言之词”,那么它们在第二和第三个层次上的存在就可以叫作“言语之词”,它们是言语交际中实际使用的词,总是带有个人和具体语境的性质。
巴赫金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带有明显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他把语言视为总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的一种社会实践,强调以往语篇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则源于语言与符号体系在更加广阔的权力斗争的社会语境中是如何被运用的。话语和外部世界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被语言中介或调节的关系,任何话语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没有话语是第一的或最后的。任何话语都只是链条中的一环,没有话语能离开这个链条而被研究”(Bakhtin 1986:136)。因此,话语的意义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其他(过去的和现在的)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网络。在言语和物体或事件之间围绕或穿插着由各具自己价值观和重音的其它话语构成的充满对话和张力的环境。没有话语能自绝于与他者话语的接触和互动,所有话语都参与社会对话。对话总是产生独特全新的东西,正是在这些对话中人们不仅表达自己并相互展示各自的内心世界,而且也塑造相互之间和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对话活动中,人们一点一点地改变着经常是不露痕迹地支撑和制约他们相互之间和与环境之间作用方式的那些现存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
既然语言活动主要是对话性的,那么人类的思维基本也是对话性的,并因此具有内在复杂的两面性。如果每一话语都既是对他者话语又是对语境的回应并自身又会引起他者的回应,那么每一话语都是由他者话语塑造的。因此,在言语实践中,话语的意义不能从个体说话者的内部心理去寻找,而是必须根据其说话时的特定对话语境加以理解。个人说出的每一个词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现实交往的结果,其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每一个词都是取向不同的各种社会声音相互冲突和交叉往来的场所”(Volosinov 1973:41)。每一个词都反射和折射其他词,“我们”的词不仅反映“我们”的思想,也反映“我们”可能与之有分歧的“他者”的思想:“所有词都带有职业、体裁、年龄段、那一天那一刻的‘色彩’,每一个词都带有其存在于其中并获得社会意义的语境的‘色彩’”(Bakhtin 1981:293)。
4 启示与问题
结构主义者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他们预设一种“主导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指主要属于统治阶级的、渗透并凝聚整个特定社会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支配者认可的信念或价值观体系。但正如Gardiner指出的,很少有证据证明从属阶级会主动机械地接受或内化统治者的价值观,而广泛的价值观分歧似乎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常态(Gardiner 1992:149)。Thompson(1984)认为,更为可信的是主导意识形态催化现代社会的分裂和碎片化而不是其和谐。巴赫金学派并不认可和谐统一的意识形态,认为各种社会语言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总是随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割而处于分裂状态。其次,Lévi-Strauss 和Barthes关于神话的分析始终与意识形态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社会条件相脱节。其实,重要的不是语篇意指什么,而是它们如何意指。Barthes倾向于从起源上演绎意识形态效果,视符号体系为自给自足的实体,理论上与现存的社会文化实践没有关系。他忽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力量,只专注于其形式结构分析。神话如何内化于语言和日常社会行为中,它以何种方式帮助霸权统治或者抵制这种霸权?Barthes对这些问题从没有充分的研究。巴赫金学派关于意识形态的语境特征和其对话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结构主义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观的修正与补充。
巴赫金学派关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们今天的话语研究和意识形态批评有如下启示。第一,如果意识形态意义并非词语自身内在固有的,而是随语境而变化,那么同一个词语或者词汇语法均相同的两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就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辛斌 2004),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就不自然。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批评话语分析:“语言中的意义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当语言学家说意义的表达是任意的时,他们的意思是任何声音或字母可以用于表达任何意义。但是什么样的意义最终得以表达却不是任意的或者偶然的”(Fowler 1987:31)。
第二,如果语言实践的相关语境内嵌于人类交往的历史,那么理解和解读本质上也具有历史性,它们必须建立在观察者自己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就排除对语篇材料超然中立的思考。巴赫金认为,感知者和被感知者无可避免地处于经由语言中介的有意义的对话关系中,社会“事实”并非先前给定的,而是至少部分地由感知者带入解读行为中的那些理论或概念所建构的:“观察者在被观察的世界之外没有立场,他的观察参与建构被观察的客体”(Bakhtin 1986:126)。在巴赫金看来,我们的大部分言语涉及对他人话语的表征和传递,这其中包含着对他人话语的评价、判断和回应,在这种不间断的表征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一种阐释框架、一种活的阐释学,以便我们去倾听、语境化、理解和回应他人话语。这种吸收和消化他者话语的过程对于发展批评性的反思和解放封闭的思想和行为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他者语言和文化的视角才能真正反思和理解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本质。
第三,上述第二点意味着,任何人文研究都必然涉及与先前的和同时代的语言实践的对话,任何这样的实践都在意指链条中发生,都构成这一链条中的一环。如此一来,意义就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对象征结构的解读被迫陷入象征语境意义的无底洞中,使之不可能像精密科学那样地科学”(Bakhtin 1986:160)。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赫金及其同伴陷入极端后结构主义的虚无主义中,他们要强调的是关于意义的共识应该通过对话达成,而不是强加于人。在他们看来,社会文化研究成功与否只能由处于对话中的主体之间所取得的相互理解程度来衡量,其最终目标是丰富自我而不是强制或枯竭他者。传统语言文化的历史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解读是终结性的或不会出错的,每一后来的时代都会体现新的经历和视角,每一历史阶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以往的语篇。因此,意义是开放的、不完整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第四,巴赫金学派的对话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打破作者视角的一统天下,挑战任何认为一种表征方式就能代表真理或者就能充分反映现实的妄想:“真理既不产生于也不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头脑里,它诞生于共同探索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于他们的对话互动的过程中”(Bakhtin 1984:110)。巴赫金在论述异体语言时也指出,“各种异体语言就像相互对照的镜子,每一面都只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世界的一点,一个小角落,使得我们去猜测和探寻其相互反映的背后的更加宽广和更多层次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比一种语言或一面镜子所能反映的包含更多样的可能性”(Bakhtin 1981:414-415)。巴赫金这里试图把读者的注意力不仅引向社会中语言形式的多样性,也引向各种语言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声音和意识之间的互动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一绵密网络中的位置,而独白则会阻碍或遮蔽这一过程。
巴赫金学派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今话语批评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理论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巴赫金夸大对话性的语言文化把人的意识从独白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作用,他对此往往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乐观态度:“今天我们是在一个自由民主语言的世界中生活、写作和说话;曾经遍布整个官方语言和语言意识体系中的话语、形式、意象、风格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等级结构被文艺复兴的语言革命一扫而光”(同上:71)。然而,今天人们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探索社会政治语境中话语是如何被实施、复制和合法化的,如何被用于制造或者抵制社会中的支配、控制和不平等(van Dijk 2001)。其次,Thompson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特定情况下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意义:“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Thompson 1990:7)。虽然巴赫金学派也认识到话语的政治性以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他们强调意识形态贯穿于意指过程,几乎等同于意义。这样就很难再把意识形态视为维护特定社会群体利益或统治的一种特殊的意指实践。另外,他们也从未认真探讨符号是如何被实际调动来服务于社会权力斗争的,其对独白的表述也没能告诉人们多少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实际情况,而这样的研究显然需要涉及支配阶级如何在各种教育、媒体、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利用话语来强加某种价值观或世界观,并使之自然化。最后,巴赫金本人对狂欢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理想化,缺乏历史性,其“人民”的概念十分模糊,缺乏社会内容。狂欢实际上并非一种天然的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实践,也不是管理社会的工具,它既可支持或维护也可破坏或瓦解现存社会秩序:“狂欢并非本质上是激进的或者保守的。狂欢活动可能只是没有任何明显政治效果的稳定的周期性仪式,也可能是实际符号斗争的催化剂和场所”(Stallybrass, White 1986:14)。巴赫金把狂欢与暴力或权力相对立的思想显然值得商榷。与任何其它文化实践一样,狂欢本身并不自然导致自由和解放,其重要性和效果取决于其所处的或发生时的具体社会文化历史场景。
5 结束语
Thompson (1984)提出,任何合理的意识形态批评都必须指出什么是真的或者什么是假的,以及真假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批评现存的权力关系,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以满足人类正当的需求和要求。意识形态批评始终是任何社会批评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分析语言和语篇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与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关系。本文对巴赫金学派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介绍和讨论至少能使批评话语分析者认识到以下几点:(1)意识形态基本是一种符号现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构成人们常识的一部分;(2)虽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但它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物质社会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虚幻或虚假的,它是一种物质力量,介入社会过程并参与社会主体和身份的建构;(4)意识形态并不一定只是统治者或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自上而下强加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斗争的赌注或场所;(5)意识形态批判不仅要批判或审视他人的意识形态,也应反思我们自己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辛 斌. 论意义的合法化、习惯化和语境化[J]. 外语学刊, 2004(5).
Althusser, L.ForMarx[M]. London: Allen Lane, 1969.
Bakhtin, M.M. Discourse in the Novel[A]. In: Bakhtin, M.M.(Ed.),TheDialogicImagination:FourEssays[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Bakhtin, M. M.ProblemsofDostoevsky’sPoetic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esota Press, 1984.
Bakhtin, M. M.SpeechGenresandOtherLateEssay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Bakhtin, M. M.TowardaPhilosophyoftheAct[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Barthes, R.Mythologies[M]. London: Granada Publishing, 1973.
Clarke, K., Holquist, M.MikhailBakhti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Fairclough, N.LanguageandPower[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9.
Fowler, R. 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A]. In:Steele, R., Threadgold, T.(Eds.),LanguageTopics:EssaysinHonourofMichaelHalliday[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7.
Gardiner, M.TheDialogicsofCritique:M.M.BakhtinandtheTheoryofIdeolog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Gramsci, A.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Lenin, V. L.WhatIstoBeDone?BurningQuestionsofOurMovement[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Lévi-Strauss, C.StructuralAnthropology[M]. London: Allen Lane,1968.
Marcuse, H.OneDimensionalMan[M]. Massachussettes: The Bacon Press, 1964.
Marx, K., Engels, F.TheMarx-EngelsReader[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Schultz, E. A.DialogueattheMargins:Whorf,Bakhtin,andLinguisticRelativity[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Stallybrass, P., White, A.ThePoliticsandPoeticsofTransgression[M]. London: Methuen, 1986.
Stubbs, M.W.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Ryan, A., Wray, A.(Eds.),EvolvingModelsofLanguage:BritishStudiesinAppliedLinguistics[C].Clevedon: BAAL/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Thompson, J.B.StudiesintheTheoryofId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Thompson, J.B.IdeologyandModernCul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van Dijk, T.A. Multidisci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A]. In: Wodak, R., Meyer, M.(Eds.),Methods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C]. London: Sage, 2001.
Volosinov, V.N.MarxismandthePhilosophyofLanguage[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Volosinov, V.N.Freudianism:AMarxistCritique[M]. New York & London: The Academic Press, 1976.
Volosinov, V.N. Literary Stylistics[A]. In: Shukman, A.(Ed.),BakhtinSchoolPapers:RussianPoeticsinTranslation[C]. Oxford: RPT Publications., 1983.
Williams, R.MaxismandLitera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BakhtinSchool’sConceptionofIdeologyandContemporaryDiscursiveCriticism
Xin B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Ideological criticism has been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clud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At present, most of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re still largely in line with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ideology;however, having traveled through a long and complicated history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two centuries ago,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has become notoriously controversial, and there are dozens of definitions of it each of which makes some claim to primacy.Through a fairly in-depth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Bakhtin School’s conception of ideology, this paper suggests several lines along which we need to understand ideology from a CDA point of view.
ideology; the Bakhtin School; discursive criticism
H030
A
1000-0100(2016)01-0021-7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1.004
定稿日期:2015-06-17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