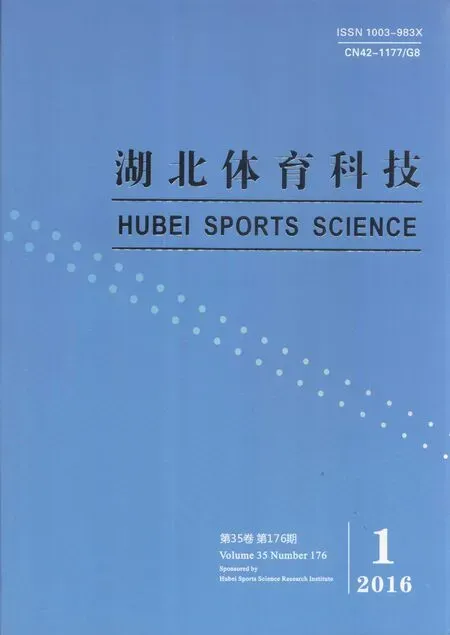文化视野下的乡土游戏演化
罗红英,罗湘林
文化视野下的乡土游戏演化
罗红英,罗湘林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乡土游戏的演化进行文化解析,探寻乡土游戏变迁的文化根源。乡土游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草根文化,在乡民的社会生活中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日常性的乡土游戏;二是仪式性的乡土游戏。不同社会文化趋势影响着乡土游戏的走向: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游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状态,一种是占乡土游戏比重大的日常性乡土游戏呈现扩大化状态;另一种仪式性的乡土游戏则受到压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土社会为大众文化侵袭之后,生活性的乡土游戏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相反,仪式性的乡土游戏则变成一种消费性质的游戏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追捧。
文化;乡土游戏;演化
游戏是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现象之一,起源广泛,并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演变成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发生、发展与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如中国古代的蹴鞠,起源于战国时期齐国故都临淄,本是作为一种军队操练的方法在军中盛行,后受儒家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思想的影响,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1],并在民间盛行。
乡土游戏作为游戏的类别之一,单独列出来研究,是为了突出乡土二字。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决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乡土性以及文化的乡土性。胡映兰认为:“乡土文化就是在乡村中的长期共同生活里所形成的乡村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3]。乡土游戏作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可据此引申:“乡土游戏是一种乡土文化现象”。而乡土文化中又有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区别,那这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现象呢?此外,乡土游戏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精英文化、改革后的大众文化相遇,又会有怎样的演化?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从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角度来分析乡土游戏的演化。
1 作为草根文化的乡土游戏
文化游戏论学者赫伊津哈定义游戏为:“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由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在自我意识”[4],包括儿童、成人中一切所谓的“游戏”。而提到在乡土社会的游戏活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乡村儿童游戏如抽陀螺、踢毽子等,这些活动内容广泛,活动形式多样,而且玩耍的性质较强、受众多、对场地器材的要求低且容易操作,是一类原生态的乡土游戏,与乡村生活紧密关联,属于情感之层面[5]。还有一类在乡土社会进化时间较长的被社会化了的乡土游戏,即仅在节日庆祝的场合、宗族活动、祭祀场所才会组织进行的一些乡村活动,属于精神层面的[5],如元宵节的舞龙舞狮、端午节的赛龙舟等。因此,笔者按游戏时间、规模以及归属等要素将乡土游戏分成两类:日常性以及仪式性的乡土游戏。故本文所指的乡土游戏,意指:在乡土社会的地域范围内,为乡民所发明、为乡村社会所发展的一切乡民可以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的游戏活动的总称。
吴妍认为:“‘草根文化’是植根于民间,包含了现实而具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内容形式和传播渠道,并综合地反映了‘草根阶层’现实意志和思想意识的文化体系,”具有“地域性、多元性、广泛性、民间性等特征”[6]。而且草根文化未受过主流文化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无须文化精英的加工和改造,是一种充满着生活化乡土气息与乡土社会顽强生命力的乡土文化;并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原生态文化谱系,是一种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相对的文化,是一种亚文化。
乡土游戏就是草根一样的存在。首先,它在乡间土生土长,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为大众所创造,并在乡间广泛流传,是一种为乡民所有的大众资本,为大众带来非生产性的价值,因此具有大众性。其次,乡土游戏是一种传承于乡土社会又可以世代相袭的文化活动事项,有些与乡村风俗习惯关系密切,存在于节庆活动、宗族活动、祭祀活动中,“具有传承民族信仰、传授生存技能、展现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交流、抒发生活激情和培养审美情趣等功能”[7],具有民俗性。再次,乡土游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村民在游戏中调节情感情绪,是繁琐生活的一种调剂;节日里仪式性乡土游戏也都是村民组织与参与的,这些活动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信仰,是民间文化传承的精神归属所在,因此具有归属性。此外,乡土游戏的发明并不受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乡村生产与生活来发明乡土游戏,游戏可以简单到只有几句口令,也可以借助任何乡村随处可见的事物来丰富游戏;乡土游戏的又一特征是自然性,乡土游戏自发产生,由农村“生态圈”中的“生物群体”——村民自发组织,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自然地运作,在乡村的生态系统内,遵循自然选择的原理,自然界影响着游戏的主体,游戏主体改造着自然,乡土游戏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丰富着。最后,在乡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乡土游戏具有可塑性,乡土游戏的主体草根阶层并不像精英阶层那么严肃,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断加强其活动的权威性,相反游戏的人往往不拘一格,只要游戏各方相互约定,游戏的内容、规则、形式都可以更改,体现着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综上所述,乡土游戏具有大众性、归属性、民俗性、自然性与可塑性,表明乡土游戏实质上是一种草根文化。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以士绅为精英阶层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乡土游戏曾受其贬低有“业精于勤荒于嬉”之说,但乡土游戏还是稳定延续着,因为那时乡土游戏基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变化,在完整生态体系中运作,无需赘述。
2 主流文化管制下的乡土游戏演化
2.1演化流程的特点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日常性乡土游戏表现为:1)种类逐渐增多,如1959年12月14日的中国体育报曾详细报道“捉俘虏”这种新发明的儿童游戏的玩法,并且在一向是男孩子喜欢玩的分队追逐对抗的集体游戏中,出现了以“抓特务”、“炸碉堡”为题材的游戏;2)旧游戏以新形式存在,如古老的“抽陀螺”游戏在 60年代的儿童那里被称为“抽汉奸”[8];3)游戏群体充实,游戏时间多,儿童成群结队自发参与游戏,玩的兴起时忘记吃饭睡觉是常有的事,经常是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归不来”;4)自然性强,游戏的过程:学、做、玩、教比较完全,家长对于儿童游戏采取放任态度。而仪式性的乡土游戏活动在当时的媒体中鲜有报道,生活中甚至受到压制,“‘文革’时,早先流行于农村的节令性民间娱乐活动,诸如舞龙、舞狮、竞渡、庙会集会活动等,作为’四旧’被一扫而光”[9],使得带有宗族竞赛、仪式性、信仰性质的乡土游戏活动大多受到打压而消弭。因此,这段时期,乡土游戏呈现出日常性乡土游戏扩大化以及仪式性乡土游戏受压制的状态,具有强政治性的特征。
2.2主流文化视角下乡土游戏演化原因分析
2.2.1政治精英文化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士绅是乡村精英结构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精英的选择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干部精英逐渐从社区体系中剥离出来,并整合到国家官僚体系中,成为国家体制内的精英”[10]。政治精英阶层取代士绅精英阶层,形成一元化精英结构,乡土社会文化逐渐向一种以强政治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方向过渡。社会一元化的精英结构,意味着其他社会精英力量尚未形成或者话语权的丧失,加上其独特的精英选拔方式,使得社会权力结构具有单一性,进一步导致社会决策的盲目性,人民公社、知青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应运动应运而生。乡土游戏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演化。
2.2.2政治精英文化对乡土游戏内部演化的影响
在当时政治精英文化影响下,仪式性乡土游戏与日常性乡土游戏几乎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运动,旨在破除封建社会的“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从1966年开始,全国上下投入到“破旧立新”的运动当中,我国历代保存下来的优秀物质文化遗产被当做封建社会的 “毒瘤”破坏殆尽;而那些活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禁止,如春节元宵不再有舞龙舞狮活动的开展、端午节不再进行龙舟竞渡。在这场浩劫中具有宗族祭祀与仪式信仰意义的传统游戏遭到打压,有的被全盘否定,有的仪式与传统被割裂,仅仅留下活动本身,仪式性乡土游戏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就像处于真空状态一样被牢牢套住,几近销声匿迹。
MOOC建设完成后上线试运行,检查MOOC建设的质量和效果。至少经过一个完整的教学周期,发现其中一些不尽如意的地方;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需要再添加一些内容或者闯关题、测试题,一是督促学生仔细观看视频,二是督促学生动脑思考,三是便于考核学生的学习过程,记录考核成绩。最后,再集中修改、完善。
在当时政治文化氛围较强的乡土社会环境中,日常性乡土游戏寻求一条向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妥协的出路。“如古老的‘抽陀螺’游戏在六十年代的儿童那里被称为‘抽汉奸’。在一向是男孩子喜欢玩的分队追逐对抗的集体游戏中,出现了以‘抓特务’‘炸碉堡’为题材的游戏”[11]。而政治号召下的集体化生产和生活使得游戏的主力军——儿童脱离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劳作的传统,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在游戏上,游戏成为了儿童的生活。此外,“破四旧”运动虽然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不安,压制了仪式化的乡土游戏,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情感的释放,人民群众从鲁迅眼中麻木愚昧的行尸走肉变成敢于抗争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与反思,从而为乡土游戏发展提供了主体力量——人。游戏群体的发展还受到当时政治领袖 “人多力量大”口号的影响发展空前,为日常化乡土游戏提供了稳定又无思想束缚的游戏群体,促进了日常性乡土游戏的发展。
2.2.3政治精英文化影响下乡土游戏的外部环境
伴随农业集体化而出现的生产大队,使得农民由原来熟人社会关系更进一层,多了一层生产上的关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民公社的这20余年,与城市中的风雨飘摇相对照,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减缓我国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状况”[12]。白天大人集体按时出工,留在家的小孩成群结队玩耍,家庭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增多,给儿童提供了良好的游戏氛围。知识分子下乡促进了乡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为填补精神、文化生活空缺,知青普遍地表现出对体育活动的偏爱和热心”[13]。这种热心刺激着城市体育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交融,给乡土游戏创造性发展创造了新机。
在我国,现代体育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百废待兴,国家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当滞后。然而,“‘文革’中随着波涌浪跌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使体育终于从几乎湮没而得以复苏”[13]。但这种体育活动绝大部分是乡土社会的游戏活动,“除了军事训练科目外,也开展很多带有娱乐性的活动,如篮球、登山、渡河、拔河、顶杠、竞舟、举重等等”[13]。体育的发展目的不是大众化,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乡村“政治棍子到处打的境况下,农村基层领导为不离‘纲’离‘线’,把体育活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很多社队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3]。然而,乡土社会没有现代体育发展的场地设备资源,缺少现代体育精英,传播途径闭塞;在这样的环境下,乡村体育虽然有政治的庇护,但乡村里的现代体育还是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在现在看来,现代体育作为外在一种并列甚至超越的存在,其不平衡的发展状况给完善与成熟的乡土游戏体系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时段内,日常性乡土游戏没有遭遇分散其发展的力量,而作为乡土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存在与发展着。
3 大众文化潮流中的乡土游戏演化
3.1演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家长开始管制儿童的游戏活动,游戏时间逐步减少。由于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游戏的重要场地转移到了学校里去,野外游戏活动减少。“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自然情趣被积压的课业取代,游戏群体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玩具商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塑料枪、刀、箭等受到欢迎,人们开始摒弃自制玩具的方式,从市场上购买玩具成为潮流,这时一些需要自己动手的游戏活动开始衰落,部分乡土游戏面临消失的困境,从而使得游戏的自然性逐渐减弱。到现在,除了学校,基本上看不到大队的儿童在游戏,村落里原来游戏的固定场所被新建筑等取代,儿童有时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自家屋旁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如捉迷藏、骑自行车,原来游戏的时间被电视、现代玩具所取代,游戏的空间受到压制。
之前在政治因素压制下的仪式性乡土游戏却作为城市人的消费品逐渐盛行起来。在开放一点的乡村,“大多游客都希望亲自参与、体验那些充满情趣、活泼欢快的民间民俗体育旅游活动”[14]。于是,游戏作为一种消费性质的活动,被操控、包装与推广,民俗文化被经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经济为主导而非文化主导的乡土游戏,发展侧重于其娱乐表演价值,而使游戏中某些重要的特征逐渐消失。此外,仪式化乡土游戏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其 “传承空间的依附载体逐步在发生流变”[15],节日关联的乡土游戏在大众文化背景中变成一种催生节日事物,功利性极强。因此,这段时期乡土游戏演化的特点是自然性逐渐减弱,商业性慢慢抬头。
3.2大众文化视角下乡土游戏演化的原因探析
3.2.1市场与消费的时代
改革开放带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促进乡村“民工潮”的兴起,未离乡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也与现代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村落不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村落,慢慢地从原来的“乡土中国”进化。“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是‘市场中国’了”[16]。与此同时,社会精英阶层分化,对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迎合现代人需求的大众文化兴起。“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17]。大众文化所包含的商业化、世俗化、碎片化、虚拟化的文化内涵冲击了农民传统的价值观,“一切宜于移动的、轻便的、一次性的东西,都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所有妨碍迁移的负累之物都被尽可能地摆脱”[18]。快餐文化的侵袭,使得无功利性的、自然的、实在的、具有精神内涵性的日常性乡土游戏逐渐遭到冷落。同时也使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因素的仪式性的乡土游戏受到不同程度的追捧。
3.2.2大众文化对乡土游戏生存空间的影响
“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通过取悦大众而赚钱”[19]。而商业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是作为草根文化的乡土游戏发展的制约所在。游戏活动商业化,游戏活动有专门的人士来组织进行,“节约”了游戏活动的时间,但却疏远的游戏的人,导致游戏群体分散化;游戏的玩具商业化,意味着现代玩具的泛滥,人们沉浸在各式各样的玩具海洋里不亦乐乎,便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自己动手制作玩具,没有付出情感与精力的玩具,也就无珍惜可言了。甚至游戏的伙伴也被商业化,那些电子游戏制造出一个个虚拟的伙伴与对手,人们在游戏中尽情地厮杀与发泄,游戏过后却还是孤身一人,情感无从寄托。商业的逐利原则使得游戏成为一种商品和产业,迎合现代人的消费观,现代游戏的批量生产与商业性质覆盖了乡土游戏的艺术内涵,乡土游戏中人与人交往的生活艺术、自给自足的生产艺术被利益所取代。
市场经济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村落空间形态在乡民的行动中迅速变化,特别是80年代以后,原来以祠堂为中心的建筑结构到插空的紧凑格局再到以交通路线为先的建筑行为,致使祠堂聚众能力削弱,原来一到晚上聚集少年游戏的公馆戏台变得冷清,充满村民集体游戏记忆的空地被建筑覆盖,抽陀螺,跳飞机图的晒谷坪搬到了自家楼上,躲猫猫的巷子拆掉了。曾经寄存着乡村儿童一切想象的空间,被那些冰冷的事物所取代。与此同时,制造业发达的现代文明,制造出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玩具,致使传统的玩具制作手艺面临失传的境地,乡土游戏失去了依凭。经济的发展承载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为达目的不遗余力,而当富余成为现实,建立也往往伴随着毁灭。随着那些满是文化记忆的符号的消失,人们迫切想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却遭遇如孙立平所描述的断裂时代,从熟人社会的联结进入一个分散的状态,造成乡土文化的失落。
3.2.3大众文化对乡土游戏活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电视、广播到手机、电脑、多媒体的盛行,乡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2003年美国《时代》杂志就曾撰文称,2015年前后世界将进入数字娱乐新时代。再加上现代体育发展,现代娱乐方式充斥在人们生活中。在一个多选择的社会里,人们不甘于局限在个人之间的互动,现代传播媒介中铺天盖地的碎片化的信息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于是动画片占领了儿童的课余生活,而现代娱乐方式也更能填补人们内心的欲望。在虚拟的电子游戏世界中尽情地厮杀,释放各种生活压力,比进行现实游戏活动来的方便快捷。现代生活方式更是改变着人们的信仰习俗,过于追求物质的丰满而忽视精神的满足,而导致传统文化的变迁。人们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现代娱乐活动中,使得乡土游戏活动时间、形式等受到挤压。然而在经历现代生活,发觉精神无归属之后,又转向商业化了的仪式性游戏中寻求片刻的满足,终究也是流于形式。
4 结论
乡土游戏是一种草根文化。将乡土游戏理解为一种草根文化可以作为用文化的视角来解析乡土游戏演化的一块砝码,在乡土游戏走向发展的顶峰时,当时的主流文化与草根文化的互动就像是另一块砝码加在了草根文化的称盘里。乡土文化以一种相互制约的常态向作为草根文化的乡土游戏方向倾斜。此时,虽然有一部分民俗性强的乡土游戏受到压制,但作为日常休闲的乡土游戏却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与当时受压抑的乡土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相反,乡土游戏的衰退,则是由于精英文化的分化不足以抵制大众文化的发展,使大众文化成为一种“非主流的主流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站在天平另一侧的一种与传统价值不尽相符的文化,是一种抛却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精神内核的文化,一盛一衰,作为乡村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乡土游戏也随之没落。
随着社会的变迁,乡土社会也站在积极迈入现代社会的行列,但乡土游戏所具有的社会人文价值并未过时,乡土社会文明应保留性地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的乡土社会,加快了乡土社会文化流动性的步伐,草根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蜕变,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也将促使乡土文化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曾是乡土社会人们生活一部分的乡土游戏,未来也可能会以新的姿态进入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
[1]丛书编委会.中国历代体育史话[M].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胡映兰.论乡土文化的变迁 [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院学报,2013(6).
[4]约翰·赫伊津哈,何道宽译.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罗湘林.村落体育——乡土上的生命关照[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6]吴妍,论“草根文化”的社会功能[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7]张文涛.草根文化视域下对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解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3).
[8]刘焱,王丽,沈薇.建国以后儿童游戏发展变化的特点、趋势及原因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1999(4).
[9]傅砚农.文革中知青对农村体育的影响及其原因[J].体育文化导刊,2001(10).
[10]胡杨.精英与资本——转型期中国乡村精英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
[11]刘焱,王丽,沈薇.建国以后儿童游戏发展变化的特点、趋势及原因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1999(4).
[12]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8 (3).
[13]傅砚农.文革中知青对农村体育的影响及其原因[J].体育文化导刊,2001(10).
[14]高松山,云林森,张文普.河洛文化中民间民俗体育的开发与利用[J].体育文化导刊,2007(10).
[15]汤立许,蔡仲林.文化变迁视域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流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
[1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陈钢.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18]耿敬,姚华.当代乡土文化的流动性特征[J].东方论坛,2007 (3).
[19]许士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J].求实,2002(6).
[20]马广宁.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8(2).
[21]孙潇雨,杨柏松,张海涛.试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与对话[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22]李松,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变迁[J].民俗研究,2014(1).
[23]谢玉,罗湘林,何斌.汨罗江龙舟竞渡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2(8).
The Evolution of Local Game i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LUO Hongying,LUO Xianglin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 games from the culture aspe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e root of the local games changes.Local Games which in essence are a kind of grassroots culture,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villagers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daily local Games.The second is ceremonial local games.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affect the trend of local game:mainstream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cal game shows two diffe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that one is for local games than major daily local Games has been expanding state and another ritual of agrestic games is suppressed.And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invasion of popular culture,life of local game development space squeezed.On the contrary,ceremony of the local game becomes to be of consuming nature in the game and to be sought after by varying degrees of.
culture;local games;evolution
G898
A
1003-983X(2016)01-0051-04
2015-07-25
罗红英(1990-),女,湖南桂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4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