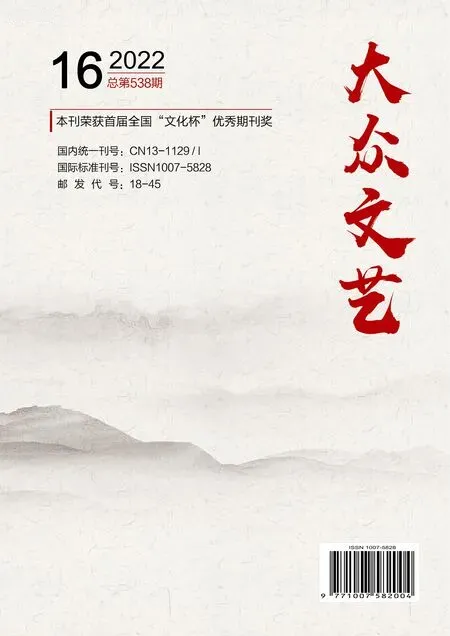中国画传统图式的意象与意境
余志春 (昆明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650000)
中国画传统图式的意象与意境
余志春 (昆明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650000)
中国画的意象造形方式别具一格,自成一体,从面对自然的观物取象,到感悟自然的澄怀味象,直至追求意境的象外之象,是境界的三个层次,即“物境、情境、意境”。诗意与画境是文人画诗画合一的文化品格。中国画对自然形象意象化的处理和对意境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画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
图式;意象;意境
中国传统文化根置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独特的形象思维属性也是与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契合的,中国艺术精神强调人作为绘画主体的绝对主导地位,象形以达意。中国画意象造形的形象传达方式和对“象外之象”——意境的追求,确定了中国画的主体精神表达与客体自然形象之间的独特关系。
一、意象——澄怀味象而生意,意蕴于象
意象之意,是人的思想情感,就绘画而言,是主体精神内在的一种体验;象,是客观事物的外在形象。佛教认为,人在观照自然的感知方式有“六识”之说,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与之对应的感知对象是“色、声、香、味、触、法”。这里的“六识”中就有“意”一识,且与其他五识不同的是,前五识皆为人与外界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对物的认识,唯有意识,是内心的念想,是集合前五识而生的心悟。合而言之,意象,就是充分体现了主体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中国画家象形以达意的艺术主旨,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哲学观之上的。这种突出主体精神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观照自然的态度,正是中国画艺术强调写意精神的宗旨。
意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画独特的图式语言形成的关键。作为主体精神的意与客体自然的象的结合,立象是为了达意。《易·系辞上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不见乎?子曰立象以尽意”。中国画写意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象形以达意,得意而忘象。象,是形象,是说明文,是对外在形象的直观描述。形象越是具体,想象的空间也就越有局限性;意,是含意,是诗意,是形象内在精神的表达,意往往单靠具体的形象是无法准确传达的。只有立于形象之上而又不受具体形象的束缚,意才能写得起来,才能得其神韵。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而气韵的生成,则是承载于笔墨意象之上。清张庚在其《浦山论画》中提出“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何谓发于意者?走笔运墨我欲如是而如是,若疏密、多寡、浓淡、乾润、各得其当是也。发于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谓之足则实未足,谓之未足则又无可增加,独得于笔情墨趣之外,盖天机之勃露也。”。 在这里,“我欲如是而如是”是一种描述,是我对所感知形象的一种记录;而“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意外之象,是因形象有感而发的心性轨迹。契合了《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中形象及其含意之间的辩证。在传统哲学观中,作为天地自然的象和作为主体精神的意,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旨在于传达人的主体精神,所以象不是绘画表现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一个载体,籍象以写意。中国画的意象造形,正是自然形象的天意与人的主体精神之人意合而为一的。
纵观整个中国绘画史,山水花鸟题材都曾达到高度发达的时期。究其原因,人物画承载了太多的教化人伦的宣教作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主体精神的自由发挥。而山水、花鸟则不同,以自然之形来寓情于景、借物抒情,更符合中国人诗意表达的艺术创作观。我们从中国绘画史上独具一格的徐渭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意与象的关系。徐渭画花鸟,多以墨色为之,他反对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依样画葫芦,只注重外在形象的写实,而没有内在的真实。有诗云:“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在他的花鸟画中,牡丹、芙蓉这些绚烂之物化为无色的墨影。真实的色与象是具体的、物质的,而意象化的墨影则是荡去了真实的外在表象而呈现的内心的真实。再看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其独特的意象表达方式,正是对中国画意象造形的写意精神准确的阐释。在八大山人的画作中,处于一片浑蒙空白之中翻着白眼的鱼、孤栖于枝头的小鸟、伏于怪石之上的猫,在外形上皆与自然的形象有很大的距离,甚至无从分辨是何种鱼、何种鸟,但正如其说:“画者东西影”,画的只是这个真实世界的影子。在意象的表达上,八大山人既受传统文人画超越形似观念的影响,同时又因其长期的佛门禅修而参透了象的本质,所以在他的笔下,形象的真,已经脱去了外在的表象,而是从内心获得的映射出立意本身的意象。
二、意境——心性驭意而达境,境由心生
何谓意境?唐代诗人刘禹锡云:“意生于象外”。象外之象是为境。象,是人可视可感的形象,而境是由象产生的联想而生成的。象是产生意的诱因,由意又体悟到境的存在。因此,意象是产生意境的基础,,而意境是超越意象的更深层次的追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讨论了境界一词,“乃是指真切鲜明的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如果按传为唐王昌龄所著《诗格》所言“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那么,意境是境界的其中一种层次。艺术作品的境界之高下,除了自然形象的物境、心理形象的情境之外,形象之外的意境的表达,最能体现艺术主体的心性修养与艺术造诣。
文人画强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苏东坡语),其实是诗意与画意的融合,论诗而言及画的可视意象;论画而言及诗的境界与格调。中国艺术精神着重于主体的主导地位,意境的产生更倾向于主体精神的表达而非客体自然的具象描述方式。故此,意境产生的高下并不完全依赖于物的描述方式,更多的则是主体修为与悟性的直接传达。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境是造不出来的,画家造的是景而不是境。境的产生是一种心悟,是因景而生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在画家作画过程中会生成,在欣赏者观画的过程中同样会产生类似的体验。前后两个过程达到融通,即完成了一次审美体验。
关于意境,这里就元代山水画家倪瓒的作品来观其一二。倪瓒可谓宋元绘画意境之集大成者,在他看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作品中,突显一种幽寂的意境。而这一独特的意境是由其特定的图式语言来呈现的。首先,画面构成常见的“一河两岸”,是对自然景观作意象式的提纯处理。远近坡岸的横线,与古松、杂树、幽篁等竖直的形态架构营造出肃穆而冷寂的一个宁静世界。近景坡岸上的树脚林间,常掩映着一座古亭。在其早期作品中,亭下时有一人独坐、或二人对谈,后期作品则更是将人物省去,空剩一座孤亭,空空落落,杳无人迹。“一带远山衔落日,草亭秋影淡无人”。画面中从有人到无人,实则是倪瓒对幽寂这一意境的强化。在有人的画面中,凸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引发观者对画中人物寂寞、忧伤、孤独心境的感同身受。不论画者还是观者,都把重点放在对画中人顾影自怜的对照上,此谓有我之境;而在无人的画面中,画者与观者是对荒天古木、碧水枯亭的直接对话,是在独面这荒寒冷寂的世界。所谓“万里乾坤秋似水,一窗灯火夜千年”。此谓无我之境。倪瓒在图式语言与意境表达的处理上,找到了那条贯通一气的线。
其次,倪瓒画中幽寂的意境,包含着其对人生际遇的感怀和对生命无常的深层次的思考。其早年的衣食无忧、中年的家道沉沦、晚年的漂泊潦倒,使他对人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如果我们只把这枯寂山水营造出的荒寒意境,仅仅理解为他对萧疏澹泊图式的沉沦,显然对倪瓒是一种误解。在这种图式的背后,是一种超脱人间,不问世事的高洁精神的追求。“萧然不作人间梦,老鹤眠秋万里心”,正是他对自己的山水画最好的注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图式语言的意象化处理,是与特定意境的传达密切相关的。见景而生情,是看见,是对景物最初的认识;寓情于景,是梳理,是图式提纯的过程;意造境生,是表现,是思与境偕的呈现。中国画在意象图式程式化的锤炼过程中,是画者主体精神以意为主的表达。其在景物的铺陈上有更大的自由,客体形象必然让位于感觉形象,最终达到高度凝练的意象图式。而籍于这种提纯的意象图式,意境的生成就显得更为典型化。
[1]林之满编.四库全书精华[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3月1版1印.
[2]周积寅编.中国画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3印.
[3]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2版2印.
[4]朱良志.南画十六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1版3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