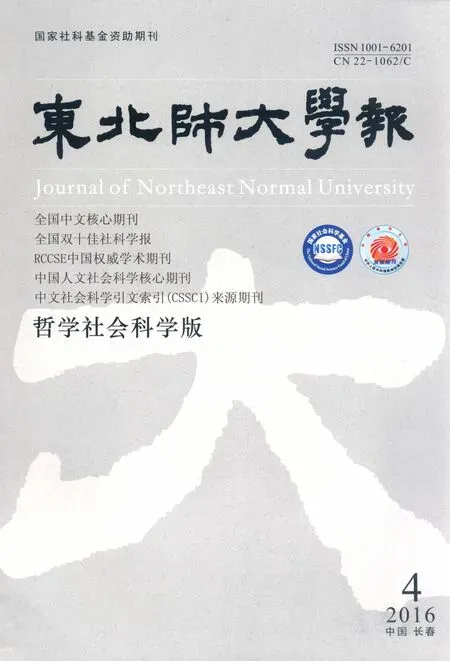破解全球投资增长困局
陆 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破解全球投资增长困局
陆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在长期则在供给方形成生产能力。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投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增长前景。长久以来,投资也一直被视作是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环节。
一、危机后各国投资水平均出现下滑
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的投资水平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发达国家下滑尤为显著,这使得促进投资增长始终是危机后各国政府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它们希望通过推动中小型私人企业投资和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使本国经济复苏迅速步入正轨,避免陷入“弱需求-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可惜的是,尽管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都施行了宽松货币政策,营造了历史罕见的低利率环境,但就投资占GDP比重而言,不少国家都距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相差甚远,尤其是欧洲和日本。2015年,欧元区和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较2008年分别下降了10.6和6.9%,占GDP比重仅在20%左右。经济复苏表现最好的美国,其投资虽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却依旧低于其长期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大都在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快速恢复了投资水平,不过,近几年,受自身结构性问题和国际金融、经济环境波动性增强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投资动能也在逐步减弱。
金融危机对全球跨国投资和公共投资也打击沉重。全球直接投资(FDI)直至2015年才首次回升至危机前水平,达到1.7万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联合会的研究,2015年FDI增长主要由跨国并购导致,表明目前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旨在推进资产重组,而非扩张生产活动,这些资本流入仅改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金融账户,并不带来资源的实际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推动有限。
二、投资下滑的政策和金融因素
公共投资下滑主要是受各国财政整顿约束影响。OECD国家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2010和2013年间下降0.6%,为财政整顿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将近1/4。财政整顿问题越严重的国家,公共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越多,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平均每下降1个百分点,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被削减0.3%[1]。因此,危机后各国面临的财政整顿约束也为投资增长带来了一定障碍。
而在私人部门,未来经济和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是导致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型企业普遍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欧洲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3%的欧洲企业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是他们对欧元区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2]。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不存在资金层面的约束,不少企业在削减投资规模的同时,还在主动选择发放股息或回购股份以降低现金持有水平[3]。相应的,在美国,企业较为担心监管、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用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EPUI)在2009、2010及2012年财政悬崖之前急剧飙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回落一段时间后重新在2014年和2015年走高。除此之外,一些长期不确定性,如在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不确定,也使得企业对进行长期投资持保留态度。
对于小微型企业来说,融资约束仍然是它们无法扩张投资的一大制约。在金融危机之后,小微企业的资金约束程度较危机前有所上升。根据此前欧盟28国的一项调查,在使用过或考虑使用的融资工具中,只有16%的小微企业选择了股权融资工具,4%选择了债券融资,而银行贷款(57%)、透支贷款或赊销(53%)仍是小微企业最常用的融资工具。因此,在银行大范围地进行去杠杆以满足监管要求时,这些小微企业愈发难以获得资金进行投资[4]。
投资环境壁垒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也是制约企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壁垒、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税收壁垒、良好商业行为准则体系的缺失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资源流向最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增加了企业投资生产的成本和负担,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当整体经济需求的波动性显著增强时,不灵活的劳动市场使得企业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出于对未来风险管控的考虑,企业将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选择主动缩减投资规模,为投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动全球投资增长的政策方向
为打破全球投资增长乏力的僵局,促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轨,有效的需求面刺激政策依旧不可或缺。但需要谨记的是,此类政策还应伴随着改善经济长期增长前景、提升市场信心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不仅如此,需求面刺激政策自身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并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协同和溢出效应。
具体来说,各国推动投资增长的政策可重点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在适度容忍政府债务扩张的前提下,有效调整和增加公共部门投资。如果使用得当,公共部门的投资不仅能在短期发挥提振需求的功效,还能够拉升经济体长期需求。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投资决策时应当对投资的种类和质量予以关注,一方面可将资源配置到投资乘数效应较高的领域,另一方面可加大投资于一些未来有益于私人部门投资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公共研发、知识基础设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气候变化应对和环境保护等等。政府在公共投资中还可积极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在撬动公共部门资金的同时,提升投资效率。此外,政府可考虑施行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小微企业投资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二是降低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在财政政策方面,各国需要明确在现有经济增长率下如何实现财政可持续的战略和路径,这对欧元区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则需要避免预算法案上的不确定性,不再反复出现债务上限之争。在货币政策方面,则需要清晰地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路径。除此之外,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各国还应当在一些国际性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和合作,包括跨国公司税收处理、金融体系监管、以及气候变化的应对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尽快落实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关国家的监管政策不确定性。
三是实施有助于长期投资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促使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的核心所在,它能够支持和鼓励企业在资本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长期投资,实现提升整体投资水平的目标。促进投资的结构性改革通常需要结合金融政策、市场监管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三者之力。
金融政策应着力于保证金融机构能够为有发展前景的长期投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监管层吸取了危机教训,意图通过防止过度金融化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对冲击的抵抗力。在这个过程中,监管当局增加了对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持有流动性较差资产的资本金要求,直接导致这类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或其他长期投资项目成本的上升。这是各国政府需要注意的,金融政策框架应该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尽量鼓励机构投资者为项目提供长期资金而非予以阻挠。
市场监管政策则应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减少市场准入管制,同时确保市场监管环境和融资安排能够使得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足够的融资渠道。放松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管制,减轻降低监管要求对企业的负担,能够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调整,从而提升企业在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时的投资意愿;确保发展前景良好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获得畅通的融资渠道则有助于提升经济体长期增长潜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拥有明确的市场监管政策框架尤为重要,因为市场监管政策的频繁变动将导致企业投资趋于保守,不利于整体投资规模的扩张。
产业政策方面,政府需加强对研发、高新科技以及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扶持。这类投资有利于推广和传播前沿理念和科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研发相关的税收激励机制应进一步得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在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鼓励市场竞争的政策相协调,以使得各项政策能够发挥最大效益。产业政策还需要对行业退出的相关条例予以关注,尤其是高新科技行业。由于技术更迭而导致的企业退出和破产,理论上不应该受到过于严厉的破产惩罚。保持高新科技行业进入和退出的活力,有助于资源的不断配置向更有效、创新含量更高的地方,进而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综上,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基本都处于弱复苏状态,实体投资持续增长乏力逐渐成为各国所关注的一大结构性难题。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财政整顿的压力、商业环境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等问题都令企业在扩张投资规模决策上裹足不前,导致全球经济较难走出低速增长的泥沼。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多方政策的配合与协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推动大范围的结构性改革,力求在拉动短期投资增长之余,增强和培养一国的长期投资潜能,促使经济增长能够重新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1] ECB.Public investment in Europe[J].ECBEconomicBulletin,2016(2).
[2] ECB.What is behind the low investment in the euro area? Responses from a survey of large euro area firms[J].ECBEconomicBulletin,2015(8).
[3] OECD.Lifting investment for higher sustainable growth[J].complied inOECDEconomicOutlook2015(January),OECD Publishing,Paris,2015.
[4] OECD.Unlocking growth: the role of investment,innovation,skills and business climate[J].complied inOECDEconomicOutlook2015(June),OECD Publishing,Paris,2015.
2016-04-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A081)。
陆婷(1983-),女,广东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