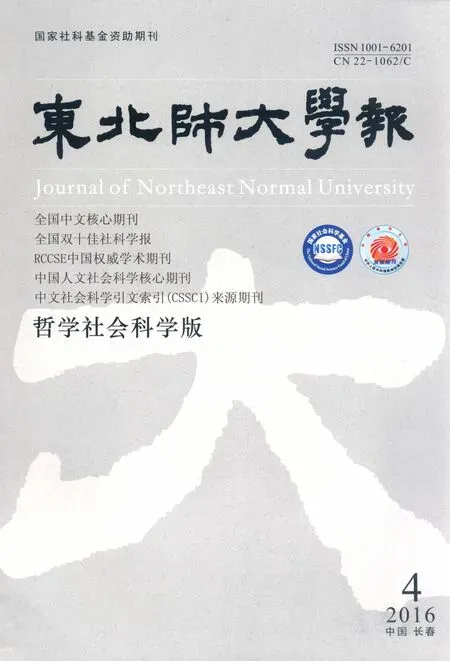象征天皇制的成立背景及其国民统合机能
田 庆 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天津 300191)
象征天皇制的成立背景及其国民统合机能
田 庆 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天津 300191)
战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主要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美国保留天皇制的战略意图体现为,既能避免占领日本时引发混乱,也可依托天皇的精神权威,将其塑造为引领和平与民主主义潮流的“旗手”,从而达成一举多得的战略目标。日本精英保守层则将维系天皇制视为维护日本国家根干的关键所在,旨在使天皇成为增强国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象征。日本国民尊崇天皇的情结与天皇富有的精神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着象征天皇制在凝聚国家认同、实现国民统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象征天皇制;美国主导;“护持国体”;国民统合
战后日本政治架构中的象征天皇制,对于日本的政治生态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日本战败后,围绕天皇制的存废问题,盟国之间、美国国务院以及日本国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并进行了激烈争论。天皇制最终以象征方式延续下来,是通过多方政治势力互动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美国主导的烙印,日本精英保守层在维护天皇制上付诸了一系列努力,日本国民尊崇和拥戴天皇的情感也成为构筑象征天皇制的民意基础。追根溯源式地厘清象征天皇制的成立背景,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探寻自民党修宪草案中缘何力争将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明文化的内在动因。同时,深入研究象征天皇制所具有的国民统合机能,才会从积极和消极的不同侧面认识天皇制的迥异效能,对于剖析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乃至社会总体保守化形成的思想根源大有助益。
一、美国主导象征天皇制形成的政治意蕴
战后日本新宪法中象征天皇制的成立背景,最早源自1942年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对日工作组”,这意味着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相关机构即已开始讨论利用天皇为战后日本占领政策服务的计划[1]4-69。1943年10月,美国国务院相关部局在涉及天皇制问题上的观点是:“中国国民之间已呈现支持废除天皇制的迹象,同时美国的舆论也倾向于以采取上述对策为宜。但是,若考虑到日本国民强烈希望继续保持天皇制的诉求,军政当局如果在统治期间着手废除天皇的话,也许会面临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2]70由此提出劝告:“盟国之间关于将来天皇地位作出何种决断,以及日本国民在败于盟国且被占领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状态,这些问题在当前时点上尚不知晓。为此给予军政当局的指示劝告是停止天皇权能,对皇族加以保护和监禁。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占领当局应发布公告传递如下旨意,只有天皇及其统率的日本国民对占领军显现出恰当态度,而且真正致力于发展立宪君主制,才会重新许可其行使权能。且力争将民众对占领统治机构的敌意控制在最小限度范围之内。”[2]70
美国国内围绕天皇制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倾向于在占领政策中将天皇作为“自由主义势力”的领导者加以利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皇是引导日本征服世界的要素之一,因此不应该利用天皇。前者的立场主要考虑到:“在日本国民尚未放弃天皇崇拜的前提下,若通过强权的方式排除天皇,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与此同时,如果在二重政治体制中原封不动地保留天皇,可能会重新滋生军国主义威胁,甚或引发下一次大战。”[2]1831944年11月,美国国务院设立“战后计划委员会”,下设远东局,5月知日派格鲁担任局长。此时国务院在天皇制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保存及利用天皇制论”与“废止天皇制论”的分歧。格鲁作为支持保留天皇制的代表性人物认为:“由于占领之际的决策受到诸多难以预测因素的制约,因此不宜采取僵化的应对之策,而应该富有灵活性地加以变通。日本国民若不在富有智慧的领导层指导之下,可能会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因此在进攻及占领日本的情况下,占领初期亟须得到文职人员的合作。如果合作顺畅,培养出得力的领导层,进而基于天皇权威发出指令,占领目标就会成百倍甚或上千倍地容易得以确保。”[2]233与之相对,罗斯则站在后者立场,认为天皇制与日本推行的侵略政策密不可分,应该废止天皇制。
美国国内有关天皇制的存废论争,最终以格鲁为首的知日派占据上风,认为若彻底排除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让日本政界和财界的稳健派成长起来,即便是在日本保留天皇制,也可以将日本改造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国家。美国此时已经认识到,利用天皇制可以有效地对日本实施占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1946年1月4日,美国政府顾问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书信中写道:“为了使民主化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尤其是天皇——乃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今后若要继续利用天皇,必须使天皇免除战犯之责;为了有效实施日本的投降条款,天皇在位甚为必要。”[3]941月25日,盟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致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申明了决定免于起诉天皇的理由:“在过去10年间,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天皇本人参与日本帝国诸项政治决策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根据彻底调查的结果显示,直至战争结束之前,天皇参与国事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仅仅给人以机械性地应对辅弼者的印象。如果审判天皇,占领计划势必将会做出重大变更。因此,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应该做好适当的准备工作。如果检举天皇的话,将会在日本国民之间引发大规模骚乱,这种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为过。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如果废除天皇,日本大概也要瓦解了。”[2]463接此电报后,综合参谋本部遵循这一建议,遂在1月末制定了不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的方针。
盟总政治秘书邦纳·F.费勒斯准将在战争末期汇总的《日本解答》报告书的结论部分写道:“天皇不仅仅在实现日军完全投降上不可或缺,也因之具有和平倾向将其作为战后日本政府的精神核心。”“美国人必须引导而非追随事态的发展。在恰当的时机,我们将允许在天皇及其臣民与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双方之间‘钉入楔子’。……只对天皇负责的独立的日本军队,是对和平的永久威胁。但是,天皇对其臣民的神秘掌控和神道信仰的精神力量,若加以适当引导则不一定造成威胁。如果日本完全战败,军阀倒台,天皇可能成为促进善与和平的力量。”[4]258
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秘密拜访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木户幸一的《木户日记》记载,这一举动在确保天皇制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如果没有这次拜会,天皇要免除战争犯罪则会变得非常困难。”[5]12371946年1月1日,天皇发布《人间宣言》,麦克阿瑟对天皇的新年诏书声明甚感欣慰。麦克阿瑟的政策更为倾向于拯救天皇、保护天皇和利用天皇,旨在操纵在日本享有最高权威的天皇。美国的政策设计是设定日本军部和军国主义者为坏人,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美国起码要将日本改造成为“天皇制民主主义”[6]11。在麦克阿瑟主导的盟总指导下,以及在日本政府的配合下,日本的国体自此从“天皇制军国主义”转变为“国民主权的和平主义”。麦克阿瑟的目的在于冲蚀和消解天皇的绝对君主神格,使日本从前的“天皇制军国主义”不再为患美国。于是公然地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让天皇换上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新装,让其充当和平主义化和民主主义化的先锋。这是麦克阿瑟的策略和日本当局为了保存天皇制“护持国体”的欲望相互结合的结果[7]35。
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成立背景,与美国主导的对日占领政策密切相关。以格鲁为首的知日派认为利用天皇制可以顺利推进占领进程,防止日本发生大规模动荡和骚乱,由此可以保持日本社会的稳定。同时,依据天皇所拥有的精神权威,旨在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与善的象征,从而使其成为引领日本走上和平国家道路的灵魂人物。美国主导的在战后日本维系天皇制的政治意蕴,具体体现了有效实施对日占领的战略设计,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
二、日本精英保守层“护持国体”的努力及挫折
日本在战败前后至为关心的所谓“护持国体”,主要体现在近卫文麿制定的《和平交涉纲要及解说》中强调的“确保皇统,天皇施政”。尽管并未详尽阐释 “天皇施政”的意义和内容,但决策层在维护天皇制问题上则明显持有共识[8]50。即便是在战败投降之际,日本依然坚持“护持国体”,由此可见天皇在日本国家、领导层乃至普通国民心目中的“至上地位”。这种坚决意志体现为日本政府在接受《波茨坦宣言》之际,甚至不惜进行“本土决战”也要顽固到底,结果遭受两枚原子弹轰炸,苏联军队进攻中国东北,并导致大量平民死伤以及出现众多“残留孤儿”,甚至引发大量官兵死亡的滞留西伯利亚事件[9]645。小森阳一认为:“裕仁与政府中枢部门在经历东京大空袭和冲绳战役之后,明显地置面临着大屠杀危机的国民性命于不顾,在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势下,毫无迟疑地选择了‘护持国体’。”[10]29裕仁天皇在做出结束战争的“圣断”之后坦露心迹:“我的任务是要将从祖先继承下来的日本这个国家传递给子孙。”田中伸尚对此评论指出:“这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前言中的‘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坚守国体是自身(天皇)被赋予的任务,如果继续进行胜利无望的战争的话,这项任务就无法完成。”[11]503-504对于裕仁天皇而言,只有“护持国体”才是对皇祖皇宗尽了自己的职责,履行了赋予自身的政治责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播放“终战诏书”,并未使用“战败投降”字样,而是声称日本“得以护持国体”,“信神州不灭”,“誓发扬国体之精华”[12]636-637。依据《波茨坦宣言》,日本的政治形态将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决定。日本政府为了“护持国体”,继续维系天皇制,亟须积极地向日本国民宣传天皇的善举,塑造天皇的仁慈形象。东久迩首相说,在8月19日拜谒天皇时,天皇指示应该迅速地让国民生活变得充实起来,8月20日早晨各报都将报道的重点聚焦在天皇关心国民生活的内容上,自中午起日本政府解除灯火管制,并停止从1941年10月以来实施的书信检阅制度[13]7。自8月起至年底,日本政府和大众传媒,一直不断宣传天皇的“仁慈”,例如天皇赐给军事遗族和伤病军人每人一定数额的慰问金,天皇将离宫的一块土地赠予民众以作保健之用,天皇将适宜农耕的皇室用地移交给国家保管等等。这些新闻都是为了达成“护持国体”之目的,而刻意向日本国民进行的宣传[14]119。
在1945年8月26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东久迩稔彦首相就“护持国体”作了如下发言:“所谓护持国体,它是我们超越理由和感情等的坚定信仰。它是祖先传来并流淌在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信仰。我坚信它绝不会为四面八方袭来的状况或风雨所动。我认为奉行终战诏书,并忠实地履行盟国所指示的条文,才是坚持国体、乃至保持我们民族名誉的依据。”[10]76渡边治认为:“在战败时点上提出的所谓‘护持国体’之‘国体’,乃是指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而且天皇应该总揽统治权,并且明确将其作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提出来。尽管在战败后统治层有各种各样的内部对立,但总体而言,他们在提及‘护持国体’时‘护持’的主要内容,明显就是维持作为政治权力者的天皇地位。”[15]16
自9月3日起,重光葵围绕“护持国体”问题与麦克阿瑟进行谈判,希望其收回对日本“布置军政”的成命,就被占领前提下以裕仁天皇的处置待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主权形态陈述了如下意见:“战败国日本之天皇,决心最为忠实地履行业已接受的《波茨坦宣言》,为此特任命史上第一个皇族内阁,以期不遗余力地履行《波茨坦宣言》。事实上,日本天皇历来反对战争,始终对维持和平展现出热忱;此次为终结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亦是陛下。陛下最为透彻地了解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宣言》,是为日本国民带来幸福的最佳手段。作为占领军,通过日本国民绝对崇拜之天皇特别任命的日本政府,实施占领政策即执行《波茨坦宣言》,方为最简易之方法也。若非如此,反而排斥作为日本国民之信念的天皇制,蹂躏日本之政治组织,或会使日本陷入混乱也未可知。总之,私下对天皇命令终战表示反对之势力并不在少数。此乃实情也。”[10]87-88由此可见,日本精英保守层的意图在于,首先通过将裕仁塑造为和平主义者的形象,称他一贯反对战争,且在终战之际以“圣断”方式结束战争时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为裕仁开脱战争罪责,而且这一点后来还成为评价裕仁的基本话语。其次,极力向盟总方面推销天皇制,主张充分利用天皇制是迅速实现占领政策的有效手段,并将其视为回避来自左和右的政变或“混乱”等的装置。最后,建议实施以天皇及其政府“主权”为前提的占领政策。显然,日本精英保守层在拥立天皇制方面巧妙地周旋于盟总与日本国民之间,也就是说,“对麦克阿瑟而言,只有裕仁能够带来和平;而对国民来说,是裕仁赋予了他们和平。他们即是以从不同侧面受惠于裕仁的借口为其开脱罪责。”[10]89
事实上,从盟总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来看,尽管天皇制以象征方式保留下来,但是日本精英保守层所坚持的“护持国体”的内涵已经大打折扣,正如渡边治所言,“从战前天皇拥有政治权力这一标准来看,象征天皇制即便不算全面失败,但是‘国体’的本质却几乎被抽空,从而成为一个屈辱性存在。尽管如此,能够将天皇保留下来已经实属不易,但却是一种违背自身意愿的体制。因此,在宪法实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裕仁天皇虽然深感从制度上不能恢复至以前作为政治权力保持者的状态,但还是试图恢复一些例行仪式,由此也界定了战后裕仁天皇的行动框架。虽然政治统治层总体上不敢公然声称复归战前,但还是尽可能身体力行地向战前天皇制拥有的权威性统治制度方面回归。每当主张修改宪法的时候,浮现在他们脑际的就是战前天皇制的统治构造。”[15]16
1945年12月,币原喜重郎内阁设置由松本烝治任委员长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12月8日,松本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四项原则,通称为“松本四原则”:1.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一大原则并无变更之必要;2.有必要扩充需要议会承认及议决之事项;3.为使国务大臣之责任参与至总体国务当中,应该创设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的制度;4.强化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加以保护[16]123。从松本草案制定的潜在意图来看,日本精英保守层根本不准备对明治宪法进行颠覆性修改,而是竭力维系天皇在形塑战前与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上下功夫。币原内阁的国务大臣松本烝治,抱着旧脑袋草拟修宪草案,仍以“天皇至尊”、“主权在君”为原则修宪,自然被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否决。
针对以“松本草案”为蓝本的宪法修正草案,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附上自身意见:“修正案是极为保守的,天皇的地位并未进行实质性变更,天皇依然保持着一切权利和主权”。同时呈送盟总司令麦克阿瑟审阅,经麦克阿瑟审定后,彻底否定了“松本草案”,决定由盟总司令部起草宪法草案,通称为“麦克阿瑟笔记”,主要内容为:“天皇居于国家元首地位;皇位世袭;天皇的职务及权能依据宪法来行使,且应在宪法中体现出对国民的基本意志负责。”[17]244其后,民政局长惠特尼及民政局次长凯迪斯起草宪法草案,由盟总主导起草的这一方案保留了天皇制,主要遵循国民主权与象征天皇制、和平主义及尊重基本人权三大原则。当日本政府收到由盟总方面草拟的宪法草案后,遭受的打击超乎想象,2月15日,白洲次郎写私信给惠特尼局长,婉转地陈述总司令部的方案是美国式的,并不一定适合日本风土[18]44-45。2月21日,币原首相再次拜访麦克阿瑟,试探寻找让步的余地。麦克阿瑟明确表示总司令部的方案是为护持天皇而拟定的,第一章为象征天皇,第二章放弃战争是基本条件,必须遵照。“日本当局见总司令部的态度相当坚决,为了换取天皇不被当作战犯进行审判的安全,只好含泪接受麦帅草案。”[7]134
由于美国方面主导制定的宪法与日本精英保守层起草的宪法草案之间存在着诸多背离,主要在关乎日本国体——天皇制问题上分歧甚巨,由于当时日本居于战败国地位,遂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宪法,这也成为长期以来战后日本政治的重要分歧点,革新阵营和普通民众大力拥护和平宪法,而保守势力则视美国主导的宪法为“眼中钉”,势必欲以除之而后快。时至今日,安倍内阁依然将废除美国主导的宪法,制定由日本国民亲自书写的宪法当作最为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以安倍为首的右翼保守势力之所以主张修改宪法,主要目标是力图在新宪法中明文界定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通过制定不受美国影响和约束的自主宪法,旨在彰显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三、象征天皇制的国民统合机能
日本战败后,根据盟总实施民主化的指示,推进了以修改宪法为首的、在国家体制所有层面从旧体制向新体制刷新的进程。1945年12月,盟总制定并发布《神道指令》,与天皇制保持紧密联系、事实上占据国教地位的国家神道遭到否定。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天皇的神格也被否定了。明治宪法事实上已经瓦解,从作为国家最高法规的宪法层面来看,实施了由战前基于神权主义的天皇主权的明治宪法,向以国民主权为基本原理的新日本国宪法的转变。由此,天皇的地位也从“统治权总揽者”(明治宪法第四条)的国家元首,转变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象征”的象征天皇[19]25。
在新宪法颁布之前,吉田茂首相在给其岳父原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信中提及象征天皇的作用:“新宪法实施后,天皇在政治层面的作用无疑会退后一步,但在精神层面上的作用则会进一步扩大,天皇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大且微妙。”[20]674第一届吉田茂内阁担任国务相的金森德次郎在述及“国体”内涵时指出:“不应该仅从法律层面的规定上理解君主制,而应着眼于在国民感情层面拥有雄厚基础的社会层面加以理解,由于一直存在着‘国民憧憬中心的天皇’,可见并未改变‘国体’。”金森在国会答辩时也明确强调:“由于作为日本国民精神统合中心天皇的存在,‘国体’未变,国家统治的主体发生了由天皇向国民的转移,仅仅是在‘政体’上发生了变化。”[21]44
日本宪法学者奥平康弘认为,象征天皇制的存续与日本国民内心的倾慕信仰息息相关,“天皇制之所以在日本国宪法中保留下来,最重要的因素归结在体制方面固然无可置疑,但同时也深刻地体现着植根于普通国民之间拥有的‘国体护持’、‘国体不变’的信念及愿望。……然而,这一‘国体’论并非围绕‘主权之所在’从法理层面乃至权力脉络中延展开来,而是蕴含着传统性、情绪性及伦理性的‘作为憧憬中心天皇’的文化现象。若将后者称之为‘内在天皇制’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内在天皇制’,才是将作为宪法制度的天皇留存下来的原动力。”[22]121
根据1946年2月每日新闻社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天皇制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期望依然保持明治宪法绝对天皇制的仅为16%,希望脱离政治成为道义性存在的象征天皇制的占45%,占据主流。在草案公布后1946年4月的调查中,赞成草案中天皇制的为85%,反对的为13%;关于废止天皇制,赞成的仅为11%,反对废除的为86%,支持天皇制居于压倒性地位。”[23]163由此可见,天皇制在日本社会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憧憬之情”,是“吸引大多数国民关心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着作为国家和国民统合象征的天皇制”[24]59。和辻哲郎认为,“天皇是国民统合的象征,即便是在国家分裂的状态下也是如此。因此,这种统一并非政治层面的统一,而是文化层面的统一。日本人在语言、历史、风俗等文化活动中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作为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国民或者民众的统一便以天皇作为象征。贯穿历史一脉承袭下来的尊皇传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性统一的自觉。”[25]118-119井上达夫也指出,“仅仅将天皇的向心力视为‘自上而下的统合’是不全面的,这里之所以产生对天皇的向心力,主要源自浸透于草根之间对天皇的敬爱之情。”[26]39
自裕仁天皇发表否定自身神格的《人间宣言》之后,普通国民对天皇的神性及其信仰遭受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但国民意识并不会立刻对天皇制发生改观,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心理及心情层面逐步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由于在公权力强制下的天皇崇拜的不自然状态得以解除,在更为合理的层面支持天皇制也就成为可能。”[27]96由此,面对即将消失的天皇“权威”,在战后不久伴随着敬爱与信赖的新型关系日益确立起来。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与民主化的同步推进,欢迎‘无害的’天皇制,虽然在逻辑上难以调和,但这种并不单纯的‘自我矛盾的事物’却由普通国民自然而然地予以接受了。”[27]95对于天皇道德上的敬爱之情,随着岁月流逝,不断暧昧化、通俗化及明星化。总而言之,天皇成为国民心理上憧憬的对象[28]62。这也被称之为变形的“天皇信仰”的通俗版,作为天皇和国民之间新的联系纽带的就是天皇在战后不久展开的“巡幸”,天皇对“受灾者”及遗族表现的“慰问”、“激励”及“关怀”等态度,进一步通过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应答及互动运转起来[29]59。
象征天皇制中的所谓“象征”其积极性表现为,通过遴选“象征”也就能通过这一“象征”看到社会或国家之姿态,由此达到强化社会或国家构成人员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象征”观念本身同时蕴含着消极性因素和积极性因素,“象征”之所以成为“象征”,也发挥着两方面机能,仅仅关注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值得警惕[30]224-240。象征天皇制在确立日本的国家认同及实现国民统合方面具有无可替代性,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大众不仅仅单纯地将天皇制视为政治机构,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将自己的心情也寄托在天皇身上,天皇成为拟似宗教信仰的对象,从而让天皇制承载了这一功效。”[31]207由此可见,日本国民对战后天皇制并非消极性地认可,而是形成了更为积极的天皇制和天皇像。这也正是深入理解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及现在的天皇像持肯定性态度的深层原因所在[28]116。
与此同时,随着大众天皇制的不断推进,从日本政府层面而言,由于象征天皇制已改变了此前所处的位置,于是遂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保障天皇的正统性,并赋予其相应权威。“为使权力行使的形态正统化,天皇的存在是最为适合的。”[32]193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战后政治史中的保守政治领导层,不断构建和推进强化天皇权威的运作机制,为此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操作和宣传,从而导致逻辑上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战后日本无疑呈现宪法体制焕然一新的事实,但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上,战后与战前之间,与断裂性相比,更多地在体制转移方面将重点放在了维系连续性上[28]65。战后日本的保守领导层始终致力于通过修改宪法强化天皇权限,以及为了强化自卫队而利用天皇权威,从而给国民心理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总之,象征天皇制的成立是国内外多方政治势力互动博弈的结果,“面对主张复归至战前政党政治、崇尚天皇至上的守旧势力,谋求废止作为军国主义和非民主主义根源的天皇制的国际民主舆论,以及为兑现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国际公约而利用天皇制谋求顺利推进占领政策的盟总,象征天皇制的形成实际上是上述三方势力达成妥协的产物。”[33]26无论是美国主导利用天皇制,还是日本精英保守层坚定地“护持国体”,其核心内涵更多地指向天皇所具有的国民统合机能。美国的知日派认为维系天皇制,既能避免占领过程中引发混乱,同时还可以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将其塑造为引领和平与民主主义潮流的“旗手”,达成一举多得的战略目标。对于日本精英保守层而言,竭力维系天皇制关乎日本国家之“根干”,是确保民族主体性和自立性的关键所在。尽管保守层向往的继续维持天皇在战前拥有的政治权力被褫夺,但天皇制最终还是以“象征”的方式保留下来,天皇仍然承载着国民统合的机能。正如米谷匡史所言,“依据将‘断绝’与‘连续’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再编构想,在由战中向战后转换的过程中,作为日本政府与占领军合作的产物,旨在将‘天皇作为国民统合象征的战后日本国家成立过程’也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34]74尽管象征天皇丧失了战前有关参与国事的权能,但依然在凝聚日本的国家认同、强化国民一体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象征天皇制的成立与发展,是融合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设计、日本精英保守层“护持国体”的努力,以及日本国民尊崇天皇情结等复杂因素的产物,由于其在国家政治架构中保留了具有前近代特征的君主形态[35]66,从而导致日本政治中蕴含着难以摆脱的“复古性”及“保守化”的内在特质。
[1] [日]五百旗頭真.米国の日本占領政策(下)[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5.
[2] [日]山極晃,中村政則,岡田良之助.資料——日本占領1·天皇制[M].東京:大月書店,1990.
[3] [日]竹前栄治.占領戦後史——対日管理政策の全容[M].東京:双柿舎,1980.
[4] [日]约翰·道尔.拥抱战败[M].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 [日]木戸幸一日記研究会編.木戸日記[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6] 许介鳞.魔鬼藏在细节里I微妙的美日关系:保护与霸凌[M].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13.
[7] 许介鳞.日本现代史[M].台北:三民书局,1991.
[8] [日]黒田展之.象徴天皇制の展開[J].法と政治53巻2号,2002(6).
[9] [日]角田猛之.神権天皇制と象徴天皇制における〈制度的の断絶性と意識的の連続性〉[J].関西大学法学論集56巻,2006(2/3).
[10] [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M].陈多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11] [日]田中伸尚.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天皇第五巻·敗戦(下)[M].東京:緑風出版,1988.
[12]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M].東京:原書房,1973.
[13] [日]辻清明編.資料——戦後20年史·1政治[M].東京:日本評論社,1966.
[14] [日]信夫清三郎.戦後日本政治史·I占領と民主主義——1945年1月—1946年5月[M].東京:勁草書房,1974.
[15] [日]渡辺治.象徴天皇制の今日[J].歴史評論,1990(2).
[16] [日]横手逸男.日本国憲法·新皇室典範制定時の天皇制をめぐる論議[J].湘北紀要第31号,2010.
[17] [日]松本昌悦編.原典 日本憲法資料集[M].東京:創成社,1988.
[18] 連合国最高司令部民政局.日本の新憲法[J].国家学会雑誌65巻1号,1951-06-01.
[19] [日]茶谷誠一.象徴天皇制の成立過程にみる政治葛藤[J].成蹊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9号,2014.
[20] [日]吉田茂記念事業財団編.吉田茂書翰[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
[21] [日]茶谷誠一.象徴天皇制の君主制形態をめぐる研究整理と一考察[J].成蹊大学文学部紀要47号,2012(3).
[22] [日]奥平康弘.日本国憲法と「内なる天皇制」[J].世界,1989(1).
[23] [日]斎藤道一.世論調査による天皇観[J].現代の眼,1966(2).
[24] [日]葦津珍彦.国民統合の象徴[J].思想の科学,1962(4).
[25] [日]和辻哲郎.国民統合の象徴[M].東京:勁草書房,1948.
[26] [日]井上達夫.現代の貧困[M].東京:岩波書店,2001.
[27] [日]小林直樹.象徴天皇制の法意義[J].思想,1960(10).
[28] [日]遠藤興一.象徴天皇制とその慈恵的性格について[J].明治学院大学社会学·社会福祉学研究140号,2013(3).
[29] [日]瀬畑源.昭和天皇『戦後巡幸』における天皇報道の論理[J].同時代史第3号,2010(12).
[30] [日]佐藤功.象徴における消極性と積極性[A].杉原泰雄編.国民主権と天皇制[C].東京:三省堂,1977.
[31] [日]菅孝行編.叢論日本天皇制上巻[M].東京:柘植書房,1987.
[32] [日]山口二郎.日本官僚制と天皇制[J].思想,1990(11).
[33] [日]松尾尊兊.象徴天皇制の成立についての覚書[J].思想,1990(4).
[34] [日]金ヨンロン.<断絶>と<連続>のせめぎ合い[J].日本近代文学第90集,2014(5).
[35] 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kado System and Its National Integrtaion Function
TIAN Qing-li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 Mikado System was dominated by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Ⅱ,the strategy intent of America for maintaining the Mikado System reflects in two aspects.It can not only avoid confusio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ed Japan,but also rely on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and mould a bannerman that lead the trend of peace and democracy,thereby realized the strategic target of achieving many things at one stroke.Japan’s conservative elite regarded maintaining the Mikado System as the key point of national traditon,in order to make the Emperor as the symbol of national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Japanese nationals’ respect complex of the Emperor organically combinated with the richful spiritual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together pushing the Mikado Syste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he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alizing national inegration.
The Mikado System;Leading by America;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National Integrtaion.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11
2016-04-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S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S011)。
田庆立(1975-),男,内蒙古赤峰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K313.5
A
1001-6201(2016)04-0061-07
[责任编辑:赵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