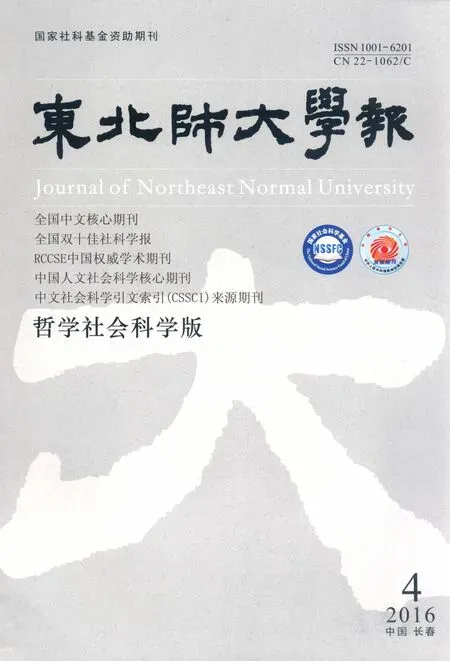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
刘 峰
(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2.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400)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
刘峰1,2
(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2.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400)
随着“亚洲”一词从“他称”向“自称”的转变,近代日本对亚洲的归属意识得以初步形成。有了这种归属意识,亚洲主义的萌生也就成为可能。然而,它在萌生之初却缺乏对亚洲的价值认同和主体认识。作为散乱意见的集合体,核心特征也不甚明确。其中虽然存在些许的“健全原型”,但最终汇成主流的,却是一种富含优越感和指导者意识的、带有“日本盟主论”倾向的东西。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亚洲主义”这一用语及其概念最终于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走向了定型。此时它所呈现出来的性质,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张性、侵略性的发展形态而已。在随后的时局变动之中,它无法避免歧途,反而在理论的架构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并沿着错误的道路渐行渐远。
日本;亚洲主义;盟主论;早期发展;概念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是使侵略正当化的思想工具。正是这一思想,最终成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灾难与痛苦。然而,亚洲主义在其早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情况颇显复杂,对其捕捉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此有过一些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又不得不承认,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比如,亚洲主义在诞生之初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价值核心是什么,到底是近代主义,还是反近代主义的东西?它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怎样的倾向?所谓的“健全原型”是否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亚洲主义”这一用语及其概念究竟于何时定型,定型之后又展现出了怎样的本质性格与理论架构?它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何联系?在此后的时局变动之中,是否又添加了新的特征,等等。为了尝试分析这些问题,拙论拟基于先行研究的宝贵成果,进一步发掘考证相关史料展开考察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他称”向“自称”的转变及其初期状态
亚洲主义,首先应该源自一种对于“亚洲”的归属意识。换言之,如果没有“亚洲”这一概念,抑或是不承认自己属于“亚洲”,那么所谓的亚洲主义就不可能诞生。众所周知,原本“亚洲”或“亚细亚洲”一词并非由亚洲人自己创造,而是作为一种区分世界的地理概念,从西方的“Asia”一词翻译而来。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明朝皇帝(明神宗)进献了标有“亚细亚洲”、“欧罗巴洲”的《坤舆万国全图》。以此为契机,相关概念首次被介绍到了东亚,并在若干年后传入了日本。而在18世纪,通过西川如见、新井白石在《日本水土考》(1700年)和《采览异言》(1713年)等著作中的介绍和记述,“亚洲”的概念又进一步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传播。
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日本人却坚持认为西方不过蛮夷,且日本与中国、朝鲜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故始终将“亚洲”视作一种对“他者”的称呼而不予接受。他们对于“亚洲”不存在归属意识,甚至还会对此颇觉反感。比如水户学的代表学者会泽安(又名会泽正志斋)就曾在1833年的《迪彝篇》中宣称:“西夷将地区分,称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夫利加洲。然夷辈对我之命名,既非天朝给定之称呼,亦非上古所定之公名。今以亚细亚称我,以为包含神州之总称,实在傲慢至极。……故各国国名可用自称,但总称不得用西夷之私称。”[1]249结果在他们眼里,“亚洲”不过是西方人擅自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私称”而已。
然而在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社会的迅速西方化和近代化,这一概念却开始被日本人积极地接受,并从“他称”、“私称”向“自称”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以往对西方的反感和抵触逐渐消退,亚洲各国的差异和多元性也被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从而促使对亚洲的归属意识得以萌生。进而,通过对“亚洲”一词的认同与使用,亚洲各国在地理上的共性被发展成了某种政治上的共性,并在这种共性的统合之下开始与“欧洲”形成对立,呈现出了“一体”的幻觉。而正是这种夹杂着幻觉的归属意识,意味着亚洲主义的萌生成为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古以来的亚洲本身并不存在“亚洲”这一概念,所以当人们抛开对“亚洲”的疑惑,开始理所当然地使用起这一概念的时候,其潜意识里存在的已经不再是亚洲土生土长的东西了。不如说,它是沿着西方人这一“他者”的视线审视自己时,逐渐开始形成的一种带有近代性的认识。因此,我们首先可以判断认为:亚洲主义是伴随着近代的到来而产生的东西。它虽然看上去与欧化主义对立,并“带有反近代主义的性格”[2]93,但这无法掩饰其自身便是欧化主义、近代主义的事实。而且,它并不是基于亚洲自身在传统文化上的亲近性自发地、主动地产生的思想,而是在西力东渐,西方势力侵入东亚的背景之下,为了应对共同的危机而不得不去追求亚洲“一体性”的东西。
笔者曾通过排查梳理日方的史料发现,本身在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前期,并不存在“亚洲主义”或“亚细亚主义”这一用词。甚至连“主义”这一词语的使用,在当时也未完全定型。即,它是由政治家福地源一郎在1881年的辞典《哲学字汇》中作为英文“Principle”的译语被首次使用的。而作为“-ism”的对应翻译被推广普及,则是明治后期的事情了。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明治前期,亚洲主义尚未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或概念正式形成。它不是从特定的思想家或者特定的理论著作中产生的思想,本身也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最初不过是一些极为散乱的,尚未完全统一的意见和主张而已。可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或者说处在这一阶段的亚洲主义,其主流特征尚未完全明确,若要对其进行捕捉并做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便能够定义,也只会像盲人摸象一般,结论变得极为片面。因此对于此时期的亚洲主义,我们顶多只能说:它看上去貌似带有团结亚洲抵抗西方侵略的,极为抽象的基本属性,呈现出了某种防御的性格。而这或许正是以往研究中提到的“最小限度的共通性”,抑或是“思想的最大公约数”[3]38。
正因为具备了这种基本属性,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尽管表述方式尚未统一,显得极为散乱,但大多具备了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那就是所谓的“亚洲同盟论”,也被称为“战略亚洲主义”[4]。比如当时的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就曾主张:“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合纵联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首先,应从游说邻国朝鲜开始,此后波及中国。”[5]50这种主张战略联合的构想,无疑说明当时以军事战略为中心的政策论正在日本盛行。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可以想象,亚洲主义最初主要是作为一种战略构想而出现的。它主张地理上接近、人种上相同,同样遭受压迫欺侮的中、朝等亚洲各国能与日本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西方的侵略,确保自身的独立。
这一构想虽然带有某种归属意识,但因为过于强调战略上的问题,以及地理、人种等自然所赋予的客观条件,反而忽略了价值上的认同感,缺乏对亚洲的主体认识。换言之,它所强调的亚洲团结的基础并非在于价值的一体性,实际上不过在于战略的便利性而已。这显然说明了亚洲主义在价值观与理论体系上的缺失,意味着这一思想日后在本质性格上极易出现根本性的变动。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到,当时为了摆脱危机,日本一方面强调与亚洲各国的战略联合,另一方面又带着巨大的失落感,从应该作为亚洲主义基底的东方文明中脱离,接受并追随了西方文明,成为“放弃抵抗的亚洲”。而正是这种接受与追随,意味着日本在对外层面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抵抗,在对内层面放弃了对自身西方化和近代化的抵抗。甚至在此后不久,他们便把近代化上的成功反过来加以利用,作为日本在亚洲树立优越感,充当“盟主”的核心根据。因此可以说,日本社会在推进近代化的同时鼓吹亚洲主义,不仅加剧了东方对西方、亚洲对欧洲的对峙关系,也将带来亚洲内部的斗争。而恰恰是后者,在日后逐渐成为更为深刻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洲主义中所反映出来的“连带性”和“一体性”也就自然会面临一些问题。虽然著名的亚洲主义者冈仓天心曾在1902年的《东洋之理想》中断言:“亚洲乃是一体。”但事实上,现实的亚洲却颇显多元。无论是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还是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各国都拥有各自的固有传统和价值取向。正如天心的继承者大川周明所感慨的那样:“亚洲的政治复杂,产业形式多样,文化样态繁多,亚洲绝非一体。或者说太过于不像一体了。”[6]354不得不说,亚洲缺乏足够的“连带性”和“一体性”,本身并非一个整体。它不过是用“欧洲”这面镜子照射自己,并遭受侵略和屈辱之际,才尝试走向一体的某种“可能态”而已。换句话说,亚洲是“抵抗”的亚洲。在“抵抗”的问题上,亚洲或许能够走向一体。然而,日本却放弃了“抵抗”。它追随西方文明并走向近代化的过程,其本身就是脱离亚洲的过程。因此近代日本所主张的亚洲主义,与其说是“抵抗西方的策略”,不如说是“应对亚洲的策略”显得更为妥当贴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随着“亚洲”一词从“他称”向“自称”的转变,近代日本对亚洲的归属意识得以初步形成。有了这种归属意识,亚洲主义的萌生也就成为可能。然而,它在萌生之初却大多侧重于战略的问题,反而缺乏真正意义上对亚洲的价值认同和主体认识。正因为如此,亚洲主义在此时期作为散乱意见的集合体,表述形式多样,核心特征也不甚明确。虽然看似具备了“团结亚洲、抵抗西方”的基本属性,但实际上作为近代主义的一种形态,随着近代化的不断推进而可能在其他方面展现出更为明确的倾向。
二、“健全原型”的衰弱与主流倾向的显现
1960年,日本学者野原四郎曾对亚洲主义做出过如下解释:“亚洲主义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要求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相互团结的主张。亚洲连带论本身与日本的独立问题相关联,在明治初年被提倡。”但此后“随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衰退、天皇制的确立、对华军备的扩张,大亚洲主义开始抬头……它在此后逐渐扮演了掩饰明治政府大陆侵略政策的角色。”[7]6可以看到,野原在这里将原本散乱多样的早期亚洲主义归纳成了两大流派:带有一定进步因素的“亚洲连带论”与富含侵略意图的“大亚洲主义”。对此,另一位著名学者竹内好在随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野原的定义与我的观点相近……但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将散乱的意见主张区别为两大流派并使之对立的做法“有些太过机械死板”。进而指出,亚洲主义中的“连带”和“侵略”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不可分离关系,需要在近代史中去找寻那种带有一定进步因素的健全原型[8]10。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在近代的日本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能够抑制侵略主义产生,能够“超克”近代的可能性。然而,他最终找到的“健全原型”,比如天佑侠和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等例子,都明显是错误的[9]。
尽管如此,在野原和竹内的影响之下,时至今日,认为亚洲主义具有“连带与侵略的不可分关系”,种类丰富但又可以大致划分为健全的“亚洲连带论”与侵略的“大亚洲主义”两大流派,本来孕育着“超克”近代的理想,却在此后被军国主义利用而发生变质,这样的一种解释依然在学界的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这难免让人质疑:亚洲主义的健全原型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散乱的意见主张中找到它并予以定位?它是否真的作为一个流派、一股潮流存在过?不得不说,此处需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事实上,对野原和竹内的研究不加质疑地予以认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将亚洲主义中的健全原型作为一个足以与“大亚洲主义”并列的流派加以把握,也是值得商榷的。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是要完全否认健全原型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即便它曾在日本近代史中出现过,比如无私支援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等人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也不过“如星星点火般存在”,是极少数的特例而已。可以说作为思想的大潮流或大流派,它并没有出现过。换言之,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主流绝不会是健全的东西。它看上去与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外在形态相反,但实际上“两者相互补足,使侵略亚洲变得正当化”[10]41。因此,归根结底应该作为核心探讨的,并不是如何在近代史中去寻找“健全原型”的问题,而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亚洲主义中健全的部分那么少?为什么它没有汇集成为一股足够大的潮流?在当时散乱的意见主张中,最终走向主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特征?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兴亚会的例子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兴亚会是日本明治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亚洲主义团体。它由1878年创立的振亚社发展而来,于1880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如前所述,因为当时尚不存在“亚洲主义”或“亚细亚主义”这一固定用语,所以它的主张主要是以“兴亚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兴亚会中,不仅有中、日、朝三国的会员存在,而且日本会员自身还成分混杂,性质并非纯一。围绕所谓的兴亚论,曾出现过很多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在很多关键性的,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亚洲主义主流倾向的问题上,其主张尚未形成统一。比如,关于“亚洲团结时,各国地位应如何”的问题。换言之,既然亚洲要团结起来共抗西方,那么应该如何团结?价值取向如何?是否需要指导者或“盟主”?“盟主”应该是谁?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不用说在中日会员之间,就连日本会员内部都尚未达成共识。通过追查史料可以发现,当时的见解大体分为如下三类:(一)以何如璋为代表的中国会员主张“中国盟主论”,希望限制西方化和近代化,继续固守传统,维持中国自古以来的宗藩体制;(二)以高桥基一为首的部分日本会员则坚持以近代化作为亚洲各国团结的基础,并认为:“我国人比清国人开化时间稍长,故宜以此诱导其进步”[11]8,即主张“日本盟主论”;(三)以末广重恭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日本会员主张“中日共同盟主论”,提出:“日中两国应消除相互嫉妒之念头,共同面对欧洲外敌,相互改良政治,以图振兴国势,联合朝鲜安南暹罗并波及印度波斯……故可为盟主者,非我日本与中国何也。”[12]这些见解时常碰撞摩擦,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早期亚洲主义作为散乱意见集合体的特征。
然而,作为决定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的根本性问题,这终究是无法回避,需要明确回答的。结果在此后不久,以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时的对朝政策讨论为契机,各方的分歧和对立最终走向了表面化。当时,已有相当多数的日本会员坚持认为:“要振兴亚洲的大势,就必须与朝鲜推进近代化的势力相结合”[13]50,并要求基于这一方针立即展开行动。这显然是站在近代主义的立场上,摆出了要与固守旧体制的中国直接对决的姿态。由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优越感本身就来自于其近代化的成功,所以主张以近代化的方式来实现“兴亚”,自然就会将其推向指导者和“盟主”的位置,朝“日本盟主论”的方向发生倾斜。而正是这种想要动摇中朝宗藩关系,甚至试图凌驾于中国的主张,立刻引发了中国会员的强烈不满。结果,这些人相继退会,导致兴亚会最终分裂。可以说,这一事件意味着当时中日两国在“兴亚”的问题,或者说亚洲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形成鲜明的对立。而原本散乱的亚洲主义,则在现实政治的影响推动之下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逐渐展露出了较为统一的主流倾向。
不仅如此,这种主流倾向的显现似乎也可以与当时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趋势形成某种关联。曾有学者指出,民权运动中本来就包含了“亚洲连带意识(对等性)与指导者意识(不等性)”两个方面,且主要方面在于后者,容易向侵略主义发生倾斜[14]238。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可以将前者理解为类似近代西方主权国家平等意识的“横向并列关系”,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延续了华夷秩序上下等级意识的“纵向主从关系”。因为“只有真正以自由平等的人民所构成的民权国家,才能最忠实于近代西方的国家平等意识”[15]263,所以可以认为,作为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在“横向并列关系”与“纵向主从关系”之间的选择与取舍,本身就能够与作为对内问题的,民权运动中的“民权论与国权论之争”相互挂钩。
众所周知,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推进的过程中曾经历了从民权论向国权论的转变。尤其是其标志性人物福泽渝吉,虽然在1881年的著作《时事小言》中宣称:“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表达了批判国权的意思。但自己却在此后公然选择了作为“权道”的国权论。因为在他看来,民权与国权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享有民权,必须先确保国权。而为了确保国权,必须首先在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中存活下去,所以日本不得不也成为“禽兽”的一员,在外交上追求“纵向主从关系”。基于这样的一番思考,福泽最终在对外问题上明确地发表了意见:“当今东方列国中,能成为东方文明之中心与西方对抗者,仅日本而已。须认识到亚洲东方的保护乃我之责任”,“绝非自卖自夸,平心而论,在亚洲东方能胜任盟主者,仅我日本而已”[16]103,186-187。这势必意味着,在日本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民权论转向国权论”的大潮之中,亚洲主义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迅速向富含指导者意识的“纵向主从关系”发生偏转。
同时,这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纵向主从关系”,还基于文明论上的优越感与“日本盟主论”形成了直接关联。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按照西方化和近代化程度的不同,将国家划分为“开化、半开、野蛮”的情况。这种做法与以往将天下分为中华、诸夏、四夷的华夷秩序观颇为近似。它将走向近代化的日本置于西方列强之下的同时,实际上也将日本放在了亚洲的上位,暗示了理应充当“亚洲盟主”的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貌似优越于亚洲的“日本文明”,绝不是基于日本固有传统和东方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东西。相反它是从西方化,即脱离东方文明的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在此之后,明确以“日本盟主论”为主流倾向的亚洲主义,无论它如何鼓吹反抗西方,抵抗西方,都不过是一种托辞。因为其自身便是“西方”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通过本节的考察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些许健全的部分,但作为思想的大潮流或大流派,却并没有出现过。相反,通过分析此时期代表性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的例子能够发现,在明治前期日本社会不断推进西方化和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原本散乱多样的各种意见和主张逐渐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在民权运动“民权论向国权论转变”的影响下,开始向富含优越感和指导者意识的“纵向主从关系”发生倾斜,并最终凸显出了“日本盟主论”的主流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亚洲主义将在日后显露出更为浓厚的消极特征,并随着时局的变动和理论的发展而进一步趋向定型。
三、概念的定型及其理论发展
如前所述,“亚洲主义”在作为一个用语或概念尚未完全定型的时候,就已经基于近代化成功所带来的优越感与指导者意识锁定了向“日本盟主论”发展的主流趋势。虽然当时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全原型”,但那不过是极为少数的特例而已,终究无法改变亚洲主义发展变迁的总体倾向。而且就在主流趋势凸显之后不久,亚洲主义便开始走向了定型。
首先,是1890年4月18日发表在政教社杂志《日本人》上的一篇名为《亚细亚经纶策》的文章。其中做出了如下论述: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缺乏理解,而中国人又对学习西方文明缺乏兴趣。与此不同,日本人“两者兼而有之,生长在东洋风教之中,乃是一度将东西文明冲突激化而成的革命经略付诸实践之勇者”,故只有兼备了“西洋文明精神”和“东洋野蛮身体”的日本,才拥有指导黄色人种实现东方革命的资格[17]。这一理论,被以往的研究视为“趋向定型化的亚洲主义理论的萌芽”[18]48,继续延续了前面所提到的主流倾向。
进而沿着这一趋势,在两年之后,“亚洲主义”这一用词也开始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调查梳理后可以发现,1892年2月1日,同样是在政教社的杂志上,曾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亚洲旨义是什么》。虽然在现代日语中,已经不存在“旨义”这一词语了,但从该词的日文发音来判断,显然与“主义”是保持一致的。故可以认为,这是近代日本使用“亚洲主义”这一固定用语之肇始。
在文章中,论者首先指出:“有三千年之史迹,东洋的岛屿帝国得以淘其精神、冶其形态而成国。以此精神形态而特立于森罗万邦,彰其特长特美,俱万邦之各所,资圆满完美之全世界大文明者,是为日本旨义也。”继而主张,作为“在国家之上的团体旨义”,存在着“泛美旨义”、“澳洲联邦旨义”、“亚洲旨义”之分。日本“位于亚洲东海,先亚洲诸国完美其文物。故于亚洲诸国中,作为先觉有开导后觉之重任”[19]。这段话,最先使用了“亚洲主义”一词,并为其做出了具体的解释。从其理论来看,亚洲主义是从日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扩大至亚洲范围并超越于国家单位之上的团体主义,与泛美主义、澳洲联邦主义形成了相互并列的关系。而且,因为日本在亚洲各国中首先通过近代化“完美其文物”,所以有必要站在指导者的位置开导后进各国。这意味着亚洲主义在此前所凸现的“日本盟主论”等主流特征不仅被加以继承,而且还进一步融入了相关概念的定型过程中去。
从这篇文章的论述来看,显然在近代,亚洲主义不过就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张性发展形态而已。因为日本终究无法等同于亚洲整体,所以这种“从日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走向亚洲主义”的过程,决不会是单纯地在地理上从国家层面扩大到了地区(亚洲)层面,也决不会是从维护日本一国利益的“小乘思想”,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维护亚洲整体利益的“大乘思想”。而不如说,亚洲主义处在日本民族主义的延长线上,是其侵略性的扩大版本。两者之间的连接最终是通过“日本盟主论”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此时的亚洲主义中,日本不仅是“盟主”,而且还是亚洲的绝对代表,其一国的利益实际上被等同于甚至凌驾于亚洲的整体利益之上。在此情况之下,亚洲主义就不可能是单纯的亚洲主义了,而是“从日本民族主义扩展而来的亚洲主义”。其价值核心显然不会是“亚洲”,而是“日本”。所以日后伴随着“亚洲”所囊括的范围逐渐扩大,日本的国家使命自然也就会越被夸大,其思想的欺骗性也就会越发浓厚,其中所包含的“连带与侵略”也就难以区分了。
而就在《亚洲旨义是什么》刊发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便爆发了。这场中日之间围绕“亚洲盟主”所进行的争夺战,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它意味着东方世界传统的宗藩体制轰然坍塌的同时,日本已然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最强国,夺取了“盟主”乃至“中华”的地位。由此,已经趋向定型的亚洲主义再次从现实中获得了根据,稳固了其概念内涵。进而在战争之后,随着东亚社会乃至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动,亚洲主义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开始“离开由部分知识分子讨论的散乱意见状态,逐渐包含着丰富的要素和政策构想,成为一股潮流推展开去”[20]177,其理论架构也在以往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当时亚洲主义核心团体东亚同文会的主张。从该会所宣扬的理论来看,显然亚洲主义在此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了若干新特征。
首先,是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理论根据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甲午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普遍开始担心日本在亚洲进一步实施改革与扩张将对自身构成威胁。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还曾下令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了油画《黄祸》作为国礼赠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大量印刷发行。这导致所谓的“黄祸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甚嚣尘上。与此针锋相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们也开始在此时期大肆鼓吹黄白人种间的“人种对抗论”。比如曾在德国留学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就在1898年的杂志《太阳》上撰文指出:“东洋成为人种竞争之舞台已在所难免……最后的命运乃是黄白两人种之竞争,在此竞争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将共同成为白人之仇敌……故所有黄人国家不可不讲保护之策。”[21]62
然而,这种强调人种对抗的亚洲主义论却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即,此时的日本效仿白人推进了近代化并对亚洲实施了侵略政策,其自身俨然已是“白色人种集团”的一员。在亚洲各国眼中,它与其说是“黄祸”,不如说是“白祸”。也就是说,日本在面对亚洲时,无论如何呼吁共抗白人国家,也终究难以获得共鸣;而在面对欧洲时,无论如何推进近代化和西方化,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白人国家的一员。它已然站在了被“黄祸论”和“白祸论”两面夹击的孤立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主义者们为了摆脱孤立,重新确立其充当“亚洲盟主”的理论根据,不得不另想办法。由此,所谓的“东西文明融合论”开始应运而生。比如,东亚同文会会员竹越与三郎就曾在当时的杂志《国民之友》中提出过这一主张:“亚洲并非人种集合体,也非文明集合体,更非政治之集合体……不过是地理上一空名而已……日本人乃不受人种区别限制的大国民,应斥退人种相争之狭隘。日本人作为取东西文明之英华,站在世界高点之国民,万不可受东洋历史之惰力所制。”[22]250即是在宣扬,日本的使命应该在于吸取西方文明的同时坚持东方文明,并进而将两种文明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明,以此来指导亚洲乃至世界的改革与发展。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之下,日本充当“盟主”的理论根据开始从以往的“学习西方之先驱”向“东西文明融合论”发生了转变。通过这一转变,日本不仅可以回避孤立的危机,而且对于亚洲的优越感也能够继续保持,以“日本盟主论”为核心特征的亚洲主义也就能够在新形势下继续成立。
其次,是对门罗主义的借鉴与模仿。众所周知,美国在19世纪中期忙于南北战争,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机。此后又主要致力于西部的开发、工业化的推进和移民的吸收。因此国内市场较为充实,尚无向海外扩展势力的绝对必要。然而进入19世纪末期,随着以上目标的达成,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势力,它开始将视线投向太平洋及远东地区并迅速崛起。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的门罗主义开始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并成为其发展亚洲主义理论的参考摹本之一。他们不仅承认了门罗主义这一外交原则的有效性,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将其与亚洲主义融合互补,以套用于亚洲地区。比如前面提到的近卫笃麿,就曾在1898年11月12日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会面时指出:“今日东洋的问题,并非仅是东洋问题,乃世界问题。欧洲列强为自身利害,皆在东洋相争。然东洋乃东洋之东洋也。东洋人不可不有独决东洋问题之权利。美洲门罗主义,盖不外乎此意。”[23]195这显然是在向康有为劝说:亚洲地区应该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在亚洲主义或“亚洲式门罗主义”的名义下实现自主的管理。然而,此时日本人所说的亚洲主义却是以“日本盟主论”为特征,以“日本”为价值核心的东西。主张亚洲人自主管理亚洲,实际上等同于主张日本人自主管理亚洲。他们真正希望看到的,不过就是模仿美国在中南美地区的政策,在亚洲抵制列强的瓜分,推行“中国保全论”,并进而实现日本一国掌控的地域新秩序而已。
最后,是从支援中国革命的行动中再次获得了现实根据。东亚同文会,原本是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因此在是否支援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问题上,最初存在着东亚会派系和同文会派系的路线分歧。但在近卫等人的中介调停之下,两派在随后不久便走向了协调统一。他们通过观察革命党人的活动发现,这股反政府的力量虽然具有一定的组织规模,但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民间秘密团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过是在“沿袭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做法”而已,事实上并没有采取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行动,也缺乏对近代化的充分认识,所以坚信“有必要引导其走向文明的样态”[24]196。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通过对革命行动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比如曾任宋教仁日本顾问的北一辉,就曾在其著作中宣称:“革命的中国,其觉醒恰似日本的国学复兴,本身在于其国粹文学所激发的东洋精神之复活。且,促使其复活并鼓励其发出东洋魂之光辉的,乃是日本及日本的思想。”[25]15进而开始期待中国革命党能继续接受日本的“启发”与“指导”,建立亲日的政权,与日本组建“日中同盟”来实现亚洲主义的“理想”。显然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日本亚洲主义者面对中国时的优越感与自负感再次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并从“指导”中国近代化的企图之中再次找到了亚洲主义及其“日本盟主论”的现实依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日本的亚洲主义在展现出“日本盟主论”这一主流倾向之后,于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开始走向了概念的定型,“亚洲主义”这一用词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本质,却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张性、侵略性的发展形态而已,且两者之间通过“日本盟主论”这一桥梁最终实现了连接。这种“从日本民族主义扩展而来的亚洲主义”,其价值核心不是“亚洲”,而是“日本”。因此在随后的时局变动之中,它不仅无法避免歧途,反而在理论架构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尤其从东亚同文会的主张可以发现,此时期日本充当“盟主”的根据开始从以往的“学习西方之先驱”转向了“东西文明融合论”,同时通过对美国门罗主义的借鉴与模仿,对中国革命活动的观察与参与,他们的主张又获得了理论参考与现实根据。由此,亚洲主义在新形势之下继续保持了发展趋势,并沿着错误的道路渐行渐远。它无法成为超越各国民族主义的地区主义普遍原理,如果要凭借这种东西来抑制侵略主义的产生、“超克”日本的近代,必然会归于失败。
[1] [日]会泽正志斋.新论·迪彝篇[M].东京:岩波文库,1969.
[2] [日]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精读[M].东京:岩波书店,2000.
[3] [日]石津朋之,威廉姆森.日美战略思想史[M]. 东京:彩流社,2005.赵军.大亚洲主义与中国[M]. 东京:亚纪书房,1997:38.
[4]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3).
[5] [日]胜部真长,等.胜海舟全集18[M]. 东京:劲草书房,1972.
[6] [日]松本健一.大川周明[M]. 东京:岩波书店,2004.
[7] [日]下中邦彦.亚洲历史事典6[M]. 东京:平凡社,1960.
[8] [日]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M]. 东京:筑摩书房,1963.
[9] 赵景达.日本、朝鲜的亚洲主义矛盾[J].情况,2007(3).
[10] [日]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6[M]. 东京:朝鲜史研究会出版社,1969.
[11] [日]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8[M]. 东京:兴亚会出版社,1880.
[12] [日]无署名.兴亚会席上欢送何先生返回清国之演说[N].朝野新闻,1881-04-21.
[13] [日]古屋哲夫.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M]. 京都:绿荫书房,1996.
[14] [日]矢泽康祐.明治前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个表现形态[J].历史学研究,1960.
[15] [日]丸山真男.忠诚与反逆[M]. 东京:筑摩书房,1998.
[16] [日]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5[M].东京:岩波书店,1959.
[17] [日]社论.亚细亚经纶策[J].日本人,1890(45).
[18] [日]日本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中的亚洲主义[M]. 东京:岩波书店,1999.
[19] [日]社论.亚洲旨义为何[J].亚细亚,1892(32).
[20] [日]东京大学社科所编.二十世纪体系:构想与形成[M]. 东京:东大出版会,1998.
[21] [日]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别卷)[M]. 东京:鹿岛出版会,1969.
[22] [日]竹越与三郎.世界日本乎,亚洲日本乎[J].国民之友,1895.
[23] [日]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2[M].东京:鹿岛出版会,1968.
[24] [日]和田春树,等.岩波讲座 东亚近现代通史3[M]. 东京:岩波书店,2010.
[25] [日]北一辉.北一辉著作集2[M]. 东京:美铃书房,1959.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ual Formation of Asianism of Japan
LIU Fe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1400,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00,China)
With the word of Asia changed from “others-styled” to “self-styled”, the belonging consciousness as Asians were establishing in modern Japan. And these belonging consciousness as Asian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birth of Asianism. However, Asianism lacked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ubject cognition of Asia from that time. As the aggregation of various views, even its main features were not very clear. It could say that there was some “positive factors” in it, but finally the inclination of superiority feelings have gone mainstream instead of “positive factors”. In this situation, the word of “Asianism” and its concept have been formed finally in the first half of 1890s. It shows that Asianism was just a developing patterns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which was full of dilatancy and aggressivity. By this reason, Asianism can not avoid going down the wrong path in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later.
Japan;Asianism;the Theory of Leadership;Early Development;Concept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10
2016-04-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H02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5M581597)。
刘峰(1984-),男,湖南湘潭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K313.4
A
1001-6201(2016)04-0053-08
[责任编辑:赵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