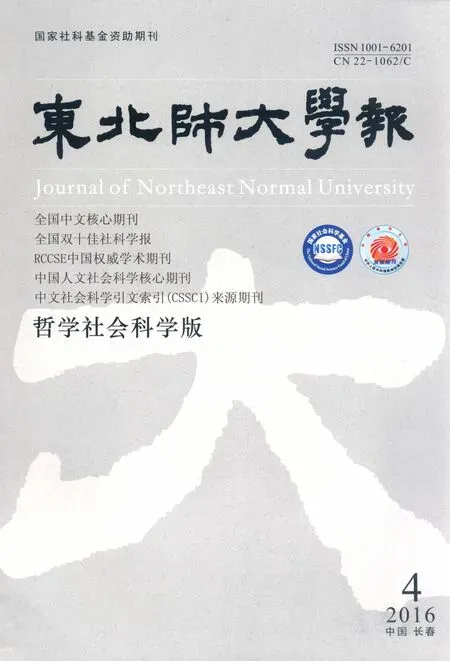海上威胁与德川幕府时期的虾夷地归属认知
陈 秀 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海上威胁与德川幕府时期的虾夷地归属认知
陈 秀 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由太平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所包围的岛屿,在1869年8月15日被正式命名为“北海道”之前,一直是“虾夷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东北亚地区,“虾夷地”处于海上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在近世,德川幕府却对这一要地经历了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再到间接管辖的过程,直到明治政府设立开拓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行政,才完成了作为日本整体国家组成部分的归属认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来自北部的海上威胁,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国家防卫上,近代日本为防守北海道建成以青森县陆奥市为中心的大凑海军基地。
海上威胁;德川幕府;虾夷地;北海道
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案》生效后,日本“根据需要”可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军队支援。而在此之前的3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宣称年内将在千岛群岛部署“舞会”与“棱堡”岸基导弹系统,为新一轮日俄之间抢占千岛群岛周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埋下了伏笔。在历史上,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北海道在内的土著居民属于阿依努族群,因而这些地区都被称为“虾夷地”。在东北亚地区,“虾夷地”处于海上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虽然虾夷地最终由德川幕府纳入整体国家版图,但在思想意识上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管理上,德川幕府对这一要地经历了间接到直接再到间接管辖的过程,直到明治政府设立开拓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行政,才完成了作为日本整体国家组成部分的归属意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来自北部的海上威胁,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此后在国家防卫上,近代日本在青森县创建了以陆奥为中心的大凑海军基地,增强了北海道的海上防卫力量。本文拟在回顾虾夷之乱的前提下,梳理德川幕府的虾夷地管辖及虾夷地探险活动,以便深度解读海上威胁与归属意识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德川中期之前的虾夷之乱
“虾夷地”即指今天的北海道、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即古代泛指虾夷(日本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称)居住的领地。关于“虾夷”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日本书纪》中,被《虾夷史料》传承下来。根据景行天皇27年2月12日条:“武内宿祢自东国还之奏言: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人,男女并椎结、皆纹身,为人勇悍,是总曰虾夷。另,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攻可取也。”[1]2当时的地方团体是“日高见国”,居民特点是骁勇善战、男女皆有纹身习俗。因人少,所以有被征服的可能性。但根据后来的史料,东国地区经常发生叛乱,而以虾夷人最甚。根据景行天皇40年7月16日条:“天皇诏群臣曰:今东国不安,暴神多起。亦虾夷悉叛,屡掠人民。……其东夷之地,村无长,邑无首,各贪封界,并相盗掠。……其东夷之中,虾夷最为强焉。”[1]2-3可见,当时虾夷的社会应该是处于原始部落阶段,部落间相互掳掠,且不断侵扰当时的大和民族。对此,中央的朝廷经常派兵前往镇压,形成你叛乱我镇压,你进攻我还击的民族关系,这和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关系相似。关于虾夷叛乱情况,据史料记载,自658年(齐明四年)至1795年(宽政七年),日本中央朝廷与虾夷的关系一直维持在叛乱与镇压的往复循环之中[2]33-36。
除了民族兄弟之间的纠葛外,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所谓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根据史料,朝廷在镇压虾夷叛乱上采取分化瓦解、诱降、欺诈虾夷首领以及杀戮等手段。其结果,随着“和人”(朝廷之所谓的大和民族)势力北进,因不堪忍受“和人”的横征暴敛和侵略,拼死抵抗而大伤元气后,阿伊努族走向衰退。叛乱被平定后,虾夷族陷入了奴隶的境地,接受“和人”的榨取和剥削,以至于迅速走上衰亡之路。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归并为种族歧视。另外,虾夷族的生存处境与衰亡史,恰好是对日本人所强调的“日本民族是慈悲深厚之民族,对被征服民族拥有慈父般的宽大胸怀”的强烈的否定。
就虾夷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大和国成立以后,其势力逐渐退缩到关东北部至新潟县北部一线以北地区。平安初期为平定虾夷叛乱,政府特派征夷大将军前往镇压,794年第一个担任此职的大伴弟麻吕和以后的坂上田村麻吕都是典型代表。镰仓时代末期,虾夷人逐渐退缩至津轻海峡以北。室町时代末期,大和民族的先头部队渡海进入北海道本岛的南部地区。1590年丰臣秀吉平定关东之后,招募东北地方的豪族乘机占领北海道南端的福山。当时的福山在秋田津轻的豪族安东氏*安东氏:日本中世纪统治本州日本海最北端陆奥国津轻至出羽国秋田郡的武家。自镰仓时代至南北朝时代,称“安藤氏”;室町时代中期以后称为“安东氏”。大约以15世纪中叶为界,之前称“安藤”,之后称“安东”。近世以来,改称“秋田氏”。明治维新后列入子爵。的控制下,丰臣秀吉占领此地后,受制于安东氏的代官蛎崎氏*蛎崎氏:战国时代以北海道为根据地的战国大名。江户时代改姓“松前氏”。本姓“源氏”,乃清和源氏的一支。蛎崎庆广统治时期,摆脱了安东氏的控制,逐渐独自发展势力。丰臣秀吉死后,他接近德川家康,1599年改名松前庆广。后来他的第五代孙于1719年正式升格为大名,成为领有1万石格的松前藩藩主。(蛎崎庆广)势力逐渐增强,并乘机摆脱安东氏的控制,上京表示归顺丰臣秀吉,从此获得整个岛屿的统治权,也就获得了虾夷岛主的称号。
然而,以1771年(明和八年)为分界,与之前日本中央政府与虾夷地之间的民族内部纷争不同,此后在民族纠纷中加入了来自北部的俄罗斯因素。同年夏,择捉岛的土著居民在得抚岛等地斩杀了几十个俄罗斯人。1789年发生了所谓的“宽政之乱”,即国后岛的虾夷人叛乱,斩杀了同岛及根室等地“和人”70多,后被松前藩兵镇压处决37人。1795年厚岸地区的虾夷人不服松前藩的施政前往择捉,后又奔赴得抚岛,以与俄人通商交易为生。可见,至少可以认为,在近代来临之前,虾夷地是东北亚地区互动的中转地。
二、德川幕府对虾夷地的间接管辖
虾夷地从东北亚地区的中转地走进德川幕府的管辖范围,是从幕府发出的委任书开始的。这个委任书清晰地表明了幕府角度的虾夷地归属意识。1604年松前藩藩主从德川家康那里得到了松前虾夷地的交易委任书,从此开启了德川幕府对虾夷地的间接管辖。委任状的内容如下:“一、自诸国出入松前者,不向志摩守报告而径直与夷人从事商卖活动,可视为不正(非法)之事。二、如有不向志摩守报告而私自渡海与夷人通商者,宜火速报告官府,且对夷人往来于何方也应多加留意。三、对夷人非分申悬者,宜断然加以制止。如有违背之辈,可处以严科者也。庆长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墨印松前志摩守殿”[3]。江户幕府凭借着家康授予松前志摩守的所谓“虾夷交易制度三章”,将幕府与虾夷地的关系建立起来。可见,双方通过交易委任的形式,间接地建立起了幕府与虾夷地的松散关系。
从这个所谓“虾夷地交易三原则”来看,德川家康将“虾夷地”视为附属于本国的蛮夷之地。因此才会有上述第二条后半强调的“对夷人往来于何方也应多加留意”的规定。根据松前藩最古的汉文献《新罗之记录》(松前藩于1643年编撰的松前藩历史的最早记录。记载了松前藩领有虾夷地统治权的过程同时,也披露了对阿伊努族镇压与屠戮的过程。成书于松前藩主公广末期。)记载,德川家康将松前藩与对马藩等同视之。1611(庆长十五)年1月15日,松前庆广拜见德川家康的时候,“时宗对马守家老柳川丰前守在座。家康公对柳川丰前守介绍道:彼乃松前伊豆守狄之千岛之屋形(贵人的尊称),北高丽与奥狄迫近边境之际,时常奏闻并处理者,今后应会面交流。(接着)转向庆广,此乃与高句丽毗邻之对马州家老柳川丰前守,从今以后以会晤交流为盼。”[4]49因此,在与家康会面之后,庆广拜访了丰前守的住所,赠与獭皮虎皮;次日柳川丰前守回访以数十两人参回敬。从这段文字的记载看,德川家康将松前藩与对马藩视为同类大名,同时将“狄之千岛”与“高丽国”置于相同地位。这实际反映了幕府尚未形成虾夷地乃日本固有部分的理念,而是将其置于距离日本最近的夷狄之地。
与德川幕府的虾夷地归属认知相似,江户中期的儒学家雨森芳洲*雨森芳洲(1668―1755):江户中期的儒学家。名俊良、东,别号橘窗,近江人,木下顺庵的门人。他精通汉语与朝鲜语,为对马藩效力接待朝鲜使节。著有《隣交始末物語》、《交隣須知》等外交名作。则表达了鄙视虾夷地的认知,并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论述:“大凡日本与外国相接之地,西有萨摩、长崎、对州(对马),东有松前。琉球乃萨州之属国,虾夷乃边僻小丑。来长崎之唐人,只要从事商卖者,上述各地并非忧患重重之地。只是一个朝鲜,乃与日本抗衡之国,如果对马武备不严,岂能成就折冲千里之功?”[5]190可见,雨森芳洲是将萨摩藩、长崎、对马以及松前藩同样看作日本与外国毗邻的边境之地,并没有将虾夷放在眼里。反倒强调的是在日本的外邻中,尤为恐惧者乃朝鲜,而对马藩正处于朝鲜与日本的缓冲地带,所以意在强调对马藩在抵御外来势力中的重要性。例如,在同书中,他指出“王代(天皇统治时期)时曾经在对马置重兵”,并将对马作为“藩屏第一要地”[5]190。
从上述的“虾夷地交易三原则”看,还可以发现“和人”与虾夷的商业往来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没有松前藩的应允是万万不可的。松前藩的权力是通过与德川政府达成的“虾夷地交易三原则”而获得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弄清松前藩与虾夷地之间的实质关系成为判断幕府与虾夷地关系的关键所在。
1512至1536年以虾夷侵扰边境与蛎崎氏出兵镇压虾夷为主。1551年,蛎崎季广曾经和东西虾夷之间缔结了《夷狄商船往来之法度》,分派“夷役(即向虾夷人分摊商船税)”。这样,蛎崎氏与虾夷的关系又染上了一层商贸关系。1593年1月2日,蛎崎庆广在名古屋拜见了丰臣秀吉。1月6日,他从丰臣秀吉那里得到了“国政朱印状”。其内容:“从各国来松前、在没有志摩守许可而自由往来于狄之岛中之商卖者,可行斩罪;与志摩守之命令有背、而向夷人煽动无理之事者,可行斩罪;有背诸法度者可行斩罪。”[4]43这一款内容成为前文提到的德川家康给蛎崎庆广的“黑印状”的主体内容。
这样,通过来自丰臣秀吉的“朱印状”和来自德川家康的“黑印状”,蛎崎庆广便获得了经营虾夷地的法律依据。而且,赋予虾夷地与松前藩以领地与所领关系的实质内涵。
1617(元和三)年12月16日,松前庆广将朱印赐给嫡孙公广,同时一并将1604年德川家康下赐的“虾夷地交易三原则”作为训诫教给了他,并嘱咐他不得违背上述事项。1641(宽永十八)年12月4日,“松前领主松前志摩守公广让长子主殿氏广袭封遗领”[6]107之记载。根据此条,松前氏的地位已经明确地被确定为“松前领主”了。公广和氏广的交接完成后,“松前领主”的地位得以确定。1658(庆安元)年10月9日,松前弁之助氏广将遗领传给其子松前高广。1665(宽文五)年11月6日,“松前志摩守高广命其子兵库矩广继承家业、并像父亲那样镇护彼地。”[6]108可见,在松前氏与虾夷地的关系上,仍然是以镇护为主的。
1721(享保六)年7月11日,史料有“虾夷松前领主松前志摩守矩广将遗领袭封给养子传吉邦广”、“同年10月15日,松前传吉邦广叙爵位称志摩守,始就封”[6]112之记载。在这两条文献记录中,“松前领主”被冠以“虾夷松前领主”之称。1743(宽保三)年8月16日,“松前志摩守邦广将遗领松前虾夷一円让与其子若狭守资广”[6]113。1765(明和二)年10月11日,“松前若狭守资广将家业传给其子外记道广。令其对松前虾夷之赏罚用心”[6]114。可见,从对虾夷地的蔑视,到公平地“赏罚分明”的用心看来,意识发生了转变,即发生了自我与他我思想史意义上的转换。
1792(宽政四)年10月28日,“陆奥国松前领主松前志摩守道广因病,其子勇之助章广袭封。”[6]1151802(享和二)年7月24日,“松前若狭守章广,被委任处理将来虾夷地之事务。东地(东虾夷,笔者注)今后归为官用地;西地(西虾夷,笔者注)仍沿用旧制(即由松前藩管理)。”[6]116原来松前领有的虾夷地,在宽政年间迎来了所谓幕领时期,即“第一次幕领虾夷地时期”。这条信息中的“东地”实际在1799(宽政十一)年就为幕府直接管辖了,只不过是又做了一次强调而已。
三、第一次幕领时期
从松前领主的继位与传承来看,松前藩主与虾夷人乃领主与领民之间的关系。在幕府直接介入虾夷地管理事务之前,松前藩一直承担着对虾夷叛乱进行镇压与调和的任务。幕府和这几个地区的直接关联发生在1799年以后,即同年德川幕府直辖东虾夷地区;1807年幕府直辖西虾夷地区,并着手经营库页岛南部。1809年将库页岛南部改称为“北虾夷地”。自1799年即宽政11年起,开始了幕府直接经营虾夷地的第一次幕领时期,该期结束于1821年12月。
(一)幕府直接管辖虾夷地的背景
就前文的松前领主的交替与对待虾夷的政策观之,从名称上没有出现“虾夷”字样,到明确地使用“虾夷松前领主”的称呼,再到“对松前虾夷之赏罚用心”的政策转换,以前的那种单纯地将“虾夷”视为“外夷”或“夷狄”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至少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种族了。应该说,这有着十分重大的思想史意义。
带来上述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北部俄罗斯的海上威胁和法国人的探险活动。自18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即以俄国人为首的欧洲人频繁地出现在虾夷地周边,直接刺激了幕府官僚的边境神经。其中,法国人拉普鲁斯沿日本海北上,抵达桦太海岸,穿过宗谷海峡,出现在鄂霍次克海。因此,宗谷海峡的名字在今天的欧洲地图上用的是“拉普鲁斯海峡”这一称呼。俄法等国人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思想家的注意,他们提出了“虾夷地开拓论”。这种开拓论虽然起初没有得到幕府的重视,但随着俄国人继续南下,由其引发的北方探险活动,却客观上迫使幕府作了意识上的调整。
(二)“虾夷地开拓论”引发的北方探险
1781—1783年,江户中期的经世家工藤平助完成了著作《赤虾夷风说考》,该书告之俄国南下,力陈北方开发的紧迫性,并提出了调查与经营虾夷的具体方策。此外,俄国势力的侵扰,造成北方边境之地告急,工藤平助、本多利明、林子平等认为千岛、桦太之地的事情一日也不可懈怠,并论述北方警备的必要性。1784(天明四)年幕府为《赤虾夷风说考》所动,遂于1785年春派遣幕吏赴北方调查。当时本多利明因病没能同行,而是让自己的学生最上德内代表自己前往。此即天明5至6年幕府第一次介入的虾夷地调查事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田沼时代的虾夷地调查。由于田沼在政治上的失脚,因此关于其虾夷地调查的史料记载不甚详细。此后在自1785—1808年的20多年间,最上德内完成了9次探险之旅。1785年最上德内随幕吏同行,到达今天的北海道、南千岛、桦太等地进行调查,写下了《虾夷草纸》。他将半生的时间用在了虾夷地探险与调查上,为当时的经世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受惠于他的见识的人中,有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兰学家;有本多利明、近藤重蔵等经世学家;还对间宫林蔵产生了重大影响。”[7]32
随着北方探险活动的展开,幕府对虾夷的认识有所加深,迫近虾夷地的意欲高涨。幕府于1791(宽政三)年开始关注所谓的“御救交易”。但是,最为强烈刺激幕府统治神经的是1792(宽政四)年,俄国军官拉格斯曼根室来航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和1853(嘉永六)年美国海军上将培理来航的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思想史意义。如果说培理来航催促了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萌生,那么拉格斯曼来航则敦促了幕府自我同一性认识的生成。这种意识生成的直接表现就是1799年幕府对虾夷地的直接经营。即1799年,幕府将虾夷地的东半部分从松前藩手中收回,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旋即在虾夷地设置“开发挂”,松平忠明等70余人前往赴任。1802(享和二)年2月23日,设置了箱馆奉行[8]133-167。1807(文化四)年,收回西虾夷地,设置了松前奉行。这样,虾夷地全部归幕府直辖。
(三)第一次幕领时期结束的原因
幕府的第一次虾夷地直辖期结束于1821年的12月。关于结束的原因,学者们各执己见。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1821(文政四)年日俄两国的关系平等化,幕府便将虾夷全地返给松前藩”[7]35进行管理。还有学者从第一次虾夷地幕领时期的经营收支状况入手,认为幕府放弃直辖的原因并不简单。首先,是松前藩想要继续管辖虾夷地,对当时幕府的权力者水野忠成进行重金贿赂的结果。其次,格罗宁事件*格罗宁(1776—1831年)事件:1811年俄国海军在国后岛登陆,格罗宁当时担任迪亚娜号的船长,被监禁在箱馆、松前。1812年在高田屋嘉兵卫的斡旋下,格罗宁被释放。过后,北方的边境危机一时得以解决。第三,幕府认为继续进行虾夷地经营“不经济”[9]42。
这一时期,幕府的财政收支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1813年起幕府被迫从东虾夷地开始,在具体模式上逐渐采取并推广了“场所请负制度”。“场所”就是指“虾夷地区”,“请负”即指承包。在虾夷地区,“场所请负制度”是在享保、元文时期成立起来的。追根溯源,这种制度的前身应该是由松前氏确立起的“商场知行制”,成立于宽永(1624—1643)年间[10]84。松前氏将虾夷地分割后分给家臣,然后家臣们亲自运载日本制品至“商场”和阿伊努进行交易,再将阿伊努的产品在松前卖给日本商人从而获利。根据阿伊努共同体(随着与和人、大陆人交易往来,以山寨为中心的阿伊努集合体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生活的渔猎圈,设置特定的“商场”,每年在商场进行一两次交易。有时日本商人也乘船前往阿伊努的聚集地进行交易。从制度或体制上讲,这是“北海道独特的知行形态”[11]253。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商场知行制”逐渐为“场所请负制度”所取代。享保(1716—1736)年间,“场所请负制度”在虾夷地区普及开来。当时的松前藩从直接经营收手,他们演变为“场所”的所有权者,而“场所”的使用权则归承包商所有。二者之间的商业利益在于,商人们要向松前藩交纳“运上金(杂税的一种,向商人、工人、渔猎者、运送业者征收的)”,而商人们为了在上缴“运上金”后还有利可图,必须提高效率,因此不得不强化阿伊努的劳动强度,强化了对阿伊努人的剥削。从1813年幕府在东虾夷实施“场所请负制度”起,大大提高了“运上金”的额度。结果相继出现了“运上金”的滞纳者。这样,1814年松前奉行所制定了减免20%“运上金”的对策,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在松前藩领时期,东虾夷地的“运上金”额度为金3 289两,幕府直领后7年平均额度为金9 293两[9]43。承包商交不起高额的运上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关于幕府直领虾夷地的收支状况,自1799(宽政十一)年至1822(文政五)年,幕府的总支出为1 143 944两,从虾夷地收入为1 275 340两[9]52,表面看来是赢利的,但是按照直领的时间推移,实际幕府的财政状况已严重恶化。1810年以将“择捉场所”承包给高田屋为发端,1813年“场所请负制度”全面复活。承包商在承担“场所经营管理”的同时,还要承担邮递事务和管理虾夷事务。1815年,幕府除了在箱馆、松前继续设置守备军队外,停止了在其他地区的驻兵。1821年,幕府将虾夷地返还给松前藩。1822年松前藩复领虾夷地之际,幕府曾给其下发了如下政令:“不得遗失于彼地实施的主法(幕府直辖时期的施政方针及虾夷抚育计划);要严守异国境之要害”[12]618。与此同时,松前奉行所还通过土著役人以酒款待虾夷人,并对其提出了“抚育虾夷与安心经营”的“申渡书”(劝告文书)。
幕府结束直接管辖虾夷地的原因应该说是幕府的管理经验不足、资金的继续投入出现困难以及幕府式的“场所请负制”本身的矛盾造成的。因此,1822—1855年的33年,在北海道的历史上被称为“松前复领时期”。但自1855年开始,幕府再次直接插手虾夷事务,即开始了所谓的“幕府第二次直辖期”。
四、第二次幕府直辖期
在幕府将虾夷地返还给松前藩之际,德川齐昭曾认为以一个小藩的力量难以经营广大的虾夷地,并指出这是幕府的失策。这种矛盾随着1853年俄国使节普提雅廷来朝并要求划定边界与进行友好通商,以及俄军进占北虾夷地的久春古丹的时候凸显出来。可以认为,对于幕府而言,北方危机及其防备成为必须解决的一大外交问题。因此,安政元年(1854)3月,“再直辖虾夷地”的论调高涨起来,幕府也因此派堀利熙、村垣范正等人前往该地调查。1854年9月二人提交的调查报告强调指出以下几点:其一,除了福山城的防御设备相对完整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防备都极为薄弱;其二,分析了虾夷地的地理概况,自然资源的情况,并强调沿海的渔业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其三,松前氏仍然采用“场所请负制度”进行管辖,“承包人”再将其转包给“支配人(管理者)”,为了在上缴“运上金”后还能有盈利,“支配人”役使虾夷的手段极为残酷,因此虾夷人有希望幕府直辖的愿望;其四,外国人出没虾夷地,以恩惠对虾夷进行利诱,虾夷有归顺外人的危险;其五,幕府直接经营,向虾夷地进行移民,实行屯田农兵制度,开发新田,经营物产并非难事,其经费可用沿海的渔业获利来补充;其六,200余年的太平盛世,结果士气流于软弱疲敝,虾夷地则恰好是锻炼身心的良好场地,士兵可经历风霜之苦,掌握航海、射击技术[12]717-18。这样,幕府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的前提下,1855年2月23日到达松前藩,下令将东部木古内村以东、西部乙部村以北、东西虾夷地的岛屿归箱馆奉行管辖,松前藩地域除外。
有关虾夷地第二次幕府直辖政策,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期的1854年伴随着开港而来的箱馆地域的直辖政策期;1855年实施的除松前地域之外的虾夷地全域的直辖政策期;1859年以后至明治维新前的东北六藩(秋田、仙台、会津、庄内、津轻、南部等)的分割分领时期[13]25。但是根据当时幕府首席老中及大老的虾夷地对策来看,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854至1857年的阿部正弘(1819—1857年)在任的积极政策时期与1857年以后自大老井伊直弼(1815—1860年)开始的消极政策时期。
阿部正弘是一个聪明稳健的政治家,在虾夷地经营问题上,他广泛征求意见,曾聆听德川齐昭和堀利熙的见解,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855年3月29日,在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给老中的上书中,强调“在与俄国粗定国境的基础上,虾夷地、择捉、国后等三所要地,应该派遣身体强健、擅武勇、深谋远虑者”[12]728-29前往担任警备任务。对这种主张,堀利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以箱馆为根据地,派役人前往东西虾夷地在勤工作,命奥羽地区的各大藩担任要地之警备任务。在开拓上,他主张从南方开始逐渐向北方推移。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老中阿部正弘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有将奥羽及虾夷地连接起来思考的意识存在。即不是因虾夷地出现边境危机,就凭着一时对策对其着重加以解决,而是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作为相互连接的一个整体由本州的东北部开始自南向北逐渐开发。应对外来势力应该说是幕府第二次直辖虾夷地的目的所在,但是如何将其纳入一个合理的范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不同开发论者们的主要分歧所在。仅就上述的两种开拓论而言,德川齐昭更倾向于为解决边境危机提出解决方策;而堀利熙的意见则重在从内部一体化的视角出发,思考的重点在如何将解决边境危机与内政建设结合起来。很显然,堀利熙的意见应该是最符合幕府需要的,被采纳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时期所谓的积极政策在1857年6月随着老中阿部正弘的病没而告终。1858年4月,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后,因国事繁忙,以他为首的幕僚们对虾夷地的关心逐渐有所回落,故1857年以后的虾夷地政策被称为消极政策期。尤其是1859年实行的虾夷地分割分领政策,将虾夷地的警备任务分派给了东北六藩。从国家史的意义上思考,该政策延续了堀利熙提出的在奥羽地方担任警备的建议。正如金森正也所指出的那样,“安政六年(1859),幕府的政策转换为将虾夷地分派给东北六藩(仙台、庄内、会津、秋田、南部、津轻)以及松前藩。这意味着抱有来自俄国方面危机感的幕府,向整个虾夷地区全面导入幕藩制国家军事力量;同时也宣告了同地乃国家内的一部分。”[14]54-55但对于其他六藩而言,任务加重,一时将这种“强制性的虾夷地支配”看作是一次大的打击[15]107。然而,从强化国家意识的角度来讲,无论是积极的前期政策也好,还是后期的分割分领政策也罢,都具有进步的意义。这是不同于第一次幕领虾夷地政策的主要所在,即不是为单纯地应付外来危机而制定政策,而是在国家整体及内部一体化的思考中选择最佳道路。也正是在与俄国、英国冲突的经验基础上,近代的日本国家意识、国境意识以及日本国家的自我认同意识才得到加强的[16]66。
在虾夷地归属意识上,1869年5月21日新政府将诸侯及高级官吏等召集到御前接受了天皇的“敕问”。这一“敕问”涉及的“虾夷地”开拓事宜,清晰地表达了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关于虾夷地意识的变迁。根据《开拓使日志明治二年第一号》记载,“敕问”内容如下:“虾夷地乃皇国北门,北接山丹满洲。虽经界粗定,然北部中外杂居之地,至今官吏役使土人极为严苛,外人却多施爱恤之心,土人往往怨恨我邦之人。……一旦外人以拯救民苦为名加以煽动,其祸必及箱馆、松前。……方今急务,于平定箱馆之上,速施开拓教导之法,使之成为人民繁殖之域。”[17]1-2其中,虾夷地已经不再是附属性的蛮夷之地了,转而变为“皇国北门”了。1869年8月15日,明治政府改松前虾夷地为“北海道”,废除“和人”与“虾夷”的区别,“虾夷地”的公称从此消失。1881年明治天皇巡幸北海道之际在青森县陆奥市大凑登陆视察民情。1886年1月26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北海道厅设置布告书:“第一,废除函馆、札幌和根室三县管理局、改设北海道厅管理全道事宜;第二,北海道道厅设在札幌,将分厅设在函馆、根室。”[18]7至此,在行政区划上,虾夷地“国内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综上所述,从虾夷地到北海道的名称演变,是日本的“华夷变态”[19]1-6,它佐证了中央政府的本国边境地区归属意识的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两次来自北部的海上威胁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是1792年的根室来航;其二是1853年俄国使节来朝以及俄军进占北虾夷地。从哲学角度观之,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历史的真实往往具有很多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又不在这一真理的辐射范围之内。仅就本文探讨的幕府为什么一改先前的间接管辖为直接管理虾夷地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是说,来自北方的海上威胁成为催促幕府采取直接管理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当一个民族面临着外部压力时,其民族情绪便会高涨,国家意识也就会明显表露出来,即民族危机感的强弱与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正比例关系。
不仅如此,一旦虾夷地被纳入近代国家版图,政府便在近代国防上加以部署。为了在北海道选设海军基地,明治政府曾做了种种尝试。1899年政府想在室兰设立镇守府,但是因俄国迫近之际津轻海峡的重要性以及室兰难以防守的现实,遂决定将镇守府设在青森县的大凑。1902年在日俄战争开战前,政府在大凑布置了水雷团,成为防御北部来袭的重要海军基地。1905年12月,明治政府在大凑开设军港,在内部铺设铁路,设立邮局、银行及兴业公司,驻扎宪兵队等,由此发展为大凑町[20]69。直到战败前,由大凑镇守府改名的大凑警备府发挥了海军基地的作用。虽然战败后,大凑警备府一度被废弃,但1952年以后随着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成立了海上自卫队大凑地方队,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今天的大凑海军基地[21]137。
[1] 東北大学東北文化研究会編. 蝦夷史料[M].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32年.
[2] 代田茂樹編集兼発行.蝦夷往来第七号[M].札幌:尚古堂昭和七年三月二十日発行.
[3] [日]高倉新一郎. 日本歴史新書蝦夷地[M].東京:至文堂,昭和34年.
[4] 北海道編集.新北海道史第七巻史料1新羅之記録下巻[M]. 札幌:新北海道史印刷出版共同企業体,1969.
[5] [日]中田易直編.近世対外関係史論[M].東京:有信堂高文社,1979.
[6] [日]海保嶺夫編.幕政史料と蝦夷地[M].東京:みやま書房,昭和55年.
[7] [日]丸山国雄.最上徳内と蝦夷地探検[J].収入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編集.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報告通号7,1956.
[8] [日]門松秀樹.蝦夷地統治と箱館奉行所[J].収入慶応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内法学政治学論究刊行会編集発行.法学政治学論究66号,2005.
[9] [日]寺崎仁樹.第一次蝦夷地幕領政策の破綻——経営収支の検討を中心に[A].日本歴史学会編集.日本歴史第712号[C]. 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9月号.
[10] [日]海保嶺夫. 幕藩制国家と北海道[M].東京:三一書房,1978.
[11] [日]海保嶺夫. 近世蝦夷地成立史の研究[M].東京:三一書房,1984.
[12] [日]新北海道史編纂所.新北海道史第二巻通説一[M]. 札幌:新北海道史印刷出版共同企業体,昭和45年.
[13] [日]麓慎一.幕末における蝦夷地政策と樺太問題——1859年(安政6)年の分割分領政策を中心に[A].日本史研究会編集.日本史研究通号371号[C].京都:日本史研究会発行,1993.
[14] [日]金森正也.安政期の幕府蝦夷地政策と秋田藩[A].収入日本歴史学会編集.日本歴史第519号[C].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年8月号.
[15] [日]海保嶺夫.近世の北海道[M].東京:教育社,1979.
[16] 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17] 开拓使日志[Z].明治二已巳年第一号自五月至八月,1-2.
[18] 北海道厅.新撰北海道史第四卷通説三[M].東京:三秀舍,1937.
[19] 周颂伦.华夷变态三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20] [日]大畑厳編集.各科郷土教育資料[M].青森:大湊尋常高等小学校,1933.
[21] 陈秀武.岸信介执政时期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J].日本学刊,2016(2).
The Maritime Threats and the Attribution Cognition of“Ezochi” in the Period of Tokugawa Shogunate
CHEN Xiu-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China)
Before officially named “Hokkaido” on August 15th,1869, the islands surrounded by Pacific Ocean, Sea of Japan, Sea of Okhotsk, Soya-Kaikyo and Tsugaru Strait have been the main parts of Ezochi. In Northeast Asia, Ezochi, whose geographic posi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s the maritime traffic artery. However, in modern times, this region has experienced the indirect jurisdiction to the direct jurisdiction and to indirect jurisdiction again by Tokugawa Shogunate. Until the Meiji Government set up the Developing History which implemented developing administration, the attribution cognition of Japan as an entire na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During this changing process, it has no doubt that the maritime threats from the northern area played a role of drive and promotion. For national defense, for defence of Hokkaido,Ominato naval base centered by Mutu has been built in Aomori in modern times.
Maritime Threats; Tokugawa Shogunate; Ezochi; Hokkaido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09
日本的制海权与自我认知研究
2016-04-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S011)。
陈秀武(1970-),男,吉林农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K313.36
A
1001-6201(2016)04-0045-008
[责任编辑:赵红]
[主持人语] 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所谓的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获取与抢占海上通道是其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手段之一,也是融入并创新现代世界体系的举措,客观上起到了东连亚太经济圈的作用。以日本为主探讨东北亚地域的制海权与东亚范畴内的自我认知及其思潮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据此,本专栏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海上帝国”建设研究》(15BSS011)为平台,组织了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海洋大学的四位学者分别就海上威胁与日本虾夷地的归属认知、日本亚洲主义的概念及其早期发展、象征天皇制的成立及其国民统合机能以及“国家主义”的话语制造等日本文明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展开了探讨。在制海权问题上,近世中后期的海上威胁,促使德川幕府及相关人士对海洋进行了深入思考。获取制海权、将海域周边的“蛮夷”之地内化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完成虾夷地的归属认知,并在近代发展成日本的五大海军基地之一等,都体现出日本人对掌控制海权的意识有所加强。在自我认知上,近代以来随着“亚洲”用语从“他称”向“自称”的转变,“亚洲主义”一词被赋予了“日本盟主论”的实质内涵。也正是在这种认知理念的支撑下,日本国家走向了战争并以陆海军惨败而告终。在战败后寻找民族的归属感上,美国占领下的象征天皇制所发挥的国民统合机能成为战后日本的出发点。2012年以来,日本不断将钓鱼岛问题右倾化,其原因一方面是掌控制海权的野心在作祟,另一方面有制造“国家主义”话语以围堵中国的政治需求。客观地再现近世以来日本海权要求与舆论准备,可为我国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