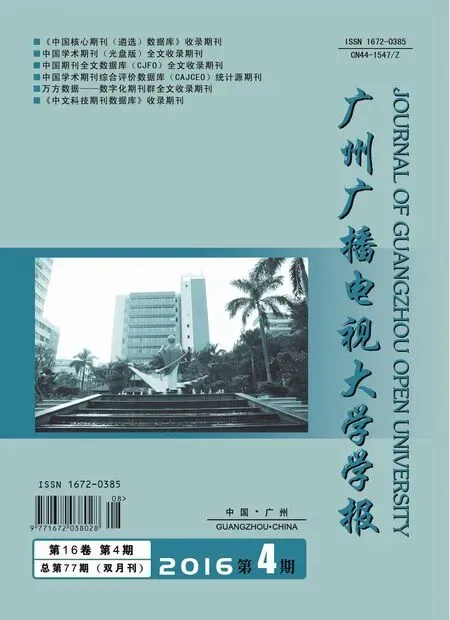论危险犯中的危险及其判断
王玉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论危险犯中的危险及其判断
王玉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危险犯的核心概念“危险”应当是一种行为的危险,但这种行为的危险本质属性为结果。在此意义上,“危险”是指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的某种危险结果,并与未遂犯这一代表实害犯中的危险有所不同。危险判断应当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以“科学标准说与一般人标准说相结合”为基准,以不被允许的危险作为判断标准,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判断应当区别对待,并且但书对抽象危险的认定具有指导意义。
危险;危险犯;未遂犯;危险判断
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加,危险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刑事立法不断增设新的危险犯,譬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刑九修正案》又增设恐怖类危险犯等。刑法上危险犯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且相关案件也是逐年增多,但与之相对我国对于危险犯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作为危险犯概念的基础,研究“危险”一词的含义,对危险犯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基础性理论的含义及其与相关用语的辨析、判断标准等理论界皆有争议,但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危险犯的危险确有必要。
一、危险犯中危险含义
近代刑法存在刑事古典学派与实证学派之争,二者在方法论、人性论及评价对象等基础理论上均有所不同。刑事古典学派坚持客观主义,以行为为中心,重视行为客观结果的危害性。而实证学派主张主观主义,以行为人为中心,重视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理念的不同导致刑法许多具体问题上都出现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危险犯之危险含义即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危险”是指行为人自身危险,即行为人通过外部行为所表现出的反社会的性格、人格、动机等行为人自身的危险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具有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可能性,如果没有实害或实害的危险,则就没有犯罪。[1]
“行为危险性说”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主张,同时也是客观主义刑法的见解,其以报应及一般预防的刑法目的为基础,认为刑法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在此种意义上,只有处罚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的危害的行为才是正当的。与之相对应,“行为人危险性说”是实证学派及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主张,其建立在特殊预防刑罚目的上,认为行为与结果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征表,犯罪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反映,应当处罚的是行为人本身而不是行为,只有消弭犯罪人的危险人格,才能有效防卫社会。
“人身危险性说”及“行为危险说”并无绝对对错之分,只是占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在当今注重人权保护的社会中,思想犯及迷信犯不处罚已经为各国所认同,而根据“人身危险性说”,行为人主观上想要实施犯罪,即表明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具有人身危险性,当然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这明显与现代刑法精
但“行为危险说”内部就危险的本质属性有分歧,主张行为属性说的学者认为危险的本质应当为其行为自身所包含的危险,而主张结果属性说的学者认为危险的本质在于行为法益侵害所导致的危险结果,只有危险行为,但并没有危险结果,及不就有侵害法益,则不能予以定罪。这种分歧的产生源于对违法性中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对立;第三种观点“行为属性危险与结果属性危险分别说”认为危险犯分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二者具有不同的构成标准,不可同一而论,具体危险犯的危险属于结果属性危险,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属于行为属性的危险。[2]
行为无价值论主张,违法的实质在于行为本身的恶,违法是对与行为人有关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违法性根据在于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其以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伦理秩序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标准。法益侵害也只有置于人的违法行为时才有意义。[3]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刑法目的在于法益保护,违法性实质在于法益侵害及其危险,对于没有造成法益侵害及危险的行为,即使该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秩序,也不可以对其进行处罚。对于结果的含义,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此处的“结果”不仅包括造成现实法益侵害,还包括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危险。[4]笔者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一)刑法的目的虽然包括维护社会伦理,规范法秩序,但法益保护的价值位阶高于秩序的维护,二者产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法益;
(二)在不能犯问题上,结果无价值的结论更为合理。行为人误将白糖当做毒药进行杀人,依行为无价值论,行为人主观具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也实施了相关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认识错误,才没有导致结果发生,其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性并对其进行相应处罚;依结果无价值论,以事后判断来看,行为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法益危险的可能性,没有法益侵害性则行为就不是刑法上的实行行为,不能对其进行处罚。
因此,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危险犯中危险的本质在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具有结果的属性。危险犯中行为产生的对法益侵害产生威胁这一结果才是对其进行处罚的根据,行为本身是客观中立的,行为只有通过作用于不同的对象时才能对其做出有关价值判断。危险犯分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危险相应有抽象危险与具体危险之分,但笔者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判断标准有所差异而已,判断标准不同并不能导致性质发生改变,因此第三种观点并不能提出合理的根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危险犯中“危险”是指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某种危害结果。
二、“危险”与“危险状态”、“危险结果”概念辨析
在危险犯理论中,“危险”、“危险状态”及“危险结果”三者概念极其容易发生混淆,有的学者甚至将它们作为同一含义来理解。有学者认为,“危险”是行为自身所包含的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倾向,危险状态是实害结果发生前的行为侵害法益的表现形态,而危险结果是一种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某种现实危害。[5]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在危险犯中“危险”表示一种结果,即行为侵害法益的可能性,是危险犯处罚的可罚性根据,虽然其本质在于结果的属性,但具体判断时,也包括对危险行为危险性的认定。危险状态更加倾向于一种过程,是行为侵害法益危险开始到危险结果发生的持续期间。而危险结果则是一种时间节点下的客观危害,表现为一静止形态。三者的区分意义在于危险犯概念的确定。
在危险犯概念界定中,有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指以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6]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的标志的犯罪[7]。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发生法益侵害之危险已足为既遂标志的犯罪。[8]“危险”与“危险状态”、“危险结果”等不同的用语揭示了理论上的分歧。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危险”这一提法更为恰当。首先,危险状态具有过程持续性性质,而既遂是指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在某一节点发生,犯罪即告成立,具有形态终止性特点,一般以危害结果发生作为标志,危险状态表述明显不当;其次,概念应当简洁精炼,不需要太过具体,“危险”一词本身就包含有危险结果的含义,其相对于危险结果而言在语言上具有简练性。况且,“危险”包含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两方面内容,虽然危险的本质属性是结果,但对行为本身危险判断也是必要的,即使有危险结果,但没有危险行为,则依然不能对行为人归责。最后,“危险”是危险犯的核心概念,以“危险已足为既遂标志”的表达方式更能显示出危险犯的危险特性,用语更贴切。
三、危险犯中危险与未遂犯危险区分
关于危险犯与未遂犯的关系,刑法理论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未遂犯是危险犯,只是对于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有争议,这也是日本刑法的通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未遂犯不是危险犯,这是我国刑法的通说。[9]危险犯危险与未遂犯危险区分对于未遂犯是否属于危险犯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未遂犯中危险是指构成要件实现可能性,即犯罪实害结果发生具有可能性,不是对法益的直接危险,而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侵害法益导致危险结果的发生,是直接作用于法益的。
其次,未遂犯的危险判断是刑法处罚前置化的体现,抽象有关客观事实与犯罪类型,判断既遂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其得以处罚的实质违法根据。而危险犯的危险是根据客观情况,判断实际侵害法益发生的可能性,是对构成要件实现与否的判断。[10]
再次,未遂犯中的危险可能性是一种抽象可能性,而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未遂犯是犯罪既遂结果未发生,但行为本身具有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是一种事后做出的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抽象危险可能性。而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实害结果虽未发生,但危险结果已然发生,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发生,实害结果必然发生。[11]
综上,危险犯中危险具有结果属性,而未遂犯的危险具有行为属性,前者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后者是违法性判断根据。再者日本刑法与我国刑法立法规定模式不同也可能为导致争议出现的原因。日本刑法分则中的罪名采用既遂的模式规定的,并且对于未遂的处罚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没有做出未遂处罚规定的,不能进行刑法处罚。而我国刑法分则罪名的规定不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是以犯罪成立为标准设立的。例如,我国故意杀人罪规定,故意杀人的,处……。从字面上看并不能得出行为人已经致人死亡的结果,其是一种行为模式,即故意杀人行为,危害结果发生与否只影响行为的犯罪形态,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处于各个形态的处罚则依据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因此,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规定并不是以既遂为标志的,存在未遂形态,则危险犯的未遂犯具有成立的可能性。
四、危险犯之危险判断
“危险”是指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是一种危险结果的判断,其有无决定着危险犯存在与否。鉴于刑法中关于不能犯危险判断的理论的成熟,众多学者在讨论危险犯危险性时多以不能犯判断相关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犯判断学说可直接用于判断具体危险结果。[12]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犯学说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不能直接用于危险状态的判断,但不能犯学说给危险判断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价值。[13]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应当在充分吸纳不能犯学说的精华上充分考虑危险犯的特点进行有益借鉴。
(一)危险判断事实基础及时间节点
危险判断中一直有主观危险说与客观危险说两种不同的学说。主观危险说应当以危险发生之前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为根据,并以行为时点为进行危险性判断,即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了危险结果。客观为危险说主张以事后的立场,以行为客观性质为标准,判断有无危险的发生。[14]由此可知,主观说与客观说主要存在两点争议:一为危险判断的时间点是事前还是事后;二为危险判断的事实基础是行为人自身所认识到事实,还是事后据以查明的事实。
首先,对于危险判断事实根据,笔者认为应当以事后查明的事实为主,行为人主观认知内容为辅。理由如下:
1.危险性判断本身就具有客观属性,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无疑不妥,并且危险结果的出现不以行为人认识与否而有所改变;
2.行为人认识事实具有不可靠性,行为人完全可能对事物存在错误的认识,与客观事实不符,及行为人为了逃脱罪责有可能进行虚假陈述,导致认定事实的不准确,而有无证据进行相关反证予以推翻,再者行为人完全可能对事物存在错误的认识,以行为人认识为标准只能是理想状态,无可操作性;
3.事后判断所认定的事实均为客观性事实,以此进行判断结论具有相对可靠性,但纯粹的事后危险判断与行为本身性质不一致,推定的危险并不能完全等于实际的危险,可能造成与事实不符。因此单纯的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事实或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为基础都不妥当,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主,并辅之以行为人主观陈述,对两者进行相互验证进而综合判断事实情况。
其次,对于危险判断时间节点,主要为事前判断(即站在行为时立场)与事后判断(即站在行为后的立场)之分歧。笔者认为纯粹的事前判断与完全的事后判断都为不妥,理由如下:
1.刑法处罚的是行为,而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事后可能会发生某种改变,危险的紧迫性只有在当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准确判断,故原则上应当以行为时来判断危险的存在,事后判断则可能出现判断失误。行为人乙往甲的茶杯里放进毒药企图杀人,但甲并没有喝茶,事后判断的话,甲没有中毒死亡,实害结果没有发生,危险性并没有那么强烈,但站在行为时的立场来看,甲具有随时喝茶中毒的可能性,危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从而认定乙的行为具有致危险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2.事前判断仅仅在于查明行为自身具有导致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能得出行为已经导致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而真正决定行为犯罪与否的恰是危险结果是否已经出现。因此,司法中应当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相结合,分步骤进行判断,第一步进行事前判断,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危险属性;第二部在行为具有危险的基础上进行事后判断,以确定行为是否已经导致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譬如,行为人乙在道路上正常驾驶,甲突然横穿道路,乙及时刹车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在案件中,乙的驾驶行为已经导致了甲可能死亡的危险结果,但并不能以此认定乙构成犯罪,因为乙的正常驾驶行为本身,并不能评价为刑法上的危险性行为。
(二)危险结果判断基准
“危险”认定实质上是一种危险结果的判断,而判断则需要遵守一定的基准,基准不同,结论可能就有差异。目前刑法理论中,对于危险的判断基准,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行为人标准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自身情况为基准进行判断,即根据行为人的经验、知识等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对危险结果有认识。
2.一般人标准说。认为应当以社会上一般人的经验、认知水平来判断有无危险结果。如果依照社会上一般人的认知来看,危险结果已然发生,则行为人构成犯罪,否则行为人不构成犯罪。
3.科学标准说。主张以科学法则为基准进行危险判断,科学法则包括科学的因果法则及全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并指出一般人的认识不容易界定,而科学标准则有相对稳定性。[15]
三种观点各有优劣。首先,因为一般人概念是一种极其模糊的概念,且由于经验、知识的不同,一般人标准很难得到统一。而科学标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能够提供一统一的危险结果判断标准,并不会因为判断主体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法律适用的同一性,也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同样的案件得到相同的处理。但科学的标准说难点在于社会规则与科学规则价值追求的不同使得科学标准,并且刑法是行为规范,对行为的评价是包含有价值判断的,而科学规则却无法对价值因素进行评价。其次,一般人标准说有可能将对危险结果的判定取决于一般人的感觉、感情,而与危险判断应以客观性为基础的原理相矛盾。最后行为人标准的缺陷在于行为人的陈述并不都是真实的,并且很难发现相关证据证明其虚假,作虚假陈述是任性使然,无法具体规制。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应当采用科学标准说与一般人标准说相结合的折衷说进行危险的判断。这样既考虑到人们的法感情及常识又有一定的科学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结论通常具有合理性并且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三)危险的判断标准
现代社会处处充满危险,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客观上虽然造成了危险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危险结果都能归责与行为人。在危险犯中,危险行为并没有导致实害结果发生,危险结果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呈现人们面前,只能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危险认定,而只有危险程度达到危险犯所要求的危险结果时才能对其进行归责,不然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换句话说,即只有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的行为才能对其进行归责。而是否制造了被允许的危险涉及价值判断,是法律对行为人进行的客观评价,作为裁判的依据,只能以社会上一般人标准进行判断。
不被允许的危险指行为违反行为规范,引起法律所保护客体遭受损害的风险,且该种危险具有让社会上一般人感觉到法益侵害的急迫性,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高,通常从反面意义上对其进行理解。首先降低风险的行为。例如,甲横穿道路,将要被车辆撞到,乙看到后,及时将甲推倒使其免于被撞,但甲致轻伤,由于生命相对于轻伤来说更值得保护,所以不能将伤害结果归责于乙。其次,被容许的危险,即行为人虽然制造了危险,当该种危险为社会一般人所允许,则行为人就没有制造归责意义上的危险结果。例如,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行为致人死亡的,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驾驶者。最后,没有制造风险的行为。甲以杀人故意劝乙坐飞机到泰国去旅游,结果因飞机坠机致甲死亡,由于甲的行为并没有制造风险,所以其并没有实现危险结果。反之,只要当行为人的行为制造或提高了不被允许的危险,并且对危险具有认识可能性,则可以判定行为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结果。
五、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的认定
具体危险的认定。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指行为侵犯的法益已经造成某种具体危险结果的发生,只有行为人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并且这一危险结果是不被容许的,才能成立犯罪的既遂。我国刑法中关于具体的危险犯都是以“足以……危险”等字样规定具体危险的具体内容,例如刑法第116条及117条的规定。
在司法审判中,具体危险的认定者是法官,法官以行为时的所有已查明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并结合具体危险犯的行为特点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导致特定的具体危险结果发生。具体危险是具体危险犯的构成要件,所以对其判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危险行为自身的判断,二是危险结果的判断。危险行为与危险结果的判定应当具有顺序性,首先判定危险行为自身危险性,然后再进行危险结果的认定,并对危险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确认其是否为不被允许的危险,如果行为本身不具有危险性,则就不用进行有关危险结果的判断。无论是危险行为的判断还是危险结果的判断都应当坚持“科学标准与一般人标准相结合”的标准进行相关判定。也就是既要考虑社会上一般人的认知水平,又要结合一定的科学规则,如此才能对危险存在与否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合理结论。例如,行为人以扒铁轨这一破坏轨道的方法意图倾覆火车案件中,对其行为能否造成火车倾覆进行判断时,以上述标准进行判断时,首先应当对行为危险性认定,很明显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其次对危险结果进行判断,一是要查清此段铁路是否正在被使用,如果是没有火车通行的废旧铁路,则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二是弄清被破坏铁轨面积,破坏的部位及破坏程度,科学判断火车时速多少时具有发生倾覆的危险,火车的重量对倾覆产生的影响等得出火车是否有倾覆的危险;三是如果得出火车通过时具有倾覆危险的结论时,要对此等危险以一般人的标准进行是否为社会所允许的判断。如果前方一座桥塌陷,行为人在无他法的情况下采用扒铁轨的方式来阻止火车的继续前行,则要进行相关的利益衡量,判断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技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得案件情况的认定需要科学标准,对于上述案件中火车是否有倾覆的危险进行判断时,以一般人的感觉来判断则结论会不可靠,模糊。通过科学的鉴定得出结论则会使得行为人认罪伏法,彰显司法客观公正。综上所述,对具体危险的判断,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加一般”的标准,分步骤审查行为与结果,并运用科学的因果法则,得出行为人是否制造了具体危险的判断。
有的学者认为抽象危险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对其不需要进行判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关行为,行为人就构成相应的抽象危险犯。[16]对此,笔者不赞同其观点。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同属于危险犯,而危险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对法益造成了某种危险结果,这也是危险犯与行为犯的本质区别,抽象危险犯同样需要进行抽象危险判断,否则抽象危险犯就属于行为犯的范畴了。刑法条文没有将抽象危险作为构成要件加以规定,但并不代表抽象危险犯不需要进行抽象危险的判断,刑法中有许多隐形的构成要件并未予以规定,如盗窃罪并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仍需对此进行判断,抽象危险应当为隐形的构成要件。
抽象危险犯的判断不同于具体危险的判断,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因为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本身具有相当高的危险性,通常行为的实施,就表示危险结果发生的极大可能性。但抽象危险并不是随着行为的实施必然发生,应当结合行为发生时的各种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并且允许行为人反证抽象危险的没有发生,如果行为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确实不会导致抽象危险,则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存在。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刑法13条但书明确规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有达到法定程度才能构成犯罪。抽象危险的判断同样应当受到但书约束,这是刑法对行为危害性实质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行为人醉驾发生在在在一些偏僻,人迹罕至的在没有其他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应当予以处罚,但行为显然不会对他人构成现实危险,危险结果不会出现,行为社会危害性小,不应当对其定罪。
总之,无论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判断时都应当以案件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科学标准与一般人标准相结合”为标准,并且严格遵守13条但书规定等进行判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1]郝守才,张亚平,蔡军.近代西方刑法学派之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87-88.
[2]舒洪水.危险犯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3.
[3]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23.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9.
[5]李兰英.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2):22.
[6]鲜铁可.论危险犯概念与特征[J].法律科学,1995(4):26.
[7]王志祥.危险犯概念比较研究[J].法学家,2002(5):81.
[8]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M].台湾:三民书局,1988:57.
[9]王志祥.危险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86.
[10]马俊驹. 清华法律评论(第一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28.
[11]王志祥.危险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89-191.
[12]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74.
[13]王志祥.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的判断[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1):15-16.
[14]熊选国.论危险犯[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2):28.
[15]叶高峰,彭文华.《危险犯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2000(6):37.
[16]李金明.论刑法中的危险[J].湖北社会科学,2012(1):156.
D924
A
1672-0385(2016)04-0100-06
2016-05-05
王玉博,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神相违背,而“人身危险性说”对此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随着社会对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鲜有学者主张纯粹的“人身危险性说”,以“行为危险说”为基础,主张危险犯之“危险”的可罚性在于行为的危险,已经成为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