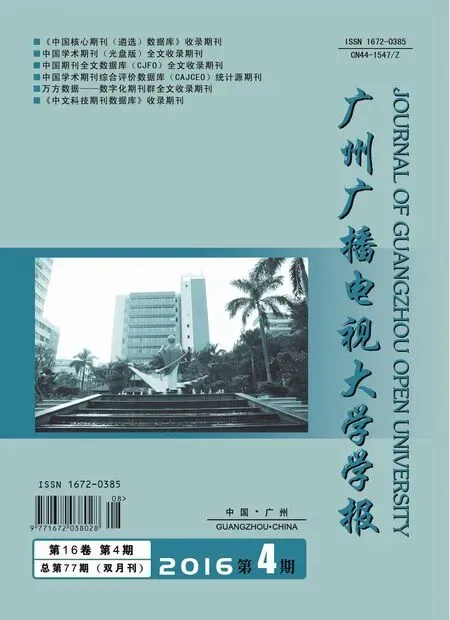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框架与实践分析*
杨梅枝
(肇庆学院西江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广东 肇庆 526061)
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框架与实践分析*
杨梅枝
(肇庆学院西江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广东 肇庆 526061)
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决定政府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提供绩效并不乐观,其成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偏差。广东省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应将提供满足民众需要的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确立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经济战略,实施科学合理的生态公共经济政策,从而建立起生态服务型政府。
囚徒困境;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排污权交易;协同治理
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是指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政策和信息等。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体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的问题,还是一个集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的制度体系。制度本身也是公共产品,也是生产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制度是否系统和完整,是否具有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良好的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先进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1]。广东省良好的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及良好的生态服务是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正如宪政经济学所言,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已不再是效率问题,而是制度设计[2]。因此,理想的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应该具备一套公开、公正和有效的程序及机制,是一个建立在由具体政策工具、行动方案和法律框架相结合的一整套明确的制度供给体系。
一、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启示
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如生态保护法律、政策和信息等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表现在任何单位在使用这些法律、政策、信息,都不会减少法律、政策、信息对其他使用单位的供应,当某单位在使用法律、政策、信息时,其他的使用单位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同样也可以使用;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其真实的价格,因而,市场不能解决其供给问题。况且,逐利性的特点决定企业的目标是经济效益而非生态效益,一些企业为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往往对生态环境过度开发,想方设法规避开发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从而产生哈丁的“公地悲剧”,引发生态危机。所以,在提供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上政府必须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承担相应的职责,提供一个涵盖法律框架、具体的政策工具和行动方案的一整套明确的供给体系,从而遏制广东省生态环境的恶化[3]。下面以一个非常简单却又很经典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来说明市场提供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困难。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诸如生态环保措施等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提供的确存在类似“囚徒困境”的现象[4]。
下面用图来分析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市场提供的“囚徒困境”:假设对企业来说,提供的成本是500元,而收益是400元(确实在目前的中国来说,企业提供生态保护措施是有些得不偿失);再假设社会上有甲和乙两家企业,通过下面的收益矩阵我们可以了解两企业在是不是要提供生态保护措施问题上的一个 “囚徒困境”即“集体行动的困境”。

(注:左上方的150是这样计算的:两企业同时提供各负担250的成本,而收益都是400,这样收益为400-250=150;-100的计算过程一样。)
甲企业想:它提供,我不提供,我的收益是400(白赚的),所以最好是它提供,我就不用了;它不提供,我提供,我的收益是400-500=-100,而它的收益是400,我是不是有问题?最好是一起提供,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它是提供还是不提供,所以在我不知道对方乙是提供还是不提供的情况下,反正我的策略都是不提供。同样的一个推理过程,乙企业也这么想,这样社会上的这两家企业就都不会提供生态环保措施了。
“囚徒困境”与奥尔森教授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揭示了人类的个人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也揭示了市场在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合作与协调的困难。
二、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市场不能解决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由政府替代。然而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由于其官僚体制、官僚行为、垄断地位、决策失误、信息和委托代理问题等导致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出现: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单一和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广东付出了昂贵的生态环境代价。生态环境状况是政府现行环境政策或法律的一面镜子,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精神态度问题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自己规制的问题。
造成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公共选择理论借助经济学方法,把政府供给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活动场域比做市场,称之为“政治市场”,由于政治市场的特征:官僚体制、垄断地位、不完全信息和高昂的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更倾向于低效率,因此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政府提供如何保证高效率是尤其要引起重视的[5]。
(一)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
近几年,随着广东省环境问题的凸显,省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如2011省环保厅编制并下发的《广东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提出污染减排是改善环境质量、解决广东省区域性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总体来看,与城乡居民的巨大需求相比,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不能满足环境和城乡居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表现在广东省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一是,污染负荷重,污染物减排任务大;二是环境质量下降,全省仍有12.6%的省控断面水质劣于Ⅴ类,空气质量下降,土壤污染问题严重[6]。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非常迫切,调查显示,城乡居民户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仅次于义务教育和疾病预防,位居第三。
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排污权交易市场还没有真正建立,没有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广东早在2013年12月就启动了排污权交易试点,但由于相关制度供给的不足,比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排污权交易制度,广东省的排污权交易完全取决于一般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致使很多地方政府对排污权总量控制不严,排污权指标分配不规范,排污企业多是从一级市场无偿获得排污权配额,从二级市场购买的必要性也就随之降低。价格机制的不完善不能促成排污权交易,因而也就不能建立真正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二)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
良好的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体现着或决定着一个区域的最终环境质量,也反映着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工作效率。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环境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缺乏需求状况的调研和民众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需脱节、供需结构失衡。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失衡,表现在有些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过度——环境计划、规划多,而有些公共产品则供给不足——环境协同治理规定少[7]。比如,为了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广东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颁布了《广东省蓝天工程计划》、《广东省燃煤燃油火电厂脱硫工程实施方案》、《广东省环保规划》和《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等,在这些办法、规划中更多强调的是各地政府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的措施也以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为目标、控制的重点也是当地的污染源,鲜有对各地政府及部门间协同治理的规定,即便有规定,也太过原则,操作性不强。殊不知,面对广东省区域性复合型污染的新形态,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中最需要的是有关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方面的法规,这是导致广东省环境协同治理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主要原因是:缺乏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各地的监管和防治各自为政,各部门和各地区遇事难以沟通和协调行动,致使“跨界污染” 频频发生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与治理。近几年,由于广东省各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各城市的集中连片,造成污染物在城市间输送和区域内各城市污染的高度关联,致使污染物在输送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区域性复合型污染的特征。在这种新型的污染形式下,依靠单个城市自身的力量、各自为政的污染物控制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环境污染防治的要求,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一体化控制模式即协同治理机制,应形成统一的协同有力的广东省一体化的监管平台。
(三)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致使我国环境执法存在执行主体混乱,受环境管理体制的制约,现行环境职能部门很多,且每个职能部门都是独立的执法主体,而对于每个部门的具体职责和权限以及部门之间配合的具体方式,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环境主管部门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其职能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8]。尽管《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分管部门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应当接受同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并向其通报环境执法监督、管理情况。实际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有关部门在执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实质上只是分工不同。所以,在分管部门不履行法定环境管理职责时,统管部门也只能口头督促,对于仍不履行的,只能报同级地方政府处理,但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大。
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从广东环境保护职能的配置来看,除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外,还有林业、水利、农业、国土、交通、建设、经贸、海洋与渔业、发改、工商、税务、旅游、城管、卫生、公安等十五个环境管理的职能部门,且各部门权限相互重叠,结果是职权交叉导致职责不分、政出多门使得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十分低下。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的强制划分割裂了行政区域之间和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阻碍了生态文明工作的开展。
三、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理性选择
斯蒂格利茨说过:“最重要的一种公共品是政府管理。我们都能从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反应灵敏的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虽然,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供给中的总量不足、结构单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已严重影响着广东省环境质量的提高,成为制约广东省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瓶颈。
前几天相安无事。吃罢晚饭,呼伦陪云梦和老人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聊一会儿闲天,再躲进书房抽两根烟,就该睡觉了。可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客厅里的丈母娘就让呼伦烦不胜烦——起因是他要给杂志社赶一篇三万字的长稿。
(一)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增加供给总量
排污权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是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排污效果,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标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污染物减排的目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各国在实施的过程中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面临的制度难题却是相同的[9]。各国的经验表明健全、规范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离不开如下两个因素。首先,是完善的法治。为此,从我国国家层面来说,要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相关规定,使排污权交易在实际操作中有法可依;从广东省地方层面来说,广东应该向排污权交易市场构建比较好的江苏、浙江学习,尽快建立起广东省排污权交易的地方性法规,而不能光靠一般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开展排污权交易的相关工作。其次,要明确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指标分配是排污权交易的基础和前提,要控制总量,就要科学、准确地测算出一个控制区域的最大污染物排放总量,要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将跟踪、监测到的排污数据进行量化,这样环保行政部门就能准确知道每个企业的排污量,从而达到相对准确地控制本地区的排污总量。有了总量控制指标后,还要形成一个公开公正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机制,确保排污指标初始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公正以及完善初始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只有这样环境污染物的治理就从政府的强制行政行为变为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排污权的交易也从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交易变成企业与企业间的市场经济交易。
(二)建立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以平衡供给结构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全省性的公共产品,任何地区可以从中获益而无法阻止其他地区也获益。如果每个地区都必须支付减少有害物质排放的花费,当前和未来每个地区都会受益,但这样很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一个地区都会继续排放远大于最优排放量的有害物质,同时,各个地区出于政治博弈的考虑,通常会在排放量和承担治污责任上讨价还价,为此要形成全广东省统一的治理行为就必须构建全省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生态协同治理实践的复杂性管理问题[10]。针对广东省环境污染的区域性复合型的特点,污染防治的重点应该是区域的协同防控与协同治理、区域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多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的创新与管理能力的提升。就广东目前环境管理的实际状况而言,正是因为缺乏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协同机制,各部门和各地区遇事难以沟通和协同行动,区域性污染事件频频发生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与治理,原因在于缺乏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为此,广东省应该出台统一的《政府执法协调办法》,对协同治理事件的目标或协同到何种程度进行硬性规定,以制度约束使协同治理事件具有应有的刚性。
(三)树立环境主管部门的权威地位以提高供给效率
环境问题也是一种体制问题。现实中,我国环保职能分散交叉很严重,“碎片化”现象突出,政出多门,环保体制效能十分低下[11]。而根据生态系统整体性理论,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这就要求生态环保管理体制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因而要优化整合生态系统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实现环境管理部门的统筹管理。同时,要把环保部门纳入到经济发展等重大规划的编制队伍中来,使其能够深度参与国民经济、贸易等政策的制定,以此来树立环境主管部门的权威地位,满足优化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鉴于现阶段生态环保基础能力薄弱,权能不匹配,尤其是执法队伍薄弱,授权不够,法律地位不明确,权威性弱,使各级环保机构监督执法独立性大打折扣;执法人员力量和装备严重不足,经费没有保障,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为此,生态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就应加强生态环保能力建设,明确环境执法队伍地位,增加人员力量,配备必要装备,提高监督执法人员素质,建立一支铁腕治污、勇于担当、公正透明过硬的环保部门及环境执法队伍。
制度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有效的,受制度资源不足以及制度创新中行动团体决策倾向于素质等影响,制度优势的拥有和使用,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能奢望通过一次制度设计或一次机构改革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社会毕竟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而且是一个长期和动态化的调整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一个复杂体系中,政府的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1]夏光.用系统完整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N].北京:人民日报,2013(11).
[2]张晋武.公共物品的概念向何处去——基于政府职能依据问题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3(4):112-119.
[3]王丰年.广东省排污权交易制度初探[J].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9(3):35-41.
[4]刘锡田.制度性公共物品的特征和作用[J].财政研究,2005(9):12-14.
[5][美]保罗· R· 伯特尼、罗伯特· N· 史蒂文森.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第2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6]王玉明.广东环境治理中政府协作困境及原因分析[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0):97-102.
[7]刘添瑞.构建广东环境价格体系问题初探[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1(12):14-17.
[8]童光辉.公共物品概念的政策含义——基于文献和现实的双重思考[J].财贸经济,2013(1):39-45.
[9]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0]樊继达.城镇化进程中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考,2013(1):24-27.
[11]龙新民等.论公共产品概念的现实意义[J].当代财经,2007(1):45-49.
D630.1
A
1672-0385(2016)04-0090-05
广东省肇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框架与实践分析”(项目编号:14ZC-02);广东省肇庆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及路径优化”(项目编号:201438)。
2016-04-26
杨梅枝,女,副教授,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政府规制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