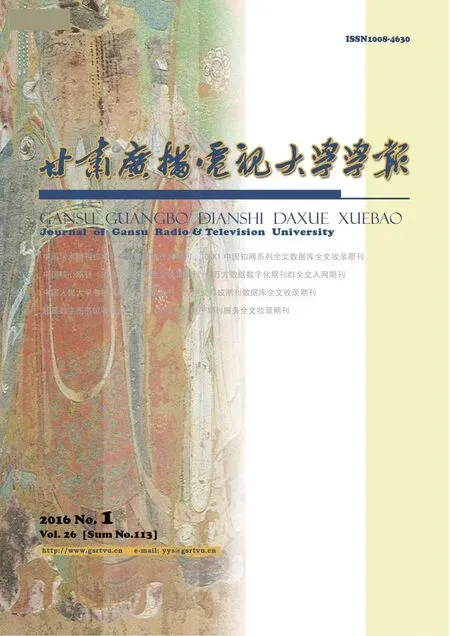雪漠小说“磨盘世界”里的形象阐释
魏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雪漠小说“磨盘世界”里的形象阐释
魏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雪漠小说在“磨盘世界”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展现了西部大漠上的个体面对命运的安排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所做出的顽强挣扎,其中对于“人”、“兽”、“鬼”尤其是“人”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探究了“人”、“兽”、“鬼”及三者之间的联系,诠释了面对同样的生存压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与顽强。而对“磨盘”里的女性形象的详细阐释,则展现了她们面对来自“磨盘”上下盘压力所张扬出来的生命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超现实的浪漫主义形象,从而定格了西部大漠这片土地上人们艰辛的生活以及强烈的生存意识。
[关键词]雪漠;磨盘;“人”“兽”“鬼”;女性
“磨盘”指用人力或畜力把粮食去皮或研磨成粉末的石制工具。推动磨盘将粮食碾碎需要不断的推动力,因此“磨盘”往往给人以艰辛、压抑和沉重的感觉。在雪漠的小说中,“磨盘”作为一个意象多次出现:因为命运的安排与生存的需要,西部大漠上的农民爬上了这座巨大的“磨盘”,在西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在一圈圈的转动中,他们忍受着粉身碎骨般的碾磨,却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的智慧,让这沉重的“磨盘”转出了混沌世界里的几抹亮色。
一、磨盘里的“人”、“兽”、“鬼”
“磨盘世界”里的形象极为丰富:有浩如烟海的大漠美景,有生命力旺盛的大漠生物,也有艰辛而又坚强的普通民众。从“大漠三部曲”对西部农民典型形象老顺一家的书写,到《狼祸》的猎人形象塑造,再到《野狐岭》中对失踪驼队的解密,作者对于“人”、“兽”、“鬼”的书写一以贯之,成为了“磨盘世界”里的主要角色。“人”指作者塑造的血肉饱满且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兽”即作品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塑造,如《大漠祭》中的鹰,《猎原》里的狼和羊,《白虎关》里的豺狗子、沙娃娃,以及《野狐岭》里的骆驼等,作者以细腻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使得它们成为“磨盘世界”里的独特符号。最后是“鬼”,表现在作品中,体现为作家的一种超现实的神秘叙事,在作品中它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人死后的灵魂,作家根据创作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形象和思维的真切存在的“实体”。在《野狐岭》中,作者为了探寻驼队神秘失踪的原因,以“招魂”的方式让已经死去的人以“鬼魂”的身份出现并与“我”进行交流。第二种是依托迷信塑造神秘感,例如“三部曲”中白福向神婆求取儿子的描写,以及因为轻信神婆的谣言而将被认为是“煞星”的女儿引弟带到沙漠活活冻死的描写等等。但是,作者并没有让他们以各自独立的形象出现,恰恰相反,作者将“人”、“兽”、“鬼”三者的书写相互联系起来,相辅相成,使得作品浑然天成而又真切自然。
(一)“人”、“兽”的共通
作为西部大漠上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生命体,面对同样的环境,无论是“人”之于“兽”,还是“兽”之于“人”,二者的契合点随处可见。例如:“按老顺的说法,他天生是个鹰的命。一见鹰顾盼雄视的神姿,他便觉得有种新的东西注入心中……鹰的力量是伟大的。它们是真正的朋友。它们会用心交谈。有时,老顺在生活的重压下濒临绝望,鹰会用它独有的语言劝他:怕啥?头掉不过碗大个疤。”[1]9搏击长空的雄鹰所体现出来的在恶劣环境中惊人的生存能力正是对老顺这一类人的激励与鞭策,他以惊人的耐挫力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这种影响并不起于一时一刻,而是西部农民这一群体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世世代代所沉淀下来的一种精神品质,即在大漠绝域之中所迸发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再如:“在沙地上行走了大半辈子的老顺很像沙娃娃。他两条干瘦的双腿挪动极快,步子碎而小。”[1]10在岁月的磨砺下,年迈的老顺如沙娃娃般日行数里,放鹰逮兔,养家糊口。到了月儿眼里,沙娃娃是她生命最后的慰藉:“她眯了眼,跟沙娃娃对视了,她觉得,那两点瓷灰里,发出了一晕晕的波,向她传来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传递不仅是对月儿形象的一次升华,而且潜在地传递出月儿的死亡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逝去,它预示着会有更多像月儿一样的女子为了命运而不断地抗争下去[2]510。此外,作者往往将“兽”人化,使“兽”具有人性,从而达到以“兽”写“人”、以“兽”投射“人”的目的。在《野狐岭》里,作者对于汉驼黄煞神与蒙驼褐狮子为了争夺“俏寡妇”而引起厮杀的描写极其精彩,使得三驼的形象跃然纸上:“汉驼蒙驼,虽然形状差不多,但心思上差别较大。在狡诈程度上,蒙驼可不是汉驼对手。”[3]69蒙驼的赢面在于体型的健硕,而汉驼善于动脑,这也正是汉人与蒙人形象的真实写照。两驼间的厮杀,又暗示着蒙汉驼把式之间的利欲之争,正如小说主人公马在波所说:“当我们将那疯驼换成了我们的欲望时,你也许会理解我的想法。”最后,作者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大多是以“兽”的视角,通过变换人称的叙述方式直击“兽”的内心世界。除了《野狐岭》中让“黄煞神”加入到“××说”的叙述形式之外,表现最明显也最为精彩的当属《狼祸》中对痛失幼崽的母狼“灰儿”的描写,“灰儿长嚎一声,噩梦呀。风沙像噩梦,但总有醒的时候。瞎瞎呢?风沙息了时,有瞎瞎不?太阳明了时,有瞎瞎不?没了。瞎瞎没了……”[4]作者的细腻描写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刻画得入木三分,感情浓烈而又真实感人。由此,我们也很容易联系到《白虎关》里对莹儿失去女儿引弟之后痛不欲生的描写,虽然一个是”兽”一个是“人”,但终究因为“母爱”而凝结在一起,令人动容。
(二)“人”、“鬼”的联系
根据前文讲到的“鬼”的两种出现方式来看,前者的出现更多是对“人”的灵魂的审视和超脱。在《野狐岭》中对于杀手讲述马在波养小鬼时有这样的描写:“我看到的鬼是一团团气。业障重的,是灰色的重浊的气;业障轻的,那颜色就会清淡些……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为小鬼们消业障,解冤结,然后变食供养。”[3]249马在波对小鬼消业障的过程,也是逐渐消掉仇恨与罪恶的过程,通过对自身的省视,放下外物而超脱自我。而就迷信色彩来说,一方面可以表现封闭的西部底层民众的愚昧与落后,但更重要的是以他们信迷信的过程来表现他们的生活、爱情、命运之苦。迷信是他们身处绝境时的一线生机,也是不堪忍受悲惨命运而发出的垂死挣扎。例如,憨头手术回来后,憨头母亲求救神婆,她希望奇迹出现,希望憨头焕发精神,纵使她明白此时的挣扎无济于事,但也是作为母亲所做的最后努力。
在庞大的“磨盘世界”里,作者借助西部大漠这一特殊的环境背景,客观叙写了“人”与“兽”,主观创造了“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性与内涵,而更因对“人”、“兽”、“鬼”三者关系的独特处理使得小说更加紧凑和丰满。
二、“磨盘”碾出来的美丽“花儿”
在以“人”为中心的“人”、“鬼”、“兽”的书写里,女性形象的塑造极好地阐释了磨盘意象的含义。在《白虎关》中,兰兰两次提到了磨盘与女人命运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是:“可那认六亲的前提是听话,一听话,兰兰就不是人了,在那个既定的生活磨道里,兰兰已转了千百圈。”[2]216第二次是:“你瞧村里女人,哪个不是苦命人?我想是不是女人们都是磨盘上的蚂蚁?只要你上了那磨盘,你就得跟了惯性转?我想,定然还有命以外的事。”[2]318和兰兰一样的女子,只要踏上了命运的磨道,“在不知不觉中,属于女孩最优秀的东西消失了”,“该得的享受被绞杀了”。再注入诸如“黄沙”、“风俗”、“家暴”、“艰苦的劳作”等腐蚀剂的时候,“麻木,世故,迟钝,撒泼,蓬头垢面,鸡皮鹤发,终成一堆白骨”成为女人们共有的生命轨迹。正如常彬所说:“母辈女性在男权桎梏下,在礼教成规中完成着她们被‘打造’被‘逼成’的妻性和母性,她们是父权的奴隶,是礼教的奴隶,长期的礼教熏陶,使她们很容易把这种奴性视为天经地义。”[5]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如此,都愿意顺着磨道转到生命的终结。当兰兰、莹儿、月儿、秀秀(双福女人)、豁子女人等女性形象出现的时候,即使明白“当一个巨大的磨盘旋转时,你要是乱滚,就可能滚进磨眼,被磨得粉身碎骨”[2]465的严峻事实,但她们依旧顶着来自上下盘的压力,如高亢动听的“花儿”一样绽放出了别样的命运之花。
(一)上下“磨盘”的压力
如果把“磨盘”看作是生命的历程,那下盘就是来自生活的压力,主要包括历史沉淀下来的男权桎梏和礼教成规以及贫穷的生活和劳作的艰辛。上盘则是来自艰难严酷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当女性爬上“磨盘”,就会受到来自上下盘的共同压力,面对上盘的压力,兰兰和莹儿因为“换亲制度”而开启了各自的爱情悲剧,常年累月的家暴让兰兰苦不堪言,而丈夫因为轻信迷信谣言活活冻死女儿引弟更是让她痛不欲生;莹儿的丈夫憨头虽然忠厚老实,但是由于“生理残疾”自卑苦闷,迫使莹儿忍受着为人妻而仍为处女的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秀秀的丈夫双福外出成为暴发户,可以说她没有物质方面的忧虑,但是却忍受着丈夫的花天酒地,失去了作为一个妻子所应得到的关爱与慰藉,成了一个“活寡妇”。总的来说,她们有着极强的抗压能力,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没有向生活和命运低头。
(二)自我生命意识的确立
虽然这些“花儿”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磨道”,但仍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努力挣脱既定的命运轨迹。支撑她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对于自我生命意识的认识与确立,无论是信仰还是尊严,它们终将成为一个支点,让她们的人性之美得到升华。秀秀和豁子女人敢爱敢恨,泼辣率真。我们可以从猛子的视角出发来探究她们俩的变化,猛子先后与秀秀、豁子女人多次偷情,她们疯狂地享受着爱欲,张扬着她们骨子里的野性与疯狂,此时,在猛子眼里,两位女子浑身散发着“骚气”,成了名副其实的“浪女”。而当秀秀的丈夫被捕,豁子女人成为寡妇的时候,她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秀秀给猛子说过这样一段话:“老天能给,仅仅是老天的本事,我能受,却是我的尊严,不怨天,不尤人,静了心,把给你的灾呀难的接过来,眯了眼,笑一笑。”[2]490同样,当豁子被土筐砸断脊椎时,豁子女人倾尽钱财为丈夫治病,当豁子医治无效死亡时,她又冷静坚强地为豁子处理后事,并且送钱给从未谋面的公婆。她们俩一开始便承受着命运的不公,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在一次次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我”,用尊严与强烈的生命意识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大漠女性之歌。莹儿和灵官有违伦理的叔嫂之恋让莹儿重新燃起了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她把最爱的“花儿”吟唱给她最爱的人。“唱这类花儿时,莹儿便成了世上最坚强的人。那份执着,那份坚强,那份为爱情宁死不屈的坚韧,仿佛不是从那柔弱的身子里发出的,而是来自天国。”[2]57当她和兰兰为了争取幸福踏上危险的驮盐之路时,大漠深处便开出了两朵夺目的“花儿”,看似是一场驮盐之行,实质上是她们二人寻找“自我”的过程,无论是兰兰面对豺狗子和沙暴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坚韧与冷静,还是莹儿用血指在衣服上写下“莹儿爱灵官”的刻骨铭心,都体现了一种自我生命意识的浓烈张扬。走出大漠后,兰兰皈依金刚亥母,寻求属于自我的一种安分与宁静。而莹儿对灵官的持续“追恋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之后的回忆,更在于从现实残存的星光中发掘出新的火种”[6]。这个“火种”是她生存下去的希望与盼头,即使这个“火种”最终遭到了现实的无情熄灭而以悲剧结尾,但是这种悲剧与无奈所带来的人性美却是撼动人心的。
(三)超现实的浪漫主义女性
雪漠说:“凉州女人都是很好的母亲、妻子,但她们不一定是好女人。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已经扼杀了她们最美的女儿性,让她们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向往,变得功利了。换句话说,你在我的作品中读到的那种美好形象,实际上是我对女性的一种向往。”[7]因而相对于西部单调闭塞的生存背景,雪漠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她们为了爱情牺牲一切的悲剧美。以莹儿为例,和兰兰在沙漠与豺狗子经过殊死搏斗之后,莹儿开始思索自己的命运和爱情:“要是千年后自己也被挖出,也会是个巨大的谜,没人知道她曾爱过……她想这秘密也没人能考证得出来。”[2]308这时莹儿的形象异常鲜活,美丽可爱,多少有点诗人的气质。回到家后,莹儿被迫和屠夫成婚,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她选择了死亡。在给灵官的信中她写道:“你不是来去无踪的风,也不是飘渺若幻的云,你是深深种在我心田上的珊瑚树,每个黄昏我用相思的甘露浇灌你,盼你在某一天托着浓浓的绿意与我相逢在小屋里……”[2]503考虑到莹儿的文化程度及生活环境,信的内容多少具有作者想象与虚构的色彩,但丝毫不影响其真实的情感表达,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2]517莹儿信中大段的浪漫追溯以及浓郁的情感表达将莹儿的悲剧爱情定格得崇高而又动人。对月儿的刻画可以说是将这种悲剧美发挥到了极致,这个美丽的“花儿仙子”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然而事与愿违,因感染梅毒,月儿再次归来,在她看来,“家乡是个熨斗,能熨去灵魂的伤痕”[2]332。但是当往昔的白虎关有了歌舞厅、搅天的喧嚣、隆隆的机器的时候,她所有的寄托跌到了谷底,在她“出走”到“归来”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与猛子的爱情让她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她大把地吃药,听信偏方,用牛粪来熏下体,甚至想要吞食癞蛤蟆。这朵“花儿”流出了污浊的液体,却活出了圣洁的心,当她站在村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望断天涯路般等候着心爱之人猛子出现的时候,那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让人心碎。面对命运的安排和苦难的岁月,莹儿与月儿选择以柔弱的臂膀苦苦抵抗,艰难挣扎,莹儿的“自杀”是为了守护自己仅有的、被她视为一切的爱情;兰兰的“他杀”也因为爱情而显得愈发具有悲剧性。
(四)女性助推男性形象的成长与升华
女性形象以其独特的人性魅力助推男性形象的成长与升华。猛子作为“大漠三部曲”的主要男性角色,其成长的历程复杂艰辛,秀秀和豁子女人成为其“磨盘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起初,猛子和普通农民一样顺着“磨道”前行,偶尔他也驻足思索,但“磨盘”极大的“惯性力”迫使他匍匐向前。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抗拒贫穷潦倒的生活,他与秀秀多次偷情。尽管猛子知道自己只是双福抛弃女人的一个“挡箭牌”,但是他依旧以睡了腰缠万贯的双福女人而窃喜,后来,他与北柱去掘双福先人的坟,好破双福的财,当双福真的出事之后,他又后悔自责甚至一度想要救双福,他向秀秀承认掘坟的事实,秀秀说道:“心不变,毛病就改不了。毛病改不了,迟早会犯事。细一想,也是定数呢。只是心变了,那定数才会变。”[2]482秀秀对于双福出事之后的态度一度让猛子感动,一句“老天能给,我就能受”,让这个铁血汉子热泪盈眶。同样,豁子女人也具有同样坚强和冷静的品行,让猛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在他眼里一度“浪荡”的女人,如果说,秀秀与豁子女人只是从做人的基本态度与心性上影响了猛子的话,那么他与月儿的爱情便让他步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从知道月儿隐瞒梅毒的事实之后,他便厌恶了这个女子,但月儿执著的爱又让他逐渐释怀,他想尽一切方法给予月儿最后的安慰与关怀,尽管月儿含泪撇下猛子离去,但是猛子未来的路还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亮色,这份微弱的光亮将指引他一直走下去。
雪漠曾说他写作的理由有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闹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其二是他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2]虽然“磨盘”已经逐渐淡出了农民的生活,但是雪漠笔下的“磨盘世界”在不经意间定格了西部大漠这片土地上人们艰辛的生活与强烈的生存意识。
[参考文献]
[1]雪漠.大漠祭[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2]雪漠.白虎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雪漠.野狐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雪漠.狼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76.
[5]常彬.中国女性话语流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1.
[6]赵学勇,孟绍勇.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2.
[7]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9.
[责任编辑龚勋]
作者简介:魏斌(1991-),男,陕西陇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23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6) 01-00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