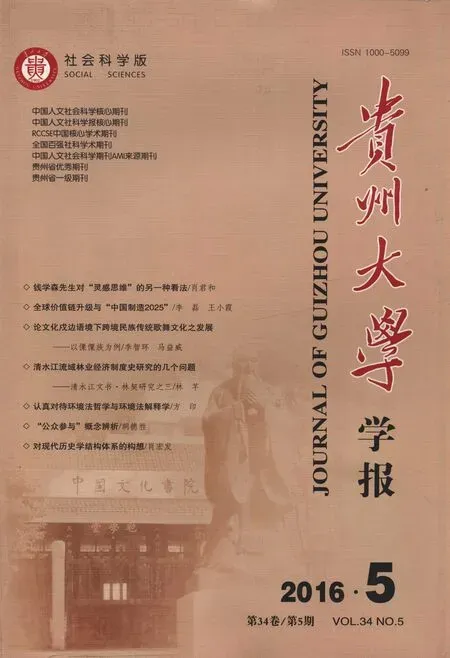论苗族古经提法与释义
于衍学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
二
三
论苗族古经提法与释义
于衍学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苗族古经提法及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国内苗学研究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古经”作为中国汉族地区口承民间故事广义上的一种地方性叫法已存在的事实有据可循;但是,苗族古经提法在内涵上有其特殊性;它进入学术界较为晚近;经历一个酝酿和演化过程;是从苗族民间文学经典向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转变和再定位的一种质变;这一提法开创指称历史上中国大陆无文字少数民族口承文化先河;学术和现实意义明显,影响深远。所指外延上,苗族古经是“苗族‘经师’在排解纠纷、祭祀大典与丧葬、巫事、庆典、动工等仪式场合吟诵的长篇说理、叙事、对话(人与神、人与人)等作品的统称。”本质内涵上,是苗族先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总结出来,世代传承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苗族古经之道是和谐之道,温和文化;此点突显苗族这一古老民族独特智慧和文化个性。
苗族古经; 提法; 释义
近3年来,中国大陆苗族古经这一概念提出,相关研究持续升温,逐渐成为国内苗学研究崭新领域。诸如,苗族古经研究专项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2013年贵州大学刘锋先生主持立项“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13&ZD137)、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先生主持立项“中国苗族古经专题”(13AZD055);苗族古经研究展示平台业已建构。2015年,《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苗族古经专栏”成功开辟;苗族古经研究机构拟在设置。贵州大学新组建二级学院拟设立“苗族古经研究中心”;诸多苗族古经专题论文亦已发表。这些事实,彰显苗族古经日益成为苗学界关注热点。
关于苗族古经,刘锋先生认为,是“苗族‘经师’在排解纠纷、祭祀大典与丧葬、巫事、庆典、动工等仪式场合吟诵的长篇说理、叙事、对话(人与神、人与人)等作品的统称。”[1]
社会事实是与科学研究相维系的一种品质。对于苗族古经近年来呈现的社会事实和研究动态,或应置其于一定时代背景下审鉴。苗族古经概念提出,大抵是与世界文化多元化取向、各民族文化自省自觉、反对文化中心霸权及争取民族话语权等密切相关。前者是宏观层面客观存在的一种人类文化必然趋势,后者是在这种取向背景下,各文化集团“自我醒觉”和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诉求;更是对“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追认和建构。这是新时期人类文化总体演进中一种反思,亦是各民族集团在生存发展境遇体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识性的一种思维理念,还是对文化相对性观念认可和践行。尽管,长期存在中心文化及其价值标准话语垄断,短期内难以破除。有些民族集团文化强势依然存在。边缘文化及其价值理念,一时尚难以彰显和确认。但是,世界民族文化多元化大势终究明晰。各民族文化发掘整理和重视程度已是空前。在此时代背景下,对于苗族这个古老民族而言,苗族古经提出,是对其传统口承文化价值一种再认识,一种自信,亦是新时期传承、弘扬苗族口承文化一种有效途径。所以,苗族古经提出,虽是或然亦是必然。它以事实,肯定和呼应世界民族文化多元化洪潮之不可逆性;践行并极力彰显其久已沉寂的、被边缘化的苗族古老文化时代价值;力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庞大文化体系中,发现其思想文化在场印迹,表达其理念;诉求并追回理应属于她的价值位次;昭示和确认苗族这一族群对于中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分享苗族先人创造智慧和文化成果。如此这般,苗族古经提出、发掘和研究,对于苗族和中国,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必将随流年而日显。
我们肯定苗族古经这一提法所具有的学术与当代价值,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苗族古经研究所处阶段性,以及当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聚共识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怎样看待苗族古经概念提出之前,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实体研究中,业已存在的概念繁杂现象?苗族古经这一提法如何演化而来?苗族古经提法的依据何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苗族古经提法适用范围怎样?苗族古经本质内涵何在?在比较层面上有何独特之处?等等。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
自2013年以来,苗族古经提法及相关研究日增,备受学界推崇,愈趋成为苗学研究领域“新宠儿”。就目前资料看,苗族古经这一提法书面完整的表述,或是在2011年12月肖凯林主编《2010年贵州宣传工作年鉴》中出现。该书“关于积极推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程”栏目下,呈现关于“完成了丹寨苗族信仰文化调研,采集苗族古经50万字”[2]这一表述;之后,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中国苗族古经专题”,均以“苗族古经”设题立项;2014年,刘锋先生曾就苗族古经概念做过初步阐述,同年5月,吴小花等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上刊出《从<楞伽经>的名相说开去——兼论西方语言哲学与苗族古经的唱诵禁忌》一文,其中用苗族古经这一提法指代传统意义上苗族口承文化;2015年5月和7月,《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4期上,先后集中刊登白林文《苗族古经“卡人”古代族属考》、刘锋《苗族古经之由来及其研究》、杨曾辉《苗族古经中的哲理探析》,以及唐莹《苗族古经及其文献价值》(载于《中国民族博览》2015年第8期)等文章,苗族古经专题论文逐渐涌现。我们不敢妄断,苗族古经这一提法,见诸于书面文献前,在苗族民间村落社会是否已经存在。但是,这里我们仅仅探讨苗族古经提法的书面表述。
苗族古经提法经历一个酝酿和演化过程。1999年,庄恩岳在《黔姿百态: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中,以“苗族经典”表述《贾理》; 2004年,出现“苗族经典”与“《贾》”(“Jax”的音译)连体表述形式。即潘广淑在其主编《丹寨民族文化旅游文史专辑·蜡染笙歌》一书中,以“苗族经典《贾》”形式表达流行于黔东南地区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一种样式。这里,显然潘氏已将丹寨地区流传“贾”看作苗族当然之“经典”;2007年,龙杰在《边城文集》中有“苗族‘圣经’”表述,其以“苗族的圣经”代称湘西地区流行之苗族“古老话”;2008年,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在其主编《本土乐话》(上册)中,以苗族“最神圣的经典”和“关于宇宙和人类意义世界的理论经典”表述《苗族古歌》,认为其在性质上等同犹太人之《圣经》;2009年1月,徐晓光先生明确表达苗族“贾”与“经”在性质上的内在关联。其在《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经’的性质”。据既有资料显示,徐氏或是第一位明确指出“贾”为“经”的学者。这一表述特别之处或在于,对“贾”而言,由“经典”向“经”转变。2009年8月,杨长泉先生在《论民族法中的道德与强制力元素的平衡关系——以黔东南苗族理词为研究途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4期)一文中,把苗族 “理词”(“贾”是“理词”的一种史诗反映样式),表述为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一种“生产经验的总结”(规律)和“规范人们(苗族)行为的‘法典’(法则)”[3]。这一观点,与徐氏有异曲同工之妙。
苗族古经这一提法,正式进入学术界视野时间较为晚近。尽管,2011年12月,苗族古经书面形式已经较早出现在肖凯林主编的《2010年贵州宣传工作年鉴》中;但是,直至2013年11月,伴随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公布,苗族古经提法方得以彰显,始受国内学术界关注。在此之前,相关苗族传统口承文化研究文献中,仍然沿用苗族古歌、理辞、贾理、古老话、史诗、民间故事等提法,指称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实体。诸如,李志勇在《谈乡村旅游开发下苗族古歌的发展——以黔东南巴拉河为例》(2010)中,采用苗族古歌指代“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和‘经典’”;胡晓东、胡廷夺在《“理辞”与“苗例”》(2011)中,使用苗族理辞代指“黔东南州及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和“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吴一文《口传经典与民族精神——论苗族史诗与苗族历史文化》(2012)、吴一方《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苗族史诗〉三语翻译刍议》(2013)文章中,有“苗族史诗是苗族(的)口传经典”表述形式等。直至2014年5月,《从<楞伽经>的名相说开去——兼论西方语言哲学与苗族古经的唱诵禁忌》发表,苗族古经概念或是正式出现在苗族传统口承文化研究论文文献中。2015年5月,随着白林文、刘锋、杨曾辉以及唐莹等人,关于苗族古经文化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苗族古经这一提法,逐渐呈现在苗学研究文献中,与苗族古歌、苗族贾理(贾)、理辞(理词)、苗族史诗、古老话等概念,共同表述苗族传统口承文化范畴。苗族古经提法的出现及使用,经历一个酝酿和演化过程。
苗族古经这一提法有依据,但亦有其变异性和特殊性。苗族先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大量民间故事、古歌、史诗、贾理、理辞、神话传说等传统口承文化样式。以“古经”这一提法统括,是否恰当?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采用“古经”这一提法表述口承民间文学样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存在;主要是中原汉族地区民间故事广义上的一种地方性叫法。
诸如,高清海早在1988年主编《文史哲百科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217)一书,“民间故事”词条指出: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重要的种类之一。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等寓于幻想的口头文学作品。有的地方叫‘古话’、‘古经’、‘龙门阵’等”。此处,高先生着重强调古经叫法的地方性;次年,郑乃臧、唐再兴主编《文学理论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406-407)一书,“民间故事”词条中有类似阐述:“人民口头流传的、具有假想(虚构)因素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作品,比较接近自然形态,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各地名称不一,诸如瞎话、古话、古经、说古、摆龙门阵、讲故事、聊天、说天古等。”这里,郑、唐二人明确指出古经的地方性、民间性及口头性;此观点与高清海先生如出一辙;1998年,薛克翘撰《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90-291)一书,在阐述“佛教与中国诗歌”时有如下表述:“印度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古经《吠陀》而下,《梵书》《奥义书》《往世书》等等,无不以诗体写成。”薛先生指出古经《吠陀》诗歌形式和诗体文裁,诗歌体的古经样式。直到2011年苗族古经提法书面形式出现,后续学者对古经与民间故事两者关系,在承续前人观点基础上,又有新认识。如,赵宗福等著《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5)一书,阐述“口承民俗”时有如下表达:民间故事“在汉族地区,将含有一定故事情节和形象塑造的叙事,也称为古经”。这里,关于古经,赵氏强调两点:“汉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和“有一定故事情节和形象塑造的民间故事”。至此,我们发现,古经原本是指汉族地区存在的、含有一定故事情节和形象塑造的、口头叙事民间故事的一种地方性叫法。常以诗歌形式存在。但是,这里需要注意:苗族古经或是借鉴汉族地区这种口头叙事民间故事地方性叫法。但是,苗族古经并不是简单地等同或类似于流行在汉族地区具有地方性的口头叙事民间故事。因为苗族古经提法在内涵上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是由苗族古经产生和传承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及其社会功能所决定的。
苗族古经提法有其鲜明民族个性。这集中体现在,它开创了指称中国古老少数民族,在封闭或半封闭村落社会中,无文字状态下,上千年口承文化的先例。在中国,大凡以汉文化方块字承载传承的、为历代官方认可的典籍文献或可能奉之为“经”。如,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相传由孔圣编订,西汉时被统治者尊奉为儒家经典。其中,《雅》《颂》二类大抵亦非采自民间。《雅》为周人“正声雅乐”。《颂》则收录“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再如《道德经》,为春秋诸子老庄学派李耳所作。汉初,景帝时始尊为《道德经》。李唐一代推崇道派。高宗尊《道德经》为《上经》,玄宗一朝奉其为《道德真经》,流传于后世;又如《易经》,或成书于战国时代。据刘大均《周易概论》考证,其为孔子后代子思和后学孟子所作,位列群经(易、诗、书、礼、乐)之首,成为历代官方“设教之书”等。然而,除汉族外,中国境内各古老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古经文化。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福乐智慧》等。它们同样由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久远,在各自民族社会中形成和演进,由各自民族文字得以世代传承,流传至今。然而,苗族古经文化,却是在封闭或半封闭社会状态下,在缺乏文字记载和传承历史条件下,以“口头传承”“口授心记”方式传承千年之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极为罕见。苗族古经文化传承,或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经文化传承的特例。
这一提法,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相对性思想和文化多元化理念。它以铁证,表明如下事实:一个国家和社会,不仅居于中心文化群体的民族和人民能够创造和传承古经文化,处于边缘文化群体少数民族,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不仅能创造古经文化,而且亦能以非文字口头方式传承自己的古经文化。每个民族或都有自己古经文化及其价值。在人类文化创造这一点上,各文化集团均具平等的天聪智慧。这一提法,突破历来由朝堂官方奉封“经文化”的惯例,非官方学界基于事实亦可以提出和确认一个民族或文化集团的“经文化”。这一提法,打破民族古经文化文字传承的通古通律,提供无文字民族在特定状态下以“口授心记”方式口传文化上千年的鲜活案例。苗族古经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统括苗族口承文化实体研究中使用和表述过的诸多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将苗族口承文化实体从苗族民间文学和民间习惯法研究视野中提升出来,使其上升到同《诗经》《道德经》《易经》《古兰经》《圣经》等世界各民族古经文化并置的高度上。苗族古经提出,对苗族和中国文化发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
前文探讨了苗族古经提法,下面,从当前学术界对苗族古经阐释、苗族古经所指外延、本质内涵及作为传统口承文化体系的苗族古经文化个性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当前,学术界对苗族古经最早做出阐释的或是贵州大学刘锋先生。如前文述,他在2014年4月1日《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上和2015年7月发表《苗族古经的由来及其研究》一文中,先后对苗族古经这一提法做出过专门阐述。比较前后两次阐发,我们发现,差异集中在分别对“仪式场合”“长篇作品”做进一步例举细化以及“吟唱”更为“吟诵”三个方面。其以凝练语言科学地指出苗族古经主要特征。具言之,苗族古经吟诵(吟唱)主体为苗族“经师”; 吟诵(吟唱)仪式场合与内容主要是排解纠纷、祭祀大典与丧葬、巫事、庆典、动工等活动中;吟诵(吟唱)功能形式为说理、叙事、对话(人与神、人与人)等;吟诵(吟唱)篇幅体量则为长篇;是苗族传统口承文化长篇作品统称。换言之,其集中概括出苗族古经吟诵(吟唱)主体、仪式场合、内容、功能形式、篇幅体量及其统括性。
事实和理论是科学研究两大诉求。理论植根于事实,事实是其邃密所在。众所周知,概念是人类思维体系中最基本构成单位,由内涵和外延构成。内涵是概念本质涵义,外延是其适用范围。任何概念概莫能外。苗族古经亦是如此。所以,苗族古经这一提法的释义问题,应从本质涵义和所指外延两方面考察。关于苗族古经所指外延,刘锋先生已有精辟阐释。关于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是与以下问题紧密关联着: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为什么能在苗族社会口授心记传承千年之久?为什么学者们将其尊奉为“苗族经典”“苗族的圣经”?在历代封建统治势力及其社会治理规则未曾真正渗透进去的广大苗族地区,村落社会秩序为什么能够和谐存续数千年?究竟是何种力量如此长久地发挥着治人理事功能?解答以上系列问题,就是探讨苗族古经文化本质,即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我们拟从民族结构功能理论、语义学以及形式逻辑学角度,探讨苗族古经本质内涵。
首先,从苗族文化结构对苗族结构运行的实践功能看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实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结构,主要地是由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以及生态等方面构成。苗族亦是如此。历史上,苗族村落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完整系统。苗族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及其生态结构,构成苗族村落社会系统主要部件。其中,苗族经济结构决定着苗族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人口结构等。清雍正王朝在中国西南边疆推行“改土归流”前,苗族村落社会长期游离在封建皇朝社会直接治理体系之外。在此社会状态下,封闭或半封闭农业山地型苗族经济结构,铸就苗族村落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类型;反言之,苗族文化结构,尤其是其中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般意义上,反映和反作用于苗族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人口结构及其生态结构,发挥着相应文化功能。它们都是属于苗族社会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文化结构中这些思想意识形态类东西,通过口承方式世代传承,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苗族口承文化体系。其内核就是苗族古经文化。换言之,苗族古经文化,就是适应、反映并反作用于苗族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它对保障苗族村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运行数千年,起到重要调节、调控和塑造作用。对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如此阐释: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1987:97)中,从人类文化需要角度指出,“文化历程以及文化要素间的关系,是遵循着功能关系的定律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则从文化结构的社会功能视角认为,各种不同结构(包括文化结构)构成社会系统,(社会)结构是通过(文化)功能维系这个(社会)系统的。两位文化大师都从功能角度指出,苗族文化结构中思想观念形态的苗族古经文化,在保障、稳定和推动苗族社会结构健康运行上千年,起到关键作用。或许两位大师上述诠释有些许隐晦。苗族贾理整理者王凤刚先生的表述直接明了。他阐述《贾》时言道:“《贾》通过历代的主要传承人理老、寨老、巫师等,广泛应用于苗族历史与文化传播、伦理道德教育、社会管理、宗教祭祀、娱乐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实用价值。《贾》在苗族社会里主要依靠它的这些实用功能所产生的文化认同、道德约束、法律(习惯法)规范、精神信仰等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维系了……长久稳定和和谐。”[4]12结合前文徐晓光先生论述,这里,“贾”是属苗族古经文化范畴,显然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已知论断。通过这个论断,我们看到:苗族内部形成一种文化认同,进而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信仰。在此基础上,在传统封闭或半封闭苗族村落社会中,这种精神信仰在生产和生活中,必然建构成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类的文化结构,长期发挥着“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效能,维系苗族村落社会长久稳定和谐。“贾”所具有的这种效能,本身就体现出“贾”的本质内涵。换言之,“贾”的本质涵义就是一种“道德约束”,一种民间“法律规范”。
其次,从语义学角度看苗族古经本质内涵。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 Edward)认为:语言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分一般是由一串音组成的词,或是词的有意义的一部分,或是词组。这些成分的特点是: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特定观念的外表标记。这观念可以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或彼此有一定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的几个概念或几个印象[5];根据萨丕尔的观点,我们认为,应当首先肯定语言学上的“苗族古经”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成分”。这是从语义学角度分析苗族古经本质内涵的前提条件,即苗族古经是一个“由一连串音组成的词”或“词组”。同时,他指出,一个单词可以是我们要研究的最简单的有意义的成分。因为萨氏认为“语言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分”,一般不仅是“由一串音组成的词”,还可能是“词的有意义的一部分”。 例如“苗族古经”中“经(名)”字部分。根据萨氏这一观点,“经”的本质内涵,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苗族古经本质内涵。考察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某种意义上,就是考察“经”的本质内涵。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十三糸部):“经,织也。从糸巠声。”这当是经字本义;《尔雅》引申:“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中华现代汉语词典》(2009):“经(名)恒久不变的道理;法则:天经地义。”这里,突出两点释义:“经”,一则为“常道”或“恒久不变的道理”;二则为“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或“法则:天经地义”。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也。”此处杜预注:“经,常也。”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这里杜预注:“经,法也。”这与徐晓光先生关于“‘贾’意译为‘道’,即法则、规律、万事之大道理之意,很大程度上具有‘经’的性质”[6]论断中,有关“道”“法则”和“‘经’的性质”的表述,前后印证,不谋而合。所以,我们认为,从语义学角度讲,“常道”和“法则”应是“经”(本义“织也”)最初级引申义。我们依据萨丕尔“语言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分……”和“每一个(词、词组或词的有意义的一部分)都是一个特定观念的外表标记”的论说,我们断定,“经”就是“苗族古经”中“真正有意义的成分”,是苗族古经本质内涵(特定观念)的“外表标记”。据此,我们认为,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是:历史上苗族先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和总结出来、为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
再者,通过“贾”的本质内涵已知论断推导苗族古经本质内涵。如前述,“贾”属苗族古经体系范畴,其本质内涵是已知论断。即传统苗族村落社会中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但是,苗族古经文化系统范畴中是否只有“贾”,抑或皆以“贾”这惟一一种称法来表述呢?该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概念表述之间关系。换言之,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实体研究中,经常使用诸如苗族古歌、古老话、理辞(理词)、苗族史诗、民间故事、苗族习惯法及苗族大歌等,其表述在本质内涵上与“贾”是否一致?有何区别?如若一致,根据形式逻辑学中关于“同一律”理论,表明它们同样都具有“贾”所蕴含的“常道”和行为法则这一本质涵义。如若不一致,通过“贾”的本质内涵已知论断推导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是缺乏依据的。根据形式逻辑学关于“不完全推理”原理,上述概念同属于苗族古经体系范畴,至少是广义上苗族古经体系范畴。由于它们构成苗族古经文化完整体系,所以这些概念本质内涵就是苗族古经文化本质内涵。以上推论如若成立,其预设前提是:苗族古歌、苗族古老话、苗族理辞(理词)、苗族史诗、民间故事、苗族习惯法及苗族大歌等表述形式,在本质内涵上与“贾”一致。
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古老话、苗族理辞(理词)及苗族大歌等苗族口承文化与“贾”,在本质内涵上是否一致?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是中国最大苗族聚居区,流传和保存众多“古风”“古俗”“古文学”等。田兵(1979)、燕宝(1993)、潘定智(1997)等选编《苗族古歌》,多采集在该地区。当地苗族习惯上呼为“古歌”。“因为苗族人民把它看成历史,所以也称为‘古史歌’。”[7]马学良译注《苗族史诗》,亦是主要采集和收录流行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苗族民间创世神话叙事诗。苗族史诗,当地习惯上亦称为“古歌”或“古史歌”;苗族古老话主要流行在湘西地区,是一种神化了的苗族史诗;从所看到“贾”的内容论,“‘贾’是以史诗形式反映的‘理辞’”;“贾”某种意义上就是苗族村落社会行为法则或习惯法;苗族大歌则主要流行于黔东方言区黔东南州黄平、施秉、镇远等县市和黔南州瓮安县自称为“Hmub”的苗族群体中,应属苗族古歌一种类别。从民间文学角度讲,它们都属于前文高清海、郑乃藏等先生阐述的广义上民间故事范畴,是苗族口承文化体系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其差异性主要集中在:流行区域(苗族三大方言区及其细化区域)、群体分支(历史上苗族存在诸多分支群体)、唱诵主体(或巫师、或理老、或寨老、或贾师或苗族群众等),以及传承范围(是苗族社会“知识分子”或“经师”等精英,还是普通民众)等方面。不在其本质内涵上。因为,如徐晓光先生所言,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古老话、苗族理辞(理词)以及苗族大歌等“内容不可能完全独立,往往相互渗透,不同程度地负担着对习惯法(苗族社会行为法则)的传承功能”[6]128。可见,这些概念表述形式,在本质内涵上与“贾”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苗族古经本质上是苗族先人创造和总结出来,为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是“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总的依据、规则和原则,是苗族村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6]128。这就是苗族古经本质内涵。亦是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在苗族社会能够口授心记传承千年之久,为苗学者奉之为“苗族经典”“苗族的圣经”,在历代封建统治势力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移植和渗透进苗族聚居区之前,长期起着治人理事功能,以及保障苗族村落社会秩序相对持续稳定和谐运行的奥秘所在。
那么,何谓之道?苗族古经之“常道”又是怎样一种道?它有何独特性?一般而言,道就是道理或常理。如清陈昌治本《说文解字·辵部》(卷二):“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预。”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这里道就是道理、真理、道德或是一种思想体系。诸如,儒家之道,讲求仁爱。其道受之于天,天子(帝王)代替天在世间管理人民。这里天、地、人合一。又主张王道,与法家霸道相对立,所以它带有些许政治倾向;释家(佛家)之道,在于悟性和大觉。通过大彻大悟解民于苦难。大觉者即为佛,没有神;道家之道,在天道无为、道法自然。包含着“无为无不为”朴素哲学思想;伊斯兰文化之道,主张信主(安拉)独一。其道由安拉降示,穆斯林信奉追随。比较而言,苗族古经之道,亦讲求仁爱。但这种仁爱是对天、地、人、神、鬼平等视之的博爱。它集中体现在崇天敬地,宽和待人,祭拜神灵,却不畏惧鬼神,追求与万物平等和谐共处。其仁爱已超越儒家“仁爱治天下”的“爱仁及人”功用范畴;苗族古经之道,旨在治人稳世,非“治国”或“平天下”。此有别于儒家王道。这显然与苗族古经形成、施用空间、群体及功用紧密相关。苗族古经之道,既非受之于天,亦非受之于神,而是受之于自然,是一种自然之道。它是苗族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自然论。它没有儒家王道,也缺乏法家霸道,是在苗族人民中间形成的一种较为温和的和谐之道,一种温和文化。苗族古经之道,本质上所反映的苗族传统村落社会,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也是一个不畏鬼神的社会。这不同于儒家、佛家无神论,也有别于伊斯兰文化中“认主独一”一神论。苗族古经之道,虽没有释家对悟性的笃信,却也包含着诸多含蓄色彩。诸如“身不曾乘船,脚不曾踏舟”,隐喻未曾与妻子圆房[4]57;“中间是田埂,两边两块田”,隐喻牛蹄印的形状[4]248;“脚劳脚有吃,手动手有穿”,隐喻谁劳动谁就有收获[4]251等朴素思想。苗族古经之道,较之于道家天道无为,也有反抗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这近似于伊斯兰文化之道,却有别于儒家积极入仕思想。较之释家和伊斯兰文化中饮食习俗领域的排他性,苗族古经之道却多了几分包容。这一点同儒、道文化颇为接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如下认识:苗族古经之道,受之于自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和谐之道和温和文化;它出自多神信仰的苗族村落社会,却不畏惧鬼怪神灵,积极寻求与之共存共处之法,创造可与包括鬼怪神灵在内的世界万物共存共生的处世哲学;它包含的仁爱是宽泛的,在苗族温和文化沁润之下,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它是治人稳世的,注重调解人际纷争,缓和人鬼、人神冲突,主张在一种温和、包容和平和的状态下,促进社会稳步发展;同时,某种程度上又具有含蓄性,从中能延伸出一种隐忍的文化性格;并蕴含着某种抗争、进取的精神气质。我们认为,集中反映苗族及其传统口承文化的苗族古经,是有别于儒、释、道、伊,具有独特地域性和民族性,一种温和化的和谐思想体系。
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苗族古经提法,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及文化相对性理念指引下,在追寻和重塑“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背景下,对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价值反思后的一种再认识和再定位,是将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从苗族民间文学视野中提升出来予以重新审视的一种历史实践。在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实体研究中经历了较长的酝酿和演化过程。换言之,它经历了从苗族民间文学经典走向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再定位的质变过程。它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视野时间较为晚近,同任何其它概念一样,将经历一个被认识、接受和趋于广泛应用过程。苗族古经,不同于《周易古经》《波斯古经》《汉志礼古经》等,由主体民族创造、官方认可、文字传承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样式,而是由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确认、口承的、一种非主流文化形态的特殊文化式样。由于苗族古经文化历史上长期游离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之外,以民间非主流文化形态存在着。所以,苗族古经这一提法,契合了“古经”一词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存在、作为对汉族地区民间故事广义上一种地方性称法这一事实。但是,与之相较又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由苗族生存的社会状态、地域环境和民族特征等方面铸就的、苗族古经文化蕴含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苗族古经提法,能够统括历史上苗族村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传统口承文化作品的各种样式。这是有据可循的。更重要的是,苗族古经提法,在中国大陆,开创了指称历史上无文字古老少数民族传统口承文化先例,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以及深远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苗族古经释义应当从三个方面予以把握:第一、苗族古经所指外延方面。如前述,刘锋先生已做出精辟论述。即苗族古经,是“苗族‘经师’在排解纠纷、祭祀大典与丧葬、巫事、庆典、动工等仪式场合吟诵的长篇说理、叙事、对话(人与神、人与人)等作品的统称。”这里,我们仅就苗族古经吟诵主体——苗族“经师”做适当延伸和诠释。具言之,上述所指苗族“经师”,在广泛意义上,或主要包括苗族村落社会中“理老”“寨老”(调解纠纷)、巫师(主持祭祀、祈禳、驱邪等宗教活动中的巫师、鬼师、占卜师、算命司、通司等)、“活路头”(启耕人)、“议榔头”(主持议榔)、“鼓藏头”(主持祖先祭祀)、“芦笙头”(主持节日娱庆活动)等苗族民间“知识分子”。从更广泛意义上,亦应将苗族村落社会普通民众纳入其中。因为他们是苗族古经文化变迁演进的实践者和传承主体。第二、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方面。我们认为,苗族古经本质内涵,是历史上苗族先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和总结出来,为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苗族古经之道,有别于儒家、释家、道家以及伊斯兰文化之道。苗族古经之道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苗族古经和谐之道及其温和文化的属性。它突显出苗族这一古老民族独特智慧和文化个性。第三、特别强调苗族古经文化形成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苗族这一命运多舛古老民族生存、迁徙、斗争的苦难历程,以及苗族古经文化不断累积和演化等方面。因为它们共同铸就苗族古经文化独特价值和智慧魅力。
[1] 刘锋.苗族古经之由来及其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2] 肖凯林.2010年贵州宣传工作年鉴[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188.
[3] 杨长泉.论民族法中的道德与强制力元素的平衡关系——以黔东南苗族理词为研究途径[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4):57.
[4] 王凤刚.苗族贾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5] 萨丕尔(Sapir Edward).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1.
[6] 徐晓光.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27.
[7] 田兵.苗族古歌(前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1.
(责任编辑 杨军昌)
2016-07-2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13&ZD137)。
于衍学(1982—),男,回族,山东泰安人,博士,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回族史学、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考古人类学与文化遗产。
C954
A
1000-5099(2016)05-0041-07
10.15958/j.cnki.gdxbshb.2016.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