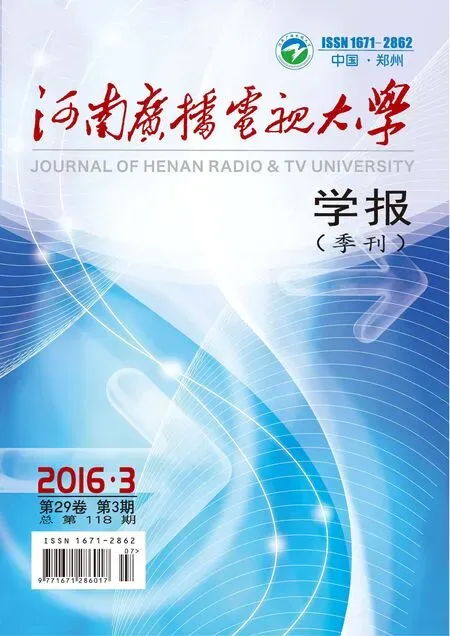读图时代的“救赎”:文本阅读与写作——兼谈大学语文教学
夏彪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学院,云南 丽江 674199)
读图时代的“救赎”:文本阅读与写作——兼谈大学语文教学
夏彪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学院,云南丽江674199)
在“读图”流行的当下,公共课大学语文的教学迎来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对大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现象进行思索,从读图时代下的文学处境、读图时代下的文本阅读、读图时代下大学语文经典阅读、大学语文教学发展四方面展开论述,结合教学实际,探索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和教材编写方面的问题。面对教学中呈现的征候,研究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应固守文学殿堂,回到文学的“诗意”之所;大学语文教学的未来应回到文学的本初之源,回到经典之乡,回归视觉生态:阅读与写作。
读图时代;大学语文;教学;阅读;写作
Roland Barthes在《图片语言》中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如今是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息。这一转变是有代价的。在传统的阐述模式中,其图像的作用只是附属性的,所以它回到了依据基本信息(本文)来表意,文本的基础信息是作为文本暗示的东西加以理解的,因为确切地说,它需要一种阐释。现在所形成的关系是,去解释或‘实现’文本的并不是图像,而是文本,是把图像升华、移情或是合理化了的文本。……过去,图像阐释文本(使其变得更明晰);今天,文本则充实着图像,因而承载着一种文化、道德和想象的重负。过去是从文本到图像的含义递减,今天存在的却是从文本到图像的含义递增。”[1]Roland Barthes的论述,精确描绘了“文本时代”与“读图时代”的特征。如今,读图时代给人们带来便捷和娱乐的同时,却也引人忧虑。往昔“诗意”的文学课堂在“读图”的渗透下逐渐被驱赶至边缘,在图像激增的大学语文课堂里,如何回到前文本时代,如何克服“如日中天”的“图像”时尚,在感性审美里,这是一个新课题。
一、读图时代下的文学处境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社会是“世界图像的时代”,我们被图像包围着。如今,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发达,从“双11”中商品的销量就可嗅出消费社会所引领的时代潮流。“双11购物的狂欢”,引领了时代潮流,形成全球、全人类的购物狂欢。这一现象,一方面使得人们进入到娱乐时代;另一方面商品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现代互联网购物消费,已经从传统的“实物”转向了“虚拟”。以“虚拟”直观的“图像”等同于现实中的“实物”。这虽然仅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在转变中,也能体察出这改变的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审美理念。一种原初的、深层次的、理性的理念逐渐在图像世界中被解压。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被图像解构,形成“诸神逃遁”“信仰隐退”,反而使得当下显出一片“虚无”。高校的课堂上,也未能幸免,特别是古典而富诗意的文学课堂也陷入图像的包围之中。在大学语文教学课上,图像充斥更甚。“读图”拉近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文学身处其中,艺术构思和想象力隐退,在“图像霸权”下,“韵味消退”“幻觉死亡”“文学终结”“艺术终结”等,使艺术处于自我解构中。艺术的神圣光环随着消费社会所引领的审美潮流导向边缘,使其进入“娱乐”“商品”的场域中。在其诱惑下,已消解了理性消费和审美理念:一种感性愉悦的追求。深层精神理念的消失,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枯萎”。正如吴子林所言:“与以高贵、优雅、严肃、庄重为内核的纯文学的沦落同步的,是以狂欢、平面、虚浮、感性至上为特征的大众审美趣味的高扬——图像、影像、视觉文化已然成为当今文化生活中的 ‘关键词’。”[2]关键词的背后,是“时尚”的追逐和“炫目性”的感官。为此,古老而传统的大学语文教学充斥“敌意”。教师在讲台上费力讲文学的“韵味”,但台下的学生在书桌上摆弄的却是移动设备,沉浸在各大商品网站上寻找“时尚”和“摩登”,使得课上出现“意义的落空”。表面上似是文学课堂的衰退,实质是“图文”关系的紧张。在大学语文教学的课上,学生在“京东”“淘宝”等网站上随意挑选着商品,不停刷屏。即便没有刷屏,耳朵里时常会有一根耳机线连通手机正在“读屏”,享受着“读屏”的愉悦。正如周宪所言:“‘读图时代’读图蔚然成风的背后也许有某种隐忧,那就是图像通过对文字的压制和排挤而产生了图像的‘暴政’。”[1]在这“敌视”的关系中,“读图”剥夺了“诗意”,消解了文学的韵味及文字中所隐藏的“悟性”。文字受到“冷落”,显得图像的“炽热”。与大学语文的“失势”相随的是文学被冷淡甚至被遗忘。
二、读图时代下的文本阅读
资中筠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好中文》中说:“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称谓的混乱充斥眼帘: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3]在资中筠的这段话语中,透出的现象令人忧虑。一方面正说明较为权威的电视媒体不应该出现错别字;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称谓的随意。这两方面表象的背后,显然有一个现象存在。第一,语文教育的缺失,母语地位被动摇,写作、写字能力薄弱;第二,经典的电视化,阅读习惯的改变,品位和趣味的流变;第三,文化的滥用,人文性匮乏,其背后是一种文化的陨落。在高校中,学生出现类似现象又何偿不多?反观其实质,学校教育应直面担当。在高校里,要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视大学语文教育,上好大学语文课程。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温儒敏教授认为大学语文的首要任务是:“以经典美文吸引学生,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重新调试过来!”[4]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欧阳友权教授在接受晏杰雄访谈时说:“大学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为中心,这一提法明确告诉我们,大学文学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大学语文教育,也不同于大学文学专业教育,而是以大学各科学生为对象,以文学经典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增强大学生人文教养为目标的崭新教育理念。”“我也在高校教文学课,我深感无奈的是:学生几乎不阅读文学经典,缺少想象中的诗意,文学感悟力已经削平,缺少思想深度。”[5]这个深度的访谈,揭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尴尬,也揭示了其背后的深层问题。
在视觉文化迅速发展的“读图”潮流中,阅读令人堪忧。“据我国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我国广义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2.2%,狭义的识字者阅读率为48.7%。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为 60.40%,2000年为51.70%,2001年为54.20%,2005年为48.70%。同时,国民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正在逐步淡化,2005年我国国民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只有84.1%,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6]从统计数字来看,读书现状“每况愈下”。正如米勒所言:“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成为主要是对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当然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但经典的概念需要大大拓宽,而且还应该训练阅读所有的符号:绘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资料。当今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能够阅读、能够阅读一切符号的人,而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里阅读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围绕并透入我们的所有符号,所有的视听形象,以及那些总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当作符号来阅读的历史证据:文件、绘画、电影、乐谱或‘物质’的人工制品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摆在我们面前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和其他符号系统,阅读是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聚集起来解决我们的分歧。这些自然也包括了理论文本”。[7]米勒的论述透出几点思索:第一,在视觉文化的发展中,图像在蔓延;第二,文学被迫扩大自己的“家园”,在文学“自为”的“阵地”上坚守维艰;第三,读文向“读图”靠近;第四,读文与读图有一个共同的根基——阅读。后来金惠敏对这两段材料解读道:“第一,‘阅读’向一切文本、一切可被阅读的符号开放,因而借助于‘阅读’米勒保持了对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的宽容和接纳;第二,‘阅读’显然又是一个暗示着现代性价值的概念,包括他这里所使用的‘符号’(sign)一词,即它总是有所指、有意味、有深度。”[7]从米勒的观点至金惠敏的解读,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第一,阅读是个宽泛的概念,涉及书本及之外的符号阅读,但有一个相同维度;第二,符号阅读的根基是文本的阅读;第三,阅读包含理论的文本阅读;第四,阅读是对经典文本的阅读。米勒强调了宽泛的阅读,但米勒又迂回至文学本身。米勒对文学的强调,不仅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而且也守住了文学的根基。李衍柱在《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中说:“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魅力。大学语文的教学的根本,就是守住语言的坚实之所,守住文学存在的根基。在读图时代,重返经典阅读之乡,让视觉生态回归阅读。
三、读图时代下大学语文教学的中心:经典阅读
王余光教授倡导“阅读,与经典同行”。对于经典的观点,不尽而然。经典,“经”即“經”,是“织物的纵线”,引申出“规范”“标准”“量度”等义;“典”即,册在架上。“经典”二字,道出了经典的规范作用和书籍的重要性。下面就从“经”和“典”两个方面对其论述。“经”的意义较为宽泛,可以指思想、道德、行为等,也可以指专著(诗经、易经、经书、经卷、经文、经义、经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黄帝内经等)。在专著方面,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十三经既是中国文人士大夫读书的内容,也是文人士大夫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衡量一个人学识、学问高低的标准,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引擎,中华文化的生命。“经”也指“经籍”“经典”,即典的用意,书籍。关于“经典”的论述,试观卡尔维诺的几点论述。其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其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其四,“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3]以上四点论述,可谓深刻。第一,经典是“重读”。相比今天,阅读是快餐式的阅读、“提及多于读过”,乃至没有阅读。第二,经典丰富生活经验,驻足于人的生命体内。一方面能够增加阅历,另外一方面也能指导、丰富人生,成为成长中的宝贵财富资源。在读图时代,与外界的“距离”消解了,真实体验和感悟也会消退,不可避免进入“无距离”的人生体验,反而使得生活单调乏味,出现如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似的苦闷与彷徨。第三,经典是潜藏在人类潜意识和无意识中的文化,深深扎根于人类的记忆里。在人类成长的时候,经典是流传的基因,是人类文明代代传承和延续的不竭动力。当人类使用之时便不知不觉走到人类跟前,走进生活。第四,经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在经典中,不仅有古人留下的思想智慧,也有古人留下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不仅有古人做人处事的根本理念和方法,也有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不仅有文人墨客的生活印迹,也有古人生活的创奇和影子;不仅有风趣的故事,也有文化典故。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然与中国众多的经典古籍分不开。然而,经典无国界,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有人提出应该加入外国文学作品。在西方,英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宁可不要100个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中国的经典不能少,西方的经典同样如此。重新拾起被抛弃和遗漏的智慧、文化、传统、历史、价值、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审美情趣和趣味等,从阅读开始,从经典开始。当大学语文教学中重新拾起经典,再次养成阅读习惯。在不久的将来,资中筠先生的忧虑和读图时代的忧虑便会随之消解。正如卡尔维诺在文章的最后说:“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3]这虽然是一句悲伤的话语,却也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无用之用”。正是缘于此,经典才真正回到经典之乡,回到栖居之所,在那里发出悠扬的笛声,回到“大美世界”。也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言:“今人不可多读古文,但不可不读”。“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审美品位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你的品位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3]
四、读图时代下大学语文教学发展:写作渗透
梁启超说:“一个人在学生时期能否养成读书兴趣和读书习惯是一件人生大事,将影响其一生的幸福和发展。”可见阅读对其人生发展有着重要性。李瑞山关于大学语文教学说:“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使学生经由包括而不是只有‘文学’的多样文体文本的阅读、领会,把握汉语文的多种境界和多种表达交流方式,以便在较文学广阔得多的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中享受语文的魅力。”[9]虽然大学语文教育不培养小说家和诗人,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下,地方高校调整了自我办学特色和理念,以“应用型”为主的本科不断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孕育而生,显然“应用型”的写作和语文阅读的能力本不可少。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强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10]陆机关于创作构思的论述,从中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阅读是创作的基础,也是创作的前提;第二,写作需要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第三,高境界的写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并受其滋润;第四,创作是融合观察、体验、品味、吸收、感悟等的活动。再看其艺术构思的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10]陆机的创作理论,不仅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阅读对创作的重要性。
写作技能的提高及运用,与阅读相关。在强调阅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写作理论的强调和学习。写作虽然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根本宗旨,但了解创作,学习创作,这样才能更好阅读。以写作为契机,以阅读为抓手,提高和加深对阅读经典重要性的认识。避免阅读仅是泛读和空读,一定的练习和写作有其必要性,至少可避免“眼高手低”的局面,甚至写错别字和病句的现象。在练习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进阅读能力的提升。试举一例。“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撒上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掉弄着丫叉的舌头,啼声宛转,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德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驽骍难得,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11]这一段话是名著《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出游时的描绘。塞万提斯如此用笔,自然不仅仅只是一种描绘。第一,塞万提斯描绘出一幅富含韵味的画面,烘托出堂吉诃德游侠时代的氛围;第二,通过描绘,为堂吉诃德出游做“漂亮”铺垫,激发读者无垠想象;第三,塞万提斯为骑士“英雄”出游做伏笔,给堂吉诃德的出游增添“戏剧”色彩;第四,对出游大肆渲染,形容词和色彩词汇的使用,为堂吉诃德的出游染上了神圣而又神秘之感。
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进行趣味性写作。创意写作在西方已经有一段时间,但中国起步较晚。其实,中国不缺乏创意,中国有丰富的创意内容和资源:经典。在经典中学习创意写作,这是中国写作的优势。当然,大学语文的教学要处理好阅读与写作关系。写作是一种引导。将学生引向文本阅读,在阅读中学习,回到文学本身和文字本身,而不是抛开阅读谈写作,也不是抛开文学、文字谈写作。在阅读中,让世界的“景象”随着文学的阅读而深入到传统的“诗意栖居”之所,回到文学、文字之美的场域中。这或许便是大学语文发展的方向——读图时代的“救赎”,即文本阅读与写作。
通过大学语文的教改,还原大学语文教育中语言之美,还原大学语文教育的诗性之美,阅读并感受经典文学的“诗意”之美:书页间散发的书香、墨香及其书中隐藏之真、善、美。体验书中包蕴的生命之真,感受体悟书页间彰显的善,享受墨间弥散出的语言文字之美。在阅读中感怀其宇宙、时间、空间、历史、生命之情怀,让生命的浪花向着理想的彼岸驶去。
[1]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吴子林.“文学终结论”刍议[J].文艺评论,2005,(3).
[3]郑思礼,主编.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9).
[4]温儒敏.中国语文:经典美文重塑大学语文[N].中华读书报,2007-04-18.
[5]晏杰雄.网络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欧阳友权教授访谈 [N].文艺报,2013-04-08.
[6]龙丽,刘青,屈会芳.读网时代的纸本阅读及其发展趋势[J].图书馆论坛,2008,(10).
[7]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8]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J].文学评论,2002,(1).
[9]李瑞山.论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与内容构建[J].中国大学教学,2007,(6).
[10](晋)陆机,著.文赋译注[M].张怀瑾,译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1]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G642
A
1671-2862(2016)03-0098-04
2016-05-18
本文系2013年度云南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科):“读图时代独立学院大学语文应用型教学模式研究”(云教高[2013]106号)的研究成果。
夏彪,男,云南楚雄人,哲学硕士,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学、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