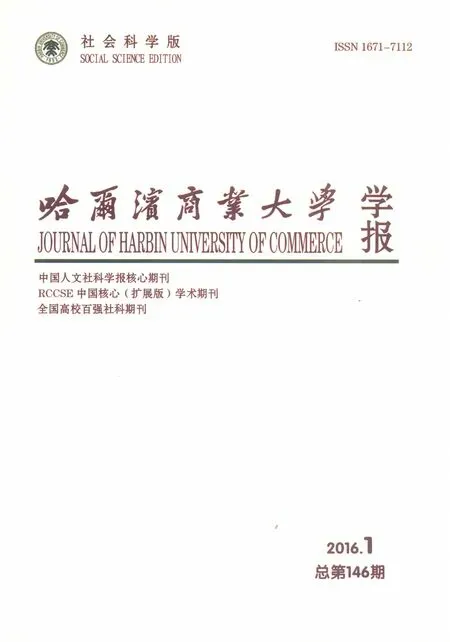论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付鹏远
(加州大学 法学院,美国 洛杉矶 900024)
法学研究
论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付鹏远
(加州大学 法学院,美国 洛杉矶 900024)
摘要:涉外协议管辖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重要制度之一,它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我国于2012年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并于2015年初颁布了最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然而其中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仍有待完善。具体来说,应厘清并拓宽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突破“实际联系原则”的羁束,探索灵活多样的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以及引入和补阙“公共政策”及“弱者保护原则”的规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完善涉外协议管辖有助于解决纠纷,并促进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涉外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原则;公共政策
协议管辖是指由当事人双方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达成管辖权协议以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1]。涉外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体现,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各国在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上的法律冲突,还可以增加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争议解决以及保障交易安全,最终促进国际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案件的结果往往主要取决于选择法院,而法律选择变得无足轻重”[2]。我国于2012年8月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民事诉讼法》),并于2015年1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并不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地不甚合理;第二,“实际联系原则”限制了涉外协议管辖法院的范围;第三,法院选择协议的形式要件较为单一;第四,关于“公共政策”及“弱者保护原则”的规定存在一定缺漏。本文将对相关外国立法及国际条约进行考察并与我国现行立法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就上述问题为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新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及变化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涉外协议管辖上较旧法而言发生了立法结构的变化,其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删除了原《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就涉外协议管辖的特别规定,并在第259条中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据此,涉外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合并适用新的《民事诉讼法》第34条关于国内协议管辖的规定,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与原《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相比并无实质变化,当事人涉外管辖协议的成立及有效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管辖协议项下的争议类型仅限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2)当事方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达成管辖协议;(3)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需要与争议存在实际联系;(4)管辖协议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另外,就前述第(4)点属于专属管辖的案件,新法与旧法相比亦未发生实质变化。根据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31条第2歀,《民事诉讼法》第33条和第266条规定的属于中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对其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具体包括四类纠纷:(1)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3)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4)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新的《民事诉讼法》将涉外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合并规定这一立法结构的变化,国内学者有的支持,认为这整合统一了立法,贯彻了国民待遇原则,符合协议管辖制度的本质[3];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涉外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存在实质不同,不应混同合并[4]。笔者认为,虽然两类协议管辖存在区别,但《民事诉讼法》第34条仅是对协议管辖的一个总体规定,其并不代表新法否定涉外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之间存在差异,也不会影响我国后续就涉外协议管辖的特殊性以司法解释等形式建立单独适用的规则。
此外,在2015年1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我国首次在“弱者保护原则”这一方面进行了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的第31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是我国协议管辖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顺应了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下越来越多的个人以私人身份参与跨境商品及服务消费的趋势,能够更好地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之利益。但是笔者认为,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在“弱者保护原则”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综上,关于涉外协议管辖,新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与旧法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较相关国外立法和国际条约而言,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以下本文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探讨。
二、我国现行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涉外协议管辖制度适用范围的厘清与拓宽
关于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从正面来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该适用范围限于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反面来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3条和第266条,该适用范围排除了应该由中国法院专属管辖的四类案件。上述规定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首先,“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这一表述比较模糊笼统,无法为当事人及法官厘清界限,不易于实践操作。涉外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外延止于何处?涉外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劳务合同项下的劳资纠纷是否属于此限,在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过是否可将某些涉外婚姻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这样的观点,比如法国法就有这样的规定[5]。
其次,专属管辖的案件种类较多,导致从反面将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的过窄。在世界范围内,涉外协议管辖制度早已被广泛接受并且其适用范围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对此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外国立法及相关条约对专属管辖的严格限制。《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第24条规定的有关不动产和土地的案件、第29条之1规定的住房的使用租赁或用益租赁的案件以及第32条之1规定的环境案件[6]。2012修订的《布鲁塞尔条例I》第24条规定了五类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1)以不动产物权或其租赁权为标的的诉讼;(2)以公司、其他法人组织、自然人或法人社团的有效成立、撤销或歇业清理,或以有关其机构的决议是否有效为标的的诉讼;(3)以确认公共登记效力为标的的诉讼;(4)有关知识产权的注册或效力的诉讼;(5)关于判决执行的程序①Regulation (EU) No. 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24.简称为《布鲁塞尔条例I》,该条例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了修改,并于2015年1月10日实施。。反观我国规定的四类专属管辖案件,较上述立法和条约相比明显存在滞后和偏差,其中仅不动产纠纷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属地性质而具有保留的合理性,而其他三类专属管辖案件则应顺应我国国际经贸的发展需要逐步放开。
就上述问题,我国立法应厘清并逐步拓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首先,在现有正反两面结合的立法模式基础上,结合相关国外立法、条约以及我国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现有规定中“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边界。比如,“合同”是否包括商业保险、不动产租赁、私人雇佣等几类较为特殊的合同,以及由婚姻、继承、侵权、收养、信托等民事关系引发的财产权益纠纷是否属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其次,调整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种类。效仿先进国家立法及相关条约的规定并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下新形势的需要,将港口作业纠纷、继承遗产纠纷、中外合作合资合同纠纷排除在专属管辖适用范围之外,而对于专利、版权、公共登记、环境方面的纠纷可以考虑逐渐纳入专属管辖的范围。这样减少了我国涉外协议管辖的国家保护色彩,增加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素,使得外国投资者、贸易合作者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机遇时减少对法律救济途径上潜在的不方便或不熟悉的担心,促进“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国际经贸的发展。
(二)“实际联系原则”对协议法院范围的羁束与突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于如何认定“有实际联系”,《民事诉讼法》第34条以不完全列举的形式规定了较常见的五类: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聚丰网络有限公司与韩国MGAME公司网络游戏代理及许可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裁定书中侧面认可了当事人选择一国法律作为合同适用的准据法也属于“实际联系”的范畴。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三终字第4号》,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http://ipr.court.gov.cn/zgrmfy/jsht/201206/t20120626_148977.html),2015年10月17日。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实际联系”的确定不应仅从“事实联系”的角度来判断,还应适当地从“法律联系”的角度进行考量[7]。
然而“实际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协议管辖制度的设计宗旨,并限制了当事人对私权处置的意思自治,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及国际公约的规定相背。例如,德国和美国在其协议管辖中都没有要求协议管辖法院与纠纷具有“实际联系”;2000年的《布鲁塞尔条例I》以及2005年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中也没有规定“实际联系原则”。而且,“实际联系原则”限制了当事人对那些与纠纷没有实际联系的中立法院进行选择。而在国际贸易中各方当事人通常来自不同国家,由于彼此不熟悉或不信任对方的司法制度,通常双方更倾向于达成妥协选择公正、高效的中立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所选择的法院一般都在该类案件上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比如,一般在外币跨境融资交易中当事人多倾向于选择英国法院进行管辖。因此,严格要求“实际联系”不利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所以现代各国国际民事程序法发展的趋势,是不要求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8]。国内许多学者都对“实际联系原则”持消极的态度。
涉外协议管辖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产物,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尊重当事人自由处置私权,方便当事人更好更快地解决纠纷。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应逐渐弱化“实际联系原则”的限制,放宽当事人可协议选择的法院范围,同时为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及国家利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涉外协议管辖的制度设计,引入“公共政策”的规定,从反面否定与我国重大利益和基本政策相抵触的法院选择协议之效力。
(三)探索法院选择协议成立之形式要件的灵活与多样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法院选择协议成立的形式要件规定的较为单一,其第34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法院选择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而反观相关国外立法和国际公约,法院选择协议成立的形式要件呈现逐渐放宽、灵活多样的发展趋势。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其管辖协议可以采取书面方式或经书面方式证明过的口头约定的方式。美国和法国的法律也未强制要求法院选择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6]。2000年12月欧盟理事会颁布的《布鲁塞尔条例I》进一步拓宽了法院选择协议成立的形式要件,该条例第25条规定法院选择协议可以是书面的形式,也可以是可被书面证明的其他形式,抑或是双方业已确定的惯常形式,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双方业已或应该知晓的该类商贸活动中已被广泛知晓且通常遵守的做法①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25.。之后,2005年通过并于10月1日生效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法院选择协议成立的形式要件作出了再一次的突破,该公约第3条规定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通过其他任何通讯方式可以表现可理解的信息②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Article 3. 中文称为《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该公约于2005年6月30日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二十次外交会议上通过,并于2015年10月1日生效。。
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时代,网络交易、电子商务在国际经贸活动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将法院选择协议的形式要件严格限制为单一的书面形式,将十分不便于当事人就国际民事纠纷协议选择法院,会极大地阻碍国际经贸活动的发展。根据我国《合同法》及2015年最新修订的《电子签名法》的规定,我国对协议的“书面形式”应作广义的理解,其中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但即使就“书面形式”作广义理解也无法冲破现有的窠臼,不能涵盖可经录音证明的口头约定、当事人默认的惯常做法等灵活多样的成立形式。因此,我国应逐渐放宽对法院选择协议形式要件的限制,规定更加灵活宽松的成立形式,使之符合当今国际民商事活动发展要求,与目前国际上逐渐放松形式要求的趋势实现一致[9]。
(四)“公共政策”及“弱者保护原则”的引入与补阙
在协议管辖制度不断发展扩张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国外立法及国际条约出现了一些对协议管辖的合理规制。这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的规定,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体现为对弱势地位当事人的倾斜性保护。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是美国法学会基于对大量判决先例和理论学说的整理研究而得出的成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指导意义。该重述第80条规定:“当事人关于诉讼地点的协议将被赋予效力,除非这样一个协议是不公平或不合理。”①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 of Laws, Section 80, 1986 Revision.《法院选择示范法》第3条也作出同样的规定,并列明违反“公共政策”的五种情形:(1)法律明确要求诉讼应由协议选择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审理;(2)原告在协议选择法院无法获得有效救济;(3)协议选择的法院不方便管辖;(4)法院选择协议是通过误导、胁迫、滥用经济权力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达成的;(5)存在其他原因导致执行法院选择协议不合理、不公正②The Model Choice of Forum Ac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7, No. 2 (Spring, 1969), pp. 292-296.中文译为《法院选择示范法》,由美国统一州法国家委员会于1968年批准。。另外,有美国学者认为,对于“公共政策”应分两步来审查,首先适用州法对法院选择协议的有效性进行判断,在法院选择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再通过联邦法对法院选择协议的可执行性进行考量③Matthew J. Sorensen. Enforcement of Forum - Selection Clauses in Federal Court after Atlantic Marine. 82 Fordham L. Rev. PP. 2552-2556.。
在德国,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协议管辖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法律主体,包括商人、公法上的法人、公法上的特别财产、在德国无普通审判籍的当事人,而且除少数例外情况管辖协议必须在纠纷发生后缔结[6],从而有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防止一些企业凭借其在交易中的强势地位通过格式合同事先选择对其方便或有利的管辖法院。
此外,随着两大法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一些区域立法和国际条约逐渐开始对“公共政策”和“弱者保护原则”进行整合。2005年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一方面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规定若承认法院选择协议将导致明显的不公正或明显违背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实际受理法院应终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另一方面又基于“弱者保护原则”排除了消费合同、雇佣合同对排他性协议管辖的适用④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Article 2 and Article 6.。
最高法2015年1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了关于协议管辖中弱势地位当事人特别保护的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第31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有权主张管辖协议无效。这条规定是我国协议管辖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在立法上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倾斜,合理地限制了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协议管辖的情况。尤其在跨境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往往缺乏交易经验、不了解国外法律,而跨国企业在法律信息、资金状况、交易经验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交易双方的地位差距更加明显。因此,从立法上预先作出倾向性设计,以防弱势一方在纠纷产生之前因格式合同、疏忽大意、判断失误、缺乏经验而接受不利于自己的管辖协议,这属于对实体正义的正当追求,是我国立法上的进步。
但是与国外立法相比,在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制上,我国仅对消费合同规定弱者保护还远远不够,应在今后立法中从以下两点进行完善:首先,在“弱者保护原则”上我们应该将劳动雇佣合同、个人保险合同纳入保护范围。其次,在立法上引入并融合英美法系的“公共政策”规定,与其把公共政策问题留到承认与执行阶段解决,还不如在管辖权阶段解决[10]。
三、结语
在法院管辖权的确定上,是否承认协议管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协议管辖,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11]。虽然我国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上作出了一定的改变和发展,但是仍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不足,这既不符合国外立法、国际条约在协议管辖上的立法趋势,也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加快发展同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实际需要。因此,笔者建议应在厘清现行涉外协议管辖制度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进一步拓宽其适用范围,就涉外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进行多样灵活的规定,逐渐减少“实际联系原则”对协议选择法院范围的限制,并通过引入“公共政策”和完善“弱者保护原则”对涉外协议管辖进行合理规制,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同国际社会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
[1] 徐卉.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4.
[2]Friedrech K.Juenger. 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 (special edition).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5.
[3]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J].法律科学,2012,(6):164.
[4]李旺.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制度析——兼论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J].国际法研究,2014(1):92.
[5]邓杰.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669.
[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谢怀栻,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7]杜焕芳.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之检视--兼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4号裁定书[J].法学论坛,2014,(4):95.
[8]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9]何其生.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民事诉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0]郭玉军,蒋剑伟.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22.
[11]李双元.关于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思考[M]//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海事法律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邹学慧]
Shortcomings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Foreign Agreement Jurisdiction System
FU Peng-yua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900024,U.S.A)
Abstract: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ur amended in 2012 the “Civil Law” and earlier this year issued a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however, where agreements concerning foreign jurisdiction provisions have yet to be perfected. Specifically, it should clarify and broaden the jurisdiction of foreign institutional scope of the agreement, breaking the “actual contact principle” custodial beam, explore flexible formal requirements governing the agree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Buque “public policy” and “weak protection principles” requirement. With that “along the way” strategy,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ore closely, improve foreign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helps resolve disputes and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Key words:foreign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the actual contact principle; Public Policy
中图分类号:F746.12;F752.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112(2016)01-0118-06
收稿日期:2015-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