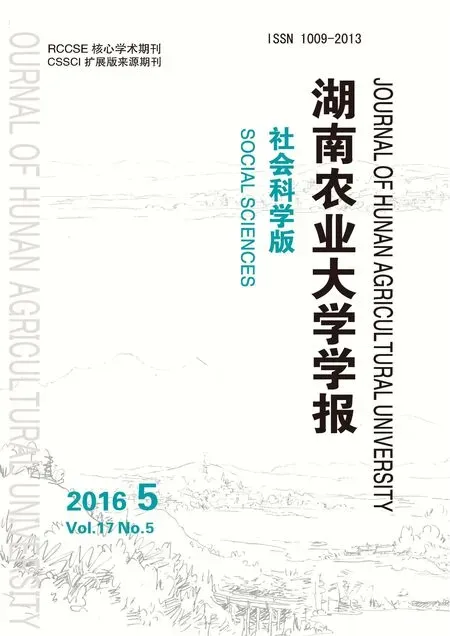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与治理启示
——以G省W村农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
周如南,朱健刚
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与治理启示
——以G省W村农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
周如南,朱健刚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以G省W村村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分析社会转型中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随着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村委会组织陷入瘫痪后,代表W村村民利益的自组织临时理事会利用社区传统中的宗族结构,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并通过娴熟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操作以及恰当的话语表述,依法依理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部门在维稳框架下展开了博弈,最终促成了事件的顺利解决。从W村农民抗争案例可得到如下乡村治理启示:必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群体事件中的压制性治理模式亟待变革;应发挥民间自组织的协同管理作用。
农民;抗争政治;行动逻辑;治理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和大规模城镇化运动的出现,农村地区由于土地纠纷引发的土地维权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已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1]。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社会议题,部分学者开始从组织和分层研究的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转向对社会变迁的关注[2-5]。在中国农村基层的集体行动研究中,初步形成了“以法抗争”[6]和“气与抗争政治”[7]等解释框架。G省W村在2009年的集体行动中成立了“临时理事会”,围绕土地议题展开了全村动员式的维权行动过程,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框架整合”下的“动员结构”[8],即一个集体运动的领导者通过发觉主流社会(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亚文化)中被广为认同的不满,以此来推动事件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集体行动又表现出与西方背景下的社会运动所不同的“嵌入式行动主义”[9-10]特征。笔者拟在描述这一个案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该集体行动从对抗到和解并得以解决的背后,其成立的村民自组织形态与代表国家权力的省、市、镇政府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与妥协?村民自组织如何利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地方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实现了集体动员?在抗争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了哪些非决裂和对抗式的行动策略?对当前农村治理有什么启示?
一、W村土地维权事件始末
W村是位于中国东南地区海滨的一个行政村,隶属于L市D镇,共有2 000余户,1.3万多人,下辖6个自然村,由47个姓氏的人群组成,其中“薛”、“孙”、“陈”等是大姓,彼此有联姻关系。各个姓氏都有宗族理事会作为村庄内的非正式组织化权力机构掌管本姓氏红白喜事和调解相互间的矛盾纠纷。W村作为一个有众多宗教信仰的村庄,遍布着十几座分别供奉着福德老爷、福德婆婆、观音菩萨、妈祖天后等各路神灵的庙社,还有体现祖先崇拜的宗祠和西方舶来的供奉着耶稣十字架的家庭式教堂,多元信仰体系和谐共生,成为W村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计模式上,该地区被称为“三半地区”①。这种混合式生计模式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沿革相关。此地在清朝时期是“巨舰舴艋大小闲集”②的重要港口。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W村于1956、1957和1960年修筑拦河堤坝并开展围海造田运动。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土地开发,W村的耕地面积达到六千亩。伴随着港口淤积带来的港口功能削弱,耕地作为生计载体的作用开始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促使W村村民生计模式进一步多元化,甚至一度盛行海上走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地贯彻“多种经营”方针,一些滨海低洼的围涂改种植为养殖,渔业的重要性有所回归并逐渐出现废耕现象。1995年大台风时,当地海水倒灌,大面积耕地被淹,导致大量土地因无法耕种而抛荒。如今青年人多在珠三角地区经商和打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营意识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城郊土地附加值增加,村集体通过公司化运作盗卖土地以获利的现象开始出现。1993年W村成立W港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认为是村委会小集团以市场化手段盗卖土地的开端。这个公司由村支书X任法人代表,注册资金500万,经济类型为集体经济。村民在此后的20多年中除得到1992年卖宅基地每人50元分红和1993年政府修东海大道的征地补偿款每人500元之外,没有其他“分的钱”③。
2009年4月3日清晨,村里各家的门上都被神秘地塞上了一张题为《给W村乡亲们的信——我们不是亡村奴》的打印传单,对村委会盗卖土地、官商勾结瓜分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控诉:……养殖猪场、海马养殖基地、虎舌尾旅游区、别墅区和亿达洲以北至外龙路口的上万亩土地等等一些不知名地皮的公款一直不知去向,敢公开吗?”这封落款为“爱国者一号”的千字公开信在村民心中引起巨大触动。
“爱国者一号”留下了QQ号,很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都加了他的QQ,“爱国者一号”还组建了两个QQ群,名为“W热血青年团”,群中成员最多达到近千人。W村的年轻人在群里热烈讨论土地贪污问题,并共享他们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包括内部协议、政府批文、占用耕地清单等等。网络社交软件的使用跨越了物理社区边界的局限,赋予村民们尤其是在外打工或经商的年轻村民以围绕土地议题展开公共讨论的空间并形成强烈认同。他们在进行激烈讨论后,决定在2009年6月21日到G省政府上访“讨说法”。这是W村村民的首次行动。
“W热血青年团”也因这次行动而正式组织起来并在网上创建了网络空间,空间上这样写道:“W热血青年团成立于2009年6月21日,因621活动而组织成立。”从此,“W热血青年团”走上了理性维权的上访之路,他们到14个部门共上访了11次,但收效甚微。面对困境,有人提出应该发动更多村民参与到维权行动中。因为之前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主要通过网络开展,所能涉及到的对象多为村里的年轻人,老年和中年人群体未能有效地动员起来,于是年轻人们决定联合更多村民开展行动。“W热血青年团”决定“在村里物色可能支持起事的人,一个个召集”。最终,他们召集了四五十个行动骨干,计划在2011年9月21日召开村民大会。当天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村民表述有三五千人,后来的LF市政府则公布说是400人),经商议决定到LF市政府上访。
2011年9月21日,以“W热血青年团”为主的组织者拉出几十米长的白布条让大家签名、按手印。集合完毕的W村村民举着请愿书,浩浩荡荡游行至LF市政府。市长出面接受了请愿书并答应解决村民的合法诉求,并承诺市、镇两级将组成工作组进入W村调查核实相关问题,每7天公布一次工作进展,要求W村“两委”要全力配合工作组,村民代表参与监督。W村村民开始往回走,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打砸事件。当晚东海镇派出所拘留了三名W村青年。
9月26日,市、镇两级组成工作组进驻W村,此时,村委会相关负责人神秘失踪,村委会组织陷入瘫痪,由全村47个姓的代表组成的临时理事会在村民大会上通过代议民主制选举正式产生。近两个月过去了,面对市镇工作组缓慢的工作进展,村民们的不满情绪再次出现。11月21日10点30分,在临时理事会的组织下,W村村民决定再次到LF市政府上访,这是一次和平的上访,并未出现暴力冲突。12月9日,村民代表XJB等在餐馆吃饭时被警方的便衣带走,ZLH等分别在深圳和佛山被警方带走。12月10号凌晨一点多钟,警车再次来到W村,对村庄进行封锁。当天,村民决定封路以防警察入村再抓人,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12月11号凌晨4点30分开始,村口再次响起警笛,双方继续对峙。当晚,村民收到XJB死讯,宣称死于心源性猝死。死者家属要求归还尸体被拒绝,看过尸体的家属称尸体有明显被殴打虐待痕迹。12月17日,W村举行村民大会,要求在5天内交出XJB的尸体,否则将到LF市政府进行游行示威。S市及其下辖的LF市政府也大为紧张,调动了更多警力前来,以防事态失控。至此,W事件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12月20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Z带领省委工作组来到当地处理事件。Z书记在LF干部群众大会上做出“人民内部矛盾”定性和“以人为本,宽大处理”的处理精神发言后,当晚政府和村民分别撤掉了自己设置的路障并准备和谈。21日早晨,LZ到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与Z书记谈话一个小时后回到村庄。他说,省委工作组基本答应了村民关于土地、选举、财务和放人的要求。“Z书记说,村民的诉求是合法的。这对于接下来解决各种问题开通了渠道。这有利于各种工作的展开,也有利于拉近感情。原来所造成的感情障碍被清除。Z书记下来工作,对工作组成员已经说明,一定要查清。涉及到哪一级就查到哪一级。我对今天的会面效果感到满意。”“接下来的村民大会还会讨论恢复生产生活,来欢迎工作组进村!”
二、W村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
在新社会运动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的综合视角下,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被认为是在文化演进与互动过程中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一种行为表现。W村农民抗争事件本质上是因土地利益而引起的农民维权活动。W村农民在其土地合法权益受到侵蚀时,维权意识日益觉醒,而以“W热血青年团”为代表的维权精英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动员能力,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表达农民的抗争诉求,最终促成事情的顺利解决。
1.W村农民维权意识的觉醒
在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地区,这类由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建嵘指出,土地纠纷占到了农村“群体事件”比例的65%以上。据于建嵘估计,自1990年以来,中国地方官员强占农村用地约672万公顷,而农民拿到的土地赔偿金和土地实际市值之间相差悬殊,所以农民相当于损失了人民币2万亿元左右[1]。一些地方政府和村干部通过秘密交易,将土地状态从农地改为城市用地以便用于建设项目,然后将土地使用权卖给开发商以牟利。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利益都落入了村干部和开发商的腰包,一些村民常常对土地使用权被甩卖感到愤慨,更对没有获得按市场价值计算的补偿感到非常不满。
村委会之所以可以卖集体土地,是因为集体土地产权具有模糊性和不完整性。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尤其在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价值的增长速度很快。那么,谁将享受土地的增值收益?根据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收益应由乡镇、村、村民小组集体和村民共有,但各相关主体分别拥有多大收益权并不清晰。冯长春等认为,主体和产权的模糊性造成征收集体土地的赔偿标准较低和城市的低成本扩张,同时也引发集体土地上的“非正式开发”蔓延。这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非正式开发背后隐藏了太多非正式利益分配的勾结,引发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正是W村村干部侵吞卖地的收益导致村民集体愤怒。W村村民的直接诉求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这一诉求诱发财务公开和选举问题,后面两个诉求由土地利益诉求引发。在W事件平息后不久的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再次重申要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信号,因为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事实上,在试图将集体产权清晰化的摸索过程中,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多种经验。已有经验模式包括苏南地区的“三集中”、珠三角地区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尝试等,而重庆和成都目前也正在改革实验区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验。1992年,珠三角地区的南海市首先试行土地股份制,后扩展至珠三角,当前G省的农村集体用地仍在推行股份制改革,这是所谓“G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制度创新,预计W村土地纠纷的解决最终也会以股份制的形式处理。
从经济收入结构来看,土地收益并未成为W村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打工经济、商业经济是W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城市中,他们多是所谓的农民工。基于来自文化传统所沉淀下来的“根”、“家”的观念与现实的情感寄托以及城市中二元社区形成的事实和一系列制度排斥,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难以实现异地永久居留。随着年龄周期的发展,结婚生子这些人生过程就会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家庭人口再生产带来的生活压力以及社会融入困难带来的孤独感等等往往成为“推-拉”理论中所说的“推力”,必然将这些劳动力价值已在城市耗尽的农民推回乡村社会。
城市非久待之地,乡村土地红利又无法获得,他们难免会对未来绝望。拿回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几乎唯一选择。这时,农民集体记忆中对土地深厚而淳朴的感情被激发,成为集体行动的情感之根。ZLH在他的网络空间中饱含深情地回忆母亲当年参与填海造田运动时的艰辛:“母亲十二岁那年就被公社叫去修水利,一支扁担要挑起八十斤的泥土,在长年累月的训练中我母亲都成铁人了。十三岁的母亲当时挑到了一百二十多斤,这可是专人称过的,因为要论工值记工分。W村修大坝我母亲当时就参与了,填海造田我母亲更是‘无夜无日’。当时我母亲才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一大片两三个人深的海就这样被她们一大班人给填平了。那片地就是后来的咸田、现在的W综合市场和正被村官和富商炒卖的土地。”
“还我耕地,耕地是农民的命脉,农民没有耕地难以生存。”这是W村村民在集体行动中喊出的口号。虽然实际情况却是W村多数年轻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生意,他们大多来到了珠三角地区,土地早已不是他们的劳作对象。这些年轻人看到了“南海模式”的鲜活案例,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家乡没有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村土地的集体出租分红模式?ZLH说,“他们的地是集体出租,有集体收入,有分红。我们W村从来没有。为什么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不是嫉妒。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在合理的增值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建立之前,随着土地增值利益不断增加,基层政权组织与民众之间“争利”的矛盾日益激化。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觉醒,表面上表现为公民维权,实际上却受到国家社会关系下社区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的影响。“土地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农民财产权保障问题引发的剥夺感导致的普通村民群体与基层政权及村委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
2.W村土地维权的集体动员
利益的受损和维权意识的觉醒是村民土地维权行为的导火索,但它的真正发生还要经历一个集体动员过程。斯科特在《道德经济学》中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农村社区共同体中的道义、情感责任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具有重要规范意义。他认为集体行动中的共同利益是农民参与其中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而柏博金则在《理性的农民》中提出,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并不足以使农民起而行之,参与到维权行动中来,农民对集体行动的参与首先是基于个体主义的利害权衡,其次需要强有力的维权精英和有效的动员机制,从而克服奥尔森意义上的“搭便车困境”。
在上述叙事中可以看到从“一张传单”到“一个QQ号”到“W热血青年团”到“五十人起事”到“全村团结”的全过程。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过程、资源动员和框架建构理论更关注个人意识如何发展到集体行动的问题,似乎集体行动是一种完全理性主义的策略性动员。其实,W村集体维权行动最初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策略性,更多是一种在既有体制框架内开展个人利益诉求的行动。这时,体制内部利益表达机制缺失问题就凸显出来。“W热血青年团”的年轻人最初是有耐心的,他们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进行了11次上访,向多达14个部门表达利益诉求,然而多数上访未有结果,也正是他们多次的温和而无效的上访促使了村民不断觉醒和团结。
W村的传统宗族力量、民间组织与信仰力量较强,各自然村都有属于自己村内部的庙社和公共空间。在集体维权过程中,自地方政府派出机构村委会组织瘫痪以来,老中青三代精英层密切配合,传统宗族资源被有效调动起来,成立了联合起全村1.3万人47个姓的临时理事会,充分发挥了地方自治的功能,带领村民进行有组织的利益博弈。一位洪姓代表说:“当时在仙翁戏台开大会的时候,就让各个姓的代表上台,每个姓按照人数多少上来3~5名代表。这样就有117人,后来在这117人中选出了80个人,最终在80人中选出12个人组成临时理事会。这个也是一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应该说我们初步步入了民主选举阶段!”
LZ、ZLH、XJB等几名带头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维权集体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LZ 是理事会和青年团体推举的“领袖”。LZ是共产党员,当过兵,“在部队做过官”,做过村官和D镇开发区干部,后来经商,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熟悉政府、市场、农民各方利益纠纷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村庄里享有崇高的威望。死去的XJB也是一个道德化社区领袖,他本身在村庄正式权力结构体制内并无位置,之前是一个小商人,外出打过工,做过鞋面半成品加工,还在家门口开过“波记大排档”。因此和村民们接触较多,大家对他正直不阿、嫉恶如仇的秉性多有了解,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理事会的集体领导下,后面发生的一二一事件成为和平可控的有组织行动。在工作组释放善意以后,富有经验的LZ们立刻回应,撤销路障,进行谈判,共同化危机为转机,促成了事件的化解。
由于W村临时理事会的自治是在体制以外的存在,这种集体行动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贯穿在行动当中,直到秋后算账阶段。地方黑恶势力和官商勾结的利益联盟也随时有反扑意愿,这种危险性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XJB的死就是一个侧证。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一个人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当中以实现他人利益而自己承担风险,这也是奥尔森经典的“搭便车”困境。那么,在W村集体维权行动中,为什么会出现有组织的行动并有人乐意担当领导者?奥尔森用“选择性激励”的解释框架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一个共同体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的人,更容易在群体压力和期待下成为集体行动的领袖。于建嵘把从普通农民到维权精英的身份转化模式分为“路见不平式”、“逼上梁山式”和“混合式”。在笔者看来,LZ等人的行动属于“混合式”,一方面他们身负着“全村利益”和“社会公平”的道德正义,是为全村利益而路见不平。另一方面,作为社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自身的利益事实上是和村民绑定在一起的,原村委会官商勾结盗卖村集体土地损害的是全村利益,当然也包括自身个人利益在内。可以说,没有ZLH、XJB、LZ这样一些富有斗争经验的维权精英,W村的维权行动很可能“在科层制惯有的推诿拖延或基层政府惯使强力打压中不了了之”。
3.W村农民土地维权的抗争策略
W村村民在利益侵害面前忍无可忍从而发起了维权行动,但他们并非从前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民群体,而是具有理性维权意识和公民勇气的现代公民。作为村庄维权群体谱系中的重要角色,“W热血青年团”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在理性维权的认同框架内依法依理抗争,并利用媒体等现代资源,进行恰当的话语表述等推动了事件的顺利解决。
(1)依法和依理抗争。在十数次依法上访并屡遭碰壁后,W村村民便从“依法抗争”④转向“依理抗争”策略,决定“团结起来,讨个说法”。在九二一事件中,数千村民集体到LF市政府门前讨说法。2005年出台的新《信访条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这次上访的人数规模显然远远超出,显然是不合法的“游行”。最终这次集体行动得到市委书记的肯定性答复,初步显示了“依理抗争”的威力。在集体维权行动中他们也在不断思考和调适行动的策略。在九二一事件中,“依理抗争”一度出现“社会泄愤”倾向,一些村民打砸了沿途的企业设施,从而使局面一度紧张。这直接为后面警察进村抓人、矛盾进一步激化埋下伏笔。LF市公安机关以打砸事件“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害公务罪”为由带走几名村民代表。12月9日,S市委书记ZYX将事件定性为“村内外别有用心者煽动”、“境外势力推波助澜”、“改变了事件性质”,并宣布W村临时理事会非法。当XJB的死使事件濒临失控时,G省委省政府开始介入,事情的转机随之出现。W村村民对省级政府的善意进行回应并积极谈判,取消进一步的游行活动。当然,W事件出现转折,主要应得益于G省的政策环境,尤其得益于政法委多元共治的治理思维,在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观念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2)对媒体等现代资源的利用。“W热血青年团”多是80后和90后,他们在网上了解到广阔的世界,建构出自己的理想和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年轻村民还是掌握现代科技的群体,这种现代性的获得使得他们成为具有时代特点和行动力的维权精英。他们充分挖掘互联网的力量,使用QQ、MSN、BBS、飞信等联系方式,构筑自己的传播网络,使得行动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开来,让更多公众了解到事件本身,进而将更多人卷入到集体行动中来。警民冲突发生后,“W热血青年团”的成员们不断通过镜头和网络传播他们的声音,以防被地方政府扣下的政治帽子压死。他们“去了趟深圳华强北,花8 000元购置了一台专业摄像机;3 000元买了20台对讲机(后来又添置10台),买了监视器、防盗网”。90后的村民张某每天都扛着摄像机跑。W村年轻人在“新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世界的目光关注在这个海滨小村,为后期与政府谈判创造了公共舆论环境。另外,微博这一新兴网络媒介,也成为年轻村民熟练运用的工具,并且发挥出很大的效用,在全村被封时成为唯一与外界顺畅沟通的通讯工具。通讯方式的多种多样及难以统一监管,为集体行动策动者提供了很多动员的空间和自由。同时,驻村境外媒体的报道形成的国际舆论倒逼效应亦十分明显。临时理事会的Z姓代表说:“如果没有境外记者进入W,没有曝光,没有新闻的压力,政府没有这么快来解决问题,因为受到媒体的压力,政府才这么快地反应。”
(3)恰当的话语表述。在维权集体行动者们的话语表述中,他们都是国家、政党和中央政策的坚决维护者。这种表述策略,通过将问题聚焦于村委会和土地利益问题,防止了问题扩大化和政治化的风险;又使得他们在维权过程中获得话语合法性,在与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对话过程中处在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博弈。这时的“说理”和“讨说法”都是安全的。“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农民的愿望也是好的,就是中间政策被执行坏了,出了贪官。”这是村民的一般性表述。在矛盾日益激化并陷入对峙时,他们将自己“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土地利益诉求”与“政治用意”加以区分,并发布《告媒体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对于我村事件,还请正面报道,避开‘起义’、‘起事’”等字眼,我们不是起义,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爱国家。”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表达的这样一种抗争逻辑。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种三方博弈的艺术:子民反“贪官”反得越厉害,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时更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前提是“保皇”。只要不反到政权根本,不会受到镇压。但问题是,子民是在反“贪官”还是在反“皇帝”,远在天边的“皇帝”是看不清楚的,因为他得到的信息多是从他的地方官员,即子民口中的“贪官”那里得到的。而因为贪官是被反的直接对象,他在向上汇报时,会依据抗争力量的强度做出两种选择。面对弱对抗,他们会试图将反对的声音弱化,以确保自身乌纱帽的安稳。一旦抗争力量大到失控的程度,地方官员会顺水推波助澜,将愤怒的力量引向“皇帝”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时,“事情闹大”就成为对抗双方逻辑中的默契。
三、W村农民抗争的治理启示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区治理被视为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实验,而乡村社区是重要的一环。这不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重要治理议题。要彻底解决当前地方基层社区中的利益纠纷,出现所谓可以借鉴的“治理模式”,需要一揽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政策结构设计、实践过程和结果检验。从W村农民抗争事件中,可以得到如下治理启示。
(1)必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1982年国家通过宪法确认村委会地位后,村委会开始取代生产队成为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法定权力持有者。1998年11月正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后,村民选举进入了新阶段。村民自治不再是试行而步入了制度化的轨道。从法律来讲,村委会本应承担村民自治的功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法律层面上村委会应承担村民自治的功能。但在实践过程中,它往往成为事实上的政府下派机构,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治理结构上,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相互交叠存在。而在W村,X之所以独权41年,产生出土地盗卖、财务不公开等系列问题,是因为并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选举⑤。在缺乏制度化民主决策和协商机制的村庄治理中,村民没有“参与”权力和表达意见的渠道。在长期的基层治理过程中,村庄政治权力还与地方黑势力组织以及基层政府之间形成了牢固而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网链,呈现出家族化、黑势力化、市场化等多重特征。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成为当前社会建设中乡村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
(2)群体事件中的压制性治理模式亟待变革。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无法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在治理的效率、成本、产出、供给、目标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着失效或危机。在当前的政治框架内,如何使行动者利益诉求去政治化,社会矛盾社会化,维权行动去暴力化,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在中国政府的治理惯性思维中,往往采用刚性的维稳手段进行压制性治理,通过对群体的分化和群体事件领袖的处理来区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和“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W村事件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初期叙事中,更是综合运用“境外势力”的话语将利益诉求政治化、事态严重化,从而为自身对群体事件的镇压式摆平手段寻求合法性。这种压制手段在短期来讲是有效的,但面对具有组织性的群体抗争,往往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弹和不满。为充分发挥社会治理效能,应对治理失败,保障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走出传统的政府包办而治理无效率的局面。
(3)应发挥民间自组织的协同管理作用。基层自治,社会协同管理,发挥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公众参与等等,应该成为新兴的社会治理理念。这其中,民间社会组织作为协同管理和自治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应该格外加以重视。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能够推动公众的参与,实现积极的社会自治。在这一命题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经验和知识都是需要给予重视的动员资源。尤其在潮汕这类宗族关系较强的地区,历史上一直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似乎在历经运动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W事件中,基于地方宗族联合,通过代议制民主形式选举产生的临时理事会组织经验具有启发意义,社区传统往往也是组织合法性和活力的重要来源。当然,该经验的可推广性还值得在“国家-社会”关系互动的变迁过程中进一步观察。
注释:
① 即半农、半渔、半工。
② (清)乾隆十年《LF县志》。
③ 在多个访谈个案中,村民们经常提到村委会没有“分钱”,这成为官民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矛盾激发的导火索。
④ 李连江等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提出“依法抗争”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实际上,W村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以政策为依据的。这里所指的“依理抗争”是一种“讨说法”的说理策略,包括以“农民不能没有土地”为口号的游行、以“入土为安”的传统惯习为资源进行讨尸等行为,都是糅合了政策和乡村伦理的综合逻辑。
⑤ 时任G省委书记的WY主导了W事件的处理。事后他曾针对W的重新选举意义评价说:“W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G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参考文献:
[1] 于建嵘.土地纠纷成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首要问题[N].新京报,2008-11-05.
[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155.
[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2):13-36.
[5] 朱健刚.空间、权力和社区认同的建构:上海一个社区地邻里运动的个案研究[J].第三部门学刊,2004(2):64-75.
[6]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2):49-55.
[7]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McAdam,Doug.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in New Social Movements,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M].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36-57.
[9] 朱健刚.国与家之间:关于上海邻里的民族志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皮特·何,瑞志·安德蒙.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曾凡盛
Logic of peasants' action in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the revelation for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peasants safeguarding their land rights in the W village, G province
ZHOU Runan, ZHU Jiang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The is a case study of peasants safeguarding their land rights in the W village , G province , which is to analyze the logic of peasants' action in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village committe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slipped into a state of paralysis, with the awakening of peasants’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safeguarding, the villagers' self-organization, which stand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asants, showed a strong power in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by using the belief and structure of religion, as well as played game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at stand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tate power in the framework of stabi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justification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the skilled technique of using the Internet and the media, which solved the problems successfully. From the case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revelation for governance: the villagers' autonomy has to be truly put into effect, the repressiv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mass disturbances need to be changed, and the NGO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lay a part i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peasant; contentious politics; logic of action; revelation for governance
10.13331/j.cnki.jhau(ss).2016.05.007
D422.6
A
1009-2013(2016)05-0042-07
2016-09-12
2014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7000-42210005);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99123-18823306)
周如南(1984—),男,黑龙江伊春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农村社会学。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流转规范与法律制度创新
- 环境行政拘留功能及其规范化适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