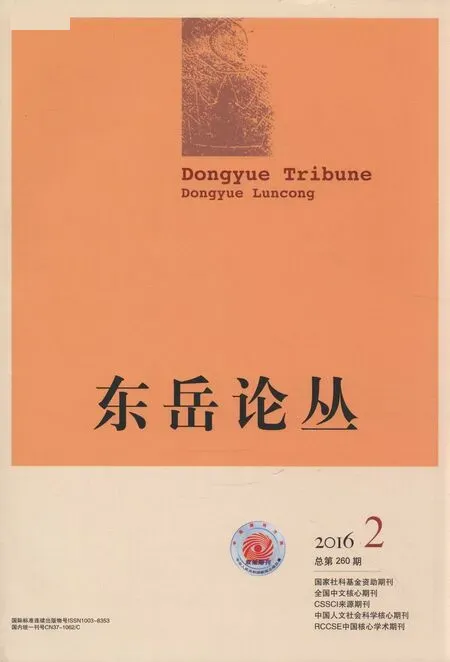试析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
邓 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鲁迅研究
试析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
邓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并不是在一般层面建立现代白话文书面语,也不是倡导某种均质而系统的语言文字典范,而是深入到生命内核去相遇与绽放语言,展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世界与生命体验,达到“思想性”与“文学性”结合。周氏兄弟所开拓出的文学语言是一种基于思想政治基质的高度心理化、精神化的深度文学语言,表明了一种鲜明而“欧化”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意识,使得现代白话文摆脱较为单纯的工具性存在,而成为具有自我独立价值的文学语言。
周氏兄弟;文学语言;白话文;现代转型;欧化
一
本文将分析周氏兄弟早期文学语言建构的理路与情形。这里所谓的“早期”,大致是指晚清与五四时期,即是“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时期。关于“现代转型”,可参考张灏的观点:“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①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就中国文学语言而言,正是在这一“现代转型”时期,发生了全局性的巨变:文学语言建构不断的破裂而又不断的聚合,在深广的思想文化基质之中不断的自我生成与创造,形成了一系列文学语言试验的场域逻辑,构筑起最为躁动不安的文化空间,直至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成为一个政治、文化与文学共同体的普遍的媒介与想象,迸发出巨大的激情、活力与创造性,确立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当我们面对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复杂性。之所以加以“践行”的称谓,是因为他们对文学语言的建树更多是在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崎岖行进,不乏失败之中的强行开拓,喧闹之中的突然转向,成为整个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之中熠熠生辉而不可消化的部分。这完全不同于胡适等人建立起的清晰白话文变革轨迹,其内在线团化的纠集势必引发许多令人深思的话题。
在1908年《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提倡无功利的“纯文学”:“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这一鲜明的“美术”立场很明显源于西方文学与文化观念,特别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理念。在另一方面,如同鲁迅长期所做那样,他又很少孤立地谈及这一“纯文学”应该使用的语言,更不会有语言与文体方面的较为纯粹的形式主义方面的追求——或许有人会认为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长期似乎并未进入鲁迅的视野。这也可以证之以晚清时期鲁迅的翻译语言的实践,《〈红星佚史〉之诗》采用的中国古代的骚体诗歌语言,《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采用的是传统章回体的白话文,遵循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多元化文学语言的潮流,其中充溢的是明清白话小说语言的意味,而翻译西方短篇小说的《域外小说集》,则是采用深奥的文言——从表明上看,鲁迅之于近代以来文学语言的发展与转型,好像并不那么“新潮”。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周作人身上。在1914年《小说与社会》一文之中,周作人认为“著作之的,不依社会嗜好之所在,以个人艺术之趣味为准,故近世小说,不复尽人可解,而凡众之所赏,又于文史为无值。”*②启明(周作人):《小说与社会》,《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1914年)。这样的看法超越当时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实用趋向,而充满精英的意味。周作人同样是追求无功利的“纯文学”,甚至漠视“社会”与“凡众”。不同于鲁迅之处,在文学语言的使用方面,周作人有明确的意见:“第通俗小说缺限至多,未能尽其能事。往昔之作存之,足备研究。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著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对立。斯则其文虽离社会,而其有益于人间甚多。”②周作人看到通俗小说的现实发展情形,同时为了规避通俗小说的“缺限”,而开出“易俗语而为文言”的药方,即以文言来完成通俗小说的纯文学改造,来达到心目中“艺术之境”,甚至可以放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实现超越一般功利束缚的目的。
这一切似乎匪夷所思——我们还知道数年之后周氏兄弟会创作出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经典作品。文学史上进化视野的逻辑线索似乎突上突下,无法进行线性的衔接,发生阐释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以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系之中,以简单的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来看待周氏兄弟从晚清而来的语言观念与实践。从根子上说,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的阐释架构对周氏兄弟的意义不大,他们并没有以白话与文言的二元对立去展开思想文化的变革思维。周氏兄弟是在新的文学与文化观念之下,不断试验,不停寻求着自己的表达方式。在某段时期,他们使用文言,也是以此追寻与实现自己的文学与文化观念,即便遭受必然的失败,但这些汇入生命体验内部的失败也具有价值——这一行为的本身就已经加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产生出不能为同时期其它文学语言建构消化的张力。我们分明看到,周氏兄弟是以绝大魄力与毅力去践行中国现代的文学语言,他们不是为了在一般层面建立现代白话文书面语,不是为了倡导某种均质而系统的典范语言文字,而是深入到生命内核去相遇与绽放语言,同时也是在相遇与绽放的语言之中,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文学世界。
二
王风认为:“周氏兄弟是以自居边缘的姿态加入《新青年》的,鲁迅所谓‘听将令’、周作人所谓‘客员’就是这种姿态的反映。首先他们接受了白话的共识,其次他们工作的重点事实上与陈独秀更为接近,即延续民国建元以来思想运动,结合自己晚清以来的思考,而进入所谓伦理革命,《人的文学》等等实际是此类问题的延伸,在他们那儿,文学即是一个实践平台,又是一个需要重建灵魂的对象。”*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所以,不是对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的倡导,而是别有自己深切的关怀,周氏兄弟以独特的姿态加入到新文化阵营之中,也规定其文学创作在语言方面的不断锻造与重要贡献: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内部,基于现代思想文化的特质,产生了一种立足中国语言文字特点而又有欧化倾向的文学作品书面语言,构成与影响了五四新文学语言内核与骨骼的部分,从而也奠基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质地。
让我们先论及鲁迅的文学语言,并以1918年的《狂人日记》为例——此文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白话小说语言不言而喻带来了一个奇异而滞重的小说时空世界。构成要素敏感的“月光”、赵贵翁的“眼光”、“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一切都内化于狂人的心理,物理的时间与空间都被聚集、纠合与变形,形成了一个诡异奇绝的构成。之前的中国文学不会有这样的小说,而将之称为“小说”也是沿袭固定的说法,否则无法归类。因为,以日记碎片构成主体的《狂人日记》,缺乏情节,没有人物塑造,所谓的“环境”也是狂人心理的环境与氛围,更多的直接是狂人的独白、意识流、潜意识、病态思维、无逻辑的跳跃、奇特的逻辑推理……在小说的白话语言之中,《狂人日记》的叙事时间构成已经不同于往。试读: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②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5页,第453页。
在这段话里,包含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织,由于《狂人日记》中小孩子多由鲁迅进化论的观念寄予未来的含义,则加上了它们与未来的意义交织。这是在一种时间的心理内化之中,与过去、未来的对立之中,产生了“现在”,产生了“怕”,产生了“无地的彷徨”。同时,不难发现,《狂人日记》白话语言叙事之中的空间显得封闭而狭窄,布满阴暗的色彩。空间的参与更一步确定了时间构成,空间意味着更为明晰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建构。在《狂人日记》之中,屋内与屋外是结构性的存在。我们在此特别关注的是“屋内”——禁闭狂人之处: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②
迫害感直接带来狂人空间幻觉与扭曲变形,这是狂人异质的思想文化参与带来的空间生成,使得这一间“屋子”形象成为一种压迫的象征性构成,物理空间完全化为了心理空间,也形成了高度内化的小说语言质地,令人惊心动魄。在如此复杂的时空关系之中,不难发现《狂人日记》中的白话文句式也空前复杂了,白话语言的使用被注入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内蕴,或言开拓了新的心灵世界。可以说,所谓口语的使用只是一种表象,鲁迅的小说语言绝不是什么鲜活的口语,原汁原味的口语。鲁迅的小说语言超越了概念化与抽象说理的倾向,超越了晚清以来报刊文字的单纯直白与过于明确,显得既复杂而精密,又充满了感性的血肉淋漓。
我们赞同陈思和的看法:“《狂人日记》一发表,立刻就拉开了新旧文学的距离,划分出一种语言的分界,……‘五四’新文学的大量欧化语言的产生,与传统的白话文自然而然的发展轨迹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另外一个语言系统进入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这是一种基于思想文化质地的高度心理化、精神化、逻辑化的深度文学语言,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内面化”的文学语言,内在具有强烈的异常感与紧张感——并且,基于思想与文化政治的含蕴进入文学语言的方式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建构的主流情形。从这一角度而言,鲁迅文学语言的成熟及其经典性,对于中国文学及其语言现代转型的意义重大。
三
周作人在五四高潮时期对于思想文化与文学语言关联的论述,较之鲁迅更为直接与外化,其言论引起极为广泛的影响,使得周作人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之中令人瞩目的领袖之一。在1919年《思想革命》一文之中,周作人基于鲜明的思想文化视角,展现出他介入文白之争的视野:
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②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第6卷第4号。
周作人完全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出发,否定了文言的合法性,认为古文没有任何的生命力了。很自然,周作人也会思考取代文言之后的现代白话文内部的思想建设问题,他明确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②
在1919 年《平民的文学》一文之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倡导与白话文的使用有所论述:
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周作人:《平民的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这里仍有周作人从晚清以来的一贯立场,包含了鲜明的启蒙意识与精英意识,白话文不能等于通俗,平民实际指向的是“人的生活”,这样的白话文自然也不能只是延续传统文学的白话文资源,而有更高、更宏大意义的追求。
众所周知,周作人随后不断反思五四高潮时期的观点,开始在“自己的园地”冷静耕耘,后还有“闭门读书论”“文学店已经关门”之类是说法。在告别与拒绝的姿态之中,周作人一改往昔宏大意识形态的腔调,他对于语言文字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改变。
可对周作人1922年《国语改造意见》一文进行分析。在此文之中,周作人审视既有的白话文资源,明确反对明清小说式的白话文,理由为“明清小说专是叙事的,即便在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不能包括全体;我们于叙事以外还需要抒情与说理的文字,这便非是明清小说所能供给的了”*⑤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第56页。。周作人也反对俗语式的白话文,认为“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文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⑤这已显现周作人在转向后对语言文字建构最为核心的观点,即是“融合论”,对各种语言资源进行选择并汇合,具体包括了“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等主张。这些观点明显已与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倡导——包括周作人自己——有了相当区别,深入到文学语言的肌理存在,完全不再持有在五四高潮时期的白话与文言二元对立的立场。
这一转向还可以与周作人此时散文语言探索结合起来。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一文中认为:
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的那种散文上,我以为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一,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周作人试图在调和之中进一步提升白话文学语言的品质,将“雅致”与“俗语文”并举,实是其对白话文再创造的持之以恒的主张。周作人散文语言创造,显然与其对白话文的重新认识紧密相关,更为重视语言文字自身的质地与特点,更为灵活、从容不迫,也更富于表现力。非常明显,其所谓“美文”的散文语言是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传统文学的资源,体味古文文字的声色情韵的结果,确是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个人化与心灵化的文学语言世界。可以说,周作人在散文之中探寻具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语言构成,使之在现代白话文之中容纳更多有价值的语言因素。
四
在分析周氏兄弟在文学语言建构的若干表现之后,我们试图彰显他们文学语言践行的道路。朱自清曾在新诗领域认为:“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欧化一路。”*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3页。木山英雄也有断言:“较之‘言文一致’更注重‘思想革命’并呼应文学革命的周氏兄弟的‘欧化体’。”*木山英雄:《从文言到口语》,《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这些都说明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的一个关键词——“欧化”,他们不是像胡适的白话文那样与明白晓畅的报刊文字有明显的联系,而是与翻译文学语言、与“欧化”有更多的亲缘联系。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周氏兄弟也偶有一些与文学语言关联的“欧化”观点,可以说他们已自觉审视自己早期的文学语言践行。
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上,有大量篇幅有关世界语倡导的论争,提倡者要求废汉字、汉语,使用世界语的Esperanto——这可谓无以复加的“欧化”与“世界化”了。在是否采用世界语这一问题上,鲁迅在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5号“通信”栏目之中有《渡河与引路》一文。鲁迅的关注在于: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唐俟(鲁迅):《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Esperanto·通信”栏目。
在语言文字变革之中,鲁迅在意的是有主体实质意义的进步,重视的是“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而不是若干的名目,为之花太多的功夫,因为这些一时眩人的名目完全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骨子里仍是旧有的东西,即便是世界语——这就是鲁迅式的冷静与深刻。“欧化”之于鲁迅的语言文学思考,充满了主体意义,是其“自性”“白心”的主张的体现,有着充沛而刚健的内容。
让我们将目光再稍作后移,在1927年《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一文之中,鲁迅谈及“陶元庆君的绘画”的特质,在意的是“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⑤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第574页,第574页。。然后,鲁迅联想起白话文的“欧化语体”: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⑤
鲁迅是将五四时期一代的“中国的我辈”与“欧化语体”直接联系,而无丝毫的退让。因为,正是在这一“欧化语体”之中,包含“中国的我辈”的价值追求,“欧化语体”塑造了“中国的我辈”的新的思想文化的质地与内容,因而不畏所谓“中国本位”人的指责,反之在欧化的“的呵吗呢”之中,区别与矗立了“中国的我辈”的主体形象,并不无自豪。
周作人在1922年《国粹与欧化》一文之中,对于“欧化”的态度为:
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所反对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模仿杜少陵或泰戈尔,模仿苏东坡或胡适之,都不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②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第13页。
在“模仿”与“影响”的区别之中,周作人所谓的“欧化”,同样基于主体需求的创造,“新空气”“新的活力”的表述,直指一个新的文学世界,而这一切构成了他对白话文的新文学的期待。对于语言文字的建构,周作人关注的则重点无疑是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到了汉字本身的特点:“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②
通过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语言践行的辨析——我们更多是着眼于他们所面对的共同历史语境之下,某些共通性的方面——进而我们确认“欧化”的实质是在特定时期中国文学在主体意义上的一种深刻的“中国体验”。“欧化”之于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动机是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的本土需求,是在当时社会与精神生活的危机之中,将外来的启迪纳入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创造力之中,也是内化于中国自己的现实与历史情境之中的,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初生的现代白话文基础之上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不懈建构。当在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之上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之时,那些奇崛的文字瞩目于“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似乎已经注定周氏兄弟将卷入与中国语言文字搏斗的壮丽事业。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现代白话文的倡导更多是倾向于语言学意义的,倾向于一般书面语的白话与文言的革命性转换,而真正跨过一般书面语范畴,达到“思想性”与“文学性”结合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正是周氏兄弟。在他们早期文学语言的践行上,表明出一种鲜明而“欧化”的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意识,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反思性的流向,乃至需要再次认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质——这也说明中国文学语言现代建构的未完成性与持续性。最终,我们可以说周氏兄弟的早期文学语言践行,使得现代白话文摆脱较为单纯的工具性存在,而成为具有自我独立价值的文学语言主体,成功地在文学领域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传达现代文化的丰富含蕴,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及其语言抉择之中强力的声音。
[责任编辑:曹振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研究(1898-1924)”(编号:10CZW048)的阶段性成果。
邓伟(1975- ),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I210.96
A
1003-8353(2016)02-01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