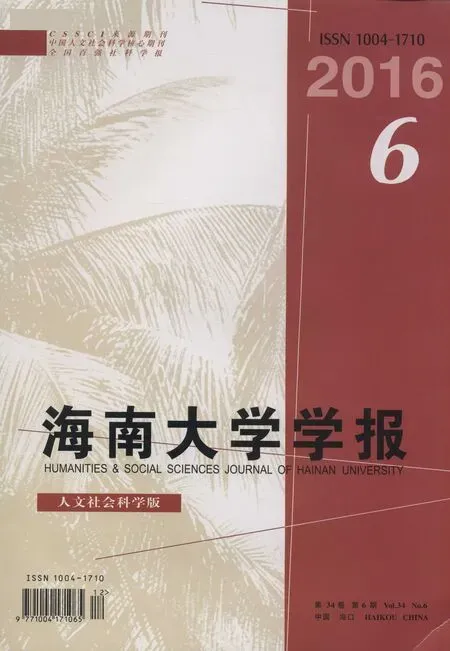论戏剧《耻辱》中的美国穆斯林精神创伤
骆守怡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论戏剧《耻辱》中的美国穆斯林精神创伤
骆守怡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2013年普利策戏剧奖作品《耻辱》是直击伊斯兰恐惧症最勇敢的声音:主人公阿米尔身处西方社会而带有东方文化基因,陷于文明冲突的夹缝中,生活陷入危机,精神濒临崩溃。文章将阿米尔“屈辱、愤怒和骄傲”的复杂心理机制置于相关历史文化以及政治背景中,力图探寻后“9·11”时代美国穆斯林精神创伤的根源——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抗衡与“他者”界定,身份认同的挑战以及中东政治冲突的后遗症。阿米尔从志得意满到一无所有的个人悲剧折射出当今美国穆斯林无法逃避的尴尬与崩溃。
美国穆斯林;创伤;东西方文化抗衡;身份认同;中东政治
戏剧《耻辱》是巴基斯坦裔美国作家伊亚德·阿赫塔尔(Ayad Akhtar)的代表作。该剧将后“9·11”时代美国主流社会对待伊斯兰的态度置于显微镜下,以紧张巧妙的剧情、机智犀利的对白和难以磨灭的社会现实意义,问鼎2013年普利策戏剧奖。后“9·11”文学是当代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乔纳森·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和德里罗的《坠落的人》等作品对“9·11”事件后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理症结进行了隐喻性的透视和呈现,其焦点大都对准美国白人。《耻辱》的关注对象则截然不同,其主人公阿米尔是一位弃教的美国穆斯林。后“9·11”时代,美国穆斯林处境尴尬,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又受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持续影响,生活得小心翼翼、困境重重。剧中四个具有典型族裔身份的美国公民——“前”穆斯林、犹太人、白人和非裔——在餐桌旁进行了一场关于宗教和政治的激烈辩论,只见“文明冲突”的狂飙席卷而来,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最初志得意满的律师阿米尔与最终一无所有的失败者判若两人。阿米尔身处西方社会而带有东方文化基因,陷于文明冲突的夹缝中,失败在所难免。《耻辱》透过阿米尔的人生悲剧,展现出“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无法逃避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崩溃。这一切背后的缘由发人深省,值得细究。
一、 伊斯兰恐惧症与“他者”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世界通常会被迫创造新词用以描述不断扩散的偏执……‘伊斯兰恐惧症’正是如此……自‘9·11’事件以来,许多西方穆斯林发现自己成为被怀疑、被骚扰和被歧视的目标……无知的鸿沟深不见底。”[1]不论是主人公阿米尔还是剧中其他穆斯林人物,都是受害者的典型代表。隐瞒了原穆斯林身份的他本是前途无量的企业律师,因为在听证会上声援一名伊玛目而受到犹太老板的怀疑和调查,原始身份遭到揭穿,前程尽毁。阿米尔起初拒绝参与该项诉讼案,“我不管什么《爱国者法案》,反正他已经有辩护律师了”[2]11。《爱国者法案》这一“9·11”事件之后最具争议的法案使得穆斯林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它认可了政府监视银行交易记录、电话内容、电子邮件等特权。一些慈善机构因“疑似”资助恐怖活动而被冻结资产。剧中伊玛目正是因为其主持的清真寺的募款行为有涉恐嫌疑而被告上法庭,并在司法过程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和正当程序的严重缺失。2001年,美国司法部长曾在美国市长会议上表示:“我们要让身边的恐怖分子得到警告。你如果签证过期,即使只有一天我们也会逮捕你。”[3]158阿米尔的侄子亚伯就是移民身份过期的穆斯林新移民,因而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别“关照”的对象。“他们对我了如指掌。在哪里上的学,父母是谁,从哪里来,感觉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信息。”[2]70对穆斯林的恐惧和戒备渗入美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
伊斯兰恐惧症的爆发除了“9·11”事件带来的强烈刺激,更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抗衡而导致的“他者”界定。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原本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的产物,一个忠实的穆斯林不需要很多踌躇就能接受基督教大部分的信条[4]4。《圣经·新约》中,东方三博士给婴儿耶稣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而乳香和没药是阿拉伯人最为出名的产品。但这种亲缘关系在东西方文明500多年的抗衡中渐渐离散。7世纪哈里发国家的勃兴、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崛起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谱写着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相互征服的历史。茨威格如此描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瞬间:1453年,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堡垒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攻陷。查士丁尼大帝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顶尖耸立的十字架轰然瘫倒在地,整个西方都被那倒塌的声音震惊了。罗马、热那亚、威尼斯都在回响着这恐怖的声音,而法国和德国也将要领略这警钟一般的轰鸣[5]。从7世纪末到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罗马在伊斯兰文明之光的覆盖下黯然失色。伊斯兰文明成为欧洲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作为以信仰盎格鲁——新教的定居者为主流的社会,逐渐成为当今与伊斯兰文明抗衡的前沿阵地,误读与偏见成为常态。
《耻辱》中,对于穆斯林妇女的着装,非裔美国人乔里认为:“头巾是邪恶的,遮盖面部就是毁灭个性,为什么男人不用戴,每次都是女人付出代价?”[2]52这种典型的女权主义观点将头巾视为穆斯林女性遭受压迫的象征。而实际上,大多数穆斯林女性认为,选择穿戴伊斯兰服装能够让她们获得自由、安宁与快乐[6]9。压迫穆斯林女性的人有时恰恰是禁止她们戴头巾的人。当西方人抨击头巾的保守落后时,穆斯林则认为西方妇女缺乏端庄,地位低下。阿米尔从小被其母灌输的思想就是“白种女人不知廉耻,靠袒胸露背取悦男人,她们都是妓女”,并且这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识”[2]15。甚至有穆斯林学者认为,人类从赤身裸体到用树叶蔽体是一种进步,因此人类越是文明,就越多地遮盖自己[7]55。
对于“打老婆”问题,几个人物之间也有一段争执。《古兰经》的原文为:
……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可以劝诫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如果她们服从你们,那么,你们不要再想法欺负她们。真主却是至尊的,确实伟大的。(《古兰经》第四章第34节)
阿米尔在描述经文大意时只提及前一句。其白人妻子艾米丽认为“打”这个字可以理解为“离开”(英语单词beat兼有二者之意)。她从字面上为《古兰经》辩解,却不能了解经文的上下文语境和历史内涵。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旨在提高妇女地位。因为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男人可以随意抛弃妻子,妇女必需在男性保护下才能生存。这段经文鼓励家庭成员之间通过沟通来解决矛盾,而不是提倡暴力。《古兰经》诞生于1000多年前的沙漠之中,如果不能正视历史背景,动态辩证地看待经文,不仅违背了《古兰经》精神,更与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不符。先知对妻子的过错不是殴打和虐待,而是善意的叮咛[8]。艾米丽自认为了解和欣赏伊斯兰,对其文化的美与智慧颇有赞叹之意。而不论是维护《古兰经》还是赞赏清真寺的拱门,都根源于文化优越感这一藏于内心深处的意识。艾米丽在阿米尔被餐厅服务员的种族歧视冒犯后突发灵感,以阿米尔为模特,模仿了西班牙画家维拉奎兹作品《胡安·德·佩雷加》,佩雷加原本是维拉奎兹的摩尔人奴隶。潜意识中,她把阿米尔看成一个“得到了主人的女人的奴隶”[2]61,这种对阿米尔的“他者”界定也使艾米丽出轨犹太人艾萨克成为必然, 正如艾萨克所指出的那样,艾米丽一定会再次背叛丈夫,即使不跟他,也一定会有别人。
从但丁的诗歌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东方的伊斯兰永远被描绘成“他者”的形象,在欧洲文明内部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穆罕默德、萨拉丁、阿维罗伊以及阿维森纳的形象都因他们各自的“功能”被永久地密封和固定在一个系统之内,欧洲与东方尤其是伊斯兰的对决强化了这个系统,使伊斯兰变成了“他者”的化身[9]70。后殖民主义时代,伊斯兰成为暴力、保守与落后的象征,并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奴隶贩子、奸商、形形色色的反派,这些就是阿拉伯人的传统影视形象。哈达德认为,穆斯林群体的同化慢于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后的其他移民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对穆斯林怀有成见。以艾米丽与艾萨克为代表的基督教—犹太教主流社群对携带东方文化基因的阿米尔的偏见,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所在,也决定了穆斯林族群同化之路的举步维艰。
二、身份认同的挑战
二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是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又一次高潮。这一阶段中,来自分治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移民人数有所增加。阿米尔的父母就是在这次移民浪潮中来到了美国。几十年间,穆斯林以自己的方式渐渐融入美国社会。清真寺的数量从1986年的598座增加到2000年的1 250座[10]24。海湾战争后,不论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每年都要在古尔邦节对美国穆斯林以及世界穆斯林发表问候。1996年,美国国会山举行了首次开斋节招待会[11]。然而,当今美国社会是源自信仰盎格鲁——新教的定居者的社会,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深刻地、更加持久地对美国的文化、体制、历史发展及特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31。艾米丽提醒艾萨克不可以再轻视伊斯兰文化,恰恰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边缘地位,例如艾萨克认为艾米丽会因为“东方主义”倾向而受到批判,并嘲笑她嫁给了一个棕皮肤的丈夫。而虽然艾萨克的妻子乔里也是有色人种,却能够顶替阿米尔得到提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非裔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程度和受认可程度今非昔比。从1968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到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人形象的淡出,到2008年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当选,这种自然的、渐进式的进步让美国人深感自豪。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由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策划的暴力活动使得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成见加深。后“9·11”时代穆斯林的美国化道路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美国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而言较为特殊,美国与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对立状态常常使得这一族群对美国的认同与对伊斯兰母国的认同发生矛盾。“9·11”事件之后美国穆斯林遭遇的挑战与一战后的德裔美国人和二战珍珠港事件后的日裔美国人以及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在美国面临的处境相似[10]78,这种处境导致了阿米尔的侄子亚伯的尴尬与愤怒。第一幕中,他通身的美国范儿,穿着名牌T恤、紧身牛仔裤和高帮鞋,改了名字,迫切地想要融入美国社会。第四幕中,他却戴上了头巾,衣着低调,恢复了原名。前后形象之所以判若两人,是因为一场与星巴克服务员关于基地组织的口舌之争使他遭到了FBI的拘捕,而FBI的审问严重侵犯了他的隐私,令他十分屈辱。“我们根本不该离开祖国,不该来这儿……他们永远也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2]73他讥讽阿米尔(及其父母)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却落得事业惨败家庭破碎的下场。此时亚伯心中的失望积累成了满腔恨意:“他们征服了世界,我们要把它夺回来!”[2]74亚伯的转变是一个美国认同感锐减、母国归属感激增的过程。
在美国穆斯林中,年轻一代的反美情绪在增长。皮尤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穆斯林中,15%的人支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进行自杀性爆炸袭击,9%的人选择不回答,实际上就是默认[9]154。美国与中东某些国家的敌对状态也给大多数温和派穆斯林造成了困扰。皮尤中心2007年的调查显示,有35%的美国穆斯林支持阿富汗战争,48%反对;2011年的调查中,有38%支持,仍有48%反对;对这一问题不表态的比例分别为17%和14%,明显高于美国公众[3]165,折射出美国穆斯林不得不面对美国认同与母国认同对抗的尴尬境遇。阿米尔也深受其扰,在艾萨克的挑衅和逼问下,阿米尔坦言自己对“9·11”袭击的感觉是“骄傲”,乔里追问原因:
阿米尔:(因为)我们终于赢了。
乔里:我们?
阿米尔: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我们”了吧。
乔里:可你明明是美国人啊……
阿米尔:那是族群的印记,乔。是深入骨血的。你不知道我从小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那些东西不是说抹掉就能抹掉的。[2]55
在西方话语霸权体系中,“恐怖分子”是对中东反美势力的模糊性统称,而在伊斯兰国家,这批人则被视作“勇敢的斗士,民族的骄傲”。抹不掉的族群印记让阿米尔难以分清自己的立场,也是阿米尔对于自己的“骄傲”感到惊慌失措的根源。亨廷顿认为,同化的最终标准是外来移民对美国的认同,是否接受“美国信念”,采纳美国的文化,从而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忠诚[12]176。这一点无论是阿米尔还是亚伯都难以做到。
另外,美国穆斯林所携带的东方文化基因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使得这一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充满坎坷。他们一方面倾向于在本族群内部获得安全感,另一方面又渴望参与主流社会生活,试图让主流社会既承认他们的不同,又真正认同他们是美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与美国穆斯林群体规模较小的现实更是让部分散居的穆斯林移民后代隐匿甚至是放弃自己的穆斯林身份[3]101。阿米尔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了弃教,篡改社会保险号码,模糊父母出生地,隐瞒伊斯兰背景,最终打开事业上升通道。他说着标准的美语,娶了白人画家为妻,穿着600美元一件的衬衫,吃着猪肉,在犹太人的公司里努力为“美国梦”而奋斗。但连他自己也承认,小时灌输的伊斯兰信仰是深入骨血、难以磨灭的。他家墙上“伊斯兰式花园”的绘画和东方格调的家具都暗合了阿米尔无法逃避的文化身份,就如同他总是呼唤侄子亚伯其原名“侯赛因”一样。穆斯林在异质社会进行身份构建时,往往面临穆斯林内在认同和社会人外在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像阿米尔那样通过完全同化的方式,还是像亚伯那样选择在主流社会边缘生活的方式,都很难弥合这种差异。阿米尔已然无法招架身份认同的挑战,这为其最终的价值崩溃埋下了伏笔。
三、暗淡的荣光与冲突的中东
公元632年到1258年,当欧洲还在贫穷愚昧中停滞不前的时候,伊斯兰文明却像流光溢彩的画卷般绵延伸展。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都城,曾经是独占世界鳌头的经济中心和大都市。阿拉伯人继承了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累累硕果,并吸收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经典智慧。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4]4。但是现当代认识到伊斯兰文明的地位及其贡献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艾米丽所说,“穆斯林给我们带来了亚里士多德,伊斯兰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帝却不允许任何人提醒我们这一点。”[2]24艾米丽以阿米尔为模特模仿维拉奎兹的画作《胡安·德·佩雷加》也有其极深的历史寓意。佩雷加是摩尔人,这是一群曾在西班牙叱咤风云的族群。71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北非柏柏尔人(即“摩尔人”)向西班牙进军,并于713年征服伊比利亚全境,西班牙改称安达卢西亚。艾米丽强调安达卢西亚的马赛克画面屈折技巧比伯纳尔早了400年,表达了对伊斯兰文明的一种敬意。但是随着15世纪基督教在西班牙全面“光复”,一些摩尔人沦为基督教白人的奴隶。
以15世纪末大航海为起点,世界进入殖民时代,伊斯兰世界由盛转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沦为英法殖民地,冷战时期直至后殖民时代的中东历史布满大国干预的痕迹。正因为伊斯兰世界曾有着无语伦比的辉煌,他们在内心深处向往曾经的历史地位,渴望结束屈从与欧洲和美国的漫长世纪。因此阿米尔坦言自己对“9·11”事件的反应是“骄傲”,正因为“我们终于赢了”。美国政府和专家认为“9·11”袭击源自“价值观冲突”:穆斯林对美国敌对情绪的深层原因在于对美国的实力感到恐惧,嫉妒美国的富有,怨恨美国的盛气凌人和剥削他人,敌视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13]。这种论调有失偏颇。要考察中东国家的反美情绪,要理解阿米尔的“骄傲”之情,必须审视中东历史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中东历史。美国人很少问及其政策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东的民主、经济发展或者人权。这类反省早已被“穆斯林仇恨我们的自由民主”等误导性回答所淹没,恐怖主义滋生的历史政治根源被刻意回避。在批判阿米尔对 “自己人”的否定和对美国白人的逢迎时,亚伯痛斥道:
300年来,他们抢占我们的土地,划分我们的国界,换掉我们的法律,让我们渴望变成他们,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娶她们的女人。他们羞辱我们。他们羞辱我们,然后他们又装作不懂我们的愤怒来自何处。[2]74
萨义德的控诉如出一辙:中东地区的地图在华盛顿高级官员的嘴里说改就改,那些历史绵长五花八门的族群就像是一个瓶子里装的花生米,摇一摇就均匀了[9]8。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许多国家成为民族国家时,殖民者给它们划定边界,指派非民选的统治者。印巴分治导致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流血冲突,强行在阿拉伯人聚居区建立犹太人的国家,酿成了半个世纪的杀戮。海湾战争更成为一些穆斯林心中的奇耻大辱。亨廷顿提醒美国人,海湾地区的人都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多国部队的占领;从1980到1995年,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是穆斯林[13]193。在最后一幕中,亚伯的朋友塔里克告诉星巴克的白人女服务生:“基地组织是美国人自己一手培养的……不管是以前的袭击,还是将来的袭击,都是你们罪有应得!”[2]69于是他们立刻遭到逮捕。而逮捕不仅不是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最终有效途径,甚至会将他们推向恐怖分子阵营。
阿以冲突是整个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穆斯林在1000多年里始终控制着第三圣地耶路撒冷,而《贝尔福宣言》却强行规定在这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1948年以后的中东历史,弥漫着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军事政治斗争的硝烟。阿拉伯人将以色列的建立视为阿拉伯人身上的殖民枷锁,是英美维持在中东影响力的一种企图。以色列担心遭到阿拉伯人袭击(和由此导致的灭亡),而阿拉伯人恐惧以色列人的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统治)[14]。双方的争斗和战争中搭进了太多枉死的冤魂,结成了无法解开的血仇。以色列的强势霸道和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都阻碍了巴勒斯坦和平进程。
剧中有两次“吐口水”情节,集中体现了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情窦初开的少年阿米尔爱上了犹太姑娘丽芙卡,鸿雁传书眼波流转的浪漫遐思却遭到阿米尔的母亲无情毁灭:“你别想娶她,除非我死了。”因为“犹太人偷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帝诅咒他们。”[2]13母亲往爱上犹太女孩的儿子的脸上吐口水,第二天儿子又往笑盈盈走向自己的女孩脸上吐口水。阿米尔与艾萨克也有一段“吐口水”情节。对于美国的眼中钉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要“把以色列扫进地中海”的言论,艾萨克说自己“和大家一样,愤怒至极”,阿米尔却意味深长地说道:“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不少人拍手叫好呢!”[2]56并在艾萨克的追问下承认自己也赞成把以色列扫进地中海,双方冲突加剧。随后,在得知前途被毁和妻子与艾萨克出轨的双重刺激下,阿米尔把全部的愤怒化成了吐向艾萨克脸上的口水。
阿米尔与艾萨克的较量以阿米尔的崩溃告终,隐射了穆斯林移民与犹太移民的实力对比。在美国政治日益成为各移民社群及其母国政府较量舞台的背景下,穆斯林移民完全不能与犹太移民抗衡。198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参议院中有7名犹太参议员,众议院有29名,欧洲和中东问题外交小组13名成员中5人是犹太裔[15]。相比之下,直到2006年,美国才有了第一名手按杰弗逊的《古兰经》宣誓就职的穆斯林众议员,2008年出现了第二位穆斯林议员。犹太人竭尽全力影响国会,积极促进其与以色列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方的基本立场。阿米尔在得知前途无望后在员工会议上崩溃痛哭,抗议说如果他帮的人不是伊玛目(穆斯林精神领袖),而是拉比(犹太精神领袖),结果会截然不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犹太老板正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重要资助人。阿米尔与艾萨克之间的较量放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考察,谁输谁赢不言而喻。而艾米丽(美国白人)必然出轨艾萨克(美国犹太人),阿米尔(美国穆斯林)注定一败涂地。
四、结 语
普利策奖戏剧《耻辱》是反映后“9·11”时代穆斯林困境的最勇敢的声音之一,抨击了美国社会横行的“伊斯兰恐惧症”——一种根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抗衡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与偏见的心理机制。白人妻子艾米丽在推崇伊斯兰文化的表象后隐藏的优越感体现了主流社会对穆斯林族群顽固的“他者”界定。在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挂钩的社会背景下,穆斯林群体遭受了“另眼相看”,国民认同与文化认同遭遇挑战,由此导致的精神创伤或成为价值崩溃的诱因(阿米尔),或成为反美主义滋生的温床(亚伯)。暗淡的历史荣光、战后美国中东政策和阿以冲突的血仇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也是阿米尔对“9·11”事件感到骄傲的根源,却也注定了阿米尔在与艾萨克较量中的一败涂地。在“愤怒”、“骄傲”和300年“耻辱”的纠结中,阿米尔终于在艾米丽的画中看清了被文明冲突的阴影时刻纠缠的遍体鳞伤的自我。
《耻辱》在激烈的宗教和政治辩论中将阿米尔的悲剧推向高潮,落幕时的死寂与绝望满含发人深省的力量。阿米尔和亚伯将何去何从?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杀手”(抑或“勇士”)?鉴于主流社会对于伊斯兰的负面态度,答案不容乐观。2004年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倾向于暴力[7]6。然而,如果伊斯兰教该为极端恐怖活动的发生负责,那么基督教是否该为3K党曾经的行径负责?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比普通的穆斯林更虔诚。将宗教视为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会削弱宗教的正面力量,掩盖问题的本质。如何理解阿米尔的崩溃和亚伯的激愤,如何抚慰当今美国穆斯林的精神创伤,避免更多“本土极端分子”的产生,是《耻辱》最切中肯綮的价值关切。
[1] 约翰·L·埃斯波西托, 达丽亚·莫格海德. 谁代表伊斯兰讲话[M]. 晏琼英,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89.
[2] AKHTAR Ayad. Disgraced[M].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3] 王国栋. 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穆斯林群体研究[D].西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14.
[4] 菲利普· 西提. 阿拉伯通史 [M]. 马坚,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5] 斯蒂芬·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M]. 亦言,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29.
[6] HADDAD Yvonne Yazbeck, SMITH Jane, MOORE Kathleen M. Muslin women in America: The Challenge of Islamic Identity Toda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9.
[7] ABDO Geneive. Mecca and Main Street: Muslim life in America After 9/11[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马莉. 美国穆斯林移民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0.
[9]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10] HADDAD Yvonne Yazbeck. Becoming American? The Forging of Arab and Muslim Identity in Pluralist America[M]. Texas:Baylor Univeristy Press, 2011.
[11] HADDAD Yvonne Yazbeck. Muslims in the West: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176.
[12] 塞缪尔·亨廷顿. 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0.
[13]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4]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 中东史[M]. 哈全安,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360.
[15] 樊为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中东政策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09.
[责任编辑:吴晓珉]
On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Muslim Americans in Disgraced
LUO Shou-y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Disgraced, as the winner of 2013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is the most courageous voice to witness Islamophobia. The protagonist Amir, living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with the Eastern cultural gene, is trapped in the cracks of civilization clashes, which expose her life into the crisis and makes her on the verge of nervous breakdown. Taking Amir’s complex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shame, anger and pride into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of Muslim Americans’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the post-9/11 period, which involve the historical confront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the challenge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the sequelae of the Middle-East political conflicts. From full achievements to nothing, Amir’s personal disaster mirrors the unavoidable embarrassment and breakdown of contemporary Muslim Americans.
Muslim Americans; trauma;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Middle-East politics
2016-12-31
I207.3
A
1004-1710(2016)06-01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