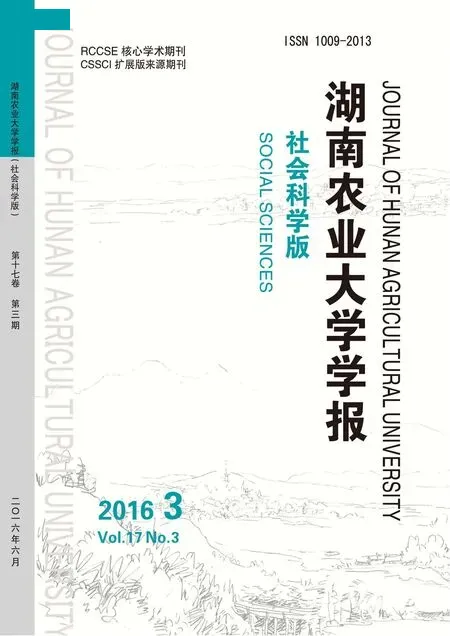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胡若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胡若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摘 要:针对现行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存在设定许可范围过大、与《物权法》立法理念存在冲突等现实困境,在对行政许可制度进行“四阶层”重新解构的基础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加以整合,抽象出行政许可制度的“四阶层”理论体系,并提出通过重构中国林木所有权分类体系以完善中国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设想。
关 键 词:林木所有权;行政许可;公共利益;特许;重构
一、林木采伐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
2012年8月21日《检察日报》曾经报道的朱绍余案件①的判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林农们提出“既然自己已经成为合法的经营主体,理应根据市场条件决定是否采伐木材和采伐多少,如果自己的林子不能自主采伐,所有权难以体现,利益更无法实现。自己获取这些林木又有什么意义呢?”[1]
近年,此类案件屡见不鲜[2],且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同案”特征:被告人砍伐自己承包地或经营地之林木;被告人未办理林木砍伐许可证。而案件在结果层面也基本上达到了“同判”,即被告人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法院的判决进行分析,发现法院的判决并无太多可非议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
由此,我们发现在此类案件中,法律与社会情理发生了冲突。在中国的传统法律理念中,天理,律法,人情必须兼得,方为正道[3]。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检讨判决及其所依据之法律本身。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法律的适用并不违反刑法规定的前提下,最终结果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便是作为法律规定本身,尤其是上文所述之构成滥伐林木罪之核心要件——现行林木采伐许可制度。
从上文对典型案件的解析中,我们已经确认,现行林木采伐许可制度之所以产生法理与情理的巨大争议的根源是作为司法推理法律前提的林木采伐许可制度,而中国的现行林木采伐制度又因何成为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呢?
对其进行梳理后的结果表明:中国现行的林木采伐许可在制度层面体现出一种“三阶层”的结构。所谓“三阶层”,即指在中国现行林木采伐许可制度设计中有如下规定:
首先,某些种类林木,如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因绝对禁止采伐而禁止设立许可③。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 31条第1、2款和第32条第1款之规定,林木允许采伐,但是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最后,对于无需采伐许可之事项予以例外设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及非生产用竹林[4]。
如此便形成了“不设定许可—一般许可—禁止设定许可”的三阶层结构。而这样的设定在现实面前显然是不完善的,而正是这样的设定导致了上述争议,其问题在于:
1. 设定许可范围过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存在冲突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除不以生产竹材为目的的竹林和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其余林木的采伐均需申请许可,其与《物权法》之立法理念及具体规定存在冲突。
依据《物权法》第124条与第125条规定,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之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范畴。按照用益物权相关理论,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定限物权,其与所有权相比仅仅缺少占有权,其他权利内容均相类似[4]。所谓物权,即为当事人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而所谓支配即为物权人依自己的意思对标的物加以管领、处分。由此,物权人对于物权标的物应当拥有自主权,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而现行采伐许可制度将绝大部分的农民收益权以行政许可方式予以限制,显然与物权本身定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物权法》产生冲突。
2. 以堵代疏,阻碍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许可设立的目的在于“危险妨害事先审查”[5]。林木采伐许可设定的目的便是保护林木资源,防止恣意采伐造成环境破坏。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堵”的策略。从实践来看,这种“堵”的策略固然在环境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但是却出现了类似篇首所述问题:当事人可以种植树木,但是在砍伐自己承包地上所种林木时却要由行政机关审批,而且所准备的材料与程序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了许可能否被批准,由此,当事人的种植积极性便会降低。国家有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权力,植树造林则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使群众乐于参与,这便是“疏”。当群众不愿意种植树木时,林木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空谈。而当下“以堵代疏”便是引发现行林木采伐纠纷最为本质的问题。
3. 审批手续多,不符合简政放权的制度改革目标
现行林木采伐的许可制度当中,几乎所有的林木采伐均需行政机关许可,公民在这一领域的自主权被牢牢限制,但是多数林木相较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并不属于稀缺资源,是否需要如它们一样进行开采限制值得怀疑,故这一现行制度设计与“简政放权”的理念存在根本冲突,难以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现行的林木采伐许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在中国主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视角下,即使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法官也必须依法裁判,否则便是枉法裁判。所以,为了避免法官与公众在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困惑与抉择困境,必须重新建构中国的林木采伐许可制度。
二、行政许可制度的解析
林木采伐许可制度亟需重新建构,但是重构必然建立在对于这一制度的充分理解之上,故而首先对这一制度进行再解析。
现行“三阶层”的林木采伐许可受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行政许可法律规范调整,故“行政许可”便是其基础理论。那么,“行政许可”是什么?《行政许可法》第二条将其界定为“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有批评者称这一定义更类似于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描述行政许可事实形成过程以提供办事程序,并非对于行政许可本质的揭示[6]25,基于此,人们无法对“行政许可是什么”这一许可的本质命题进行解答,也无法回答类似“为何要设置这些许可程序”以及“如何才是符合许可本质的程序设置”的命题,而后者对于林木采伐许可才是至关重要的命题。
又有研究者称,在第二条的概念界定中,“准予”是关键的要件[6]27。“准予”即为“允许”从事某些行为,从一方面来说,其意味着这些行为在被允许之前是被限制的,必须由行政机关的法律行为予以创设,从而形成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层面的自由[7]。相对人的自由与权利,也因为“准予”而被切割。虽然理论界对行政许可之前相对人的自由程度如何届分所持观点不同,但行政许可在实定法层面,无疑是以国家公权力为手段对相对人创设了一种可实际享有的、具体法律关系层次的自由。正因为对“准予”之前的相对人自由与权利的界定不同,使得行政许可的性质也显得“云山雾罩”,所以对其加以厘清至关重要。
1. 一般许可
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人相对于国家具有先验性,仅在个人利益膨胀以致危害他人利益之时方可限制,而这也是行政许可制度设立的内在目的,其不是一种国家基于主权者身份的施恩行为[6]30,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危险妨害行为[8],需要在特定事项上设定限制以防止侵害。更为重要的是许可设定的限度仅在于防止危险,此时,个体的自由被置于崇高地位。按照学理与《行政许可法》第 12条的规定,可以相对人为视角采取一个简单的四步框架来展现其发生机理:“即自由—限制—创设许可—自由”。针对这一情况设定的许可,虽是基于公共利益,但是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此时许可设立的条件应在保障危害审查目的达成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简化。而基于这一原理,所建立的许可制度,学界一般将其界定为“一般许可”,其在中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中有解释。
2. 特许
在权利的谱系当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些权利,它们天然地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虽然可以通过许可制度由私主体取得行为的自由,但与一般许可相比许可条件更为严格,而且并非符合条件即可以获得行为之准予,而是需要通过市场竞争等方式,这便是“特许”制度。同为许可制度,基于公共利益,其创设权利的程序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此,仍以“四步框架”为标尺。首先对第一步“自由”的界定颇为不同,即许可前的自由并非归属于个人,而是国家所有,原因正在于公共利益。因为类似土地、矿藏等公共利益过于巨大,不能由私人任意开发,必须交由国家处置。通常而论,一般许可中的自由被国家限制后并未纳入国家所有范围,而是更多地保持了一种被限制后的自由权属状态,在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国家监管但是并不直接所有;而特许之中国家将自由纳入自己限制之后,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以所有权制度加以明确,如《宪法》与《物权法》中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何对于权利需要采取两种不同的“限制后方式”,笔者以为原因同样是由特许制度的限制客体所承载的公共利益较一般许可而言更为重要,必须由国家所有才能达到保护的强度。而给付行政时代,国家为了谋求公共利益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利用市场规则和私人牟利的内在动力,将这些公共产品提供交给个人[9]。公共利益为“特许”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是“特许”的创设,却附带着比一般许可更为严格的要求,须以更加严格的程序方才可“准予”个人。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许可,其实质是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调节方式,无论是“一般许可”还是“特许”制度,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永远是其天平的两端,影响着行政许可的设立。许可制度如此,是否设定许可以及是否可以通过许可予以“准许”同样如此。
借由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将行政许可制度梳理为四个层次,即不设定许可,一般许可,特别许可以及严格禁止许可。在四个层次中,公共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影响逐渐增加,而个人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抵抗力逐渐降低。当特定事物进入行政许可的视野时,要对应上述四阶层的理论划分原则,根据事务本身的特性予以分化,以形成符合事务本质与比例原则的管制强度。这也应视为是现今林权改革“分类管理”要求的理论滥觞。对这一点的疏忽,也是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弊病根源:未能根据“林木”本身的性质厘定背后的权利性质从而对症下药。
三、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重构
科学的行政许可制度应当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林木采伐许可也不例外。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根据实践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的结合状态,以公共利益的强度为标准,阶梯化设定许可类型。中国现行林木管理体制的目的是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森林资源合理配置,较好地解决林业作为物质生产部门和公益事业部门双重功能的矛盾,满足社会对森林不同功能的多样性需求[10],其具体方法是:首先按照森林主导功能的差异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进而在此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两种林木各自特点和生长规律构建不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由此不难看出,建立在林种基础上的公益林与商品林二分法即源于对个人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的期待。但是从现实来看,公益林与商品林的届分未能达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目的。究其原因,在于公益性与商品性在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均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且缺乏具体标准予以参照[11]。这使得林木种类难以科学划定,进而导致林木采伐许可难以形成适当的创设体系,所以重构这一体系的要点是重构林木采伐许可客体——林木的基础理论划分框架,以更为切实可行的标准完善公益林与商品林这一基础划分方式。
1. 林木分类体系的重构
既然公益林与商品林二分已难以引导实践,故应引入新的标准对于林木进行重新划分。而所有权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
林木采伐许可是针对林木采伐而设定的行政许可,其客体是林木,国家关于林木权属的限制的态度显示了林木本身具有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属性,而这一国家态度的法律体现,便是所有权制度。所有权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配比,故林木中所蕴含的利益关系便在所有权制度中得到体现,从而作为构建许可制度与具体林木客体之间的桥梁,也可弥补因相同理念创设的公益林与商品林的二分结构的漏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9条、《物权法》第48条、《森林法》第27条等规范中对中国现行林木所有权进行了规定,将林木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以及个人所有,因三种所有权性质体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动态平衡,故而对其所有权客体的界定也应当遵照此原则。
(1)国家所有权。林木属于自然资源,故林木所有权属于自然资源所有权概念体系[12]22。而所谓国家所有权,以中国通说,就是国家对国有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13]。于林木资源领域,其实定法依据在于《宪法》第9条与《物权法》第48条所规定的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宪法》规定林木所有权的目的在于为国家统筹管理林木资源设定正当性基础,而非国家在实然层面直接支配所有的林木资源[12]27。《物权法》虽然直接规定了权利主体对于权利客体的支配性,却规定了但书情形,其意义在于即使国家能够在实定法层面直接支配林木资源,但是国家权力也存在界限,并非所有资源均可直接支配,而这一界限便应当是公共利益。
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利用的正当性在于自然资源具有的高度的公益性与权属不确定性[12]33,在此两种特征中,权属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公益性紧密相连,所以高度的公益性便成了国家所有权产生的核心正当性基础。
在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客体都有着公益性,但是并非所有客体都需国家的直接支配,否则便是对于社会活力的过度侵害,而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将导致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以及对最初使用者的不公平。所以林木国家所有权所伴随的公益性必须是“高度”的,而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林木本身也须具备高度的公益性。
(2) 集体所有权。林木集体所有权来源于《物权法》第43条、第58条,以及《森林法》第27条之规定。所谓集体所有权就是集体组织对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其享有者主要是农村集体组织,也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合作社集体组织。集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生产组织,更是社会自治体,其核心特征便在于对于自我事务的自我规制、自主决定,在权限范围内排除国家权力的直接干涉,国家仅有监管职责。在此原则之上,集体所有权也具有了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的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与国家相对分离的民间社会和社会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14],国家不可能也不必掌握全部资源,故国家仅需对高度公益性林木客体以所有权制度加以直接掌控,而对于公益性较低、可由社会自治体决定的林木客体则可交由其自主规制。从现实出发,经过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实践,以村集体自治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自我规制经验与内部规则,能够胜任该任务。
集体所有制并非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完全退出,虽然《宪法》第 9条“;”后以集体所有制规定对林木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正当性限度加以规定,但是国家成立的天然正当性基础在于排除国民利益危险之妨害,所以即使集体对于某些林木资源具有直接的支配权利,也并不能排除国家基于危险妨害而具有的监管职责。而另一方面,基于集体对林木资源的直接支配性,国家对集体所有林木资源的限制程度、程序均应以危险妨害为限。
(3) 个人所有权。个人所有权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管理。在上文所示行政许可的“四步”结构中,自然状态下从属于个人的自由被国家与集体以所有权的方式所限制,分别归属国家与集体管制,而所剩余的自由便被保留于个体,依然为个人所有。这种公民自治相较于集体所有权的社会自治,于个人而言具有更加开放的自由限度。因集体的决议来源于利益的平衡,个人利益在集体之中无论如何保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削弱,所以集体与国家所有权均为限制个人自由的“魔阵”[15]。只有个人能够直接支配权利客体时,其自由才是完整的,而其前提也在于最大限度地排除国家与集体干涉存在基础——公共利益。正因如此,建立在个人所有权之上的具体林木客体包含的公共利益也应为最小程度。
林木分类体系以林木的所有权作为基础,将比例不同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分别嵌入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个人所有权之中,能够通过将公益林与商品林的区分实在化,以所有权为基准划定不同类型的林木,进而设定不同类型的行政许可,以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完成对于中国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的重构。而这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林木设定也能够与《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规定衔接,从而避免上文所述《森林法》与《物权法》的理念冲突。
2. 采伐许可制度的重构
(1) 不设定许可。行政许可制度的实质在于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平衡,具体制度的设定也必然涉及事项所具有的公益性与个人利益之比例,由此,必然存在此类事项,其极少涉及公共利益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此类事项不应创设许可。
不设定许可在实定法上对应《行政许可法》第13条第1款,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自主决定的事项可以不设立许可”,这一规范核心要件在于“自主决定”。在林木采伐许可领域,这一规定具体体现为“不以生产竹材为目的的竹林和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可以不设定许可”[1],由于非生产竹林与农民自留地及房前屋后自己种植之土地均为生活资料,而非商品交易用林,在实践中基本也源于农民自己种植,故在林木采伐许可实践中,不设定许可的核心要件是“个人种植”。抽象规范中的“自主决定”与具体林业规范中的“个人种植”相对应。其可能带有偶然性,但对于理解林木采伐中的“自主决定”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依上文所述,将“个人所有”等价于个人所有权而后结合,将不设定采伐许可的林木设定为个人所有的林木,并以《森林法》第27条为依据,将林木个人所有权的核心设定为“个人种植”,即由林农个人种植之树木,因个人享有所有权,均不设定采伐许可,而非以林地或非林地作为标准⑤。
(2) 一般许可。一般许可要求政府仅在必要的限度内对于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要求政府保证公民自由,即使在作为限制的行政许可制度运行当中。关于这点,研究者易于忽视是:政府必须在“必要”限度内“高效率地”防止个人自由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妨害。显然,“必要性”的限度与“高效率”的结果要求存在审查强度与时效性的紧张关系,所以,作为许可主体的行政机关必须选择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妨害审查。
面对这一困境,实务与理论界均将目光转向了“公私协力”,即由社会体对一定社会事务进行自我规制,而行政机构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监管的新型管理模式[16]。本研究范围内,公私协力模式可由集体所有权建立,即一般许可的对象对应集体所有林木。
集体所有权的客体为公共利益较个人所有权大而小于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林木,对于此类客体,因为集体所有,故而其采伐主要借助集体的内部规则与决策程序,当相对人申请采伐时,其自身通过内部程序进行公共利益的判断,进而对许可相对人采伐集体所有之林木做出是否“准予”的决定,此种审查亦作为行政机关最终许可的前置“预审”程序,极大减轻行政机关的负担,提高效率,而在此过程中,行政机关并非放弃职责,而是藉由对于集体许可审查的监管,如审查集体决策材料是否齐备等方式判定申请人的采伐行为是否具有妨害后果,从而最终决定是否“准予”许可。
(3) 政府特许经营。如上文所示,具有高度公益性的林木资源应被纳入国家所有权范围。因其高度的公益性,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条件与程序尤为严格,但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所有权客体不可被纳入市场化运作,相反,此类客体在公益价值外往往蕴含着极高的经济价值,一旦选择得当,会带来公共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但如上文所言,由于国家所有权于初始的自由被限制后发生个人向国家的所有权移转,故而当其再次向个人移转时,即带有“赋权”的特性,如此,便与特许经营制度不谋而合。
实践中政府特许经营指政府作为特许人将国家的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的经营权许可给被特许人经营,被特许人向政府支付特许经营费[17]。特许是政府的一种行政许可,是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和批准的行为,在这一层面上,特许权具有公法上的性质无疑。而当特许申请人得到行政机关的特许之后其便取得了特定事项的独占权。在实践中,这种特许多以特许契约的形式得以建立,故而此又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也具有私权的性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特定条件下行政机关有权单方面变更和解除合同;而且在特许经营权发生变更和终止时,行政机关必须保证公用产品供给和服务的连续性与服务性[18]。基于上述分析,特许经营制度无疑是能够兼顾公共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善治”。
(4) 严格禁止。虽然对属于国家所有权的林木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有利于公共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但是林木本身存在的公共性与私利性双重属性决定了当公共利益极端大于个人利益,以致个人利益极端微弱时,便存在不可让渡于私人的公共利益,否则便可能对国家根本秩序产生危害。对于此类林木资源,必须坚持由国家直接支配,并且直接行使所有权。但是,“公共利益”作为法学中最神秘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之一,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次以列举方式在立法上界定了“公共利益”,但是这样单一的实体标准是否能够实现规制目的着实令人怀疑。为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坚持实体界定标准的同时,引入公民参与的程序,双管齐下。
首先,在实体标准上,应当为“公共性”的判断寻找具体化标尺。有“民营化大师”之称的E.S.萨瓦斯以“集体物品”为公共性的顶端,即物品无需合意即可给付,且多人同时使用不会影响使用品质[19],而满足此两项标准的林木也应具有最强的公共利益而严格禁止采伐。实践中,烈士陵园等地的保护树木,以及《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的一级公益林因在陵园景观、环境保护、树种存续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一般不需要支付对价且为公众共同享有,应被纳入严禁采伐范围。
另一方面,针对实体标准滞后等缺点,应当导入公民参与程序,即在禁止采伐林木的确定过程中,召开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让多元利益的冲突与妥协得以在规范化、有序化的框架中进行,让不同的声音得以有效的表达,逐步确立以重大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禁止目录”形成机制。
3. 采伐许可证制度重构的原则
面对实践问题,林木采伐许可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其作为以“合理设定许可权”为重要目标的改革,自然应当坚持国务院“简政放权”的基本部署,即应当坚持法治化改革路径。
首先,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解决合法性困境,即无论设定许可、许可批准与实施,以至最后的事后监管,都必须以上位法律法规为准绳,不能以制度改革的名义违反法律规定,这也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与集中体现。
其次,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虽然既定林业采伐许可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违法行为正当化的理由,而“简政放权”改革同样也必须以坚持法制统一、维护现行法制权威为出发点,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明显违反许可设定的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查处,这样才能保证“简政放权”的顺利进行。
最后,给予基层部门以合理限度的裁量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监管部门直接面对群众,监管行为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接受程度,而基层部门的实践也可以为顶层设计提供经验。在目前林业采伐许可改革中,很多制度设计来自地方创新,而为其提供保证的,正是现行法框架为其保留的合理裁量权空间,对这种空间,无论是立法还是上级行政机关,均应当加以鼓励,从而做到合法与合理并重。
注释:
参考文献:
[1] 李媛辉.林木采伐管理或应进入微调期[EB/OL]. (2008-10-20)[2015-9-3].http://www.greentimes.com/gree n/news/zhuanti/lingai/content/2008-10/20/content_17659. htm.
[2] 杨流辉. 村民未办采伐许可证砍伐自家树木被判刑[EB/OL].(2012-11-26)[2015-9-5].http://news.jcrb.com/Bi glaw/CaseFile/Criminal/201211/t20121126_993949.html
[3] 陈林林.古典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取向——以宋“阿云之狱”为分析样本[J].中外法学,2009(4):636-637.
[4]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251
[5]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23.
[6] 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J].法学研究,2004(5):25-35.
[7] 霍费尔德.基本法律概念[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6.
[8]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88.
[9]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03.
[10] 国家林业局.LYIT 1556-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公益林与商品林分类技术指标[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1.
[11] 俞心慧.关于政府规章罚款限额问题的几点认识——重温《行政处罚法》[J].上海人大,2006(9):28-29.
[12] 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J].法学研究,2013(4):19-33.
[13]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与立法解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205.
[14] 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1(1):3-17.
[15] 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86.
[16] 刘宗德.公私协力与自主规制的公法学理论[J].月旦法学杂志,2013(6):1-21.
[17] 黄进.构建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制度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9(5):158-161.
[18] 马闻声.森林公园经营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政府特许经营为进路[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1):15-17.
[19]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47.
责任编辑:黄燕妮
中图分类号:D9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6)03-0077-07
DOI:10.13331/j.cnki.jhau(ss).2016.03.012
收稿日期:2016-04-15
基金项目:司法部资助项目 (13SFB3010)
作者简介:胡若溟(1990—),男,陕西韩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第五条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的核心要件便是未经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之规定②。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rest cutting licensing institution
HU Ruoming
(Guanghua Law School, Zheng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China)
Abstract:Considering conflict between legal concept of the Property Law, and licensing system of forest cutting whose limits have been too excessive,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ystem must be reconstructed by four steps, so we can re-integrate the private interes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o abstract the so-called “Four-Level” concept system for the Administrative Law. By this course, we can rebuild Chinese forest cutting institution in four levels with reconstruct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rest ownership.
Keywords:ownership of forest;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ublic interest; concession; reconstruction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工业化与乡村集市社会空间萎缩
——以胶东P市为例 -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西方的经验及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