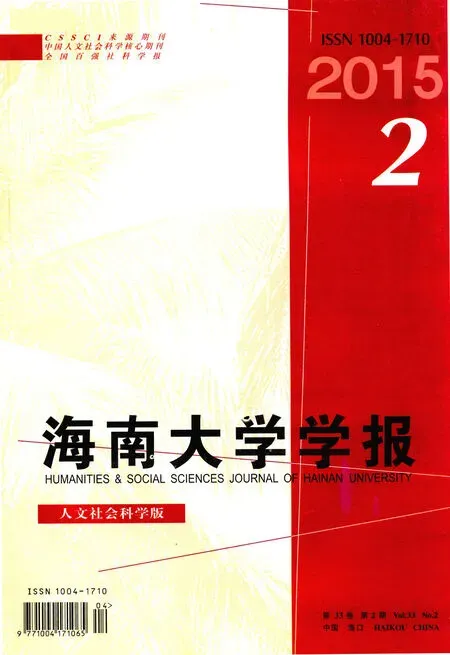论美国诗人斯奈德生态思想的美学特征
毛 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论美国诗人斯奈德生态思想的美学特征
毛明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具有明显的美学特征,这既表现在它具有一般的美学特征,更表现在它具有生态美学特征。其生态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强调人在面对大自然时的审美情感、秉持更加多样的审美标准、肯定生态过程中因“流变”而体现出的“不确定性”。上述特点符合其诗人身份,并为进一步了解其生态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生态思想;生态美学;美学特征
美国斯奈德研究专家派屈克·墨菲指出,“深层生态学”的“桂冠诗人”( laureate of deep ecology)加里·斯奈德的诗歌主题有三大思想来源:美国印第安文化、东方文化、生态观念[1]。具体说来,三大思想来源的核心内容分别是美国印地安民族的生态观念、佛禅思想、深层生态学。这三方面如何统一?学界大致有两个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者统一于以传播美国印第安民族生态观念为目标的观念革命、佛禅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被斯奈德用于证明自己既有的印第安式的生态观念。一种观点认为三者统一于推动环保运动的社会革命,这是斯奈德落实“深层生态学”八条行动纲领中第六、第八条的具体实践,而三大思想来源都是为斯奈德的环保“行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上述观点都在强调斯奈德的环保主义者身份,对斯奈德的另外两个身份——诗人和佛禅信徒身份重视不够。而对后两个身份、特别是诗人身份的忽视可能导致对斯奈德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
本文认为,如果说环保主义者身份更多体现了斯奈德生态思想的“求真”与“向善”,那么诗人和佛禅信徒这两个身份则体现了斯奈德生态思想的另一个特征——超越了“求真”与“向善”的“尚美”,特别是对生态美的崇尚。
一、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具有“尚美”的特点
首先,与人们通常具有的对生态思想的功利性理解——为人类谋生存求发展(包括将人类伦理道德观推广到生物界)——不同,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具有符合审美判断要求的超功利特征。
斯奈德生态思想的超功利特征最突出地体现在打破善恶界限,将一切解释为宇宙间能量传递与转换的思想之中。这一思想源于佛教“业”的理论,经由阿兰·沃茨被斯奈德吸收。斯奈德说:“华严宗视世界为庞大、互为关联的网络,这里所有的物体与生物缺一不可且受启智。从一个观点来看,政府,战争,以及其他我们认为的‘恶’,都是不折不扣地被涵盖在这个范围内。”[2]230-231最能显示斯奈德这一思想特点的事实是他不忌讳杀生,斯奈德在诗里写道:“我什么都杀/除了野狼我什么都不怕/从考立兹口到其源头,/只有野狼吓唬我,/我有酋长的尾巴/——臭鼬鼠。/我们把山鹿咬在嘴里/我们把山鹿咬在嘴里/我们弄黑了我们的脸——野狼之歌。”斯奈德认为杀生不仅不是恶,甚至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爱,在《神话与本文》中的《打猎》第八首,他将被猎人杀害的鹿描述成慈悲的献身:“鹿不想为我而死亡/我将会饮用海水/雨中睡在海岸的圆石上/直到鹿躺下死亡/为了抚慰我的苦痛。”[3]斯奈德认为杀生可以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在《献给盖娅的小诗》第十九首中,诗人笔下的盖娅既是女猎人,又是生育女神;作为生育女神。盖娅使地球上的生命得以延续,使万物充满活力。因此,斯奈德说:“狩猎术的设计是使猎物自动送上门——他们听到你的歌、目睹你的真诚、因为惺惺相惜朝你而来。狩猎的目的不仅是杀死猎物,还要帮助他们生——增加他们的生殖力。”[2]236-237斯奈德认为,即使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环,也要接受“被别种东西摘采”(被吃、被毁坏)的事实,他说:“地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自己小小的分水岭、人与其他生物能和平共处、有一个可唱可默想的地方、有摘苺果的地方,更有被别种东西摘采的地方。”[2]323在《初到日本》这首诗里斯奈德写道:“盐—藻—鲱鱼—渔民—我们。在吃。”[4]这些词连在一起,表明事物因为互相吃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被问及什么是所谓“真正的工作”时,斯奈德甚至说:“真正的工作是互相吃……(与写诗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他们全都同样地真。”[2]53-54
康德指出审美判断具有超功利性。他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当然,具有超功利性的判断未必都是审美判断,但超功利性的确是审美判断的必要条件。
其次,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强调大自然带给人的愉悦感,称之为“美的纯粹感受”,并将自由感作为其核心内容,这些思想也符合审美判断的规定。
斯奈德笔下的大自然是“欢乐”的,他说:“我宣誓成为/龟岛土壤的/以及那些/生活在其上的人的盟友/一个生态环境/各式各样/在太阳底下/每一样东西均享有欢乐的诠释。”[2]324身处自然的人是愉悦的:“我们的爱混合着/岩石和溪流/一次心跳/一次呼吸/一次凝视/让在令人晕眩的地方/活在这个古老而清晰的方式里。”[5]康德认为,审美判断的先验原则在于情感能力,它通过情感能力来判定一个对象是否是符合目的;因此,在审美判断中“情感能力……是决定性的。”由此可见,自然界给人以愉悦感,这就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提供了基础。斯奈德认为人与自然的这种愉悦关系是天然形成的,他将此归为两个原因:一是人与自然共有的“无形、纯然的欣喜的本性”;诗,特别是使诗成为诗的“美”就是从中产生的:“诗源于‘空’,源于无形的、纯然的欣喜的本性……(诗)真正的美丽、深刻,贴近人类。”[6]18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转移关系,他在诗《能源是永恒的愉悦》里写道:“水源的循环、空气的循环是神圣的,自然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大自然的能量是我们愉悦的源泉。”审美恰恰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康德所说:“惟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和自由的愉悦;因为没有任何利害、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由此不难理解斯奈德将这种愉悦称为“美的纯粹感受”。他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生生的——树,草,风和我跳舞、讲话;我也听得懂鸟儿的歌声。这种古老的经验……是美的纯粹感受。”[2]240“美的纯粹感受”的核心内容是自由感,斯奈德说:“对美国人而言,‘自然’代表荒野,代表充分的自由、不受拘束的范围。”[2]235《达摩流浪者》里,雷蒙描写了自己在杰菲·赖德(其原型是加里·斯奈德)的指引下,经由自然审美获得的自由感,他说:“到底,当我思考到我自己就是空与觉、思考到一切无非空与觉的时候,所意味着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意味着,我就是空与觉,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就是空与觉、知道我和万物是没有分别的吗?换言之,我和万物已经一体了,我已经成佛了。我对四周的树木满怀柔情,因为我们本是同一物。”[7]162在物我交融中,雷蒙证悟了自我的存在以及身心的自由:“在东方,是一片灰蒙蒙;在北方,是一片令人心生敬畏的庄严;在西方,是狂暴的落日;在南方,弥漫着我父亲的雾。杰克山戴着它一千英尺高的岩石帽子,俯视着一百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冰原;肉桂涧宛如一只披着苏格兰雾的猛禽;沙尔在金角湾的苍凉中迷失了行踪。我的油灯在无限中燃烧。‘可怜凡夫俗骨啊,答案是不存在的。’我终于明白了。我已经不再知道些什么,也不在乎,而且不认为这有什么要紧的,而突然间,我感到了真正的自由。”[7]263
再次,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主张人类持有开放的心态,认为开放的心态让人成为“通灵”的诗人,在主体建构上做出了具有审美特性的规定。
斯奈德认为禅境是一种更加开放,甚至不得不保持开放的状态:“日本的禅院较之东俄勒冈州古老的派尤特族或肖松尼族印第安人会对我将更加开放,因为他们不得不保持开放——大乘佛教就是这样一回事。”[6]137禅宗是为了发动和维持开放的心态而设的:“如果禅宗教导了什么,那就是日常应让身体以一种冥想姿势静坐,这是一个极好的(可是绝不是唯一的)发动和维持开放心态的方式。”[8]
放弃对于自我的执着、维持开放心态的目的是和世界“整体”保持联系。他经常引用日本禅师道元的名言:“我们研究自我是为了忘掉自我,当忘记了自我,就与大千世界合二为一。”他强调指出:“‘大千世界’意味着所有的现象世界:当我们保持开放,世界就能拥有我们。”[9]150
和世界“整体”的联系让人成为通灵的诗人,成为审美主体。阿兰·沃茨认为人和艺术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禅的艺术不会仅仅或主要是具象的。即使是在绘画作品里,艺术品不仅仅被视为表现自然,艺术品本身就是自然的艺术品。”斯奈德非常认同该观点,他还特地对“艺术”一词作了一番考证,认为“craft”的词根源于古英语“croeft”,源于德语“Kraft”,意为“力量”或“价值”,说明艺术品同自然物一样,体现着自然的力量与价值;艺术品的制造者,包括诗人,作为这个艺术化的世界和人生的特定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使命:觉悟并表现人与自然的深刻联系。他说:“作为神话——掌握者——治疗者的诗人同时也为其他的地方、深处的潜意识发声,为内在、未知的心灵领域与当前瞬间直接的自利意识的整合起作用。外在自然界与内在无意识界被剧作家——仪式举行者、艺术家——诗人带到一个焦点之下……伟大的神话传说可以给予一个小型、孤立的社会提供心灵的呼吸,借以避免鄙俗并了解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6]172
需要补充的是,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强调感性表现,这样的表现方式也具有审美特性。斯奈德是一位诗人,以诗歌为媒介对生态思想进行艺术化的表达是其一贯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兹不赘言。斯奈德生态思想的关键词是“野”( wildness),他用“自由的”、“富于表现的”、“身体的”、“性开放的”、“心醉神迷的”等词对“野”进行描述和界定,也体现了其生态思想的审美特性[9]9-10。
二、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具有崇尚“生态美”的特点
首先,前文有述,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强调人在面对大自然时的审美情感,这符合生态美学的观点。因为“与以往的种种生态学不同,生态美学既不是想从技术手段上解决生态问题,也不是想从经济策略、政治制度、伦理观念上解决生态问题,而是想从人类的审美情感上介入生态问题。”[10]
其次,斯奈德的生态思想秉持更加多样的审美标准,这与生态美学的主张相似。“生态美学比之普通美学,在审美标准上更灵活,也更具有容忍度。美没有唯一标准,自然界的混乱与秩序,残缺与完整,喧哗与寂静,起伏与平坦,乃至生物世界的和平与吞食,诞生与死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对自然物体存在的逻辑和自然生物生存逻辑的充分尊重,对造物创造的痕迹及其成果的充分谅解和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社会生存的逻辑本身的尊重。”[11]207-208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斯奈德生态思想中生态世界的典范——野域( wilderness)与普通/传统美学的界定相去甚远,野域“潜藏着混乱、性爱、未知物、禁止的领域,是狂喜与恶魔的聚居地( wilderness has implied chaos,eros,the unknown,realms of taboo,the habitat of both the ecstatic and the demonic)[9]11。他还认为:佛禅主张的“慈悲”之心“表示肯定最大范围、不构成伤害的个人行为——保障吸食大麻、吃龙舌兰、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同性恋的权利……这表示尊重智慧与学习”[2]231。
最后,与其他生态思想偏重于强调大自然的“确定”的“完整性”不同,斯奈德认为世界“整体”的本性是“空”( emptiness),变动不居,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应该肯定生态过程中因“流变”而体现出的“不确定性”。上述观点与生态美学思想一致。“在高级的核心层面上,生态美学更加强调和注重的是美的生命涌动性和流变性。”[11]152生态审美“关注自然进程,而非仅仅是自然的事物……诸如失衡、无序和混乱等可以视为积极的美学品质。流变这个词汇强调了自然系统中的变异、变化、流动,而非静止,而这正是平衡一词的意指。尽管这个隐喻并不否认自然中稳定时刻的存在,但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都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可以持存的自然系统乃是各种流变的结果。”[12]在一次谈及艺术灵感时斯奈德说,缪斯的到来是意想不到的:“这是发现自己不需要自我的一个惊喜,与工作合一,在纪律严明的轻松与优雅中前进……在这里人是可以自由的,与工作合一又超越工作。”[9]148这种创造性的自由对斯奈德而言是伦理原则的结束,与永远变化的万物本性相和谐的自由生命的开始,斯奈德将这样的状态称作“逍遥游”( free and easy wandering),并注明这是一个来自庄子的术语( a Zhuang-zi[Chuang Tzu]term)[9]150。斯奈德有时将“逍遥游”与“失路”( off the trail)相提并论,他在《这条路不是一条路》一诗里这样写道:我开下高速公路/在一个出口转向/沿着公路走/直到一条侧路/开上侧路/直到泥路出现/满是坑坑洼洼,停车。/走上一条小路/但路越走越难/它消失/在开阔之处/哪里都能去[13]。没有路的地方处处是路,这就是“哪里都能去”的“逍遥游”,像行云流水一般。斯奈德说:“我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获得某种自由和变动,就好像是古代的云游僧一般,只要打上背包、背上睡袋,你就可以上路了,进入乡间,穿越高山。中文对这些禅僧用‘云水’相称,字面意思是‘云彩’和‘流水’,取自中国的诗行‘浮云流水’……”。斯奈德认为,拥有生态审美意识之后,人类可以生活在“永恒的当下”(“the perpetual present”),即永远流变不已的生态“过程”( process)之中[9]14。这是“梦想时刻”(“dreamtime”),该“梦想时刻”“流动易变、富于变化性,有着物种间的交流和雌雄间性、彻底创造性的运动,整个人类的景象都将改变。”斯奈德特别指出:人类期待完美,但“完美的路”不是带我们去能够轻松定义的地方,去到进步停止的特定地方[9]153。因为那将是一个破除了二元对立并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极具审美意味。他在诗中如此描绘该世界:“浮动着在小舟里/轻轻地在水上,石头和每一朵涟漪,/另一表层随水滑动/悬挂在天海之际/绵绵青山到/层层白云/轻滑,靠着……/我们没有定点/但可能在这儿。”[14]130-131“行行重行行/脚下地球旋转/溪山流动不止。”[14]9
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在“求真”与“向善”两个维度里,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仍然体现出审美特征。斯奈德认为生物间、生物与非生物间能量的传递促成了创生、共生的状态,他用佛教理论解释万物间因为能量转移形成的生态关系,说:“肉体化了因陀罗网中的一颗颗明珠,说明生态系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捕食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每一种生物都被包含在因陀罗网中,如果生物种类愈多,因陀罗网所反射的镜像也愈多,这也就象征着生物多样性,反映生态系有着更活泼的生机。”“明珠”、“活泼”、“生机”等用词表明斯奈德的理解带有审美特点。此外,作为佛禅信徒的斯奈德一方面非常重视大乘佛教“慈悲”、“众生平等”、“社团”等伦理主张,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美学追求。作为诗人的他曾说:“宗教一直倾向替社会制度护航,成为权力谦卑的侍仆,而不能大胆地解放人心,治愈、启迪人们……只有诗人光凭他自己的声音和母语,游走于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如云翳般的状态,与语言晶亮剔透的纲目、闪闪发亮的利刃之间。”[2]234尽管身为佛教信徒的斯奈德有时认为宗教的境界不需要诗歌:“宗教习俗和佛教习俗的另一极将超越艺术。那就是能够使一切现象达到完美境界的东西。真的进入了这个世界,你就不再需要艺术,因为一切都是醒目的、鲜活的和迷人的……”[15]但“醒目的、鲜活的和迷人的”这些表述本身就有审美特征。由此可见,艺术(审美)特征、宗教特征与科学特征在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均有体现并已融为一体。
三、结论
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他的生态思想具有超功利性,将以自由感为核心的审美愉悦置于优先位置,赋予具有审美人格的诗人以崇高的地位,强调对自然的感性体验和表现,体现了美学特征。此外,他的生态思想由于秉持更加多样的审美标准、肯定生态过程中因“流变”而体现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具有生态美学的独特品格。可以说,生态美学特征体现了其生态思想的独特性。正视这一事实,给予该事实以应有的重视,或许至少可以纠正下列偏颇:斯奈德仅仅或主要是印第安古老生态观念的传播者、环保运动实践者。作为一位诗人,斯奈德生态思想的美学特征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艺术化的形式、一系列修辞手法的运用,它似乎还包含着更深刻的含义:确有神圣的、神秘的、让人心旷神怡并值得皈依的大美、大智慧、大自由潜藏在一个被冠以“生态”之名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切生态保护观念、行动的原初动力与终极目标;对这个世界的体认从根本上讲不能依靠科学和理性,混合了宗教式觉悟的审美体验才是唯一的途径。
[参考文献]
[1]PARICK D Murphy.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M].Orangeburg: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2: 12-14.
[2]加里·斯奈德.山即是心[M].林耀福,梁秉钧,译.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0.
[3]GARY Snyder.Myths&Texts[M].New York: Toterm Press,1960: 28.
[4]PARICK D Murphy.Critical Essays on Gary Snyder[M].Boston: G.K.Hall&Co.,1991: 235.
[5]GARY Snyder.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M].Washington,D.C.: Counterpoint,1996: 128.
[6]GARY Snyder.The Real Work: Interviews&Talks,1964—1979[M].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Corp.,1980.
[7]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M].梁永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MARK Gonnerman.“On the Path,off the Trail”: Gary Snyder’s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Zen[D].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2004: 351.
[9]GARY Snyder.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Essays by Gary Snyder[M].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1990.
[10]陈炎.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11]党圣元,刘瑞弘.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李庆本.国外生态美学读本[[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187.
[13]GARY Snyder.Left out in the Rain: New Poems,1947—1985[M].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1986: 127.
[14]GARY Snyder.Endless Streams and Mountains[M].Washington,D.C.: Counterpoint,1996.
[15]艾略特·温伯格,加里·斯奈德.温伯格与施耐德对谈诗歌的艺术[EB/OL].[2015-05-12].http:∥www.jintian.net/bb/thread-21153-1-1.html>( accessed 2010-01-16).
[责任编辑:吴晓珉]
On the Aesthetical Features of Gary Snyder’s Ecological Thought
Mao Ming
( College of Literatur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nan Province,Haikou,571158)
Abstract:Gary Snyder’s ecological thought show obvious aesthetical feature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normal aesthetical features but also ecological aesthetical features.The latter include aesthetical attitude to nature,more aesthetical standards,the affirmation of“uncertainty”caused by continued ecological changes.The ecological aesthetical features are in keeping with his identity the poet,and provide a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his ec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Gary Snyder; Ecological Thought; Ecolog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al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I 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6) 02-0110-05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毛明( 1974-),男,四川广元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