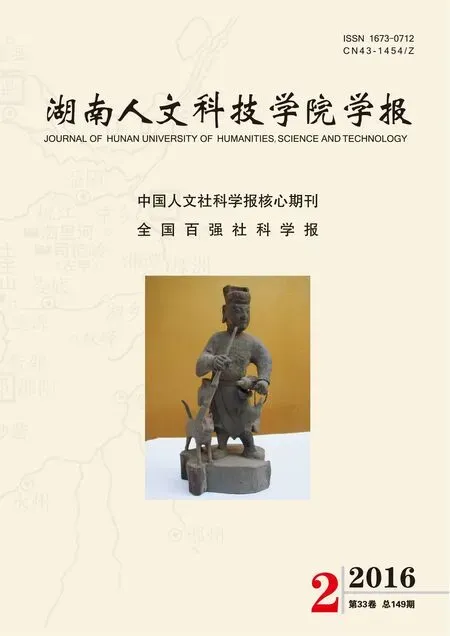论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防治策略
袁爱华,林怀满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论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防治策略
袁爱华,林怀满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要]我国在惩治跨境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相关罪名设置不合理,拐卖外籍妇女、儿童到我国不属于情节加重犯,对买方的打击偏轻,关于被害人的同意能否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争议等。对此,建议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改为“拐卖人口罪”,并将“将外籍妇女、儿童卖到中国”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加大对买方的打击力度,规定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阻却违法。我国在司法惩治这一类犯罪时存在案件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相关外籍涉案人员身份核实难、遣返难等问题。对此,应加强国际合作,正确识别非法移民和拐卖人口犯罪的被害人,并履行好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受害人的义务。同时,国家应该允许非政府组织设立中介机构,为外籍人士来我国通婚和就业牵线搭桥;各国应加大法律宣传,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只有多方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跨境拐进人口;立法不足;司法障碍;犯罪预防
跨境拐卖人口到我国的犯罪已成为我国拐卖人口犯罪中比较突出的、发展比较快的犯罪现象。这一类犯罪从立法惩治、司法追究到预防犯罪都和国内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对策,因此,有必要研究防治这一类犯罪的策略。
一惩治跨境拐进人口犯罪存在的立法不足及完善策略
(一)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现状
我国于2010年2月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下文简称为《补充议定书》)。刑法规定了一系列与拐卖人口相关的犯罪。我国拐卖人口的犯罪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拐卖行为构成的犯罪,刑法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本罪的被害人不包括已满14周岁的男性;第二类是拐卖之后的目的行为构成的犯罪,刑法规定了以婚姻、收养为主要目的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以性剥削为目的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罪名,还规定了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强迫劳动罪;第三类是针对拐卖行为的渎职、妨害公务、妨害司法方面的犯罪。刑法规定了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妨害公务罪等罪名。
(二)刑法惩治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立法不足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属地管辖原则,外籍妇女、儿童被拐卖到我国,犯罪行为有一部分发生在我国,我国刑法对该类犯罪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拐卖妇女罪中的妇女既包括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因此,不论是从立法规定还是从管辖的角度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跨境拐进人口的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刑法的规定对惩治跨境拐进人口到我国的犯罪存在以下不足,影响了打击这一类犯罪的效果。
1.罪名设置与国际惯例不协调
《补充议定书》用的是“贩运人口”这一概念,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用“拐卖人口罪”[1]。唯独我国法律设置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从长远来看,我国使用的罪名把本罪的犯罪对象锁定为妇女、儿童,会导致拐卖14周岁以上男性的犯罪行为不能依照本罪得到应有的或较重的处罚,且该罪名和《补充议定书》中的规定不协调,会招致履行国际义务不力的批评,同时,该罪名和其他国家规定的罪名不协调,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会因罪名的不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未将“外籍妇女、儿童卖往中国”规定为情节加重犯
我国刑法规定了8种情况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升格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乃至死刑。其中第8种加重情节是指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并未规定将外国妇女、儿童拐卖到中国定为情节加重犯。但拐卖外籍妇女、儿童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容小觑。首先,拐卖外籍妇女、儿童到我国也严重侵犯了外籍妇女、儿童的人权,他们在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等障碍会使其获救更难,处境也更艰难。其次,一部分被拐卖的外籍妇女和我国男性非法通婚形成事实婚姻,一旦被解救就要遭到遣返,收买者被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收买家庭妻离子散、家庭破裂的现象,成为影响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非法通婚的被拐卖外籍妇女及其子女在我国的社会化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加之,跨境拐进外籍妇女、儿童到我国的犯罪涉及到多个犯罪地,侦查、解救、善后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工作耗时长、花费大,加重了财政负担。
3.对买方市场的惩治偏轻
因为我国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很多男性出现失婚现象,特别是边远偏僻的地区,男性失婚现象更为严重,而拐卖来的外籍新娘娶亲成本低,易于解决男性失婚问题,所以跨境拐进外籍妇女到我国的犯罪猖獗。只有斩断买方市场,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我国刑法针对买方市场,设置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但和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相比,此罪的法定刑偏轻。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做了修改,规定实施本罪,“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本罪的法定刑最高才到3年有期徒刑,刑罚本身就偏轻,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更轻,对买家不能形成震慑。加之司法实践中主要注重打击拐卖行为,还有大量的收买行为没有被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买家的犯罪行为仍然有恃无恐。
4.关于被害人的同意能否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存在争议
刑法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被害人同意能否阻却违法,对此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张明楷认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侵犯的是妇女、儿童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所以,如果行为征得了妇女的同意,行为人的拐卖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拐卖儿童的,即使征得儿童的同意,拐卖儿童罪仍然成立[2]。在《补充议定书》里,对该问题是这样规定的:即使人贩子在其行为之前,已经得到了被害人对侵害其权益的同意或认可,也不能消除贩运行为的违法性[3]。可见,我国主流的观点和国际条约的规定有冲突。
(三)惩治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立法的完善策略
1.将拐卖妇女、儿童罪修改为拐卖人口罪
建议我国立法把拐卖妇女、儿童罪修改为“拐卖人口罪”,同时把拐卖妇女、儿童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这样一是顺应拐卖人口犯罪的新趋势,可以更好地保护14周岁以上男子的合法权益,二是可以更好地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打击贩运人口犯罪的义务,三是可以让我国相关类型的罪名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类型的罪名协调起来,便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2.将“将外籍妇女、儿童卖往中国”规定为情节加重犯
基于拐卖外籍妇女、儿童所具有的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也应该把这一情节设置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才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使拐卖外籍妇女、儿童到我国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3.加大对买方市场的惩治
建议刑法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提升到5年有期徒刑。同时,司法加大对买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使犯罪分子能得到应有的处罚,才能震慑买家的收买行为。
4.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既然我国已经加入了《补充议定书》,就应该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对此问题,应当和国际条约的观点保持一致,即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阻却犯罪行为人行为的犯罪性。
二司法惩治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困境和对策
(一)司法惩治该类犯罪面临的困境
1.案件发现难
跨境拐进人口的犯罪比起国内拐卖人口的犯罪更不容易被发现。因为境外的人贩子往往以找工作、介绍好人家为名将外籍妇女带走,所以这些妇女及其亲属在本国境内根本不知道其已经被拐的事实,自然无从报案;当被拐妇女到我国境内发现自己被拐卖后,大多数人由于语言不通或者被人贩子威胁而无法寻求司法帮助;还有的因为被迫卖淫或涉嫌非法偷渡,担心因为这些违法行为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敢到司法机关报案。所以,司法机关在查处这一类案件时,多是基于卧底人员提供的情报信息[4]。因此,降低了实施这一类犯罪的人贩子被查处的风险,在高额回报和低查处风险的诱惑下,这一类犯罪受到了不法分子、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青睐。
2.调查取证难
跨境拐进外籍妇女案件由于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在不同国家,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管辖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机制不同,加之双边合作的衔接不够,导致跨境调查取证很难。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协助仍然不够深入,目前,与我国既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又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只有老挝和泰国。因此,无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的支持,发案双方协作调查取证、共同追捕犯罪嫌疑人、引渡逃犯、刑事判决的通报等方面的操作均很难开展[1]。加之,由于被害人未及时报案,司法机关发现案件线索时已经时过境迁,很多证据都已经湮灭,只能依靠被害人、被告人提供的言词证据,一旦双方均翻供,前期的侦查工作就相当于付诸东流了。再次,被拐妇女被卖与中国男性为妻,当对婚姻状况满意的时候,不承认自己被拐卖,当对婚姻状况不满意的时候,便说自己是被拐卖的,这也给司法机关查案带来很大的困难。
3.外籍涉案人员身份的调查与核实难
在侦查审理跨境拐进案件时,核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个很重要和必须的环节。对外籍犯罪嫌疑人,核查其身份只能委托给该犯罪嫌疑人所在国的司法机关协助完成。有时案件在我国都快审理完结了,可被告人所在国仍然未落实其身份。同时,对被拐妇女要进行遣返,也必须要核实其身份。可有的妇女被人贩子控制,不敢跟警方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导致其身份根本无法核实。如果该妇女的身份未能在所属国核实清楚,其所属国往往拒绝接受该被遣返妇女。该妇女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回国,只能把她送到边境,让其自行回国。可这一类妇女在边境又极有可能被人贩子二次控制和二次拐卖,从而加深其受害程度。
4.被拐的外籍妇女遣返难
很大一部分被拐的外籍妇女在我国被卖为人妻之后,和我国男性非法通婚,已然形成事实婚姻,并且生儿育女了,家庭关系基本稳固。司法机关一旦查出其被拐卖的身份,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必须对该被拐妇女进行遣返。然而,一旦遣返,就意味着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因此,遣返会受到被拐妇女夫家的抵制,得不到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的被拐妇女舍不得家庭孩子,不愿意被遣返,就算被强制遣返回国,又自己悄悄回到在我国组建的家。因此,遣返的难度很大。
(二)司法惩治该类犯罪的思路转变
1.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贩运人口的行为
我国制定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这一计划规定了我国跨国贩卖人口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具体工作目标,要求我国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国际交流合作,联合执法,共同开展反拐培训,利用双边、多边的合作机制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警务合作渠道,开展跨国拐卖人口犯罪案件侦办合作和情报信息交流,及时发现和解救被拐卖入中国的外籍被害人,做好外籍被害人的救助、中转康复和遣返工作[5]。这一目标具有可行性,但各项工作有待落实到位。目前,我国应该尽快和东盟国家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和东盟各国建立类似在广西建立的跨国拐卖执法合作联络官办公室。以此为平台,召开打击跨国拐卖的警务联席会议、警务会晤,交流打拐的信息和情报,进行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核实、解救和遣返被害人的合作等[4]。同时,加强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包括在交换、传递犯罪情报,协助调查案件,缉捕罪犯,依法引渡给有关国家,追缴跨国犯罪收益等方面进行合作,更有力地打击跨国贩卖人口的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跨国贩卖人口的犯罪。
2.正确识别跨境拐进的受害人和非法移民
在打击跨国拐卖人口的犯罪中,被拐卖的被害人因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涉及到非法偷渡、非法卖淫、非法通婚等违法犯罪问题。被拐卖者不能因其违反移民法或在拐卖目的地国所从事的非法活动而受到起诉,即确保被拐卖被害人的无罪化,这一精神已经被联合国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反复确认[6]。同时,要防止一些人冒充拐卖人口犯罪中的被害者,以此逃脱非法偷渡、非法卖淫等行为的处罚。因此,需要司法机关正确识别跨境拐进的受害人和非法移民,以便于准确打击拐卖犯罪行为人,保护跨境拐进人口的被害者。有学者建议从犯罪行为人是否对被害人实施欺骗、胁迫,是否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是否存在交易环节的存取款,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通话清单、交通票证等来区分[7]。司法机关应该从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得出一套有效、正确识别跨境拐进的受害人和非法移民的标准和流程,以便于司法部门统一遵照执行。
3.落实《补充议定书》对被贩运受害人的保护义务
《补充议定书》确立了打击贩运犯罪者、保护贩运受害人和预防人口贩运的三大原则,三大原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6]。根据《补充议定书》的规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应该获得隐私权的保护,法律援助,住宿、医疗等物质方面的帮助,就业、人身安全的保障、培训、赔偿,暂时或永久居留权和出于自愿的适当而合理的遣返[3]。我国作为被拐妇女、儿童的输入国,近几年来对被解救的外籍被害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比如广西省东兴市成立了被解救外籍妇女、儿童中转中心,专门对被解救外籍妇女、儿童进行安置和救助。但这些救助措施离《补充议定书》里规定的以保护被拐的被害人人权为核心的救助措施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被拐妇女作为被害人,其陈述是指控人贩子罪名成立的有效证据。司法机关保护她,不应该仅仅因为她对指控犯罪有帮助,更要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的角度出发,切实为被拐妇女、儿童提供庇护、信息咨询、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等帮助。这些工作由政府主导,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民间力量,让其来完成,效果更好[8]。同时,如果被害人在中国已经生儿育女,并且愿意留在我国,应当遵照被拐妇女的意愿,给予其在我国的暂时或永久居留权。这样,可以让被害人没有后顾之忧,更好地和司法部门配合,实现对贩运人口犯罪分子的惩罚,同时,也落实、履行了《补充议定书》对被贩运受害人的保护义务。
三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预防措施
对犯罪的预防远胜于打击。如上所述,《补充议定书》确立了打击贩运犯罪者、保护贩运受害人和预防人口贩运的三大原则。对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预防措施做好,才能从源头上杜绝人口贩卖。
(一)国家允许非政府组织设立涉外中介机构
大多数被拐的妇女都是因为在本国生活的贫困,想通过来我国找工作或嫁人改变命运。她们的这一想法无可厚非,但却无法找到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这一愿望。于是人贩子便利用这种心理,带被拐妇女偷越边境来我国,然后再物色合适的买家将其卖掉。因此,为我国失婚男性和真正想嫁到我国的外籍妇女牵线搭桥,让其有机会合法接触、了解,双方自愿缔结婚姻,为其提供婚姻登记方面的帮助,使其成为合法的跨国婚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失婚男性的问题,又满足了外籍妇女的婚姻需求,一举两得。此项工作实施的障碍在于它和199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有冲突,该通知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笔者认为,涉外婚姻介绍机构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但它能顺应跨国婚姻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我国男性失婚的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国家对这一类行为放开并实施监管。同时,我国人口多的红利正在逐渐消退,为应对这一问题,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还可以考虑引进外籍劳动力。引进外籍劳动力的障碍在于1996年劳动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的明文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只鼓励国内短缺的外籍专家、技术人员来我国就业。20年前我国人口增长旺盛,这一规定具有合理性。而现在时过境迁,该规定限制了没有技术含量的外籍劳务人员来我国就业的需求,引发了对外籍人员非法用工的黑市,对跨境拐进人口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建议国家立法删除这一禁止性规定,同时,鼓励边境城市设立针对外籍用工的涉外劳务派遣机构,帮助那些想来我国工作的外籍人士合法进入我国劳动力市场。这样既能减少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跨境拐进人口到我国的犯罪的发生,还可以吸纳外籍劳动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些涉外的婚姻介绍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可以交由可靠的非政府组织去设立,政府对它进行支持和监督,将之定位为公益组织,同时,这些机构的收费应该很低廉,使贫困人群能负担得起。
(二)加大法律宣传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资助
各国都要进行拐卖妇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是犯罪行为的宣传,特别是在拐卖妇女的高发区,相关国家要对本国的妇女进行防拐和被拐之后的报警、救助手段的宣传,使得妇女确实能够提高防范意识,拒绝偷渡。对我国而言,国家还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和资助,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同时,逐渐减小、消除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这一社会问题,使男性能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婚姻难题,拒绝买卖婚姻。
各国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保护、安抚好被拐的妇女,同时,各国应该尽可能加强刑事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最后,各国发展好本国经济,消除贫困。只有多方合力,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拐卖人口犯罪的滋生。
参考文献:
[1]刘凌,李光懿.论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75-81.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99.
[3]曾怡然.打击跨国人口贩运的国际法律制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法学院,2012.
[4]蒋慧.广西地区打击跨境拐进妇女、儿童犯罪的调研报告[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12-13.
[5]兰立宏.论国际视阈下拐卖犯罪防治策略的完善路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7-28.
[6]张浩.应对人口贩运过程中的被害人人权保护[D].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2014.
[7]刘国福.我国反贩运人口法律的理性回顾和发展思考:以国际法为视角[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9):74-85.
[8]黎巧萍.中越双边预防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工作实施情况及相关问题[J].东南亚纵横,2003(6):49-52.
(责任编校:舒阳晔)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Cross-border Human Trafficking
YUANAi-hua,LINHuai-man
(Business Schoo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106, China)
Abstract:China′s legislation aimed at punishing cross-border human trafficking is hindered by many problems. 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hange the Crime of Women and Children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into the Crime of Human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define inbound trafficking of foreign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China as aggravated offense by circumstances, increase efforts to crack down the buyers, and prescribe that the victim′s consent should not remove the human traffickers′ criminal liability. Judicial punishment in China for human traffickers is not easy as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cases and investigate and collect evidences.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verify the identities of foreign victims and human traffickers and repatriate them. Therefore, China sh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mprove its ability to identify illegal immigrants and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provide comprehensive victim protection services to foreign victims. Meanwhile, China should allow NGOs to establish agencies to provide foreigners with information on marriage or job opportunities. Each nation should improve legal education and develop its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By tackl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rim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make each country mor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such crime.
Key words:cross-border human trafficking; imperfect legislation; legal obstacles; crime prevention
[收稿日期]2015-12-14.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调查与研究”(YB2013037)。
[作者简介]袁爱华(1977—),女,云南宣威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林怀满(1980—),男,福建南平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2-00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