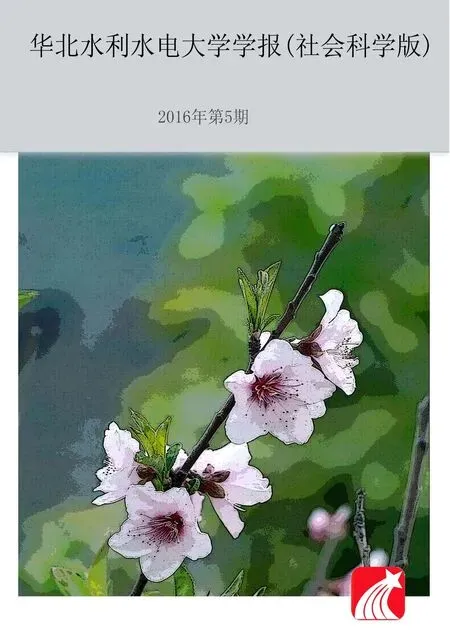魏晋南疆社会管窥——以佉卢文盗窃文书为例
张婧
(陕西中医药大学 社会科学部,陕西 西安 712046)
魏晋南疆社会管窥
——以佉卢文盗窃文书为例
张婧
(陕西中医药大学 社会科学部,陕西 西安 712046)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反映魏晋南疆社会日常生活的佉卢文文书,主要包括官方文书、契约和公私往来的书信等,这些珍贵的文书反映了其时新疆南部地区存在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垄断的现象。因此,在当时人口买卖、土地买卖现象时有发生。并且,由于大地所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奴隶盗窃问题更为严重,所以同时期记录的佉卢文书内容表现为被窃物品种类繁多、以生活用品和牲畜这两个方面为主:被窃衣物以绸、麻布、毡等为质地,刺绣工艺已经出现,毛织品也已经使用;被窃牲畜有骆驼、绵羊、牛。文书一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南疆地区失窃者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盗窃者无法生存的悲惨命运,这为城邦国家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佉卢文书;盗窃;南疆社会
佉卢文书的发现和解读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魏晋时期新疆南部地区土地私有,人口买卖、土地买卖时有发生,社会上存在一批人,他们既担任政府官职又参与土地买卖、人口买卖,其时封建制度已经发生但也保存了奴隶制度的残余[1]153。文书所载,当时被卖人口毫无人身自由,经常被买卖、转卖、抵押、甚至被作为物品赠送他人,主人对之为所欲为。这些人在巴罗先生(T.Burrow)笔下被称为“slave”,王广智先生将其译为“奴隶”。他们生活困苦,甚至因生计所迫走上盗窃道路。通过对所收集到的三件有关奴隶盗窃的佉卢文书的解读,可以管窥其时的南疆社会。
一、三件与奴隶盗窃问题有关的文书
有学者指出:“研究西域历史,至魏、晋以后颇感困难”[2]318,因为魏晋后国家分裂,对西域记载也很少,因此佉卢文书无疑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和社会生活最为珍贵的资料。在已经解读的诸多佉卢文书中,和奴隶盗窃问题有关的文书共三件,分别是318号[3]76-77、345号[3]84-86和561号[3]143文书。
318号文书是政府对窃案的判词,窃案发生在鄯善王伐色摩那在位9年3月19日,僧人祗啰的奴隶迦凯诺窃取了啰苏的财产,失窃财产涉及诸多生活用品,多名审讯人参与案件审理工作,审讯人之一弗那陀是一名“且渠”[4]638。345号文书涉及的窃案发生在鄯善王伐色摩那在位9年3月5日,据该文书载,奴隶盗窃他人物品,法庭判决负责赔偿的是其主人,“这种判决赔付的方式反映了奴隶在人格上的不健全:他们是主人的财产”[5]192-193。561号文书属于国王敕谕,即国王给地方政府的谕令,其中涉及的审判人楼偷是一名“元老”[4]638,盗窃者是夷莫耶的奴隶,被盗窃物为不同品种的骆驼。
研读以上文书不难发现:首先,提及窃奴,三件文书之共同点在于,奴隶名前冠以主人之名,这说明他们地位低下,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即使犯罪也不能独立被起诉,而要以主人之名义应对法庭审判。其次,皇廷对奴隶窃案非常重视,对财物追缴不遗余力。如318号文书所载负责审讯的有州长、且渠等官员,345号文书所载的证明人也有且渠等官员,而且三件关于窃案的记录均以文件形式保存。甚至据561号文书所载,国王亲自命令地方政府审理窃案。再次,561号文书记载奴隶盗窃的财物全部是骆驼,骆驼在当时是私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途广泛[6]137。并且,寺庙中也有众多奴隶,这在345号文书中有所反映。
据史书记载,时西域诸国刑法严苛,“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7]2260甚至“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鼻刖若髡,或剪半鬓,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系之终身”[7]2271。但是318号文书和345号文书所载窃案仅仅相差14天,这说明,虽刑法严酷,但也无法阻止奴隶的盗窃行为。
当然,在诸多佉卢文书中,关于盗窃问题并非仅限于318号、345号和561号文书,据13号[3]4、15号[3]5、17号[3]5-6、566号[3]145和676号[3]177-178文书所载也存在盗窃问题,只不过前三件文书涉及奴隶盗窃,以上五件文书涉及自由人盗窃。例如,13号文书记载,有人将国家牧场内的马打伤并窃取若干酥油,于是国王敕谕地方官员严令禁止在国家牧场狩猎。15号文书和13号文书反映的事实几乎相同。17号文书记载,摩色提吉和钵吉耶盗走了克利耶和苏莱多埋藏在洞穴中的财产,国家法律规定,如事实确凿,盗窃者应作价赔偿,文书所载被窃之物能明确看到的是皮制物品。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国王进一步敕谕地方政府“凡在战时所取之物,皆作为无罪处理”,这说明若为战争需要拿走了百姓的物品并不违法。566号文书所载失窃物品有七串珠子、一面镜子、一件锦绸、一件耳饰。676号文书所载一头六岁母牛被人偷走宰食,地方官员查明真相之后严令偷食人赔偿并将偷牛人各打五十大板。
以上五件文书中盗窃人在法庭之上均作为独立个体被起诉,姓名之前并未冠以任何人名,这和奴隶盗窃文书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奴隶无法生存走上了盗窃道路,社会上时时也有其他窃案发生,盗窃是明确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奴隶的法律责任是由其主人代表的”[5]181因此,相对于自由人而言,奴隶盗窃行为更为严重、窃取物品更为繁多一些。
二、奴隶盗窃文书所载之被窃物品
涉及一般盗窃问题的13号、15号、17号、566号和676号文书所载之盗窃物品,前文已有所提及,特别是566号文书所载被窃物品之耳饰印证了史书中关于西域“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7]2265的记载。涉及奴隶盗窃的318号文书所载盗窃物品有刺绣、白绸短上衣、麻布短上衣、金饰品、毛织物以及色彩各异的衣服。345号文书所载盗窃物品有丝绢、绳索、毡衣、绵羊等。561号文书所载盗窃物品为品种各异的骆驼。
从以上内容看,被盗窃物品种类繁多,以形形色色的生活用品和牲畜为主。其中生活用品又以衣服、毛织品、丝绢为主。丝绸在魏晋时期的新疆南部地区虽然珍贵但并不稀缺,因为文书记载曾有对僧侣违规问题的处罚,处罚方式就是罚丝绸。还有一件关于丝绸收支账目的660号文书[3]175,其中列出的丝绸数量较大、色彩丰富。据史书载,西域诸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剪发,锦袍”[7]2281,也有学者指出,当时“在精绝,人们身着用丝、毛、棉各种纺织品以及皮革缝制的服装”[8]102而且“当时西域纺织物已采用大麻、毛、丝、黄金凡四种纺织原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西域纺织史的认识。”[9]394。
由此观之,其时西域统治阶级的生活已经非常奢华,他们所穿衣物不但质地精良而且色彩艳丽。被窃物品中也有绳索和金饰,但数量较少,如345号文书所载被窃物品中有三条绳索,318号文书的失窃物品中有四个金饰。文书涉及金饰虽少,但至少印证了史书中关于西域诸国“山出金玉,亦多铁”[7]2269的记载,甚至嚈哒国,“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7]2297。至于失窃的牲畜以骆驼居多,也有绵羊:如561号文书所载失窃的三峰骆驼;345号文书所载失窃的四只绵羊。骆驼和绵羊在当时属交换媒介,也是财富的象征[1]100。另外,345号文书所载被窃物品共计100穆立,据有关学者研究,穆立在西域是一种货币[10]87-88,这说明魏晋时期新疆南部地区已经使用货币,否则不会出现将物品折合成“穆立”的说法。只不过“当时的交换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货币已经出现了,但是使用的频率并不高”[1]151。
三、魏晋时期的南疆社会
(一)人口及土地买卖现象的存在
魏晋时期新疆南部地区中存在一批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同时担任政府官职,在诸多佉卢文书中出现较多的、非常典型的一名官员叫做罗没索蹉,他在222号[3]53-54、336号[3]83、571号[3]147-148、574号[3]149-150、579号[3]153、580号[3]153-155、581号[3]155、582[3]155-156、583号[3]157、584号[3]157-158、586号[3]159-160、587号[3]160-161、589号[3]161-162、590号[3]162和592号[3]163-164文书中都曾经出现,该人担任过司书、税监等职,占有相当数量的财产,从事土地和人口买卖。
例如,据581号文书和586号文书所载,罗没索蹉置办葡萄园一所,在其他几件文书中购买到的都是土地,甚至571号文书记载他不但买到了一块土地,而且连同地上的树木也一并购买,说明他很有经济实力。此人从事人口买卖可见诸于589号、590号和592号文书,589号文书所载他购买到女孩一名,590号文书记载他购买到妇女一名,592号文书所载他购买到男人一名。从文书时段看,罗没索蹉从鄯善国安归迦王6年至34年的28年时间里,见诸记载共购买土地6次、葡萄园2所、人口三名,而且每次交易不赊不欠,货到付款,这说明他拥有相当的财力。另外,583号文书记载这位当地名人与他人发生争执上了法庭,584号文书记载他因为绵羊和他人打官司,584号文书所载,他也有受贿行为。总之,罗没索蹉曾担任过司书、税监等职务,拥有大量土地和葡萄园并买卖土地和人口。统观巴罗先生解读的七百余件文书,罗没索蹉绝不是个例。
(二)盗窃者之处境
魏晋时期新疆南部地区存在一批可以被主人随意买卖的人口,他们毫无人身自由,这批人据文书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来源:
第一种,饥荒卖人。例如589号文书所载女孩被卖的原因为自然灾害,至于究竟是何种自然灾害,文书中并未详细提及,仅指出由于自然灾害导致了饥荒。第二种,逃亡人口。此种情况可见于136号[3]32、149号[3]34、161号[3]38、217号[3]53、292号[3]68、296号[3]69、333号[3]81-82、355号文书[3]89。该人群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生产资料,国家对其统一安置但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国家掌握的可供赏赐的人口,这类人被赏赐之后就成为私有财产,甚至成为人口市场上的被买卖人口。第三种,战争俘虏。例如324号文书和491号文书对该情况有所提及。据以上两件文书记载,当时居民常为鲜卑人入侵所苦,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政府没有任何力量保护自己居民的权益,只能听任这批人被任意买卖、转卖。第四种,拐卖人口。这在106号[3]25、400号[3]106、436号[3]115-116、575号[3]150-151和564号文书[4]138-139中都有反映。第五种,主人的奴隶,这在24号[3]7-8、33号[3]11、39号[3]12-13、49号[3]15、56号[3]16、133号[3]31、143号[3]33-34、144号[3]34、152号[3]35、225号[3]54-56、318号[3]76-77、327号[3]79-80、358号[3]90-92、364号[3]94、491号[3]124、506号[3]127-128、528号[3]135-136、538号[3]138、550号[3]141、561号[3]143、574号[3]149-150、585号[3]158-159、593号[3]164、621号[3]166-167、666号[3]177、696号[3]180-181和709号文书[3]182-183中有所提及。这批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将之抵押、出卖或者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许多文书多次提到主人可以弄瞎他们的眼睛,对之为所欲为。这些人的生存状况窘迫,为此有人甚至为生计所迫走上盗窃道路。
(三)丰富的社会物产
与奴隶盗窃相关的三件文书所载之失窃物品都是实物,第一类为生活用品:包括衣服、毛织物、丝绢、金饰品、绳索等。文书涉及到的衣服质地多样,色彩绚丽。第二类为牲畜:包括绵羊和骆驼。而据同时期其他与盗窃问题有关的文书所载,被窃物品包括酥油、皮制物品和珠子、镜子、锦绸、耳饰以及一头六岁母牛等物品。其中酥油在这一时期产量较大,它是当时很重要的税源,其中以酥油为征税对象可见于42号[3]13、158号[3]37、162号[3]39、165号[3]41、207号[3]49-50、211号[3]51、382号[3]99和714号文书[3]183-184,这更进一步印证了西域诸国“国无常税”[11]2538的记载。皮制物品已经出现,锦绸在日常生活中开始使用,人们对装饰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耳饰这样的装饰品,至于牛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牲畜,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的发现,他曾经提到相当于晋代的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175号洞窟中的壁画耕作图上不但绘有钅矍和锄还有梨耕[12]45-46,这表明该时期西域已经使用牛耕和铁犁从事农作物生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南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农业方面已经使用牛耕和铁犁;畜牧业繁盛,饲养马、牛、绵羊和骆驼等;手工业分工更为精细,产品多样,如色彩绚丽的各式衣服、毛织物、丝绢、金饰品、绳索、皮制物品和珠子、镜子、锦绸、耳饰均有出现。但同时也有一些社会问题出现,例如贫富分化严重,土地甚至人口集中在一些富裕并掌握公共权利的人手中,被买卖人口生存状况窘迫,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也客观的反映了魏晋南疆地区生产力水平已步入封建社会阶段,但社会制度仍滞留在奴隶社会阶段。
[1] 张婧.佉卢文人口买卖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2] 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 巴罗.新疆出佉卢文残卷译文集[M].王广智,译.乌鲁木齐: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所,1965.
[4]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5]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张婧.鄯善国骆驼用途归类初探[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2(3):137-140.
[7]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刘文锁.走进尼雅:精绝古国探秘[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0] 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J].敦煌学辑刊,1995(2):87-88.
[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J].文物,1962(增2):45-46.
(责任编辑:李晔)
Society of Southern Xinjiang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A Case Study of Theft Documents in Kharosthi
ZHANG J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2046, China)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unearthed in Southern Xinjiang reflecting the social daily life include official documents, contracts and letters. The documents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ern Xinjiang area, including population and land sale business, social wealth possessed by the few monopoly, theft often occurred, slave theft problem particularly serious. A variety of items were stolen, mainly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livestock. Stolen clothes were made of silk, linen, felt and other texture. Embroidery technology emerged, wool was used. Stolen livestock include camels, sheep and cattle. The documents reflect the luxury life of the people who were stolen and the tragic fate of the thieves, which foreshadow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state regime.
Kharosthi documents; theft; Southern Xinjiang Society
2016-06-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疆出土佉卢文人口买卖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14YJC770043)
张婧(1974—),女,陕西永寿人,陕西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
K235
A
1008—4444(2016)05—01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