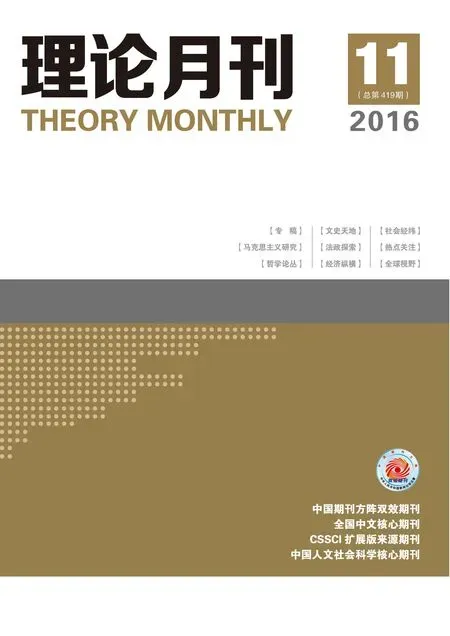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透视
□黄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上海 2002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透视
□黄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上海 200233)
基于“当下主义”的立场,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再认识,意欲设定若干伦理与政策边界。本文有两大伦理判断: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个人正义、国际正义和世界正义三大价值取向,但基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现实,必须把国际正义置于首位;第二,中国外交经常表现出“利他主义”,但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基于当下的内外政治需要,必须把“开明的自利”作为首要的伦理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正义;利他主义;开明的自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而快速发展的中国,有能力和意识思考整个世界的当下和未来,它既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又是中国对人类的重大思想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正因为意义重大,有必要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再认识,设定若干必要的边界,深挖其切实的政策内涵,以期使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避免承受不需要的代价,并富有成效地推进中国外交实践。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国际正义
从伦理角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三种正义:个人正义、国际正义和世界正义。由于含有“人类”二字,再加上对“共同体”概念的一般性理解,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个人正义或世界正义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价值取向,这值得商榷。下面依次讨论三种正义,并重点分析它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上的优先次序。
1.1 个人正义
个人正义指的是赋予个人以权利和义务的道义规则,它曾以自然法学说的形式出现,国家最初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正是因为个人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1]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追溯现代国际法理论形成的历史,从中世纪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的传统,聚焦格劳秀斯、普芬多夫、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沃尔夫、瓦泰勒、卢梭和康德等政治理论家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自然状态下行为主体的道德限度的辩论,充分说明个人正义思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行进。[2]而《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等也从实践上说明个人正义问题常常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显具有人文关怀,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深刻意识到人类已经步入“地球村”时代,国家之间甚至是人人之间日益福祸相依、安危与共的客观现实,也不仅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从“虚假共同体”迈向“真正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的高度契合,[3]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中国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国际关系学著名学者秦亚青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风格极为独特的文化体系,它构成亿万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自然也会在中国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上打下鲜明的烙印。[4]牟钟鉴就指出,源自农耕文明的早期黄帝尧舜之道确立了民本、重德、贵和、创新的中华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化之根;孔孟集三代之大成,阐发仁者爱人、义者利人的为人治国之道,形成以仁为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忠孝为核心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5]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与人的需求完全一致。
作为具体的个人,其差异性需求使得寻求所有人的满足不仅不现实,而且满足某个人或者某部分人的需求往往伤及他人的合理需求,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反对的;而作为抽象的个人,又因为人权的政治化而被不少国家谨慎地对待。在当代,关乎个人正义的一个显著弊端,就是倾向于将人权作为个人正义的唯一内容而忽视个人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便是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人权与国权之争直至近年关于“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辩论均与该义务有关。没有人否认当代世界仍然存在国家欺压个人的现实,但事实同样表明,当代大多数国家,无论其形态有何不同,是个人人权的主要保护者和促进者。“对世界上许多数十年前还处于殖民或半殖民奴役的人民来说,他们现在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他们人权所曾有的第一个保护者和促进者,(国家的)独立、安全、稳定对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福利来说非常重要。”[7]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布尔(Hedley Bull)也认为,漠视国家的积极作用,包括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错误的。[8]
1.2 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往往也称为全球正义,其思想渊源甚至比个人正义更为久远,与宣称每个个人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正义不同,世界正义关注的是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相比个人正义的个体主义视角,世界正义体现的是一种整体主义视角。[1]例如,在讨论军备控制问题时,关注的焦点不仅是诸如核大战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何种伤害,更是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存亡;在探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发达国家具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等问题时,关注的焦点也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境况的改善,而更是整个人类世界均衡发展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富有世界关怀。首先,从现实角度,它深刻认识到当下的世界“依然不算太平”。发端于资本主义框架体系内的、以追求最大化利益和权势的行为,以及长期以来自恃真理化身和文明标准的西方“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使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种族仇恨、民族对抗的阴霾挥之不去;全球性问题,诸如核扩散、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毒品犯罪、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资源枯竭等无时无刻不在危及人类整体利益;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现代性拓展使得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享受为典型表现的道德蜕化弥漫全球,成为当代人类的一大根本性病症,而这一病症深刻影响现今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解决。[9]其次,从文化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蕴含中国“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和“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是中国传统“大同”文化的当代体现;又与人类共同价值相通,体现了人类社会本质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历史发展至当下,人类共同价值显然是客观存在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为此需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0]再次,从理论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与近年中国学术界极具世界关怀的“天下”主义(尤其是其“天道”“无外”“生生”等新天下词典)[11]和“共生”理论(特别强调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和谐共生的世界演进逻辑)[12]具有相通之处,同时又与西方世界主义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尤其是和主流建构主义温特(Alexander Wendt)的三种无政府文化(又特别是康德文化)[13]具有理论契合点,因此具有理论根基。最后,从价值观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价值观基础,[14]它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时代高度,强调世界的整体性,是中国外交之“道”。
在当代,世界正义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生存、繁荣、尊严和道德进步。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丰富的世界正义伦理,甚至可以认为世界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取向。但是在当下,世界正义同样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价值取向。这是因为:
能把国家、人民和自然界联系起来的世界共有价值尽管存在,但却较为稀薄,普遍的认同感和忠诚仍然只对国家甚至民族或种族而言,脆弱的全球共识还因各种自私的民族主义、“不确定性”(如领导人更换)和披着普遍主义外衣的西方特殊主义而时刻面临崩塌的危险,“所谓具有共同利益的世界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念或神话,这种理念或许在今后某一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迄今为止它还不具有这种影响力。整个人类作为一个大的政治集合体,并不具有产生和表达整体利益的手段,也不具有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的手段。”[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当下世界的深刻反思后对于未来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并力所能及地通过外交实践实现它,但绝非表明世界正义构成它的首要价值追求,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有责任确保外交战略的选择更多基于当下的需要,而非不确定的未来。①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与当下收益的吸引和相对确定,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关注当下,国家总体上是保守理性,而非富有远见的。见:Arthur 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89,189.
1.3 国际正义②国际正义也称作国家间正义,由于很多国家自称是“民族-国家”,因此,国际正义往往又等同于民族间正义,当然两者有重要的差别,典型地表现为民族自决权与主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这并非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所以不作区分。
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之所以不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价值取向,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际正义。在当今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世界政治环境中,国际正义的思想在日常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正义指的是赋予国家以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它主要包含两种正义形式,第一是平等正义,核心是主权平等及其互惠承认,因此也叫作“交换正义”“形式正义”。平等正义意味着任何国家对国际事务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不容干涉;主权国家隶属的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开放、包容互鉴,共享尊严。第二是分配正义,也称作“实质正义”。不管“正义”被怎样解读,它总是在探究资源应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正的分配。[15]正如个人正义那样,国家平等正义的绝对化往往因国家在资源禀赋、政府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容易加剧国家的不平等。因此分配正义强调,为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必须赋予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发达民族与欠发达民族在某些方面不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侧重维护弱国的主权,增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隐含相对限制若干强国的某些权势;经济上在贸易条件、资源开发、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给予穷国更为优惠的权利,并规定富国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文化上尊重和保护欠发达民族的传统文化,支持其文化和教育,限制发达民族的文化渗透、传媒优势和话语霸权。[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鲜明的国际正义内涵,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它同样体现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国家之间的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和共进。[16]通过新时期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若干重要论述,我们发现,不管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的“三个共享”(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还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六个坚持”(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继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四个必须”(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最后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全面系统提出的“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都深刻表达了中国对于平等正义和分配正义的价值追求。
青瓷自从跟了李光北,就认了命。再漂亮的女人,一但名声不好,哪个男人还愿意娶?特别像青瓷这样儿的,18岁就大过肚子,不敢去医院堕胎,就自己买了打胎药,结果差点丢了小命儿,闹得满城风雨。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乃至核心的价值取向是国际正义。这是因为: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深刻认识到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也深刻认识到国家间“结构性暴力”(即虽无大规模战争的直接暴力形式,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使得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处于间接暴力之下[17])依然存在的客观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国家作为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势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模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观政策并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的首要责任主体,因此唯有首先实现国际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新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的逻辑脉络表明,维护国家平等正义和分配正义一直是中国特色外交的核心要义。[18]“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和种种至关紧要的利益,中国差不多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提倡和实践一种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国,这种哲学基于主权平等不干涉和中国所称的国际政治生活民主化观念。”[19]在最深层面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如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正义诉求等,早在革命时期就酝酿成熟并最终转移到60年的外交之中并逐步扎根。[20]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该核心要义作为基本遵循。
最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话语表达和政策宣示表明国际正义依然是首要关注。关于平等正义,中国极力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而“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障,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中华民族对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高度敏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时,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关于分配正义,中国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以及真实亲诚对非外交方针,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亚投行”等务实行动,实现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共享尊严、发展和安全。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须以“开明的自利”为伦理原则
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谙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现实,且蕴含三大正义取向,那么它必然含有不容忽视的政策启示和伦理意义。
2.1 责任共同体意识
理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辩证统一、有机联系、互为保障的三个共同体——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安全上的命运共同体以及政治上的责任共同体,其中,责任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障。这意味着,作为当下最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必须树立重要的“责任”意识。这责任自然包含内部和外部责任。就内部责任而言,它显著地要求每一个国家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不因自身的发展而损害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就外部责任而言,它也显著地要求每一个国家必须抵制最大化权势和利益的诱惑,必须尊重他者,在平等包容的基础上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同时还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软实力”理论代表人物奈(Joseph Nye)在探讨伦理与外交政策关系时就曾指出,一国之于他国最低限度的义务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国家必须承担一些消极义务,如不屠杀、征服或摧毁其他民族的自治权;第二,结果主义原则,即国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承担责任;第三,撒玛利亚主义,即乐善好施,向急需帮助的人立即提供帮助的义务;第四,推行善行,促进他国人民生活改善的义务。[21]
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皆是伦理问题。以上政策启示的伦理含义是:每一个国家在紧密相互依存的当下,必须具有“自律”和“利他”习惯。自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他,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总体上假定国家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颇具影响力的古典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甚至认为国家不应该利他,因为这会导致自损。但自利并非自私(selfish),它并不排斥利他行为。①古典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有:[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常犯的一个概念错误便是把自利等同于自私。见:Arthur 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P186-188.实际上,自私的个体只索取不付出,他们只想占有他们认为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从不考虑这样的获取对他人进而对自己有何影响。尽管自私可能获取即时的收益,但作为社会本质要求的互惠利他意味着自私的人最终是自损的人,弗洛姆就此经典概括为:“自私和自爱(即自利),实际上是对立而非统一的。自私者并不十分爱己,或很少爱己;事实上,他憎恨自己。”见:[美]埃·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0页。关于共同体的大量理论研究证明,构成共同体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积极情感和利他行为。例如,阿德勒和巴内特(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就认为,共同体有三个特征:一是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认同和价值观;二是成员国之间能够进行多方位的、直接的互动;三是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22]而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23]、外交辞令(如“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被人过得好”)以及政策实践也同样表明中国的利他倾向。就政策实践而言,新时期中国一系列对外援助与合作共赢的举措(如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以及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的方案和担当(如应对埃博拉、伊核、阿富汗、叙利亚问题等),都表明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定会存在频繁的利他行动。
2.2 “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尽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的自律和利他,但这绝非表明中国在推进这项伟大外交工程的过程中需要以“利他主义”作为主导的伦理原则。在一篇关于“利他主义”的文献综述中,利他主义被认为具有比利他行为更高的道德要求,那就是它不仅要求行为上而且动机上也必须是利他的。学者普遍的一个认识是,旨在真诚地使他人境况改善和福祉提高的利他主义而非仅仅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构成人类本质的一部分。[24]利他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国际社会中虽不普遍但却意义重大的真善美。[25]中国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就常常表现出这种真诚的“利他主义”,在新时期中国外交话语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诸如“真诚”“诚意”的字眼,例如,“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中国……真诚希望非洲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非洲人民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中国愿意……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等等。
但是,利他主义在当下并不能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导伦理原则,因为“当代中国领导和人民念念不忘最大甚或最经久的中国特性之一,那就是‘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中国在拥有它很可能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若干重大和严峻的挑战。”[26]此外,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曲折经历及其国际影响大大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审慎和忧患,那就是中国决心走不称霸不扩张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伴随中国权势的增长,“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也注定是力所能及、相对温和和有分寸的。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不同于利他主义的主导伦理原则。
首先,该原则以“自利”(自我利益)为核心。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生活于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如果我们生活于一个无比丰裕以致于个人各国的任何利益追求都不影响他人他国需求的满足时(即和谐状态),苏联史研究权威卡尔(E.H.Carr)笔下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天堂”和“利益自然和谐论”便是自然的结果了。[27]任何合作与冲突,包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既不存在也不需要。
第二,国家利益而非共有利益仍是中国外交的根本依据。国家利益决定一国外交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常识。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两个100年”目标。习近平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8]包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所有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都要服从服务于该国家利益。
第三,“压倒性的国内功能”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特征之一。新中国外交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向性”,所谓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29]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为实现该最大国内政治目标而营造最佳的外部环境。实际上,在外交部党委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诠释中,[30]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列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双重目标,不过民族复兴排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可以认为,国内目标仍然是逻辑优先的。
第四,执政党的合法性。任何一项对外政策能够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能够反应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中国对外关系不论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要回应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持久的。”[20]当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突出的表现为三大方面: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即现代化),社会核心价值的构建与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在这三大方面大有作为,才能夯实包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整体中国外交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第五,自利具备道德正当性。自利等同于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爱(self-love),斯密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斯密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做是“人生的伟大目标”。[31]自利从来就不是反道德和非道德的,因为自利“所要求的只是获得自己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正当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权利。”①贾旭东:《利己与利他:“亚当·斯密问题”的人学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相比自利的道德性,自私是反道德的。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认为,对个人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光明磊落的,(但)自私的人是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人,……是一个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人,他是一个公平游戏和游戏规则的违反者……所有的人为了普遍的善会团结起来反对他。见:[美]查尔斯·库利,包凡一等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53页。
其次,自利是“开明的自利”。何谓“开明”?就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共赢而非独占,利他而非自私的方式来达到自利的目标。正如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Holbach)所言:“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32]斯密也说:“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不行的。……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33]这种互惠利他的策略及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ord)改进”据研究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的稳定性,吸引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并构建群体的信任边界,最终有利于共同体的形成。[34]由此,“开明的自利”不仅可以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原则,甚至可以成为使其成功的现实路径。
3 小结
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问题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荒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35]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避免世界归于毁灭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深刻反思当下世界种种弊端后对未来世界的一种状态描述、理论模式、外交政策和价值取向,突出体现了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本质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意义自然重大。基于“当下主义”的立场,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再认识,意欲设定若干伦理与政策边界。有两点结论:第一,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三大正义取向,但基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现实,必须把国际正义置于中国外交价值取向的首位,实现国际正义是实现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的前提;第二,中国外交经常表现出“利他主义”,但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基于当下的内外政治需要,必须把“开明的自利”,即通过合作、互惠利他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作为首要的伦理原则和政策原则。以上两点,既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最终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65,67.
[2]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M].罗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3]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4]秦亚青.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1,(5).
[5]牟钟鉴.共同体:人类命运中国经验[N].光明日报,2015-12-14.
[6]R.J.Vincent,“The Idea of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Ethics”,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le eds.,TraditionsofInternationalEthics[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 12.
[7]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J].欧洲,1996,(1).
[8]Hedley 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Affairs[J].Daedalus,V.108,No.4,1979,P11-123.
[9]ZbigniewBrzenzinski,Outof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M].New 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P102-115.
[10]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1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2]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3]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391-425.
[14]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
[15]布莱恩·巴里:正义诸理论:上[M].孙晓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6.
[16]王存刚.论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5).
[17]Johan Galtung,Cultural Violence[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7,No.3,1990,P291-305.
[18]王公龙.中国特色国际战略思想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172.
[19]时殷弘.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J].外交评论,2009,(3).
[20]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405,409-410.
[21]Joseph Nye,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J].The Aspen Institute Quarterly,Vol.3,1991,P1-26.
[22]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0-31.
[23]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J].国际观察,2014,(1).
[24]Jane Allyn Piliavin and Hong-Wen Charng,Altruism:AReviewofRecentTheoryand Research[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16,1990,P27.
[25]黄真.国际互惠的基本类型及其伦理取向—兼论国家利他主义的动力根源[J].教学与研究,2010,(6).
[26]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9).
[27]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44-57.
[28]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5 /c1024-28303283.html.
[29]牛军.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9,(5).
[30]外交部党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J].求是,2016,(6).
[3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00,101,102.
[32]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49.
[3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14.
[34]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M].梁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5]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M].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
责任编辑 刘宏兰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09
B82-02
A
1004-0544(2016)11-0049-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KS009)。
黄真(1983—),男,江西广昌人,法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