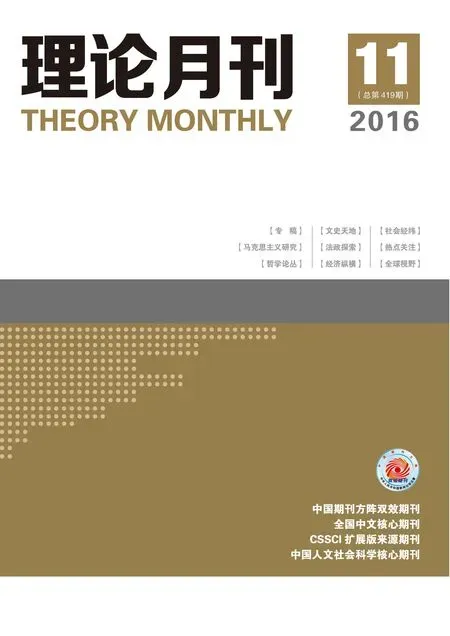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外交行为
□赵炜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外交行为
□赵炜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在与西方世界主导下的体系长期敌对过程中,伊朗因自尊遭遇羞辱、荣誉遭到贬低、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遭到威胁,形成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由此对体系产生恐惧与愤怒,引发了伊朗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伊朗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精神与秩序的边缘化行为,冲突在双方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中持续发生。由于边缘化身份引发的冲突是基于霍布斯式的敌意文化结构,而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抵制变化的,[1](P272)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冲突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
边缘化身份;反体系行为;伊朗外交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与西方世界处于长期的敌对状态,美国将伊朗当成主要敌人,指责伊朗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反对中东和平、支持并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于是美国不仅把伊朗排除在所有的中东事务之外,并带头推动对伊朗的国际制裁。[2](P296)美国及西方世界对伊朗实行长期的遏制、打压与孤立政策,并在伊朗周边等多个国家进行军事战争或军事干预,这一系列外交与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伊朗的外部环境,伊朗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伊朗为改善外部环境,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锁与制裁,缓解孤立无援的外交困境:一方面选择边缘行为方式来增强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另一方面则积极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机会来发展经济,其主要方式是通过与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世界的大国进行经贸、军事武器、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伊朗这些行动有利缓解了因地缘政治权力衰弱、以及文化与宗教信仰遭遇羞辱引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所导致的恐惧、焦虑与不安等情绪。
1 引发伊朗边缘化身份认知的因素
伊朗对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主要来自其与西方世界互动的两个方面,即地缘政治权力的衰弱、文明上的歧视导致的国家荣誉与尊严遭遇的挫折与羞辱。其中,前一种属于权力因素,它奠定了伊朗边缘化身份的基础;后一个方面属于文化因素,促成了伊朗与西方世界之间敌对与冲突文化的形成。
1.1 权力因素:地缘政治权力的衰弱
地缘政治权力的衰弱是伊朗边缘化最直接的体现。驱使伊斯兰狂热的是对衰弱的恐惧,这是一种影响着所有文明、帝国、民族和文化的情感,但它有着不同的时机和强度。[3](P58-P59)伊斯兰对衰弱的概念,始于17世纪欧洲世界的觉醒与扩张,并在20世纪西方世界主导全球体系的时刻达到新的低点。伊斯兰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与纷争也从早期的经济或政治领域更多地集中于文化和道德方面,这一地区逐渐成为贫穷、混乱、冲突与杀戮的代名词,同时也成为当前体系中最边缘化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现在无关紧要了,塑造他们生命的是西方的影响力。给予他们选择的是西方的敌对性。”[4]伊斯兰文化中的羞辱感根源,正是来自这种长达近四百年的历史衰弱感的体验。伊朗对自身衰弱认知的最近标志性事件要追溯到1953年,发生在这一年的政变一直被伊朗视为国家衰弱的耻辱,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被美国指挥下的政变驱逐下台。美国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转而扶持亲美独裁政权的行为,使美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声誉受到重创,导致伊朗国内的反美情绪持续高涨并延续至今,这一事件对引发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有直接影响,并对此后美伊间30多年的冲突关系奠定了基础。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发表演讲时提及美伊关系,曾谈及1953年的伊朗政变事件:该事件是导致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源头。多年来伊朗的反美旗帜鲜明,我们之间的历史动荡不安。[5]
二战后,随着整体局势趋于稳定,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更多的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并开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转型。但在一些非西方世界或地区,全球化所带来的变革却加速了它们的边缘化地位。伊斯兰世界正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落者,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远不及其所遭遇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羞辱感。伊斯兰世界透过全球化广泛的接触,痛苦地意识到西方与亚洲借助于全球化运动获得的成功与它自己未能利用全球化而遭致失败之间的巨大反差。从教育投入与研究经费的不足,到缺少经济核心竞争力;从糟糕的人权状况,缺少民主进步,到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所有这些领域的表现都强化了伊朗等伊斯兰世界国家“被遗弃”的感觉。全球化虽然在世界较大范围内实现了整体性的经济发展,贫困化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原先诸多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融入西方主导下的现有国际体系。但那些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遭遇美国及西方世界制裁与孤立,反而在全球化过程遭遇挫折与失败处于相对力量衰弱的国家则处境更加恶化,成为体系中最边缘化的成员。伊朗政权本身的特点及其在伊斯兰革命后的遭遇,使得伊朗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状态。在事关伊朗国家安全的波斯湾地区国际秩序与安全机制中伊朗被刻意忽视,美国长达30年的经济制裁与孤立更是将伊朗排除在全球化的经贸活动之外,因此,伊朗的边缘化地位十分突出。伊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恐惧与焦虑,以及遭遇西方的羞辱等体验也随之增加,由此极大引发了伊朗对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
1.2 文明因素: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抗
第一,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对广大穆斯林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西方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活动正持续遭遇伊斯兰世界的抵制与反抗。伊斯兰教如今遍布全球,正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进行扩张,全世界的伊斯兰朝拜者人数,包括北美和欧洲,正在稳步增长。相比之下,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其核心区域欧洲,则是一种持续呈现衰退的宗教。但这并不表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与基督教世界的衰退,事实与之相反,伊斯兰教的崛起并没有伴随着令人满意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进步,伊斯兰内部却日益呈现出分裂、混乱、贫穷与失落。越来越多的信教人口不但没能消除穆斯林的羞辱感与恐惧感,反而在这种日益衰弱的环境中感受到更多的挫折、失望与愤怒,这种情绪又进一步刺激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寻求传统的宗教信仰力量,这势必引发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西方人的世俗化与伊斯兰世界的越来越宗教化造成了双方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西方人指责这些国家或组织寻求传统宗教,特别是回归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伊朗不合时宜,甚至是邪恶的,穆斯林则将西方人的现代化转型视为道德沦丧、贪婪自私的。面临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辐射与渗透,伊斯兰世界难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信仰,除了激烈的言行表达愤怒与反抗之外,很少能以有效方式来反击西方文化的冲击。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诉诸伊斯兰教教义,其中包括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些观念不仅在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国家的穷困无产者之间得到共鸣,而且在社会、经济与教育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群中得到回应。事实上,当前伊斯兰世界中的很多恐怖分子,并不是在最穷的人群中招募的。他们通常在财富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处在社会的平均水平上。这表明羞辱已影响到伊斯兰社会中从最穷的人到最富有、最西方化的人的所有阶层。”[3](P77)这也是最令人失望的进展,伊斯兰世界通过寻求宗教教义来应对西方冲击,却在很大程度上为恐怖主义暴力的滋生与扩张提供了机会,各种极端宗教主义思潮以复兴伊斯兰世界或文化的名义崛起,引发更多的暴力与冲突,也加剧了原本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宗教与文化冲突。
长期以来西方将伊斯兰复兴运动视为威胁。在认知上,正如亨廷顿在其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由此将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为伊斯兰文明固有的反西方特征。[6](P110-P125)伊朗的激进主义宗教色彩,使其与各种极端或恐怖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度被美国列为“支恐国家”。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实践与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伊斯兰世界推向了国际体系的边缘,特别是长期遭遇西方最严重制裁,与西方处于敌对关系的伊朗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成为引发伊朗边缘化身份认知的重要因素。
第三,伊朗与西方之间的敌对文化直接体现在其与以色列的长期冲突、与美国及西方的对抗之中。首先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到冷战结束前这一阶段,美国与伊朗之间从盟友关系走向对立并最终彻底成为敌对国家的时期,其中“美国人质危机”、“伊朗门事件”以及美国与伊朗在波斯湾的军事冲突是双方交恶、冲突的标志性事件。冷战后,美国对伊朗转向全面遏制阶段,并试图以颠覆德黑兰伊斯兰政权的方式来消除伊朗给西方带来的威胁。萨达姆倒台后,美国认为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稳定、对中东地区的和平、对伊斯兰世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突出。在美国看来,伊朗既是“暴政国家”,又支持恐怖主义,更谋求发展核武器,因此在2006年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被“圈定”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7]伊朗在众多与美国处于敌意或冲突的国家之中,是集反美国家、“邪恶轴心”、支持恐怖主义、阻碍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等于一身的敌对国家。[8](P211-P212)正是基于伊朗与西方之间的长期对抗、冲突实践,营造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文化,并在短期内难以打破,它将长时间内塑造双方的认知,进而影响双方间的行为方式。
2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建构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重新塑造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急剧转变,使得随后的伊朗与西方世界都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身份与利益。某种程度而言,伊斯兰革命后的几十年可以看作是伊朗重新寻求自我身份与角色定位的过程,伊朗虽极力要保住和重振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强国地位,但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诸多表现来看,都不可避免的沦为边缘化角色。伊朗边缘化表现的这些方面,揭示了伊朗在历史与现实、行为与心理等多领域的边缘化体验,特别是在冷战后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其边缘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建构。
伊朗民族对自身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边缘化的深刻记忆,对其边缘化身份的建构起到了“自我实现”的作用。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激进的方式迅速开启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伊斯兰文化长期遭遇西方文化的侵蚀与羞辱,以及最近几百年伊斯兰世界在西方世界崛起下的悲惨遭遇,这些历史的悲痛记忆一并被提及,这种“集体记忆”帮助确立了他们在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即视彼此为敌人或威胁。伊朗认为美国主导下的体系对其极尽孤立与遏制之能事,时刻威胁着伊朗的国家安全、文化与宗教信仰,无论美国在对伊目标上出现如何变动,都很难打消伊朗对美国行为的敌意与担忧,他们需要以自己的“国际体系观”来适应或改造当前的国际秩序,以克服被主流国际体系边缘化所引发的恐惧与焦虑。伊朗的这些历史记忆,既包括辉煌的波斯帝国史,也包括近代以来的屈辱史,“其政治心理学后果是大国心态与受害者心理两者认知与情感模式,表现为对外部威胁的敏感及夸大威胁的认知特点,对强权的否定性情感,以及认同和同情反抗强权的弱者心理特点。”[9]正是在这两种预设的认知模式下,“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伊朗对自我的边缘化身份建构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伊朗与西方之间在核争端与国际体系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再加之伊朗以反体系运动的方式来应对美国主导下的遏制与封锁,这种依靠边缘行为方式来突破美国的封锁,并塑造自我威慑能力的行为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冲突,也使得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孤立更加严厉,伊朗的反西方体系行为在事实上加速了其边缘化身份的建构。
3 边缘化身份对伊朗外交的影响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意味着伊朗在国际体系中遭遇羞辱、排斥与漠视,基于自尊与安全的国家利益难以得到关切与保障,并时刻处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高度压力与威胁之下,恐惧与焦虑感蔓延。为消除恐惧与威胁,对内伊朗加强复兴伊斯兰文化传统,借助于能源与核武器来增强国家力量;对外则积极发展与非西方大国的关系,寻求与反美国家或组织合作,从而改善孤立无援的处境,提升与西方周旋对抗的实力与信心。
第一,寻求与西方世界之外的大国合作。边缘身份引发的孤独、恐惧与焦虑情绪促使伊朗积极寻求非西方世界大国的帮助与支持,以寻求强有力的联盟来对抗西方的压力与威胁。在西方以外的大国中,俄罗斯无疑对伊朗的作用最为关键。1953年美国领导的政变推翻了伊朗首相摩萨台,这对伊朗而言的意义就相当于苏联解体之于现在的俄罗斯。两国都利用羞辱感作为一种宣传武器,将对西方愤怒的呼声联合起来。[3](P138-P139)边缘身份所包含的羞辱感、挫折感、孤独感,以及与此相伴相随的因排外传统而加重的恐惧,加强了它们双方之间的合作以共同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反西方体系的行为,才能向西方世界显示自己的力量与存在,增强信心,从而逐步消除其所遭遇到的羞辱与恐惧。在涉及地区安全的诸多事务上,诸如2011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危机等事件,伊朗与俄罗斯两国互相支持,共同反对由美国主导的政策。当然,伊朗学者也认为,“如果能够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那么对自成立以来一直深处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压力之下的伊朗而言显然是一个理想选择,所以两伊战争爆发后不久伊朗就主动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来自中国的帮助。”[10]伊朗一方面通过与这些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友好关系来寻求政治支持与鼓励,改善孤立无援处境,结交更多有实力的朋友来消除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另一方面,从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积极双边关系中获取经济发展机会,同时得到长期稳定可靠的武器来源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从而提升与西方世界作长期对抗的信心,以此来促使西方改变当前的敌视政策。
第二,支持反美国家或武装组织。与西方处于长期冲突与对抗状态的伊朗政权,由于其激进主义色彩,它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中也较为孤立,并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边缘化身份引发的恐惧与焦虑心理在充满敌意的文化中更加深刻。从全球范围内看,伊朗与美国及西方处于敌对状态,从地区范围内看,伊朗则与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沙特等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为了摆脱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孤立处境,回应西方的羞辱与指责,增强与西方及其盟友对抗与博弈的实力,消除边缘身份引发的恐惧与不安,长期以来伊朗一直都在或明或暗支持那些致力于反对以色列、与美国及西方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或组织。这些国家或组织主要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其中叙利亚、黎巴嫩与伊朗一样,同属什叶派执政的国家或组织。因此,2003年伊拉克战争导致什叶派在伊拉克上台后,伊朗凭借这一层关系迅速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诸如“沙特、约旦等逊尼派执政的国家,也由此感受到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组成的‘什叶派新月带’势力扩张的压力”。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为了阻遏以伊朗为主导的什叶派影响力的扩张。”[11]
第三,加强和复兴伊斯兰文化传统。伊斯兰复兴运动自西方兴起,伊斯兰世界衰弱之始,在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过程中一直存在至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复兴过程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迅速衰弱,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遭遇挫折,构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背景。”[12](P14)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范畴及其表现形式不一,中国学者认为它主要以新泛伊斯兰主义和政治伊斯兰为主。前者指“以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相关国际性组织机构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伊斯兰复兴运动,它以自上而下的温和稳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后者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派别众多、思想主张与行动方式各异的中东各国政治反对派组织的总称,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席卷世界的当代国际伊斯兰潮。”[8](P141)
伊朗作为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一种形式,即政治伊斯兰,在当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伊朗伊斯兰复兴的成果,而且极大地激励了伊斯兰世界的、首先是宗教的复兴,随之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复兴,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非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相对聚居地区的伊斯兰复兴,从而把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复兴推向高潮。[13](P208-P209)政治伊斯兰排斥并攻击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在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名义下极力倡导走“伊斯兰发展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伊朗的伊斯兰复兴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开展起来。在霍梅尼提出的“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指引下,它把伊朗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外来的、一切非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习俗风尚,认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伊朗的传统习俗和民族文化,均在其反对之列。
伊朗为了复兴伊斯兰文化所具体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忠于伊斯兰革命政权、有狂热伊斯兰信仰并有别于世俗军队的革命卫队;开展伊斯兰文化革命,确立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建立起清洗组织——各不同机构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以肃清西方文化与东方无神论的影响,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伊朗伊斯兰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十分突出地表现在其对外政策领域,它以向外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为目标,两伊战争正是在伊朗输出革命的威胁下爆发的。[13](P207)伊朗的极端伊斯兰化政策,造成其在国内外的艰难处境,此后,为了应对伊斯兰化引发的紧张局势,伊朗国内的极端伊斯兰化政策有所缓解,并开始着重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这就造成了伊朗在实行经济开放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问题上,仍持续其一贯的严厉政策,时刻保持对西方文化渗透的警惕与抵制。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伊朗的伊斯兰化色彩并未褪色,它仍是当今世界少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国家之一。
第四,借重能源与核武器来加强国家力量。伊朗以能源和发展核武器作为抗衡西方敌视与制裁的有力工具。当前,美国主导下针对伊朗的敌视行为,除了军事威慑、政治孤立以外,更多以在金融、贸易、能源等经济领域的制裁为主要手段,以此对伊朗现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现行政策。因此,伊朗为回应西方的威慑与制裁,集中在能源、核武器与导弹等军事威慑武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以寻求反制西方的威慑能力,同时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
4 结语
无论是支持与西方处于敌对关系的极端组织或国家,还是坚持寻求发展核武器,抑或是大力复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指责并攻击西方等行为,都被西方世界视为极端的边缘行为方式,是体系的冲击者与破坏者。从根本上说,伊朗与西方主导下的体系之间的冲突,是诸如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国际体系观与主流国际体系格格不入,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世界里边缘化造成的。因为“它们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体系的世俗性本质”。[12](P20)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体系而言,“它们的西方文化与世俗政治的至高无上地位遭遇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挑战”。[14]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正是在国际体系中打开的一道缺口,因此它们的行为令西方感到忧虑和担心,当然它们也很难获得西方承认,诸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哈马斯等政权和组织均是如此。刘中民认为,从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角度看,伊斯兰主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及其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复杂联系,直接导致西方在战略层面对“伊斯兰威胁”的围堵、打压和防范,从而严重恶化了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处境。[12](P 3 0)在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中,核心问题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关系的相互调整、适应与重塑,当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广泛冲突关系中,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东方晓.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Bernard Lewis.The Roots of Muslim Rage:Why So Many Muslims Deeply Resent the West and WhyTheirBitternessWillNotBeEasily Mollified[J].Atlantic Monthly,1990,(9).
[5]BarackHusseinObama.Remarksby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EB/OL].https:// 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Cairo-University-6-04-09/.2016-01-10.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7]张继业,郭晓兵.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6,(4).
[8]唐宝才.伊斯兰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9]金良祥.伊朗的“历史包袱”与其对外政策[J].现代国际关系,2011,(6).
[10]MahmoudGhafouri.China'sPolicyinthe Persian Gulf[J].Middle East Policy,2009,(2).
[11]高祖贵.中东大变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崛起[J].外交评论,2012,(2).
[12]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5).
[13]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4]MarkJuergensmeyer.TheNewColdWar:ReligiousNationalismConfrontstheSecular State[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责任编辑 朱文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33
D83.1(373)
A
1004-0544(2016)11-0184-05
赵炜(1985-),男,湖北荆州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