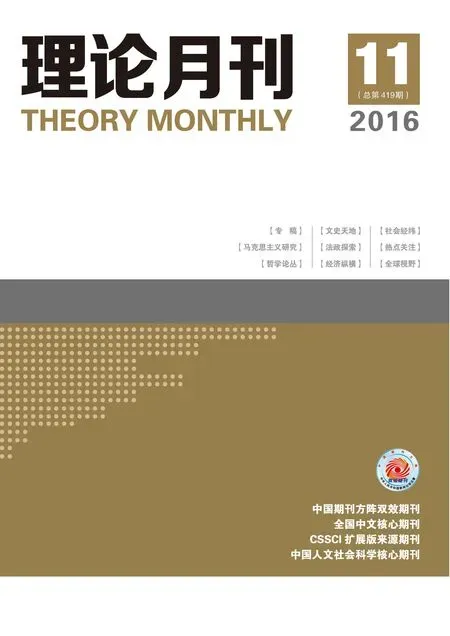欧洲考古-文献比照分析路径的实践与功用
——以中古但泽农作物研究为例
□刘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欧洲考古-文献比照分析路径的实践与功用
——以中古但泽农作物研究为例
□刘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考古发现与文献比照互证的研究路径在欧洲较早实现体系化,涉及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如今在经济-社会史领域也焕发生机。在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中欧和北欧地区,相关实践皆取得较大成就。由于历史因素、史料数据和语言等特殊性,波兰学者引入该路径对中古但泽的农作物考察独具学术价值。他们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常见的农作物概分为五大类群作以考察,通过进一步鉴定、互证、分析和诠释进而发掘出更深层、更全面的历史认知。相关实践已展现出考古-文献比照路径的多重功用,特别是在补阙史料、塑造信史和发掘深层学术价值等层面意义显著。
中古但泽;农作物考古;文献比照
0 引言
19世纪以降,世界考古学取得极大进步,研究成果拓展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展现出独特的功用与价值。一方面,考古学家发掘出若干已被湮没的文明,将缺乏文字记录的民族带进史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对“有历史”的民族来说,考古学揭示了其文献记载中被忽视的社会经济状况,重现大众生活生产、商业交换和技术水平等细节,弥补了传统经典或史料文献强调政治事件和伟人传纪的片面性,使史学研究更趋平衡。[1](P133-135)中国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其兴起相较迟缓,但将考古发现与文献比照互证的研究路径却早有实践。民国初年,面对顾颉刚等古史辩派对东周前是否存在“信史”的质疑,王国维、傅斯年等人在探寻新材料、新问题之际促成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他们利用重大考古发现(如殷墟)与史记的相关记载详作比照,最终证实了晚商历史的真实性。如今,中国考古学已析分出多个分支和方向,在诸领域与西方考古学同途互鉴。
考古发现与文献比照互证的研究路径在西方最早实现体系化,涉及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多个领域。从地域上讲,考古-文献比照的分析方法在文字史料相对匮乏的北欧和中东欧应用最为广泛,如对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汉萨史研究就意义匪浅。德意志汉萨同盟在时间(12-17世纪)和空间(横跨北海-波罗的海)上的巨大跨度造成了文献的分散、遗失,亟需考古发现以作裨助。[2](P640)如今,相关研究已覆盖汉萨同盟的所有活动区域,涌现出朗纳尔·布罗姆奎斯特(Ragnar Blomqvist)、安德斯·马腾森(Anders W.M· rtensson)、安德斯·安德朗(Anders Andrén)[3](P239-241)、大卫·盖玛斯特(David Gaimster)等著名考古学家。他们从未止步于考古材料的简单堆积,不满足于补阙史料,而是对汉萨文化提出了构塑“信史”的要求,将考古-文献比照分析方法提升为汉萨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新史学兴起后,汉萨史学的研究视角又转向大众物质生活,注重对维系人类生存的农作物研究。因为农产品的生产交换一直是中古经济-社会活动的主题,是西方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远程贸易的主要内容,因此备受学界关注。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自然科学技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农史研究在广度、深度和实践领域都获得极大拓展。但考古学仍存在某些短板,如考古数据的碎片化、[4]考古结论的标签化和理论化趋势等又限制其优势的发挥,不利于考古学家获得更深层认知。[5](P720)实践证明,唯有将考古学与文献分析相结合才能弥补各自不足,复现历史本相。近30年来,中、北欧学界在城市考古和植物考古学领域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因此本文尝试以近来波兰学界对中古汉萨城市但泽(今格但斯克)的农作物研究状况为例,概述其考古-文献比照分析路径的具体实践,望有助于国内学界交流借鉴。
1 中古但泽历史及其农作物研究状况概述
但泽位于波罗的海南岸,地处维斯图拉河河口,是中古早期北欧重要的琥珀交易中心。1308年,条顿骑士团围攻但泽,大量文献毁于兵燹。[6](P139)1328年但泽重获政治-经济特许权,政局复归稳定,经济重见繁荣,文献档案渐多。值得注意的是,但泽与波兰民族国家建构重心的中南部存在较大差异:[7](P22)但泽因保留强烈的德意志因素,与波兰人在民族认同上长期存在某种疏离。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但泽作为联结多国、多文化的历史边疆区(Borderland)日益展现出独特的研究价值。[6](P22)政治身份的多元化赋予它特殊的史料优势——相对完备的拉丁语、低地德语和波兰语文献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细节。
中古但泽的城市布局大致可分为主城(新城)、旧城和市郊三部分。主城是全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心,富裕阶层和市政机构皆驻于此。旧城和市郊则相对落后,主要担负补给主城的经济功能。但泽在14世纪中叶加入汉萨同盟,与尼德兰、瑞典、德意志、佛兰德、英格兰和比斯开湾贸易频繁。15世纪40年代时,但泽为谋求更加独立的自治地位,与埃尔布隆格、托伦组建普鲁士联盟(Prussian Confederation),宣布脱离条顿骑士团,承认波兰的雅盖洛王朝为宗主国,导致波兰-普鲁士联盟与条顿骑士团间长达十三年的战争(1454-1466年)。条顿骑士团战败后,双方于1466年签订《第二次托伦和约》,承认但泽自治。[8](P604-628)波兰史学家通常将波兰中古史的终点定格于1492年雅盖洛王朝的终结。[9](P7)目前但泽存世的大部分史料文献皆集中于此时段,因此14、15世纪就成为但泽中古史研究的主要时阈。
欧洲中古研究主要依赖于三类常见史料,即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自然遗迹。考古学致力于探索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及其特征,注重对水井、庭院、公厕、器皿和动植物等空间或遗存的研究,以重现过去生活的方方面面。[10](P85-114)历史文献主要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编年史或传记的方式记录重大事件。[9](P2)环境科学则揭示历史人群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开发。在中古农作物研究领域,鉴于历史文献仅记载特殊作物的局限性,现代学者愈加重视植物考古学的考察路径,倾向于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作比照分析以评估农作物的利用状况。[11](P99-114)在欧洲,类似的比照工作已在英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瑞典展开,波兰最先将其应用于克拉科夫的农作物遗存研究。[12](P98-115)1998年,格但斯克大学古生态-植物考古学研究所和中古史学系组建的研究团队对中古但泽农作物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以考古-文献比照路径重构当地历史环境,探寻城市转型之路,发掘和重现但泽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物利用情况。[13](P249-252)该团队以植物考古学专家莫尼克·巴杜拉(Monik Badura)、中古史专家比雅塔·莫热耶克(Beata Mo ejko)为核心,以该研究所的数据统计和史料文献为基础,开启数据梳理、比对和分析的研究路径,[14](P43)真正实现了跨学科合作、优势互补和成果共享。
巴杜拉团队的考古数据源自对但泽城内14处遗址——包括谷仓、住宅、庭院、沉船、公厕、多源文化堆积的土样采集和植物学数据统计。[14](P443)有关农作物利用状况的文献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14、15世纪但泽市议会的财政记录。(2)条顿骑士团的行政和财政统计。具体包括:骑士团存货清单、骑士团但泽分团的管理文献、马尔堡账务清册(Malborska accounting book)、税赋清册(Pile duty books)等。(3)汉萨同盟规章条例。(4)但泽市议会通信集。[14](P443)中古史学家翻译、核实并统一了诸上文献中各农作物的低地德语、拉丁语和波兰语形式,为英语学者的关注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2 实例:但泽农作物研究中考古-文献比照路径的具体实践
考古-文献比照研究的关键是将发掘、保存和提取(或记载)的农作物按种属分类群进行考察。巴杜拉团队详细罗列出但泽考古学和文献史料中常见的84种农作物,以吉利安·普兰斯勋爵的《植物文化史》[15]的行文架构为参考,将研究对象概分为淀粉类农作物;蔬菜和调味品;肉质水果、浆果和坚果;油料和纤维作物;啤酒花和其他实用作物等五大类群。然后再将这五大类群进一步鉴定、互证、分析和解释,以获取深层认知。
2.1 淀粉类作物
但泽文献中提及最多的农产品是谷物。14、15世纪里,谷物是但泽参与北欧贸易的主要农产品,由汉萨商人出口至丹麦群岛、斯堪的纳维亚、荷尔施坦因、梅克伦堡、立沃尼亚和波罗的海东岸等地。但泽的骑士团存货清单和税赋清册中提到的谷物包括燕麦、黑麦、黍子(小米)、小麦、大麦和水稻等,模糊提到过裸麦、面粉和麦芽等物。其中出现最早,记录频率最高、最明确的是水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已有发现)。[16](P144)稻米不仅是食物,也是但泽向骑士团上缴的实物税种之一。稻米通常在但泽集中,然后分运到条顿骑士团的其他支部。但直到15、16世纪之交才在考古发现中获得证实。除但泽外,北欧很多城市都发现有稻米遗存,当时皆属进口奢侈品。[16](P159)其他农作物则集中发现于15世纪的文献,最常见的是大麦和黑麦,它们是中古欧洲高纬度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盛产于波兰北部。[15](P49)小麦也常见于文献,是13年战争时期军队订购的主要补给品。[17](P1149)14-15世纪但泽的关税记录表明黑麦和小麦在地方谷物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前者是非特权阶层的主食,后者主要供给社会中上层。[9](P104)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还出现了燕麦,用于酿酒和喂养战马。赋税清册则记载了大麦和麦芽,前者频繁出现于15世纪波兰各地的文献,[9](P104)后者则出现在但泽与日德兰、荷尔施坦因或梅克伦堡的进出口记录中。
但泽考古学家从多处遗址选样中证实了上述作物的存在。首先对但泽郊区谷仓的选样分析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大部分淀粉类作物的真实性,其中碳化遗存中保存最多的正是黑麦。在但泽郊区的遗址选样中,黑麦和小麦遗存比例最高,雅辛斯基认为这可能与市郊磨坊专门加工此类作物有关。[14](P449)据A.穆勒-比尼克、A.瓦兰努斯和蔡茨等人的观察,同类现象也出现于克拉科夫:该城大部分的谷物贸易和加工都被限制在城墙外的特定区域。[12](P98-115)小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比考古发现略早。燕麦则生长于湿冷之地,常见于波兰南部,但泽的考古采样中也常见燕麦遗存,但存量远不及大麦和黑麦丰富。其次,对水下遗迹——但泽港内15世纪的沉船进行考察,发现了黍子、狐尾麦(foxtail millet)和荞麦等作物遗存。[14](P447)黍子常见于波兰各地的历史文献,17世纪时仍是波兰民众的主粮。[9](P104)狐尾麦和荞麦源自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后经中亚传至欧洲,是中古波兰东部和东北部的重要副粮。此三类作物都未见文献记载,或是因其太过普通,难得社会精英关注。[14](P449)另外,中欧地区最常见的马唐草(Crabgrass)也未见于文献。该作物是中古斯拉夫地区下层民众熬粥煲汤、喂养牲畜的重要作物,[15](P47)其遗存在考古采样中极为丰富。
2.2 调味品与蔬菜
古代的调味品、香料及草药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区分。[15](P153)历史学家在梳理但泽文献时发现香料和调味品这两个名词经常交替出现。文献中出现最多的调味品是胡椒(pepper)。如但泽市议会的《财政记录》就多处提到胡椒买卖的信息;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中也有关于胡椒和番红花的记载。胡椒源于梵语“pippali”,原有果仁之意,因其价格高昂常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以流通。[15](P167)波兰的修道院编年史中还曾记载僧侣在饮食中加入胡椒以抑制个人欲望的轶事。[9](P42)番红花在诸多香料中最昂贵,约七万朵番红花才可提炼出半千克香料。在中古欧洲,番红花被视为治愈疑难杂症的万能药,常年供不应求。15世纪时,为防止不法商人利欲熏心出售劣质香料,德意志诸邦国曾严正法令:凡是在番红花中掺假的商人一经发现,即刻判处火刑。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中提及最多的正是胡椒和番红花,它们也是骑士团按惯例征缴的实物税种之一。[15](P168)
另外,14世纪的马尔堡账务清册和15世纪的存货清单中还多次提到豆蔻、肉桂、肉豆蔻、丁香、芥末和姜等香料。关于豆蔻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3世纪汉萨城市埃尔平,[16](P160)14世纪时被但泽市民熟知,但直到15、16世纪之交的浮选土样才证实了它的存在。[14](P449-450)针对考古发现晚于历史记载这一现象,德福斯作出如下解释:香料作物可供食用的部位比较特殊,如肉桂的食用部位是树皮,番红花是花柱,丁香是花骨朵,姜是根茎,这些有机质成为化石后很快又粉末化了,唯一可供研究的遗存形式就是它们的孢粉,而对孢粉等微观遗存的研究仍是当今考古学界面临的难题之一。[18](P337-342)在但泽考古学家确定出的27种调味品里,除已获文献证实的种类外,另有欧芹、小茴香、芹菜、天仙子和马鞭草等未见记载的作物。[14](P447-448)欧芹在波兰和俄国较为普遍,多与酸性水果搭配以补充日常饮食所需的糖类。[15](P110)小茴香产自南欧,为罗马人所爱,中古时意大利人用来熏猪肉,英格兰人用来调制咸鱼,[15](P103)德意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兰人将其榨汁,作面包、糕点和白酒的调味品。小茴香还有愈合伤口,治疗胃病的功效。芹菜主要产自欧洲沿海地区,其茎叶多作奶酪或色拉的配料。马鞭草盛产于德意志,香味浓烈,主要用作草药。[15](P111)总之,与谷物类群相似,香料价值的高低决定了它在文献中的地位:16世纪豆蔻等香料大量涌入欧洲导致其价值和利润骤降,因此与之相关的专门记载就逐渐淡出了文献。[16](P160)
但泽史料中关于蔬菜的记载有25种左右,主要有豌豆、洋葱、甜菜、卷心菜、大蒜和菜籽等。但土样中发现的蔬菜遗存远比文献丰富,如蚕豆、萝卜、防风草等。另外,15世纪文献中关于蔬菜的记载在14世纪的选样中也已出现,诸如在沉船残骸中发现的洋葱和大蒜遗存,[19](P4066-4072)在庭院遗址中发现的卷心菜和豌豆遗存等。但考古选样并未提供充足的样本或数据来探究此类作物在日常饮食中的具体功用。因为所有食用其根、叶或茎等部位的蔬菜都很难留存于矿岩层或文化堆积中。它们在成熟前即被食用,也少有种子存留。[17](P1149)对此,历史学家多以考察当时的沉船遗迹进行辅助研究:[19](P4066-4072)沉船因海水(特别是在含盐量更高的波罗的海水域)的防氧化作用保存下完整遗存。[20](P181)14、15世纪的但泽文献只对部分蔬菜的种类和利用情况有过详细记载。如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中出现了泡菜和新鲜卷心菜的食用记录;1543年的文献还详细区别了红、白两种卷心菜。豆类作物遗存也屡现于考古选样中,它们是但泽居民的主食之一。史料文献也证实了但泽社会对豆类作物的巨大消耗,如豌豆作为船员出航时的首选储备而屡被提及。[14](P451)
2.3 仁果、浆果和坚果
此类群在文献中出现时大多为舶来品:1385年,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上记载有无花果、葡萄、葡萄干、杏仁、松仁和栗子等信息;1447年时又提到了柠檬、枣、梨和苹果的进口。14、15世纪的考古选样证实了上述记载,只是杏仁遗存直到17世纪才被发现。这些进口水果较为昂贵,如无花果产自地中海地区,当时难以规模化种植,因此价格高昂。此类群信息主要集中于但泽市政府的贸易记录、骑士团的存货清单和十三年战争时期的通信中。如15世纪的《税赋清册》就记载过“坚果”(nuss)的储存与消费情况;吕贝克与但泽的商业信件则反复提到坚果和胡桃贸易。[14](P448)奇武胡夫(Czluchow)的但泽兵团司令官在给但泽市议会的信中也多处提到无花果等物。另有文献记载无花果、麸皮和橄榄油的混合物有治疗咽炎的疗效。[21](P402)15世纪里,从安特卫普、多德雷赫特、斯希丹、阿姆斯特丹、伦敦、吕贝克和罗斯托克等地与但泽的商品往来中还涉及某些特殊农产品,即葡萄干等脱水水果。相较于文献,考古发现更直观地反映了本地水果的消费情况。考古发现约有22种未见文献记载的水果和坚果遗存,如欧洲李、甜樱桃、酸樱桃、黑栗、草莓、野橘、橡子、榛子和山毛榉等,此类群的化石遗存广布于波兰北部的中古土层之中。考古发现,此时但泽社会对野生水果的消费可能远超种植性水果。[17](P1149)但泽市内的种植性水果主要来自市郊的修道院果园,如西多会修道院的大片地产中就有各类果园,只因战争殃及,相关文献极少留存下来。[14](P450)
2.4 油料与纤维作物
此类群主要包括罂粟、亚麻、大麻和油菜四种作物。罂粟源自地中海西岸地区,其碳化遗存最早见于新石器中期的考古选样中。在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中更是屡见不鲜,多用作调味品或药品。[15](P168)亚麻和大麻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油菜主要用来炼油,其渣滓可喂养牲畜,但直到15世纪,文献中才出现了亚麻和大麻。1384年条顿骑士团的存货清单上首现罂粟的记载。罂粟籽是非常重要的食材,可作食品添加剂或炼油。[14](P451)罂粟的药用价值也很大,但泽市民多用作止痛药。这些作物皆在但泽的考古发现中获得印证。油菜遗存出现于14-15世纪的考古选样当中,但未见文献记载。[14](P448-449)
2.5 啤酒花和其他作物
啤酒花也称“葎草”,早在公元700年时就见诸文献,当时的波兰尚处于部落时代。[9](P7)中古但泽消费的啤酒花大多从汉堡等地进口,15世纪的《税赋清册》中就有提及。另有文献记载在啤酒中加入甜梅入味的细节。[17](P1149)啤酒酿造业成为但泽15、16世纪城市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当时有上千名酿酒工在但泽地区谋生。啤酒花遗存在14至15世纪的考古发现中获得证实,它们遍布于但泽市内作坊、庭院、棚屋和畜栏附近的土层当中。另有很多作物或因太过普通,不具价值而未得社会精英们关注,因此未见文献记载。这些作物既有种植性作物也有野生作物,前者如上述诸类水果,包括樱桃、梨、苹果、桃子和李子等;后者如野草莓、荆棘枣或橘子等,此类群作物便于采集但也易腐烂,不适宜中世纪长周期的远程贸易。另外,历史文献也未记录那些装饰性或观赏性作物。它们出现于16世纪左右的浮选土样之中,主要有熊果、金菖蒲、灯笼草、欧洲蕨、缬草、刺荨麻、薄荷、橡子和松子等。[14](P449)中古晚期的但泽可能还出现了集中外域植物的景观园林。[14](P451)
3 考古-文献比照分析路径的功用与价值
综上可见,历史文献和考古数据作为独立路径皆无法完整反映农作物的利用情况,更难以了解农作物所承载的更深层的指向意义——无法追溯区域文化历史轨迹、解读物质材料中的社会信息,阐释其发展动力。[22](P1)唯有将二者结合,以比照分析的路径方可弥补各自欠缺。[23](P509-515)波兰学界的成功实践正展现出该路径的多重功用。
首先,补阙史料。考古学家的首要贡献在于为古代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史料,为缺乏文献记载的历史提供文化发展的编年学。[22](P6)中古但泽文献偏重政治-经济事件的特征局限着历史学家对大众物质生活的考察。文献内容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当时知识精英的偏好:他们几乎只关心具有特殊价值而不具代表性的“奢侈性”作物。[16](P160)因此对普遍性和广泛性作物的研究就必须求助于考古学。如波兰学者对但泽豆类作物的考察论证了豆类作物在波兰北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地位,[12](P98-115)弥补了文献只关注特殊谷物的短板,为经济-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史料数据。
其次,塑造“信史”。尽管考古学呈现出“比文献记载宽广一万倍的人类历史的全景”,可以摆脱不相干的“意外”和“暂时的失真困扰”,[22](P124)但对考古材料的阐释仍未摆脱“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当下社会的“关注和偏见”。[24](P191-199)而且,单纯的文献解读也难以传达或阐释真实的历史信息。如15世纪的骑士团存货清单中出现了有关“vulgare”(香料属)的笼统记载。在现代语境中,该词即可译为茴芹,又可译作八角茴香(大茴香)。普通史家对该词的实际指代一筹莫展,被迫求助考古-文献比照的研究方法。亚历山德拉·里瓦尔达和马里耶克·范德维恩通过该路径推断出该香料实为茴芹。他们发现,茴芹源自地中海东部、亚洲西南部,中古时就已移植南欧和中欧,其茎叶和种子有丝丝甜味,是上好的草药。而八角茴香属木兰科,源自中国南方,其星状果实和种子富含油料,与小茴香和茴芹相似。14世纪的波兰宫廷文献就出现过茴芹的食用记载——它常被用作招待宾客的焦糖。[16](P201-209)15世纪时茴芹在波兰的精英家庭中已相当普遍,[17](P1149)同时代的英格兰文献也有所记载。八角茴香进入欧洲贸易网络的时间则相对较晚,直到16、17世纪时才发现其遗存,与之相关的最早记载则出自1588年菲律宾与欧洲的贸易记录中。[15](P169)
最后,考古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古代文化遗存的琐碎描述和对已构建的古代时空框架的反复印证,而是进一步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人类完整的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25](P2)目前覆盖整个中古欧洲的历史研究正极力配合新旧史料,力求重塑乡村、城市的自然景观和经济-社会模式。[26](P5)如在历史文献保存较为完整的意大利地区,考古-文献比照的研究路径正开启古代文明的整体研究之路。在此形势下,考古-文献比照分析路径兼具着更深层的指向意义。其中,对中古城市内部各阶层的贫富状况,对社会复杂关系的综合考量就具特殊价值。[21](P402)如戈登·柴尔德较早指出的那样:典型遗存的组合将成为特定人群的代表。[22](P6)因此考古-文献比照路径始受关注大众生活的经济社会史学者青睐。如亚历山德拉·里瓦尔达以罗马和中古早期欧洲进口水果为考察对象而作出有益尝试:他将考古数据和文献记载综合考察后,大致描绘出各类水果的集中消费区,以此判定城内各阶层的居住分布,然后再深入探究市内复杂的社交网络。汉萨学者则通过对进口食品遗存的考察,推断出汉萨城内富人与平民的分布与流动状况:如黑尔维希(Hellwig)曾由豆蔻遗存的分布复原了哥廷根上层市民的居住环境,而阿尔斯里本(Alsleben)则通过稻米遗存推断出吕贝克富商的日常生活。[16](P159-162)
4 余论
欧洲学界对城市考古学和农业考古学的平衡关注与中古欧洲城市的特殊地位有关。后者通常被视为封建体制内的特殊“公社”,其史料文献和物质遗存丰富,适宜考古-文献比照研究的实践。但这并非与中国学界当前的研究趋向南辕北辙,背道而行。近十几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也尝试以植物考古学的研究路径复原古代农业文明的面貌,对经济社会史作出深层探究。另外,尽管考古学拥有着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能够对考古材料和人类行为的意义获得更准确的洞见。[27](P72)但如果不对研究对象(主要是考古遗迹)加以保护和适当处置,那么再完善的理论体系最终也无处实践,毕竟发掘与保存遗迹才是提取历史精华的根本。近年来,中欧和北欧国家在考古学领域的异军突起,一方面在于它们较早实现了大学(史料与理论)与研究所(技术与实践)间的联合,奠定了考古科学长远发展的基础;[26](P1)另一方面就在于它们对古代遗迹的有效保护。如丹麦政府自17世纪起就确立起保护文物遗迹的传统,二战期间还颁布过《古代遗迹法案》(The Ancient Monuments Act),将多种形式的历史遗迹纳入该法案的保护之下。20世纪50年代时波兰政府对考古学科增加投入,鼓励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此后,全面的保护与发掘行动遍及欧洲,已取得丰硕成果,这对中国学界的长远发展皆有借鉴之处。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Len Scales.“Review about Religion und Familie inderHansestadtLübeckanhandder Burgertestamentedes14.Jahrhunderts”[J].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2002(472).
[3]HansAndersson.“AncientMonumentsAct-Exploitation-MedievalArchaeology-Research Thoughts on Manifest Connections”[J].Ian Wood &NielsLund(edt).PeopleandPlacesin Northern Europe,500-1600[M].The Boydell Press,1991.
[4]H.P.Zhang,H.E.Jiang,Y.B.Zhang,E.G.Lü,Y. M.Yang and C.S.Wang.“Early processed triticeae food remains in the Yanghai Tombs,Xinjiang,China”[J].Archaeometry.2015(2).
[5]Visa Imonen.“Defining a culture:the meaning of HanseaticinmedievalTurku”[J],Antiquity,2007(81.313).
[6]Paul Milliman.The Slippery Memory of Men:the Place of Pomerania in the medieval Kingdom of Poland[M].Brill,2013.
[7]Andrzej Buko.Archaeology of EarlyMedieval Poland[M],translated by Sylvia Twardo,Brill,2008.
[8]EricLindberg.“Clubgoodsandinefficient institutions:why Danzig and Lübeck faile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9(62).
[9]Maria Dembińska.Food and Drink in Medieval Poland,Rediscovering a Cuisine of the Past[M]. Translated by Magdalena Thoma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
[10]C.Dyer.“The Archaeology of Medieval small Towns”[J].Medieval Archaeology.2003(47).
[11]F.J.Green.“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plants from the medieval period in England”[J].In:Van Zeist and W.A.Casparie(eds).PlantsandAncientman:studiesin Palaeoethnobotany[Z].Balkema,1984.
[12]Aldona Mueller-Bieniek,Adam Walanus?,?Emil Zaitz.“Cultivated plants in medieval Kraków(Poland),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maranth(Amaranthus lividusL.cf.varlividus)and ruderal communities”[J],Acta Palaeobotanica.? 2015(55).
[13]MonikBadura.“Pimentaof?cinalisLindl(pimento,myrtle pepper)from early modern latrines in Gdansk(northern Poland)”[J].Veget Hist Archaeobot.2003(12).
[14]Monik Badura,Beata Mo?ejko,Joanna??wieta-Musznicka,MalgorzataLata?owa.“The Comparison of archaeobotanical data and the oldest documentary records(14th-15th century)of useful plants in medieval Gdańsk,northern Poland”[J].Veget Hist Archaeobot.2015(24).
[15]Ghillean Prance,Mark Nesbitt.The Culture History of Plants[M].Routledge,2005.
[16]Alexandra Livarda.“Spicing up life in northern Europe:exotic food plant imports in the Roman and medieval world”[J].Veget Hist Archaeobot. 2011(20).
[17]Chris M.Woolgar.“Review about Medieval food traditions in Northern Europe”[J].Antiquity. 2008(82).
[18]K.Deforce.“Pollen analysis of 15th century cesspitsfromthepalaceofthedukesof Burgundy in Bruges(Belgium):evidence for the use of honey from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J].J Archaeol Sci,2010(37).
[19]MonikBadura,BeataMo?ejko,Waldemar Ossowski.“Bulbs of onion(Allium cepa L.)and garlic(Allium sativum L.)from the 15thcentury Copper Wreck in Gdansk(Baltic Sea): apartofvictualling?”[J].Journalof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3(40).
[20](英)理查德·A.古尔德.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M].张威,王芳,王东英,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21]LaurentBouby,AnneBouchette,Isabel Figueiral.“Sebesten fruits(Cordia myxa L.)in Gallia Narbonensis(Southern France):a trade item from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J].Veget Hist Archaeobot,2011(20).
[22]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M].方辉,方堃杨译.陈淳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12(中译本序).
[23]K.Viklund.“FlaxinSweden:the archaeobotanical,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J].Veget Hist Archaeobot.2011(20).
[24]MarkP.Leone.“Viewsoftraditional archaeology”[J].Reviews in Anthropology.1975(2).
[2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简史[J].中国文物报,2009,(7).
[26]Juan A Quirós Castillo.“Agrarian archaeology in EarlyMedievalEurope”[J].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4(346).
[27]布鲁斯·G·特里格.时间与传统[M].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1.
责任编辑 朱文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32
K13
A
1004-0544(2016)11-0177-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多卷本《德国通史》子项目(13&ZD104)。
刘程(1986-),男,山东乳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