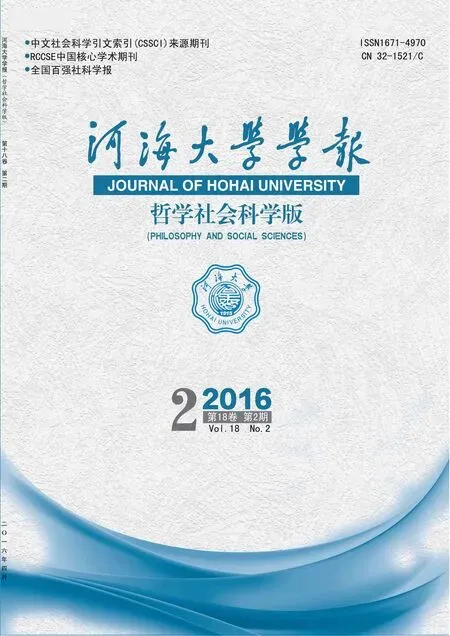论思想政治教育与“规训”的根本区别
常宴会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规训”的根本区别
常宴会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揭示了教育管理制度的心灵操控功能,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同规训的相关性。但由于未能认清规训权力的性质,使得人们误把思想政治教育认作规训。规训本质上是压迫性的权力,它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环节,并将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而被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它作为针对思想观念的政治实践活动,只有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中才能超越规训,找到自己的支点。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规训;马克思;福柯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在1975年出版后,引起了各国、各领域的关注。教育学领域率先运用福柯的分析方法,指出了教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规训权力,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逐渐关注到了规训权力理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规训[1-2]。这个判断能否成立,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方法和时代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仔细考察辨析。基于此,笔者意在思考规训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它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又该如何对待这种权力。
一、规训:从身体管理到灵魂操控
了解规训的内涵、特征、方法和后果,是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和规训之间关系的前提。规训是discipline的汉译,discipline同时具有纪律、学科、权力等含义,福柯用它来指称种种规章制度对人的规范化训练。在《规训与惩罚》中,规范化训练就是犯人按照监狱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生活,最终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规训是一种微观权力形式,福柯用这个词意在区分宏观的制度权力和微观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宏观权力指国家、政党、政体等制度性权力,微观权力则用来指称潜藏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控制机制。作为普通的个人,在生活中很少直接面对宏观权力,却时时刻刻在某种规章制度的要求下生活,因此,规训可能无处不在。用福柯的话说,规训不是监狱的专利,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监狱群岛。
福柯指出了规训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权力不再表现为抑制性的支配,而是具有生产性。惩罚并不直接与肉体残害、痛苦体验相联系,而是通过温情脉脉的形式,希望充分开发出被惩罚者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对惩罚的警觉和反抗来源于权力的抑制性,而对奖励式的“惩罚”可能毫无感觉,在欢乐中被奴役。其二,“知识—权力”机制的诞生。在传统的酷刑式惩罚中,群众透过血腥的场面看到了残暴的统治者,认识到终有一天这种酷刑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统治者在展示这种权力时也面临着被觉醒的民众颠覆的风险。在现代的惩罚技术中,人们识别出的是前台的法律,此时施加权力的主体隐蔽起来,权力的运行更加非人格化。同时,法律(知识)赋予了这种惩罚以合法性,因为法律是我们按照“科学”的方式,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此时群众革命的风险就大大减弱了。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相互制造,“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29
规训在社会管理中具体化为多如牛毛的监控技术,这些监控技术在顺序上不分先后,共同构成一个监控系统。第一,身体的动态定位。身体的定位不是限制人的行动自由,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一个人所在的空间和所处的社会角色进行精准的定位,以保证权力能够准确地到达每一个人。人们可以暂时性地躲避宏观权力,却永远无法逃脱微观权力的影响。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对监控有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每个人都有一份详细的电子档案,既包括身份证、车票等留下的空间转移轨迹,也包括社会角色变化的各种档案记录。身体的定位通常伴随的是个人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于是规训权力通过划定流动的层级激发起系统中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肉体被刺激起来、思想关注某个特定的对象时,那些胡思乱想就会消失,灵魂会重归于平静。”[3]272
第二,力量的规范化管理。“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的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3]201这个规训系统确定了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它会制定多如牛毛的内部规则,比如学生被要求早上几点钟起床,迟到扣几分,担任学生干部加几分,发表论文加几分……每过一个阶段就进行一次考核,总分数与各种资源的分配直接挂钩。定期的检查与层级流动、资源分配,是每一项规训权力实施的阶段性总结,这种检查和奖惩伴随着庄严的仪式,赋予权力以崇高的地位。如此,规训权力造就了每一个按照规则精密计算自身力量的获取与支出的个人。规范越是精确量化,对力量控制就越有效;同时,规范越是琐碎,权力控制下的个人生活也就越发琐碎。权力按照其自身方式建构了权力对象的生活。
第三,规训权力最终形成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格局。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监狱的设计理念,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圆环形建筑,圆环建筑中每个人被分配到单独的房间,窗口均朝向中心,中心设置微高瞭望塔,以形成瞭望塔对每个房间的绝对俯视,而每个房间的人无法知道塔中是否有人。这样,权力伴随目光的延伸如水银泻地般进入个人生活,保证了它的可见性和不可确知性。按照监视者的要求行动会有逐级增长的优厚回报,反之则有严厉的惩罚。来自瞭望塔的持续“凝视”就是一种权力,每个犯人为自身利益考虑,形成了自我管理。按照要求办事,能够得到逐级增长的回报,抵抗这种秩序就会成为边缘人,被这个系统排斥。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价值观。
以规训形式进行的管理活动,容易造成很多消极结果。比如,通过各种精细化的规章制度构建起来的评价体系,使得每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竞争,更加造成了人的个体化;按照规范的要求能够获得成功,而违背规则就会被边缘化和矫正,诱惑和惩罚并存,使得每个人照着各种评价指标安排自己的生活,成为无个性的被驯服者;规范越是细化,对人的生活的控制就愈加全面,人成了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零件和被开发的工具,而不是当作人来看待。规训权力造成的消极后果,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大量讨论,这里不再详述。
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自诞生以来就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在这里仅将关注点聚焦在它所呈现的新式权力观:权力不是压制,而是调动积极性、“奖励式惩罚”;权力没有施行的主体,而是非人格化的知识;权力虽然作用在身体,实际上却构成对灵魂的操控。
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
福柯认为,监狱只是将规训运用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已,而现代社会的军队、工厂、学校等机构中都充满着规训权力。因此下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将思想政治教育认作规训,规训权力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有哪些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与规训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使得两者的对比成为可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以教育的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某种政治价值观,是“意识的政治”[4]。而福柯所说的各种规训技术同样也指向着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和规训在思想、政治和教育3个层面上有相似之处:第一,学校中的各项规章制度,虽然是在管理学生的身体,但客观上会造成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发挥价值观改造的功能。比如迟到早退的处罚和奖学金评比挂钩,从未迟到早退是参评奖学金的前提,表明不迟到不早退在价值上是更被认可的,于是奖学金制度客观上发挥了心灵管理的功能,这是规训的思想层面。第二,每一套规则都暗含着一种价值观,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生活”,怎样实现“好生活”,众多规则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人生活的全部。价值观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这种政治的运作不是通过强权压迫实现,而是通过告诉人们如何做能够活得好,把人们的身体调动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做事的过程中就认同了既定的游戏规则。这是规训的政治层面。第三,价值观教育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是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崇尚什么。一个群体中颁布的规则指向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在教育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对,这是规训的教育层面。思想政治教育针对的是人的思想观念,主要从事的是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内容极为丰富的活动,不仅包括课堂教学,各项管理制度也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样,人们将思想政治教育同规训做对比就不足为奇了。
思想政治教育同规训有本质的区别,将思想政治教育认作规训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未能把握规训权力的性质,进而造成无法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支点。
福柯曾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3]248并且,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规训与惩罚》同《资本论》的亲缘关系:福柯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中工厂的协作、分工和监督中蕴含的微观权力主题化。因此,回到《资本论》对分工的描述,是厘清规训权力性质的不二法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劳动的总时长是法律规定的,因此只能通过改进劳动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为此,分工和对工人劳动动作的精密开发诞生了。在分工的基础上,工人群体就像一列军队一样,资本家则是指挥。后来,监督和指挥的职能逐渐形成文本,构成工厂中的规章制度,监督的角色也转由工人承担。“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5]384这里的特殊性质,指的就是深入毛细血管中的规训权力。马克思继续指出在协作生产中,工人就是总体的一个零件、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5]386-387为了让工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一系列关于管理的理论成果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环节是规训的发源地,资本的逻辑——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使得现代管理制度成为压迫人的规训权力,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使得规训权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结合各种规章制度造成的精神后果,马克思所言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意也在此。
规训本质上是压迫性权力,生产性只是其表面形式。相比以往的流血式权力运作方式,或许可以说它更加文明,但无疑对人的支配更加全面、更加隐蔽、更加残酷。由于权力的隐蔽性,工人阶级并不能认识到自己被规训的社会机制,由此产生了虚假的政治认同。而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不是说任何一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是规训,而是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与规训权力格格不入。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把人当作工具,而是努力通过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起到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整合意识形态的作用,且这些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压迫的形式实现的。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理应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中确立自己的支点,从而保障政治实践活动与个人幸福生活的统一。
三、规训权力理论的遗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支点分析
规训同思想政治教育有本质区别,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关性。从两者的相关性角度来看,规训权力理论能够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提供一份遗产;就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只有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视野中,能够超越规训,为思想政治教育寻找一个稳定的支点。
1. 规训权力理论的遗产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新
规训权力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微观权力值得深入研究。在实践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自然始终伴随着宏观的制度化权力,如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设计。相应的,在宏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研究也相对充分。但在微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国家权力并不直接在场,每个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院或班一级的,甚至在学生同辅导员、班主任的日常交往中就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中,微观权力的样态和运作过程是有待研究的。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还是教育学心理学,都已经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自律的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向多态化的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的这一深层次转变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例如,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传统的理论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权的更迭、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为对象,而很少关注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控制机制。”[6]规训权力理论是微观研究的范本之一,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研究的借鉴资源。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福柯对规训技术的发掘展示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为田野调查,即通过亲身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进而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理解。教育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制定各种制度的时候也秉承为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宗旨,但制度的落实环节对学生的心理产生怎样具体的影响,是需要亲自参与其中才能体会的。福柯之所以能够揭示出现代刑罚技术中的微观权力,是他亲自参与到监狱的日常生活中的结果。1971年2月,福柯发起了一个“监狱报道小组”,深入到犯人的生活当中,通过对在押犯人、被释放犯人及其家属的深度调查,弄清楚权力机制的具体运作。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主要是高校教师,他们更能理解学校一系列管理制度对学生的深刻影响。因此,人类学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之一。相比之下,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则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倾向,研究成果还远未达到生动活泼的程度。
最后,规训权力理论启示我们重新检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人们通常以为,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教育活动,那么其着力点应该是一系列精神产品,如教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但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恰恰表明:对灵魂的影响,着力点重新回到身体。不仅要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更要让教学管理制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校园生活的日程安排,包括早操、上课、午休;教育教学的管理制度,如奖学金评比、学生干部的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等活动中师生的具体交往活动,都有可能重新提取出思想政治教育因素[7]。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训权力理论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探照灯。
2.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支点
以福柯的规训权力为视角观察今天的教育,会让人陷入绝望,而且一定会有人质疑福柯,难道不是所有的管理都会滋生规训权力、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尽管任何管理都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但规训形式的压抑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逐步形成的。面对规训,人们必然会思考如何“走出”规训。现有研究在考察规章制度带来的压抑之后,在“走出”规训的努力上主要呈现两种趋向:或是认为制度设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或是认为既然规训权力是微观的,对它的反抗也应该是微观的、零碎的,比如受教育者故意不合作,能够形成人和制度之间的互构。这两种抗拒规训的方法尽管有意义,却没有抓住规训的本质和政治(权力)形态的历史性。福柯没有“走出”规训的视野之外重新审视规训,和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一方面福柯丝毫不吝啬对马克思在微观历史叙事的卓越表现给予赞美;另一方面,福柯对规训的考察建立在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之上,此时黑格尔、马克思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是福柯的批判对象。所以在福柯那里根本无所谓“走出”规训。笔者认为只有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下才可能超越规训。
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地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5]874当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公共地使用,并以剩余价值为最终追求,自然需要精密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科学的管理方式,此时所谓“采取新的形式”就是理性化的形式、规训的形式。追逐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统摄一切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断生产着关于管理的知识,权力—知识的联结让权力的运作更加非人格化,这正是规训的根本特征。由此可见,规训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的副产品。但规训强调的是理性化管理的消极方面,而马克思既看到理性化管理的消极方面,又看到其积极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超越资本主义时代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锻炼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5]874应该承认资本的积极功能,比如资本的教化功能,它使得人们学会了团队精神、纪律观念、敬业精神、竞争精神……这些都是现代人的美德。进一步说,现代教育的规范化管理,使得大众教育成为可能,实现了知识的高速、普遍的传播。现代学科分工下的知识生产,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对理性化的管理制度应该做出历史评价,而非道德评价。资本作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是历史性的,由资本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政治、教育制度也是历史的,从这里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超越规训的视野。
以往一种经典式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阶级社会的诞生,因为从阶级社会开始,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就分为物质性权力压迫和精神上的操控,后者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中,这种观点是存疑的。一方面,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正确,因为人类社会距离消灭阶级差别有相当长的距离,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必然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随着资本主义逐渐被扬弃,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压迫阶级被消灭,此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吗?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存在,因为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只是那时政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对政治形态演变的把握是同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是压迫性的政治,政治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在宏观上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表现为遍布于工厂、军队、医院和学校的规训权力。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是旨在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应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后一种政治形态上。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而以规训形式进行的所有教育活动终将被时代抛弃。
参考文献:
[1] 魏永强,郑大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分析.求实,2014(9):79-88.
[2] 潘欧文.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症候群”:交往哲学的视角.教育学术月刊,2009(5):46-49.
[3]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金林南.从政治的意识到意识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政治哲学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 2010(19):29-3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6]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7] 常宴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析:基于H大学的田野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3(2):82-97.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hinese Peaceful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ZHANG Heming,et al
(History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exercising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reasonably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friendly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Chinese peaceful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traditional harmonious culture, China has kept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ancient times.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ffair. Chinese behavior pattern of foreign policy originates from harmonious thought and China keeps show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safety and development in many regional affairs. Chinese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only historic heritage but also practical choice, which shows China’s sincerity on settling the dispute and may lead to safe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future. Foucault’s theory about discipline indicates tha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may lead to soul manipulation, which show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However, people regar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discipline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 The essence of discipline is oppressive power.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link of capitalism and may be surmounted with the subla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discipline and as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ideology, it can only transcend discipline and find its foun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Key words:the South China Sea; management;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y; harmonious though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Marx;Foucault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CHANG Yanhu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2-0037-04
作者简介:常宴会(1989—),男,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收稿日期:2015-05-26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