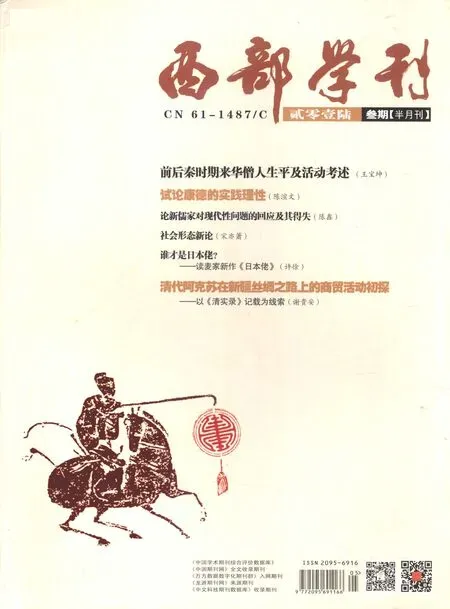论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及其得失
陈 鑫
论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及其得失
陈 鑫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后果,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理性的界限并恰当运用理性。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性的诸问题都有回应,在回应中体现了新儒学的现代性特征:理性、自由和批判精神。其回应之所得主要在心性论方面,所失主要在政治学方面。新儒学作为多元思想中的一元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有借鉴意义。
儒学;新儒家;现代性;现代哲学
儒学是先秦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自古及今,凡历三变:从先秦儒学到两汉经学,诸子淡出,儒家独尊,是第一变;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融摄佛老,阐扬义理,是第二变;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旧邦新命,“西学中取”,①是第三变。其中第三变在所涉问题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前两次,因为传统君主制已不复存在,与之相应的人伦关系也随之消失或变异,中国现代新儒学是伴随着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运而生的。从空间上看,新儒家要与西学相抗衡;从时间上看,新儒家维护自身道统之延续。新儒学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中建构自身,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冲突中寻求会通。理解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是我们理解新儒学及其意义的一大关键。
一、“现代性”的含义及其问题
(一)现代性的含义
“现代性”(modernity)源自“现代”(modern),相关于而又不同于“现代化” (modernize)。每个时代对于当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现代的”。一方面“现代”即现在、当前之“现时代”;另一方面,“现代”又是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时代”。从构词法上看,“现代性”是modern一词加上表示性质、关系、程度等意义的后缀-ity构成的,其一般含义是现代社会及其中的人和事物所具有的性质。[1]
对于“现代性”的具体含义,自20世纪晚期以来众说纷纭。俞吾金先生曾概括出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历史时期,即中世纪之后的那个时代(代表人物是凯尔纳和贝斯特);二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模式,即工业社会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代表人物是吉登斯);三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即关乎理性、自由、资本、技术等元素的、一体化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代表人物是利奥塔);四是把“ 现代性”理解为一个自启蒙以来尚未完成的方案(an unfi nished project),以“客观科学、普遍道德与法律、自主艺术”的发展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2]34其中第三、四种观点主要从哲学维度揭示了“现代性”含义,第一种观点更接近于“现代”,第二种观点更接近于“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即社会获得“现代性”之诸特征的过程。[3]10“现代化”属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意味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性”属于哲学范畴,意味着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新的权威。如果说“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原因,那么“现代性”则可以看作“现代化”的结果。[4]
(二)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的概念。传统断裂处,“现代性”生根发芽。从思想史角度看,“现代性”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我们首先可以从康德和福柯的两篇同样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探寻“现代性”的若干特征。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intelligence),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reason)。[5]23“理性”之中的“认识”能力即“理论理性”(即“思辨理性”),被运用于科学知识领域;“理性”之中的“意志”能力即“实践理性”,被运用道德和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
而康德用来联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拱顶石”是“自由”:“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6]2康德以先验的自由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让人为自然和道德立法;黑格尔则将主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建基于客观的伦理现实: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其中市民社会是公民联合起来,为维护其私利和公益而建立的,不受国家干预的自治领域。[7]32“自由精神”是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
福柯认为,启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批判性的:在理论上,考察我们的界限:我们如何在与物、他人和自身的关系中被建构为自身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在实践中,把我们自身交付于“现实”和“现时”的检验,寻找“越界”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态度体现了我们对自由渴望。[8]“批判态度”是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
(三)现代性的主要问题
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神明隐退,理性登场。我们身处一个批判的时代,宗教的、法律的、习俗的一切权威都要经过理性的批判。但理性是否是一位可靠的法官?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制造出一个虚构的理性世界,理性在其中成了压制人的本能和生命的新的暴君;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人的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成为主导,功利性追求成为主流,启蒙思想所向往的社会公正等价值已被抛弃。[7]312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崇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消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9]48
“现代性”的困境也就是理性本身的困境。传统理性主义主客二分的文化心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现代世界问题,理性自身的“范式”已经转变。“主体”的“普遍性”日益为“个体”的“差异性”所取代。因此,重新认识理性的限度和使用范围,在后理性主义时代重建理性秩序,让它更加合理化、合法化,更可接受,是我们面临的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其他“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如技术异化、资本奴役、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二、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西学的学习经历了从“技术”到“制度”的深化,而现代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相当于中国的“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进一步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引介西学并反思“国学”——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而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主张吸收“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主张回到比“科学”和“民主”更为本源的“道德主体”中,借鉴西方“学统”“治统”,契接中华之“道统”。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主要是在此背景中展开的。
(一)理性的用途与限度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识论很不发达。先秦儒家已有“格物致知”之萌芽,并在宋明理学中有进一步生长,但其所重者多为“德性之知”(“大知”),对“闻见之知”(“小知”)讨论得不多。前者关乎“实践理性”,后者关乎“理论理性”。
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科玄论战”训练,现代新儒家对“理论理性”,或理性的理论维度,具有了超越传统儒家的认识。熊十力区分了“性智”和“量智”两种认知能力:“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底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在宇宙论中,赅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10]249简言之,“性智”和“量智”之差异是“本体”和“作用”的差异:“性智”内省,可用于哲学;“量智”外驰,可用于科学。梁漱溟区分了两种理性:“情理”和“物理”,前者关乎品性,可称之为“理性”;后者关乎智能,可称之为“理智”,“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11]113熊十力的“量智”和梁漱溟的“理智”比较接近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其作用主要限于科学领域;而“性智”“理性”(即“情理”)则可运用于哲学和人生。新儒家认为理性若向科学以外领域无限扩张,则会造成危机: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在1958年元旦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书》中所说,西方人“在其膨胀扩张其文化势力于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运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其理想中之观念,直下普遍化於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其力量扩张至某一程度,即与另一群抱不同理想之人,发生冲突。”[12]96而文化冲突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二)从精神自由到政治自由
儒家自由观偏向于主观自由(意志),而非客观自由(权利)。一方面,在伦理现实中,儒家主张个体从属于群体,个体之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君臣父子夫妇之伦理关系、长幼尊卑之等级秩序中才能显现,个人为了共同体(家、国、天下)利益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被看作是正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者代不乏人。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上,儒家则提倡“为仁由己”“人能弘道”,强调主体之精神自由的主导作用。
这种精神自由为新儒家所继承。熊十力云:“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13]20这种将主体的自主、自觉与家国天下的兴亡相关联的自由观,与西方把个体及其权利(right)作为开端和根据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不尽相同。牟宗三认为,自由精神是一切文化中都具有的,但西方的自由首先是“知性自由”,而中国的自由首先是“德性自由”。其中“德性自由”更为本源,“知性自由”需从“德性自由”中吸取营养。自由精神延伸到政治领域,则成为“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又为“德性自由”和“知性自由”“提供以确切不移的保证”。[14]简言之,“德性自由”为“知性自由”和“政治自由”奠基,“政治自由”为“德性自由”和“知性自由”提供制度化保障。
(三)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态度
新儒家继承了传统儒家“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内省精神,此精神运用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则表现为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文化领域,新儒家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较为深刻的批判。之所以说这些批判是深刻的,是因其批判西方文化之所短不忘其所长,批判中国文化之弊病不忘弘扬其益处。熊十力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优质”和“毒质”共存的:“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之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西方文化之优质既已显著,然率人类而唯贪嗔痴是肆,唯取是逞而无餍足,杀机充大宇,既造之而亦畏之,既畏之而又力造之,飞蛾投火,猛虎奔阱,犹曰无毒质也,自非小知溺俗,其谁肯信?”[15]122
在社会领域,张君劢主张“公道”是社会根本原则,同时又注意到不能以“社会公道”为借口抹杀“个人自由”,二者之关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并以此为依据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自优劣得失:资本主义社会人民自由而贫富不均,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可以均贫富却妨害人民自由,唯有“混合经济”可以平衡“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12]173
在政治领域,徐复观认为“政治是人类不得已的一种罪恶,它是由现实的政治权力生长起来的”,[16]他区分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学术上的民本思想,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治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但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三、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回应之得失
从上述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来看,新儒家在倡导“理性主义”时区分其结构,限定其边界;在弘扬“自由精神”时强调“精神自由”、特别是其中的“德性自由”比“政治自由”更本源;在表达“批判态度”时遍及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包括对儒家自身的批判。由此可见,新儒家力图在知性与德性、个体性与公共性、民族性与普世性等二元对待中寻求均衡,这可以看作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现代表现,也体现了新儒家力图融汇古今中西之学的“综合性”取向和“过渡性”特征。
总体上说,新儒家回应现代性问题之“得”主要集中在心性论层面。儒学的特质不在于理论建构,而在于道德实践,特别是在以“性善论”“良知说”等思想为主的“人性论”和以“慎独”“知行合一”等方法为主的“功夫论”方面,对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缺乏价值维度的“现代性”末流有纠偏作用。梁漱溟的“宇宙生命论”、熊十力的“良知呈现论”②、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圆善论”等都是对传统儒学(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深化和发展。
新儒家回应现代性问题之“失”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层面。新儒家继承传统儒家“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精神,认为“道统”和“治统”应当是贯通的,有“仁心”然后有“仁政”。徐复观一方面承认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正轨和坦途”,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才可以真正为民主政治奠基。[16]247牟宗三认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内圣”就可以开出“新外王”——民主与科学。[17]215这些思想本质上仍然是强调德性为政治奠基,意识到了“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却未阐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联,相应地也没有解决个体的“德性”如何向公共的“伦理”过渡,缺乏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我们在新儒家对于“现代性”问题回应之“得”与“失”中可以看出:探讨并实践价值观念(如“仁”与“义”)的“心性儒学”在当代世界仍有较大价值;而与特定历史内容(如“礼”和“法”) 密切相关的“政治儒学”则相对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价值观念具有普遍性,历史内容具有特殊性,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关联,更需澄清二者之差异。
四、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中的地位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通过“集体无意识”世代相传。我们作为“现代人”既要审视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更要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张志扬先生提出:“中国现代哲学”不同于“现代中国哲学”,它既不是“新儒学”,也不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国版”,它是什么仍悬而未决,我们只有进行一个“根本性反省”和“自身形式的探索”,才有可能让“中国现代哲学”从“中西古今之夹壁中”“破门而出”。[18]363
“现代性”和“中国现代哲学”都是未完成的课题,“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首先跨越“现代性”这道门槛。“中国现代哲学”虽不就“是”新儒学,但新儒学作为一条中西古今交汇的河流,仍然可以提供许多启示,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只不过在“现代”这个经历了“现代性”洗礼的多元文化时代,新儒学已不复是且不应是居于诸文化之“上”的、“大一统”式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且应是位于“百家”之“中”的“一家”。
注释:
①张志扬先生认为应该用“西学中取”替代“西学东渐”,因为“西学中取”主位在我,西学东渐则反客为主。参看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②冯友兰认为王阳明所讲“良知”是一个“假设”,而熊十力认为“良知”是当下即是的“呈现”,前者是一种倾向于知识论(量论)角度的理解,后者则是倾向于本体论(性论)角度的理解。
[1]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2]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4]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5](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法)福柯.什么是启蒙?[J].政治思想史,2015(1).
[9](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熊十力.新唯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3]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4]徐复观.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J].民主评论,1956(21).
[15]熊十力.十力语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7]程志华.中国近现代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8]张志扬.偶在论谱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李直)
B26
A
CN61-1487-(2016)03-0029-04
海南省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HNSK(QN)15-97);海南师范大学2015年“助飞工程”政治组教学改革项目。
陈鑫(1982-),内蒙古海拉尔人,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