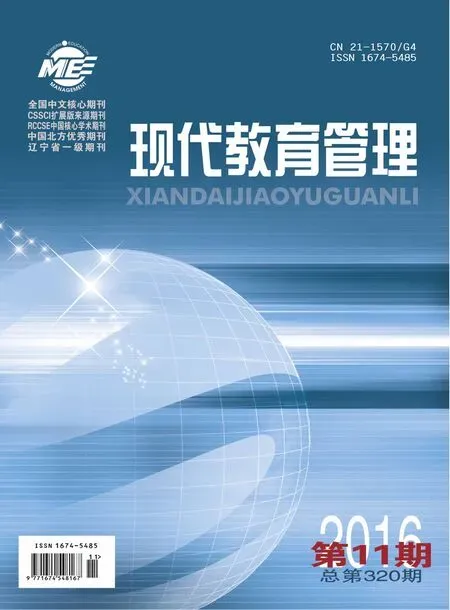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模式、动因与内容①
何淑通,何 源
(1.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医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1166)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模式、动因与内容①
何淑通1,何 源2
(1.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医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1166)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内外多元利益相关者博弈后处于均衡状态的结果,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与缓慢变革当中。从变革模式的维度来看,可以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分为内部革命型、内部演化型、外部渗透型和模式移植型四种类型;从变革动因的维度来看,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包括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往往起到量的积累作用,而外部动因则起到质的飞跃作用;从变革内容的维度来看,寻找大学内部纵向权力分配的“平衡点”、横向权力的分工合作机制和最高权力主体的权限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三个重点内容。研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特征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更好地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改革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一个系统,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的增减和排列组合方式的变化都会引起结构的变化,治理结构的变革与主体、内容、方式、趋势等多个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怎样变革(变革的模式)”“为何变革(变革的动因)”和“变革什么(变革的重点内容)”三个维度出发来分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将变革的主体(来自大学内部还是外部)和变革的方式(剧烈还是渐进)作为考察的两个维度,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划分为内部革命型、内部演化型、外部渗透型和模式移植型四种类型。
(一)内部革命型
所谓内部革命型,就是指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主要由大学内部某个权威的推动,以一种比较快速的方式确立新的治理结构。这种变革方式往往都与大学内部一些权威人物密切相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甚至整个大学在他们的形塑下,真正变成了另外一种新的样式。从大学史来看,这种变革类型往往容易发生在一所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阶段,其推动人物多数发生在大学校长的身上。这种情形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校长和我国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
在蔡元培来北京大学以前,北京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全是政府的翻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的治理思想着手建立新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新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设立评议会。二是成立行政会议。三是废门改系,各系成立教授会。四
是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五是设立总务处,管理全校的人事和财政工作。[1]蔡元培在北大主持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奠定了北京大学制度的骨架,以至于“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2]。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时间不长,很快就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体现了内部革命型变革模式的特点。
(二)内部演化型
所谓内部演化型,是指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主体比较模糊,变革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大学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在“无声”的变革中最终演化成为另一种新的治理结构。这种变革模式既与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或减少相关,又与治理主体权力的增强或减弱相联系。这种类型的变革发生在所有大学里,但是由量变引起质变却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且需要一定的契机和外部力量的推动。
这种传统演化型的变革模式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其变革主要“依靠许多基层的创新;依靠劝说和自愿而不是命令进行的创新;依靠渐进的而不是全面的革新;依靠静悄悄地渗透院校边界的变革”[3]。譬如,近代以来,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大学内部的管理活动日益增多,大学日常运行的保障任务加大。同时,由于教师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加重,导致教师日益不愿意承担兼职的管理任务。这个时候,在部分大学开始出现一批专门从事保障工作的管理人员,他们专职从事管理服务工作。随着行政人员在大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逐渐参与到大学内部治理中来,从而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改变。
(三)外部渗透型
所谓外部渗透型,是指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主体主要来源于大学外部,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对大学内部治理主体实施影响,使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其变革的方式是渐进的、间接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密,大学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介入到大学内部治理活动中来,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这种外部渗透型的变革模式往往发生在传统大学和民主国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虽然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外部政策意图必须与大学逻辑相适应后才能发生作用,其变革往往都需要在大学内部取得共识后才可以逐渐展开。
大学以外通过渗透的方式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发生影响的主体有政府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组织。这种渗透最典型的事例便是政府通过立法、资助政策、基金会等方式对大学外部或者内部治理主体产生影响,从而使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譬如,19世纪70年代,为了促进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改革,英国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介入到这两所大学的内部治理中来。1871年,英国颁布《大学考试法案》,正式废除了牛津和剑桥学者的宗教特权;187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877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案》,通过立法的形式促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4]
(四)模式移植型
所谓模式移植型,是指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主体主要来源于大学外部,外部治理主体往往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方式使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迅速发生变化。这种模式表现在外部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通过整体移植其他国家的大学制度或者直接干预大学内部治理的方式使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迅速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模式效率较高,但也存在着外部力量与大学传统的适应问题。日本筑波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建立过程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变革模式的特点。
近代以来,日本大学在移植德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讲座制”为基本特征的组织模式。评议会是大学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是学部重大事项的决定机构,校长和学部长往往都是根据评议会和教授会的决议和意图去行使职权。1973年成立的筑波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日本其他大学均不相同。它首先加强了学校一级的管理权限和力量,除校长外,增设了5位副校长(其他国立大学均不设副校长)。大学评议会由校长、副校长、部局长以及各学群和学系推选出来的教授组成,但是其职能由过去的决策机构变成了咨询机构。同时,为了让社会意见能够参加到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中来,还专门设立了参与会这一机构,参与会由校友和有识之士组成。参与会的成员由校长根据评议会的建议确定,文部大臣任命。为了保证筑波大
学的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得以落实,日本国会专门通过了《部分修改国立学校设置法等的法律》,对《学校教育法》、《国立学校设置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等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筑波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全体现了文部省的意图,被称为“文部省大学”,体现了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一次突破日本大学传统模式的尝试。[5]但是,由于其他大学的反对,筑波大学的模式并没有推广到日本的其他大学中。
综上所述,我们依据变革的主体和变革的方式两个维度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模式划分为内部革命型、内部演化型、外部渗透型和模式移植型四种类型。这种划分当然是一家之言,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思路,便于更有效地了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特点。在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相对于大学外部治理结构而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较为缓慢,最终往往都有赖于偶然事件或者外部治理主体的推动方可发生质的变革。
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影响事物变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其中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而外因则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而言,其变革的动力也主要来源于大学的内部和外部,大学内部各个构成要素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都会引起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一)内部动因
1.利益相关者的变化
现代大学中存在着多个利益相关者,而治理强调的是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通过利益(害)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一群人”,是一个范围广泛、成分复杂、性质各异的群体。[6]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由于规模较小,大学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于是就产生了三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大学、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大学和由学生与教师共同掌握治理权的混合结构。但是总的来看,中世纪大学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简单,治理主体都是学术群体。近代以来,随着大学组织的日益复杂,大学内部逐渐产生了一个管理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体开始逐渐介入到大学内部治理中来。二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在美国率先出现了所谓的“多元巨型大学”,同时随着民主化思潮在大学中的兴起,大学内外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要求参与到大学治理中来。以上每一次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增减都会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
2.知识演进
大学以知识为材料,知识的变化也是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而每一次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和知识范式的转型往往都会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在中世纪大学中,神学是知识上的皇冠,所以神学院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而近代以来,一个个新的学科在大学不断诞生。德国大学顺应了知识发展的历史趋势,首创“讲座制”作为大学内部的基层单位,并使之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一个个细胞。而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学者个人掌握的知识越来越狭窄,因此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可避免,这时美国大学的“系科制”应运而生,学者之间通过联合和选举代表的方式参与大学内部治理就成为必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的经济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资本主义”开始在大学中兴起。“学术资本主义”不仅导引大学内部治理矛盾向外部治理矛盾局部转移,在大学内部治理中还拉动治理权力向治理结构的顶层和基层延展。[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的地位、知识的价值等都会影响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3.大学理念
大学是一个知识组织,也是一个文化社群,这决定了大学的内部治理离不开文化和理念,大学理念的意义在于为不完美的大学制度提供一个完美的参照,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努力追求完美、实现大学的理想。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甚至政治人物,都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理念,而这些大学理念都在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纽曼大学理念所对应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一定与学院制紧密相连,洪堡大学理念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一定是教授治校的,而“威斯康星”大学理念所对应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一定会有校外董事会的参与。不同的大学理念铸造不同的大学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离不开
大学理念,一所大学中人们所信奉的大学理念的变迁和博弈往往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
4.大学校长
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大学校长处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交汇点上,其身上担负着众多的责任和义务,“大学校长是董事会和大学之间的联系枢纽,没有校长强有力的领导,大学的管理系统不可能有效运行”[8]。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西方大学史上,埃利奥特、赫钦斯、科南特、博克等知名校长都为自己所在大学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大学史上,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朱九思、刘道玉等知名教育家都为自己的大学留下了无数的故事。一个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校长一定是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校长,大学校长所具有的特殊力量是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不可预测的力量。
(二)外部动因
1.权力控制
自治与控制是伴随大学发展的一对永恒矛盾,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得每一种政治势力都不会轻易放过大学。当然,大学外部权力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的控制往往需要通过外部治理来完成,而通过大学外部治理结构间接影响或者直接控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不同国家经常采用的两种方式。[9]权力的控制往往都会促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在中世纪,教皇和皇帝的争夺往往会导致大学内部领导权的更迭,并且导致大学内部自治范围的增减。而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政府不能放任大学不管,会采用种种方法来控制大学。近现代以来,大学外部各种权力的作用都会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这从历史上的“达特茅斯案”、清末以来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等事例中都可明显看到,这里不再赘述。
2.资源状况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资源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大学必须依靠获取和利用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才可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旦遭遇资源匮乏,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致命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衰败。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不仅包括大学运行所需要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文化、精神、声誉、信任等大学组织中的无形资源。整体来看,大学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需要大学去争取。[10]因此,大学的资源状况是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动因。譬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西方各国都普遍削减了对于大学拨款的数额,在这种形势下,“创业型大学”在很多国家兴起,其主要特点包括: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得到扩大和提升,大学校长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权力,处于大学权力的中心位置。[11]大学的资源状况推动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
3.竞争
在大学史上,由于大学的多样性,所以大学之间的竞争现象无处不在。大学之间的竞争导致大学的组织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又使得各个大学之间的治理结构越来越具有同一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同,导致这些院校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另一方面,在相互竞争中,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模仿,又使得各个大学之间组织结构的差别趋于缩小,向着名牌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12]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中也呈现出这种现象。大学的竞争导致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走向多样化和趋同化。世界大学的“美国化”、“研究型大学化”等事例可以说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趋同化,而一些国家率先兴起的“创业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又可以看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多样化。这些事例无不说明竞争是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动因的反思
1.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外部的力量,也有来自大学自身的力量,还有内外部的合力,但是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大学的惰性,与外部因素相比,内部因素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所起作用的时间相对较慢。因此,内部因素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往往起到量的积累作用,而外部因素则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起到质的飞跃作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力是多种的,有内部因素主导型、外部因素主
导型,但更多时候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型,它们的综合作用促进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2.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因素可以互相转化
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情况下,这些因素甚至会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作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内部动因较为稳定,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也会产生惰性。而外部动因则比较易变,往往今天的积极因素会变成明日的消极因素。譬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改革中,为了使大学中教学功能达到最大化,不但进行了院系调整,对教学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还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由之前的三级管理体制转变为二级管理,以使得管理重心上移。[13]但是,20世纪90年代,这种教学功能最大化的治理模式遭遇挑战,又不得不重新调整为“校—学院—系”三级模式。这说明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中必须综合考虑大学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因和外因,而不可只考虑单一因素。
3.外部因素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现代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除了政府的强势,大学对于外部资源依赖的增加以及大学间竞争的加剧以外,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内部因素也逐渐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学利益相关者日益向大学外部扩展,知识的应用性日益得到重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大行其道;随着知识的日益专业化,大学教授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范围开始缩小;而随着制度主义的强势,校长的个人作用也在减弱。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外部因素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三、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容
从大学演变的历史来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重点内容集中在处理大学内部治理中纵向权力分配、横向权力分配和大学内部最高权力分配三个问题上。
(一)纵向权力分配:不断寻找“平衡点”
从大学史来看,权力分配问题一直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主要内容,而大学和基层之间的纵向权力分配问题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不变主题。依据大学类型的不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纵向权力分配一直处于不断地调整中,一直在寻找大学和基层学术组织之间权力分配的“平衡点”。下面我们以历史悠久的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法国大学历史悠久,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历史比较全面地诠释了大学内部治理中纵向权力分配的问题。在中世纪的法国大学中,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出“重心在下与教师至上”的特点,大学内部治理的重心位于大学基层,而校级层面的权力相对较小。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19世纪初“拿破仑体制”的建立,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法国建立起来。但是,大学内部治理仍然呈现出中央集权之下的学部自治特征,其内部治理结构也呈现出“重心在下与学部自治”的特点,这种结构特点一直延续了150余年。1968年,法国爆发了战后规模空前的史称“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直接催生了《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该法案提出了大学办学的自治、参与和多科性三原则。随后,1984年和1989年法国政府又分别出台的《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指导法》进一步确认和实施了这些原则。在这些法案的指导下,法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重心上移与校级权力增强”的趋势,校长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但是高级学术人员的治理权力仍然没有受到多少削弱。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政府又相继对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校级权力。其中,在2007年法国政府通过的《综合大学自由与责任法》中,校长和校务委员会成为了大学治理权力的核心。大学内部的管理决策权逐渐集中到了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手中,基层单位的治理权力空前缩小。2013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高教与研究法草案》,该法案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削弱校长和校务委员会的权力。[14]从以上的简要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近千年的岁月里,调整大学和基层之间的纵向权力关系是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法国大学的校级权力一直在增强与削弱中呈
现出“钟摆”现象(尤其是在近代以来)。
从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变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法国大学具有自治的悠久传统,治理重心下移和保证高级学术人员的参与是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永恒追求。但是,随着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学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与外界开展合作交流,从而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获取资源,于是校级治理组织和校长权力的加强也就成为必然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在大学内部,权力开始高度集中到高级管理者尤其是校级管理者手中。[15]当然,对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往往表现为校级权力过大,但是由于大学的知识生产往往在基层实施,所以逐渐加强基层权力也是一个趋势。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寻找大学内部治理纵向权力分配的“平衡点”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永恒主题。
(二)横向权力分配:从“模糊混沌”逐渐走向“分工合作”
在大学诞生之初,由于规模较小,大学内部的事务多数属于学术事务,所以治理权力一般掌握在学术群体手上。而在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中,治理的客体开始逐步分化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两大类。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发展目标,共同治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在多个国家得到实践,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横向权力分配呈现出从“模糊混沌”走向“分工合作”的趋势。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可以看作是大学内部治理中横向权力走向“分工合作”趋势的最佳注解。
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的形成有着曲折的过程。殖民地时期,美国大学的决策权掌握在外行董事会的手中,教师的权力局限在教学事务上,甚至在运行中还多次发生董事会直接解聘教授的事件。19世纪下半叶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兴起、20世纪早期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二战”及之后的学术革命等因素都促进了教师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开始在美国大学中逐渐得到确定。在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大学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行政系统和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评议会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董事会主要关注反应性、校长主要关注效率、而教授则主要关注学术价值。共同治理出现的原因在于:学术决策的制定应该规避短期的管理主义和政治考量,而教师是教学、课程和研究政策的最佳人选;但是同时行政人员在资源分配、目标设置、选取领导者和指导学生生活等事务上比教师具备优势。因此,共同治理特别强调不同群体之间权力的分享和注重尊重、平等、沟通的程序两个原则。[16]共同治理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参与到大学的每个决策当中来,而是指每个人在清晰的职责范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参与度。美国学者William Brown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教授对大学事务的最优参与度与决策类型有关。其中,教授参与管理学术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糟糕。[17]正如美国学者埃伦伯格所言:“大学管理中的变革不是要建立集权化的命令——控制系统,或界定过分简单的利益中心和绩效标准,也不是向大学注入商业价值——这将置大学于死地。另一方面,如果大学仍然掌握在教师手中,它也必将走向灭亡。管理变革,即是指要设计出鼓励竞争、保护多样性和保持大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分权式结构。”[18]这些无不说明,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横向权力必须建立在分权合作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实现大学的治理目标,也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特点。
(三)大学内部最高权力主体: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
大学内部治理中包含着多个治理主体,而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治理结构。与传统的管理相比,治理强调多中心和权力的分享,因此最高权力掌握谁的手中、如何掌握也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在传统大学中,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最高权力要么掌握在单个人的手中(如校长)、要么掌握在某个委员会的手中(如评议会、教授会、董事会、党委会等),大学内部往往都有一个权力中心。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主化思潮的推进,各个国家的大学在进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过程中,往往都是通过设置新的治理机构来削弱或者分散原有的治理主体的权力,大学内部最高权力分配越来越有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
趋势。这里我们以“国立大学法人化”实施前后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状况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传统的日本大学中,评议会是大学主要的权力形式,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有着最高的决策权,大学校长由评议会的教授推举,政府任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日本大学中的最高权力中心是评议会。20世纪末,日本政府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改革后,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构架为:由校长、校长指定的理事、若干教职员和校外人士组成经营协会,专门负责大学的经营战略决策;而教育、研究评议会专司学术事务;在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上,由校长来指挥协调;而校长之上,还设有管理人员会,包括校长1人、理事2-8人、监事2人,其中要求有校外人士参与。这种新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讲求效率,提高大学的经营活力。[19]由此可见,日本大学的内部最高权力分配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由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为了处理大学内部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寻找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权力分配关系就成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容。其中,寻找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纵向权力分配的“平衡点”、横向权力的分工合作机制和大学内部最高权力分配的方式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重点内容和发展趋势。
四、借鉴与启示
自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以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研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动因和内容将有利于指导我国大学当前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对于我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需要外部治理的“助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是缓慢的,但是近代以来,外部治理的助力是必不可少的。有学者经过研究后发现,我国公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变化缓慢。而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差别不可忽视。我国政府在对大学进行制度改革时,往往都采用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导致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低效率的困境。政府的主要作用和职责应该是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提供外在环境支持和约束、确立秩序以及治理结构变迁的方向和范围,[21]真正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提供制度助力和保障。
其次,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需要发挥大学内部的动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内部动因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恒定因素,外部变革往往需要通过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大学内部的因素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在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其关键仍然是要调整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为大”的治理观念、“高度集权”的治理体制、“长官意志”的治理行为和“法治淡薄”的治理习惯。[22]通过激发大学内部的动因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第三,降低治理重心、促使多元主体参与是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当前,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内容可谓是千头万绪,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通过降低治理中心、提升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能力应该成为一个可资考虑的选择。因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和制衡,而在纵向上实施学院自治有利于在横向上实现学术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分工合作,有利于最高权力主体走向“多元化”。因此,可以将学院自治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将目前我国大学校级层面的治理权下放到学院一级,让学院的教授委员会行使学院事务的决策权,院长行使执行权,学校党政领导集体及全院教职工行使监督权,从而形成分权与制衡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23]要通过培育基层学术权力,为进一步做好大学内部各个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1]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7-110.
[2]韩水法.大学与学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4.
[3][12][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7、145.
[4]郑成琳.剑桥大学治理结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14.
[5]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208.
[6]胡赤弟.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55.
[7]谢艳娟.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治理结构变革[J].现代教育管理,2014,(6):61.
[8][美]弗兰克·H.T.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王晓阳,蓝劲松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60.
[9][22]胡建华.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关系分析[J].江苏高教,2016,(4):2-4、5.
[10]钱志刚,崔艳丽.论大学组织变革的制约因素——内部的视角[J].高校教育管理,2014,(5):22.
[11][19]熊庆年,代林利.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异[J].高教探索,2006,(1):43、42-43.
[13]王世岳.一次教学功能最大化的尝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49-50.
[14]周继良.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历史嬗变与价值追求——基于中世纪至2013年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5,(3):137-146.
[15][德]乌尔里希·泰希勒.迈向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国际比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体系[M].肖念,王淀蕊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97.
[16]孟倩.大学内部治理的分权与制衡——博弈论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4-39.
[17]张维迎.大学的逻辑(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8.
[18][美]罗纳德·G.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M].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8.
[20]杨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迁的比较研究——以中日两所大学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70.
[21]史彩霞.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困境——对中国大学治理结构低效率的制度解读[J].复旦教育论坛,2006,(5):50-56.
[23]仰丙灿.学院自治: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J].复旦教育论坛,2015,(5):19-23.
(责任编辑:赵晓梅;责任校对:徐治中)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Mode,Motivation and Content
HE Shutong1,HE Yuan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7;2.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1166)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which is the result of an equilibrium state through a game between external and internal multiple stakeholders within a university,has always been in a dynamic balance and slow change.From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reform mode,th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s follows:the internal revolution type,the internal evolution type,the external infiltration type and the model transplant type.From the viewpoint on the dimension of reform motivation,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Internal motivation often plays the role of accumulation,and external motivation can lead to the qualitative leap.If we focus on the reform content,the three key contents of the reform on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as follows:seeking the balance point of university internal longitudinal power distribution,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horizontal power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highest power subject.Th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m on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It ca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university;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change;reform
G647
A
1674-5485(2016)11-0001-08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地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2015/01/52)。
何淑通(1980-),男,江苏新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何源(1978-),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