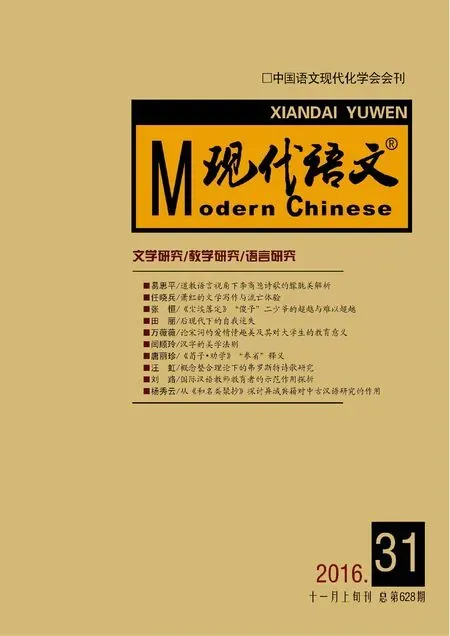谈文学作品中的移情
○王艺馨
谈文学作品中的移情
○王艺馨
情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所共有的特征之一,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当然不会例外。有情感的物种并非都尽如人类,但是就人类来说,却一定是有情感的。人不光有情感,而且情感还颇为丰富,有喜悦,有悲伤,有担忧,有畏惧,有惊恐,有愤怒……并且人类也不仅仅局限于玩味自己的情感,而是给世界万物都赋予情感。针对这类现象,学术界提出了“移情”的概念,所谓移情,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把主观感情移入客观事物”[1]。它自从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手法被提出之后,就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本文就试着从它的本质、表现、以及形成的内在根源来对它进行探讨。
一
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审美心理活动,它最早由德国美学家R·菲舍尔提出,之后的立普斯在他的《空间美学》一书中对“移情”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所谓“移情”就是我们的情感外射到事物身上去,使情感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统一的境界。英国美学家V·李在《美与丑》一文中提出,移情是自身对经验的反思,移情作用是长期的观念、情绪和意识积累而形成的心理过程。德国J·伏尔凯特在《美学体系》和《审美意识》两书中认为,移情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心灵活动,是审美观照中最重要和最有特征的一个方面。而中国的移情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诗学之中,认为移情并不止于人情外射于物,而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移情于物,自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一是情与物同,心物交感,情境交融,意境自然天成。显然,中国的移情思想较西方更为全面,但却在无形间渗入了哲学齐物的思想。近代美学大家朱光潜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认为,移情是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外物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了解外物,它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既然谈及移情的本质(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跟“现象”相区别,对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就不可能超出人的情感的范畴。总的看来,它是人类在思考情况下的产物,是一种自然不自然,自觉不自觉的情感外泄。
二
移情作为情感外泄的产物,它便会牵涉到到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人和物主客交织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移情的主要表现。具体来说,应有三个方面:
第一,以己度人,人与我遂成知音。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和两张面孔,因此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情感也肯定会不尽相同。我们对于他人,对于前人,特别是已故的前人的理解总是根植于他的一些遗迹和遗留的文学著作。苏轼说的“其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对于作品的理解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我们感受着作品中的崇高、悲壮、静穆、宁谧,就用以指明创作者的创作风格、作家风格。然后进而指出创作者的个性,是书生意气,还是丈夫情怀,亦或是柔中带刚,刚中兼柔。其实我们并非创作者,我们很难彻底明白创作者究竟是什么意图,有什么情感。只是从他的作品中凭着主观感性会知一二,就给他冠以高拔、低劣,盛世之音、萎靡之作。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当然要首推李商隐。他的《锦瑟》一诗,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爱情诗,“锦瑟”就是令狐楚家的婢女的名字(见刘攽《中山诗话》);有人认为是悼亡诗,是为追忆他死去的妻子王氏而作(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认为是咏物诗,瑟有适、怨、清、和四种声调,诗的中间四句每句各咏一调(见《缃素杂记》);也有人认为是自伤身世之辞,是晚年追述生平之作(见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然而这么多的情感竟会是李商隐在这一首诗中都要表达的吗?恐怕不是。他本人或许只是借以抒发某一感慨,但由于读者多了,过于工于词句了,便产生出这诸多的情感来。其实这众多的情感是读者所怀有的,并不一定为李商隐在那一刻所同时涌现出来,然而由于欣赏者的感知差异,就说李商隐在诗中表达某某主旨和情感。这样我们便把自己的情感移到他人身上了。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莎士比亚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但每个读者又都留有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因为作品是作家创造的,所以每个读者就用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去比附作家心中的哈姆雷特,都认为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就是莎士比亚心中的哈姆雷特,这样莎士比亚的心中就被填充了数以千计的哈姆雷特。情感就从自己身上转嫁到他人身上了。
第二,以己度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例证。杜甫在《春望》中写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它的一种解释为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亦惊心。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评曰“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这可以说是以己度物的一个最好范例了。另一个就是在《庄子·秋水》中广为人所熟知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庄子所以能体察到鱼的快乐,这也是由于他把自己本身的快乐推及到鱼。其实鱼本身快乐与否或不可知,但庄子是快乐的却一清二楚。倘非如此,鱼或许就该是忧愁的了。欧阳修在《蝶恋花》中写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至于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引之为例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2]他这里的有我之境就是人主观的赋予客观事物以人类的喜怒哀惧,从而借外物含蓄而不直接的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情感。“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点‘清苦’”。[3]“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蜡烛信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这些都是表现自己主观情节的最好诠释。
第三,以物度人,物与人和谐统一。自然界具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色彩,形体和图画。根据它们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可以粗略的把它们区分开来。如动物有猪、马、羊、牛、鸡、狗等的不同,植物有黍、稷、麦、桑、麻等的差异,颜色有红、黄、蓝、白、黑等的区别,文学有诗、赋、词、曲、小说等的划分……然而音乐的高低、长短、急缓、宏纤等带给人们的除却它本身的旋律外,还有音乐中流淌着的崇高、激情、快乐和忧伤。《命运交响曲》听起来使人精神振奋,心潮澎湃,《小夜曲》则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自然山川的挺拔、宽广,让观赏者心旷神怡,冶游其间,忘乎所以,仿佛感受到青山的厚重、深沉和坚韧不屈,绿水的淡泊、清静和虚怀若谷。青山和绿水都俨然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人也俨然成了青山绿水。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无生命的物体是没有情感的,但却有它的运行规律。花开花谢,四季轮回,月圆月缺,这些表现出来的不同勾起了人类潜在的情愫,花开时满心欢喜,花谢时满腹愁容。正是许许多多的不同成为激发人类情感的源泉,从某一点上说,这是自然事物在把同的特性移附于人类的情感。于是才有了这么许多牡丹的富贵,莲花的高洁,腊梅的傲骨。
三
移情的外在表现由于主客间的相互关系较易为人所感知和理解,但形成这一表现的深层根源却很复杂,也很值得深究。
首先,世界是一个联系的世界,人与人、人与物都时时相通,这就构成了移情作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正是有了这普遍的联系,人和人、人和物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倘若世界中没有联系的存在,人与物便都是这星球上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孤立的点。再没有了复杂的联系,当然也不会有情感的需要。人凭借着联系感受到自己和万物的存在,自然也就会时时倾泻出自己的情感,有了倾泻便会溯求情感的载体,或人或物,都会不自觉的充当情感的对象。因为联系,人也能观察到自然的某种曼妙,从而引起自己的同感和共鸣,激发美感享受,在感受万物的同时早已与物合而为一,物的特性为人所具有,人的情感也为物所具备。普遍的联系沟通着人与人,人与物,让人显得多情,而让世界也充满了情意。联系的世界造就了情感的世界,让整个世界不再沉寂,到处都充斥着真纯善美。
其次,人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会对世界万物有自觉不自觉的感知,移情是人感知自然社会的真情流露。情感为有生命的物体所独有,而在这所有的物体之中,人毫无疑问处于最高层。所以谈及移情必然会考虑到它的重要组成——人的存在,移情必须以人作为考察中心。人是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一员,但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多元的,真实的世界有时无法满足情感的需要,便幻想着也存在一个多元的、复杂的并且充满情感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中,万物可以和人一样拥有各自的情绪,也可以共同承担着寒潮、风雷和霹雳,分享着流岚、雾霭和虹霓。但是究其根源,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人在思维中的幻象,是人情外化的体现。多情的人类不甘于独自高歌的寂寞,倾注了世界以情,欢快时处处都明亮鲜美,万物都在微笑,悲痛时处处都弥漫着灰色和阴沉,万物都在垂泪。水满则溢,当人类自身怀有过多,也承担过多的时候,便会不自觉的向外逸散。于是万物都得以拾取人类的情感种子,接受人类情感的馈赠。人的多情让整个世界在美的同时增添了一份情。
最后,自然万物各有特色,丰富多姿,容易勾起人类的情感,达成物我同一的境界。杜鹃的叫声凄切,让人联想到国仇家恨,身世浮沉,不胜悲凉;黄鹂叫声婉转,悦耳动听,仍人沉溺其中,感受到欢欣和喜悦。满园春色,勃勃生机,欣欣向荣,使人留恋,自然想到青春的美好;满城秋景,万物凋零,北风萧瑟,金铁皆鸣,一派肃杀的情景,更容易让人悲叹穷困孤苦,风烛残年,功业未竟。没有人听到杜鹃声会感到愉悦,也没有人会因听到黄鹂的鸣叫而悲伤。韶华春光,很少会有人独作愁苦,满目秋景,也少有人闲适喜悦。这些原本毫无必然联系的物象,却能引起人们相同却很少相异的感觉,除却人类情感的相似性外,还应归结于自然世界中的一些物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特性,才会引起人们迥异的情感,而每种情感和自然的物象之间总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情感可以用不同的物象来共同表现,这也就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论及的意象问题。这些意象的组合契合了作者的心境,在作品中便会呈现出统一的整体和谐美。另外同一物象也可以因作家情感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陶渊明笔下的菊花和苏东坡笔下的菊花各有特色,陆放翁眼中的腊梅和毛泽东眼中的腊梅也性情各异,这正是同一事物不同风貌,不同情感的体现。但每种情感又都与彼时的事物在时间和逻辑上达成圆融的统一,物我的相溶。事物呈现出的特征是诱发移情的因素,而事物的差异又能呈现出各异的情感,是物的各具特色给了人们以丰富的情感表现,成为情感的接收者和体现者。
人类的移情装点着整个世界,它固然是人类单向的,一厢情愿的,是人类为释放出自己的情感而采取的尝试。但它让整个世界除却美的享受外,又多了一份情的可贵。正因为有了移情,整个世界才会呈现出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才会形成真、善、美的完整统一。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4页。
[2]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页。
[3]朱光潜:《谈美》,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页。
[4]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页。
(王艺馨 山东省泰安市泰安一中 2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