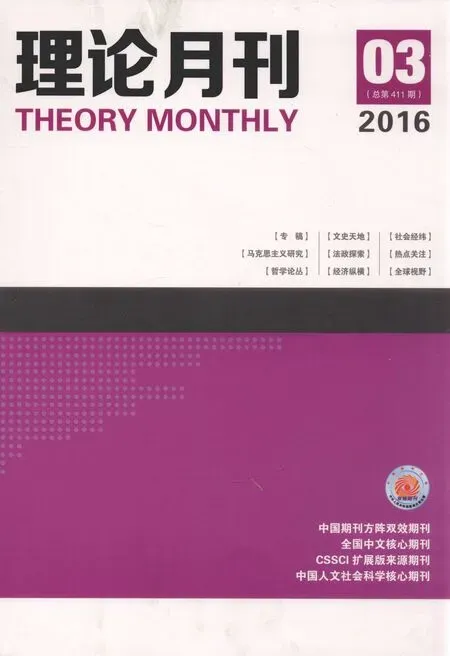胡绳理性主义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
□韩爱叶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天津300070)
胡绳理性主义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
□韩爱叶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天津300070)
[摘要]胡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参加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各种论战。胡绳对新儒家冯友兰的理性观进行了批判,指出道德需要经过理智的审查才能进入理性的境地。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西化派胡适的实用主义理性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胡适思想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他认为超越五四才能继承五四。胡绳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理性和自由,在写作上形成了彻底的“理性主义”的风格。
[关键词]胡绳;理性主义;新启蒙运动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4
1 胡绳与“新启蒙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
1936年秋,艾思奇、何干之等左翼人士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爱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彻底的新理性主义,从而“扬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
胡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在1935年到1948年期间写了大量文章,参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各种论战,并形成了彻底的“理性主义”的写作风格。胡绳自1935年下半年起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及写作,他在1935年到1948年期间的文章大都收录在了《胡绳全书》第一卷。在这个时期,胡绳已经表现出写作的“理性主义”风格。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精神,胡绳做过以下描述:“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传统文化中间,我接受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接受了一种对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思考,进行逻辑的思维,加以论证,这样一种我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精神。这些使得我多少能够抵制一些错误,所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叫《理性与自由》。简单通俗地说,理性就是讲道理。自由当然不是说绝对自由,是跟着正确的走,要有权力自己来选择。”[2]《理性与自由》是胡绳1946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于《胡绳全书》第一卷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胡绳认为“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是他这本文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思想文化评论”一辑,胡绳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这一辑的内容,总的说来,贯穿着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3]本文主要以《胡绳全书》第一卷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为依据,揭示胡绳的新启蒙思想以及他的理性主义风格。
2 对冯友兰道德理性的批判
胡绳认为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非常接近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理性与自由是贯穿于启蒙思想运动的基本精神。黑格尔说:“理性和自由永是我们的口号。”[4]康德对“什么是启蒙”做了如下回答,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5]“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6]可见,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唤醒人们有勇气独立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使人们认识到必须破除阻碍人们运用自己理智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使人们认识到只有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社会变迁的实质是文化的现代转型。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石。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胡适高举实用主义理性,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实现中国的文化转型。新儒家冯友兰高举道德理性,试图在捍卫中国固有文化的前提下对东西文化进行调和折中。胡绳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性,基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对冯友兰“道德理性”和胡适的“实用理性”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理性和自由。
冯友兰把理性分为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认为道德高于理智。他在《新世训》中认为理性有两重维度,即道德和理智。他写道:“所谓理性有二义:就其一义说,是理性底者是道德底;就其另一义说,是理性底者是理智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道德的理性,有理智底理性。有道德的理性,所以他能有道德底活动。有理智的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底活动及理智的活动。”[7]冯友兰把道德置于理智之上。他说:“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注重人的道德底活动,亦注重其理智底活动,或可问,如此二者有冲突时,则将如何解决?于此,我们说,专就人的道德底活动及其理智底活动说,此二者有无冲突,虽是问题,但即令其可有冲突,但在我们所讲底生活方法中,则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所讲底生活方法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底。”[8]可见,冯友兰把道德看做是永恒不变的,认为道德高于理智。这样理智受制于道德约束,而道德却在理智的审视之外。
胡绳指出,道德要接受理智的审查,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任何道德律令都须经过理智的审查,才能进入理性的境地。道德是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在经过理智的审查后,理性的道德维度就和理性的理智维度统一起来,道德的理性同时就是理智的理性。他指出:“要根据现实的社会生活来判断某种道德规律之是否合于理性,那就只能靠理智的审查。”[9]冯友兰《新世训》一书,共有10篇,第一篇就是“尊理性”。冯友兰把道德置于理智之上,道德偏离了理智的审查,道德也就偏离了理性。胡绳认为,我们不仅要尊理性,也要尊理智。因为理性的就是理智的。而尊理智就必然包含着“重客观”。只有重客观而尊理智,才能真正做到“尊理性”。一切主观的产物,都须经过理智的审查。因为只有经过理智的审查才能把握客观现实的真相。“不仅道德须经过理智的审查,而且对于一切主观的产物——感情、欲望、意志、信仰等都应该承认理智有加以审查的权力。”[10]于此胡绳得出“所谓理性,在我们看来,正确的解释就是理智的综合。”[11]
胡绳主张道德等须经理智的审查,并不是主张取消道德。他写道:“我们以为,在健全而完善的生活中,人是以重客观为前提,而在理智的光下使感情、意志、信仰、道德观念这一切都互相和融而像春雨下的百草一样一致地欣欣向荣。”[12]胡绳主张尊客观,并不是意味着主张灭绝主观;主张尊理智,并不意味着主张以理智取消感情、意志、信仰、道德观念等等主观的产物。他号召人们要在理智的统帅下去除琐碎、狭小、无意义和虚伪的感情,发展博大、深厚、真实的感情。这种经过理智审查的感情不但不会妨害理智,而且是对理智有益的补充。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把低级的感情提升到更高级的感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情感和理智都不能抽象地谈论,都需要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弄清楚其产生的经济的、思想的、政治的等等原因。当一个社会阶层在历史上处于进步的地位时,它的理智和情感是一致的;当一个社会阶层处于没落地位时,它的理智和情感就会冲突,这个阶层会抬高个人主义的情感甚至失去理智,走向非理性主义。感情有低级和高级之分。感情越提升越和理智的内容接近,并最终达到一致,这样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所以,胡绳认为,那些愿意追随顺应时代的新的阶层的人,就要扬弃旧时代残留的感情,在理智的审查下在生活的实践中培养新的感情。
关于理性,马克思有过如下表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13]马克思认为理性向来就存在,它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能把理性当成衡量现实的尺度,而应该从社会现实出发来引出不同形式的理性。这里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的思想:“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4]作为西方启蒙思想孕育的产儿,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这就是把现实生活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把实践作为检验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尺。
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绳正确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指出这种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性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他写道:“破除盲从与迷信,推翻独断的教条,从现实中确立远大的理想,在实际中作实事求是的努力,这是代表着一种什么精神?是清醒的现实的理性主义的精神。”[15]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理性主义,是彻底的、科学的理性主义。这种彻底的理性主义要求科学,科学要求实事求是,所以必须反对迷信。彻底的理性主义要求思想的自由,所以要反对独断。彻底的理性主义要求合理的思考,这就是要求逻辑与现实的一致,这样才能根除愚昧。在民族解放的战争年代,胡绳大声疾呼“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精神,坚持思想的自由发展,矜持合理的思考,从这里培植我们远大的理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一切盲从和独断,打碎一切反理性主义!我们一面要排斥因袭的传统的成见,一面要排斥西方腐败思想的传染,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充分发扬清醒的、现实的、科学的理性主义。”[16]
3 对胡适实用主义理性的批判
胡适是五四启蒙思想者的代表之一。对于胡适,当时思想界或者对其完全抹煞,把胡适作为个人主义、买办的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把他看做一条“死狗”进行否定和批判;或者把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最好的思想家、新文化的创始者一味颂赞。胡绳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站在实践的立场上,没有运用历史主义的视角,没有对胡适的启蒙思想进行辩证地分析和批判。胡绳在多篇文章中对胡适的启蒙思想进行了辩证地批判。正确评析胡适的启蒙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五四启蒙思想。
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胡适呼唤人们过一种“理性的生活”,对于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追问一个“为什么”。胡适还倡导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使人生观建立在近二三百年科学常识的基础上。胡适提倡用理性主义的生活反对封建礼教盲从的生活,提倡用科学的人生观反对玄学的命运论人生观,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胡绳所评价的:“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17]
然而,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胡适的思想本质上包含着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中国的启蒙思想者从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拿来了“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但是并没有达到西方启蒙思想的高度。西方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和盲从,用自然科学战胜了宗教的信仰。不仅如此,西方启蒙思想家还借助“理性”和“自然科学”达到了彻底的无神论和机械唯物论,形成了唯物的宇宙观。依据“理性”,西方启蒙者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真理。胡适并没有形成唯物的认识论,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他说:“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18]胡适把真理看做供人使用的工具。
胡适思想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他常常回避世界观中的根本问题。对于“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胡适认为“简直是废话”,是“不成问题的争论”。对于“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他认为“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19]
胡适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实用主义方法论让胡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胡适关注的只是一个个零碎的、枝节的问题,只注重具体的事实和问题,而不承认问题的“根本解决”。胡适所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实用主义方法论使胡适所看见的都是孤立的事物、局部的问题、表面的现象,而看不见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看不到事物现象里面的本质。所以,胡适看来,打骈文古文就是打骈文古文,打缠小脚就是缠小脚,打“孔家店”就是打“孔家店”,而没有看到这些行为和反“封建主义”的联系。
胡适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最终体现为实践上,表现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的“好人政府”主张,他向溥仪跪拜的行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者的胡适,由于其思想的不彻底,最终向封建势力妥协,沦落为一个保守的学者。可见,胡适以“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为标志的启蒙思想是不彻底的。因此,胡绳呼唤“让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科学方法论者立足”。[20]
胡适所宣扬的理性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理性。实用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胡绳主张人们应该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现实,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从运动、变化与发展中观察事物,要求人们用联系的观点分析事物。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是和实践密切相连的。人们在实践中丰富思想,又以思想指导实践。
4 胡绳论五四启蒙思想:在超越中继承
胡绳认为中国启蒙运动起始于戊戌变革运动。虽然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君主立宪的要求没有实现,但是在文化上却表达了反封建的思想诉求。康有为不仅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挑战了封建权威,而且在《大同书》中构想了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谭嗣同用朴素的唯物论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伦常名教”作了斗争。梁启超的《新民说》描述了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和国家观。虽然戊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模糊地意识到“变法图强”的需要,模糊地提出反封建思想的各种要求,在政治上提出君主立宪的口号。但是,戊戌时代的启蒙者始终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架构下来构建新文化的。他们的思想文化活动和封建思想有着各种联系,并没有彻底反对封建思想。他们的思想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一样,把群众隔离在外。
胡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反抗斗争,助长了“人的发现”,助长了理性的发扬,在帮助人们建立理智的思考和独立的个性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胡绳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各种问题进行的判断都是建立在直接的感觉上,而不是建立在稳定的理论基础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石。在胡绳看来,这个坚实的理论基石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论与动的逻辑”。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是非常局限的。五四时期所谓“人的发现”只是包括少数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排除在外的。这就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弱点:文化与人民大众的隔离。[21]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起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写道:“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22]胡绳认为,共产党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仍然要提倡民主和科学。但是,必须把实事求是作为科学的基础,把人民群众作为民主的基础。新启蒙运动仍然要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但是个性解放不应是少数人的个性解放,而是绝大多数人民在共同生活中自由发展个性。胡绳指出:“实事求是的科学,人民大众的民主,民族实践生活的需要,三者结合,才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23]
胡绳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必须实现人的现代转型,培养现代人。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束缚了个性的发展。五四启蒙思想家号召个性解放,呼唤人的觉醒,促使了“人的发现”。这正是鲁迅在1907年说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24]一个又一个人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的觉醒,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巨大力量。唯有发现了每个个人都能、也都应有其独立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有其独立的生活价值,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创造出现代的新人。共产党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扬弃,集体主义并不抹煞个性,集体主义依赖于每一个人自己能力的展开,依赖于每一个人个性的张扬。五四运动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中国青年和广大人民的个性发扬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但是,五四“人的发现”很少甚至没有包括农民。如果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个性不得解放,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胡绳指出,今天我们要继承“五四”的事业,就必须超越“五四”,只有超越了“五四”,才能真正继承“五四”。在胡绳看来,“民主与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民主事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科学事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研究的发展);另一层意思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包含反迷信、反神权、反专制、反盲从、反武断等等含义。胡绳认为,五四所提倡的主要是“民主与科学”精神,主要立足于破。现在要超越五四,不仅要对旧事物破,还要对新事物立。要超越五四,不仅要培养“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还要建设民主与科学的事业。胡绳在1989年5月5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呼吁;“我们在继续促进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同时,还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破除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中。对于习惯势力,不能靠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而要通过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通过教育来解决。”[25]要继承五四的事业,我们不仅要继续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继续破除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而且要超越“五四”。不仅要破,而且更要立。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没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不可能完成现代化事业。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的培养也需要科学和民主事业的发展。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才会不断地提高和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胡绳积极响应新启蒙运动的号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对当时的各种旧有思想和反动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理性主义”写作风格,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了理性和自由。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7]胡绳的文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的理性主义品格,唤醒了无数遭受压迫和奴役的劳苦大众。
参考文献:
[1]俞红.论新启蒙运动[J].浙江社会科学,2000,(6).
[2]胡绳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3.
[3][7][8][9][10][11][12][13][15][16][17][19][20][21][23][24]胡绳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24,123,124,125,126,126,127,92,100,19,13,19,3 09,371,754.
[4][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M].苗力田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8.
[5][6][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2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
[1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9.
[18]郭建宁,张文儒主编.中国现代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3.
[22]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引论13.
[25]胡绳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4.
责任编辑刘宏兰
作者简介:韩爱叶(1974—),女,河南汤阴人,哲学博士,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讲师。
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32801)。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3-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