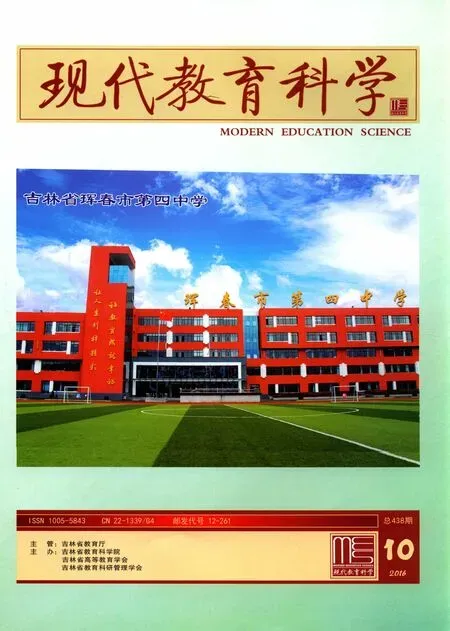地方教育集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
崔岐恩,张晓霞
(岭南师范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地方教育集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
崔岐恩,张晓霞
(岭南师范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简政放权”未能真正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却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教育权力,形成了地方教育集权。地方教育集权并不具备合法性,根据有三:教育政策本身的不足、教育权利归属不明和权力越位、地方教育权的非独立性和条件性。地方教育集权也不具备合理性,根据有二:地方政府未能实现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未能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权。重构地方教育管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应从重新分配地方政府教育管理权限、转变地方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落实学校的法定权利等三个方面着手。
学校办学自主权 地方教育集权 合法性 合理性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13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借鉴了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改革模式,结合了当时所施行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简政放权”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简政放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二是政府向学校放权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从政策文本看,后者才是改革的重点。《决定》指出,政府对学校尤其高等学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令学校丧失活力。现在一定要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切入点,通过简政放权、扩大自主权提升学校的办学活力。而实际上是随着地方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大的教育财政责任,其管理权也在逐步扩大,形成了“地方教育集权”现象。这种趋势似乎与《决定》本意背道而驰。
因此,地方教育集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地方教育集权既非合法、又非合理,如何改变就值得深入思考。类似问题在国外也存在,如美国公立学校管理中的“市长控制”现象[1],实质上就是一种地方教育集权,不过由于中美在人事权、经营权、财权以及拨款方式、管控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难以复制。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中的同类现象还未能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希望笔者的探讨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地方教育集权的合法性分析
根据哈贝马斯“合法性意味着被认可的某种政治秩序有着一个好的根据”[2]的观点,一种现存的制度能有“好的根据”,也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好的根据”包括道德的、法律的和习俗的“根据”,所以,一种制度要被承认需要具备道德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合法性,至少也要具备其中的一种合法性。同时兼备三种合法性的制度是最理想的,也是运行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地方教育集权在法律与政策方面的合法性。
从法律和政策文本看,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中的地方集权有一定的依据:(1)《决定》提出简政放权:“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2)《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3)《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在教育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4)《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从上述法律和政策文本看,教育行政管理中的地方集权似乎具有合法性,有直接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但是,这种认识经不起仔细推敲。一是政策文本的缺陷。张树义教授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称为“主体一元化社会”——社会尽管存在着众多的个人和组织,但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都程度不同地隶属或依附于国家机构,由国家机构对其发号施令,国家称为唯一的主体[3]。这种体制下,个人服从于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服从于政府,地方服从于中央。城市的改革从国有企业开始,最初的措施是扩权让利或进行利税改革,但当时尚未全面推行两权分离改革,因而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和利并不十分清晰。参照国有企业改革的某些做法,《决定》提出实行“简政放权”,但同样未能理清楚地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笼统地规定将基础教育管理权交给地方。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对各级政府间的权利分配做了简单规定,但《纲要》也没有指出公立中小学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提及地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义分配。由此可见,《决定》和《纲要》都明确规定实行“简政放权”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但政策文本对学校拥有哪些“自主权”则语焉不详,导致人们在理解上产生偏差,从而使政策的基本精神得不到落实。二是权利归属不明和权利越位。劳凯声教授指出,应该明确公立学校的举办者、办学者与管理者三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政府作为公立学校的举办主体、教育事业的管理者,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也要保证公立学校的合法权益,改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真正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4]。但现实情况却是,地方政府的举办者责任履行不到位,同时也侵犯了公立学校办学者的权利,从而形成了所谓“缺位”与“越位”并存的乱象。邬志辉等学者也认为,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政府处于优势地位,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行使不当给学校和政府本身都带来负面影响。应该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和权力,摈弃“全能政府”观,树立“有限政府”理念,放弃“不该管”的职能,强化“该管”的职能[5]。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举办者责任和学校监管者责任,而不是深入学校内部。《教育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教育工作”。“主管”是指宏观上的管理,而非微观干预。而第二十八条则明确规定了九个方面的学校办学权利,涉及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所以,与学校相关的权利主体有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相应的权利也包括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教育法》赋予学校一系列办学权利,意味着法律明确了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不得侵犯学校办学自主权。三是地方教育权的非独立性和条件性。要理解教育权,首先要厘清何谓权利。夏勇教授认为,权利概念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利益、要求、资格、权能和自由,可以其中的一个要素为基础,辅之以其他要素对“权利”进行界定[6]。据此观点,教育权就是教育主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根据自身意志作出的作为或不作为,同时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能力或资格。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结构,是由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组成的。西方近代教育史上,国家之所以控制教育权,首先是为了打破教会的教育权威,使教育服务于世俗政权。其次是为了培养有初步文化基础的公民和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培养有一定知识的劳动力。总而言之,国家掌握教育权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如斯特赖克所说:“因为学校教育能够服务于某些重要的公众价值(即共同利益),所以,国家就拥有了建立公立学校的权力。”[7]因此,地方教育权并非独立的教育权利。四是地方教育权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宗旨,如果偏离或者不能实现公共利益,地方教育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根据。
二、地方教育集权的合理性分析
马克思·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别,认为形式合理性主要关涉手段和程序的科学核算性、技术可行性;而实质合理性则主要关涉价值立场和目的合法性。倾向于科学真理和技术路线的标准明晰而易于量化,故对形式合理性的认定比较客观、唯一。相对而言,实质合理性很难统一,往往会在政治权力、多元价值甚至民主自由等合法化主张下,给判定标准带来更大弹性[8]。
国家教育权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这种社会功能的发挥程度正是评估地方教育集权合理性的关键性指标。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有学者将教育的社会功能分为初级社会功能与次级社会功能。初级社会功能表现为受教育者的“文化形成”及其“群层”(数量和结构)状况;次级社会功能表现为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特定层面、特定领域)的运作状况。初级社会功能是“本原性社会功能”,而次级社会功能则是“衍生性社会功能”,后者依赖前者而存在[9]。因此,地方教育集权的合理与否首先要接受个体发展的检验,也就是看其能否有效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198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的本质属性,学界尚有分歧,有自由权说、社会权说、学习权说和发展权说。本文接受龚向和博士的见解:受教育权本质上属于学习权,是在自由权和生存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综合了两者的内容。受教育权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和学习成功权。学习机会权又包括入学和升学机会权、受教育选择权、学生身份权;学习条件权则可分为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教育条件利用权和获得教育资助权;学习成功权包括获得公正评价权和获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10]。受教育权体系中,需要政府履行积极作为义务的是学习机会权和学习条件权两个方面。本文从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选择权两个角度考察地方政府教育集权的合理性。
(一)从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看,地方教育集权不具备合理性
首先,教育的非均衡化发展损害教育机会均等。地方政府之所以应该成为基础教育的管理主体,在于它能推进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教育均衡发展,为每个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和速度上存在着巨大落差,而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在难以保证全国性的教育均衡发展的情况下,谋求县(区)内的教育均衡,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长期实行的教育非均衡化发展政策造成了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小学重点学校政策促使许多地方举全县(区)、全乡(镇)之力办好一、两所学校,将绝大多数的教育资源向重点学校集中,结果形成了层层重点的“金字塔”结构,普通学校和薄弱校则受到排斥和忽视[11]。其次,教育乱收费损害了教育机会均等。公立中小学教育乱收费的滋生和蔓延,也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教育乱收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教育乱收费问题,主要有生存性乱收费、垄断性乱收费和腐败性乱收费[12]。生存性乱收费和垄断性乱收费与许多地方政府掌握教育行政权力但不积极作为有直接关系。生存性乱收费源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而垄断性乱收费则与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有关。中央曾多次下文整治教育乱收费,最近更是下决心在五年之内解决此问题,但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笔者认为,教育乱收费的根源不在公立学校而在地方政府,在于他们是否积极履行教育法所规定的义务。再次,公立学校转制损害了教育机会均等。公立学校转制可谓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创举”,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作为,以制度化手段推动薄弱学校转制,创新学校办学机制,赋予部分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转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改革之路,堪比中国式特许学校。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制度保障和有效监管,转制实质上成为政府推卸财政责任、学校要求增加办学经费和改善教师福利的借口。公立学校转制浪潮中,部分优质学校为了追求金钱,也在不失时机地寻求转制。正如赵中建教授所说,这样的学校转制能为政府和学校自身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教育局的“钱袋子”[13],其结果必然损害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二)从受教育选择权看,地方教育集权不具有合理性
首先,否认学生和家长的(受)教育选择权。家庭教育权是一种源生性的教育权,先于国家教育权而存在。克里藤登认为,家庭教育权是一种基于血亲关系的权利,“父母在决定子女教育发展方向上有优先权利,这个论点的提出维护了几个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其中最明显的是,它维护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的自由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包括国家的不当干涉,并且使父母有机会行使选择正规教育或学校教育的权利”[14]。(受)教育选择权既是学生受教育权的内容,也是家庭教育权的内容。(受)教育选择权的实现,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但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履行义务,(受)教育选择已经成为了家长的一项额外义务。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政府以“就近入学”为由否认(受)教育选择权。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无论从法律文本理解,还是从法理角度分析,“就近入学”都是受教育者的权利而非义务,但该权利被许多地方政府曲解为学生和家长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家长对当地公立学校不满意,只能选择周边的民办学校,或者交高昂的“赞助费”进入其他公立学校,并承担相应的教育成本。其次,未采取有利措施保障(受)教育选择权。不同家庭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资本决定了不同家庭的教育选择能力。文东茅教授研究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及本人户口与教育选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与学生择校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优势群体有更多的教育选择自由和政策优势,而弱势群体则只能被动接受现实。教育常常被当做促进社会流动和推进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也被视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因此,就教育本身而言,它与社会公平并非线性关系,关键看教育的制度设计。作为(受)教育选择权的义务主体,政府应该保障每个学生都能选择适合自身并能使其受益的受教育机会。
三、重构地方教育管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地方教育集权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因而必须重构地方教育管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重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重新分配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权利责任,使教育管理的权责重心上移。二是转变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建立服务型教育行政。三是落实公立中小学的法定权利,使之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85年颁布的《决定》仍然有指导意义,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其关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不明朗,省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责任不够明确。科层制理论告诉我们,提高教育管理的权责重心是合理的。建国之后,我国建立起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公立学校系统,集权化、等级性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构成了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征。科层制理论认为,距离基层实践者越近的科层权威对实践的干扰越明显。法国学者克罗齐耶认为:“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明显地厌恶自己被上级支配和控制的处境。”[15]由于直接受制于地方政府,公立学校自主办学行为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如果在政府层级之间重新分配教育行政权力,将权力重心提升到省级或者地级市政府,结果会怎样呢?克罗齐耶指出:“等级关系似乎并未在面对面的关系上造成冲突和严重的感情问题。利益差别乃至观点差别使彼此没有直接接触的群体相对立。……紧张总是越过一级,无论冲突还是随指挥关系而产生的情感问题,都不会严重影响彼此过分隔阂的个人和群体,不会使个人及群体产生不愉快的相互碰撞。”[16]学校远离权力中心,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博弈,都能增加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还会减少学校之间的摩擦,因此应该将基础教育的管理重心提高到省一级行政机构。
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目的在于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17]。笔者认为,公立学校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因为公立学校是公共组织,公立教育是公共事业,政府是其最重要的依托力量。显见不争的是,管的很宽的政府必然不是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政府也受制于知识和信息的不足。但“小政府”也不一定是强政府。政府施政有力与否不在于其管理范围的大与小,关键在于能根据时代的需求适时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满足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的功能需求,也就是能够提供满足特定时代的功能性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因此,强有力的地方教育职能首先体现为举办充足的、优质的、均衡发展的学校。此外,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所留下的行动空间应该由谁来填补,比如转制学校和委托管理学校的行为监管、绩效考核以及公益性评价,即原为地方政府的管理者职能。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公立学校改革的现实问题,是市场机制、公民社会组织,抑或是公立学校自身?政府至少不应该忽视该问题——职能转变迫使政府放弃部分权力,但同时也会赋予政府新的职责,需要辩证地看待政府职能转变与公立学校改革之间的关系。
针对如何真正落实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学者们做了许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确立中小学的法人地位,这是被讨论最多的建议,也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二是实行中小学产权制度的多元化,这类建议属于市场化路径,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具有实践上的依据,比如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和股份制学校等。三是校长承办,政府制定质量标准,即由经验丰富的校长承办学校,政府或中介机构定期对学校进行绩效考核。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有助于提高公立中小学的效率和质量,如有学者发现,有效率的学校比薄弱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自主权受限是薄弱学校难以通过改革实现发展的根源。这些学者认为,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公立学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代理机构——学校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发展其专长、进行专业评定,仅是依据他人的意愿,代他人做嫁衣裳。这些学校并不能真正为自身发展设定目标[18]。因此,打破地方教育集权和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应该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向,但也要加强对自主办学行为的监管和绩效评估。
[1]曾晓洁.“市长控制”:美国城市公立学校治理新模式——以纽约市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2010(12):42-47.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4.
[3] 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
[4] 劳凯声.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3(2).
[5] 凡勇昆,邬志辉.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类型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4(01):27-33.
[6] 宋吉鑫,刘铁雷. 权利、义务、责任、约束——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0):54-58.
[7][14][澳]布莱恩·克里藤登.父母、国家与教育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64,179.
[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99-182.
[9]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98-399.
[10] 刘杰,时长江.公民教育权义观的分野与整合[J].教育评论,2014(06):24-26.
[11] 董辉.给择校热“降温”:从“内部治理”到“社会治理”[J].全球教育展望,2014(02):50-62.
[12] 范先佐.教育乱收费的类型及其治理——以基础教育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117-118.
[13] 文东茅.转制学校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建[J].教育发展研究,2008(07):31-34.
[15][16][法]克罗齐耶.科层现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57.
[17] 尚虎平.政府绩效评估中“结果导向”的操作性偏误与矫治[J].政治学研究,2015(3):91-100.
[18] 孙翠香,王振刚.“委托——代理”关系视域下的学校变革:问题及策略[J]. 教育科学研究,2013(08):40-45.
(责任编辑:刘新才)
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Local Education Centralization
CUI Qien, ZHANG Xiaoxia
(LingnanNormal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524048,China)
Devolution doesn’t broaden the autonomy of public schools, rather broadened the powder of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promoted the local education centralization. Local education centralization isn’t legitimate, there are three evidences for it: educational policies’faults, obscure ascription of right, and dependence of national right of education. Local education centralization isn’t rational, there are two evidences for it: regional governments haven’t assured the equal right of education and the right of educational choice.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re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lo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redistribute the powder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transform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assure the legal rights of public schools.
school running autonomy; local education centralization; legitimacy; rationality
2016-05-26
广东省哲社项目“教师价值品质研究”(项目编号:GD13CJY04);广东省教科项目(项目编号:2014GXJK119);广东省教改项目(项目编号:GDJG20142380);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ZW1303、QW1308);岭南师范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计划资助项目。
崔岐恩(1975-),男,陕西勉县人,博士,岭南师范学院粤西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张晓霞(1976-),女,陕西西安人,岭南师范学院教科院讲师;研究方向:教师专业发展。
G520
A
1005-5843(2016)10-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