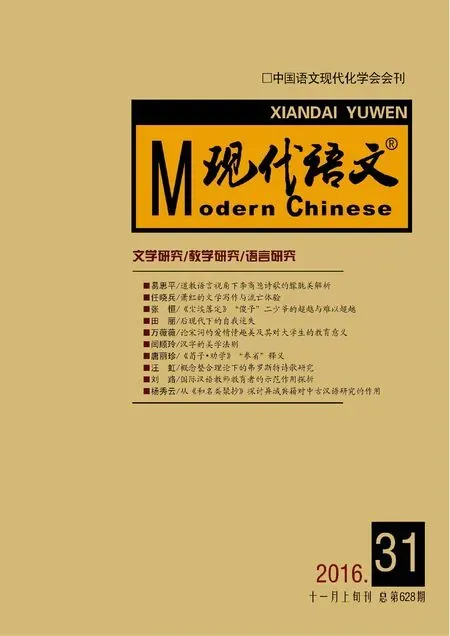萧红的文学写作与流亡体验——以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任晓兵
萧红的文学写作与流亡体验——以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任晓兵
流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借助写作的方式寻求对自我流亡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无家情境中心理上“在家”的慰藉、对自己逃脱种种破碎、断裂生活状态的安抚。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与其流亡的生命体验相随,其文学活动始于自我流亡,然亦终于自我流亡;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流亡话语,“流亡”成为其写作最基本的叙事动机和叙事主题。然而任何流亡话语都是一种隐含着多维度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话语形式,个体的发声可以被看作是一类人的发声,从而使个体性的话语演变为公共性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萧红在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与文本表现,亦是如此。
流亡 萧红 文学发生 流亡话语 公共性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
流亡(Exil)作为一个话语符号,它同时也意味着逃亡、畏避、放逐、补救以及避难等;作为一实体行为,它是人类个体或群体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与自己的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过去割裂,处于一种生命断裂的状态。作为人之个体或群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流亡”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意味着“(流亡者)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存体验每每使得流亡者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存在和精神情感上的双重创伤。这又即如萨义德所言说的另一句话:“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2]流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论现象,无论中外,自古即有;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就是对这种生存论现象的文字记载与叙述,即流亡话语。“流亡者在自己的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这样认为,而历史上的情境也高度验证了阿多诺此番言论的正确无误,诸如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荷马史诗《奥德赛》,我国先秦时期爱国主义抒情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等等,不一而足。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范畴中,有一个语词概念“认同”,它指的是“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4]。对于处在流亡生存体验中的流亡者而言,其写作活动的终极目的即是寻求对自我的“认同”,以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生存论上的安全感和历史感。更具体地阐述,这样的“认同”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一种主体性的反思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主体关系中生成,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最终扬弃他者、回归自我的过程。其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需求具有生存论的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归属感是将个体连结为族群的重要心理指向。这即如鲍曼所言说的:“‘共同体’意味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5]其三,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话语的影响,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萨义德曾说:“人没有国家或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不被任何国家主权或制度保护,过去除了留下苦涩、无助的悔恨,别无意义,现在则无非日日排队、满怀焦虑地寻找生计,还有贫穷、饥饿和羞辱——凡此种种凄凉,我也是经由她而戚戚共鸣。”[6]类似于具有这样一类人的生命存在体验,都是流亡者的生命体验,这些人都会产生一种认同上的自觉。
因为对于大多数流亡者而言,“流亡”对他们来说绝对就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处境;流亡者的空间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他们既在群体之内,然而又在群体之外。相对于任何限定在边界内的社群来说,流亡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因此,流亡者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7]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流亡者一方面既没有失去对自我“家乡”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没有在新的不断变动的流浪环境中被完全同化而失去自己的认同意识。基于以上这些源与流,流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借助于写作的方式来寻求对自我流亡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无家情境中心理上“在家”的慰藉、对自己逃脱种种破碎、断裂生活状态的安抚。
一、流亡者萧红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8]说这番话的是萧红,一位文学创作活动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萧红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此番言说,清楚地表明她具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身份符号标码:流亡者。从最初的1930年秋萧红因逃婚而首次离家,萧红即开始了自己短暂生命历程中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涯: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再回到上海、武汉、临汾、西安、再回到武汉、重庆,直至1942年最后的客死之地香港。
1911年6月萧红出生在关外偏远松花江畔的一座小城——呼兰县城。萧红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男性形象是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萧红的父亲是封建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一类知识分子,其思想有着明显的双重性。依幼年萧红的心理感受,父亲的形象总是那么面目可憎:“父亲常常因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和疏远,甚至于无情。”[9]萧红9岁那年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娶,这使得萧红与父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10]任何人童年时的心理都是单纯的,不懂天高地厚,都会用自己的性情对亲人做出审视与评判,从此,“父亲”在萧红的心理就被定型:要么凶神恶煞,要么缺失。萧红童年时期唯一的欢乐来自于祖父。这位童心未泯的老头对萧红的出生喜出望外,视其为掌上明珠:“等我生下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11]祖父是萧红在童年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亲情关爱的核心,对萧红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2]祖父一天到晚在后花园中,萧红也从早到晚在后花园中,与自然对话,在自然之中无限遐想。“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13]从童年时代萧红的眼中看去,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这些都使得萧红内心充满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祖父在给予萧红爱和温暖的时候,也给予了萧红最初以古诗词为主的启蒙教育,这使得萧红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对萧红而言,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祖父的去世,彻底斩断了萧红与呼兰县城、与那个没有给予她温暖和爱的父母家的牵连纽带,使得萧红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流亡之途。萧红自己是这样言说此种情境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从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14]
人类童年时代的成长体验会转化为一种记忆符号,沉淀在意识深处。当进入成年阶段之后,一旦遇到恰当的外界激发点,这种记忆符号便会以某种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故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15]童年、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和老祖父的离世均在萧红的心里永远播下痛苦的种子。因此,当孑然一身处在社会上的时候,“平生尽遭白眼冷遇”,当再次身处现实生活种种不幸境遇的时候,萧红不得不让自己成为彻底的流亡者:肉体上的流亡——背井离乡;精神上的流亡——无所依托。因为流亡者在流亡生活中都会产生挥之不去的认同意识。都会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诸如写作来使得自己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历史感。一种对自我的反思。所以,对流亡者萧红而言,这也是她无法避免的处境与模式。这也即如学者王宁所言说的:“(流散作家)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16]
二、萧红的文学活动:始于流亡、终于流亡
萧红的一生都在逃亡,她始终让自己流亡在路上。她逃出了父亲的家门,北方的旷野,却逃不出战争与时代的灾难,逃不出女性的情感宿命。她的文学生涯始于流亡,却也终于流亡。萧红孑然一人艰难跋涉在战乱的尘世,跋涉在命运的生死场,跋涉在自身、人类、国家、民族命运的思索和表达中,在流亡飘泊中寻求自我存在的空间,寻觅一方可以自由飞翔的蓝天。“经验的唯一价值,因为它是痛苦的结果,为了痛苦,经验在肉体上留下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转变了”[17]莫洛阿如是说。正是在这种漂泊的孤独情境之中,受伤的心灵不甘于堕落,萧红意欲用情感的理念思考表达女性的流亡、人生的流亡,乃至人类形而上的精神流亡。
萧红的文学活动起始于1933年,小说处女作为《王阿嫂的死》。从这篇小说开始,到其写作于1941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的绝笔散文《九一八致弟弟》,期间萧红全部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其流亡生涯中完成的:成名作《生死场》写于青岛的流亡漂泊岁月中,代表作《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则写于流亡香港的战乱岁月中。即如萧红小说文本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样悲苦的人生境遇,在1942年的时候流亡中的萧红也在香港结束了自己凄凉悲苦的一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一个人遭遇挫折,而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过去失败的例子。他必须告诉自己:‘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不幸的。’并只选择能被解释为他不幸命运之例子的事件来回忆。记忆绝不会和生活的样式背道而驰。”[18]因此,在萧红叙述溃败人生生命故事的所有小说文本中,流亡都成为其写作最基本的叙事动机。
小说《生死场》中叙述的农妇形象王婆,是小说中唯一有感情的灵魂。她在婚姻方面大胆地摒弃了传统的思想意识: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好,她就带着孩子另嫁他人,而后又嫁给赵三,然而男人们却不断使她失望。但是王婆却坚韧地流亡生存在命运的“生死场”上。王婆最后服毒自尽了,和自杀的母亲一样,女儿的命运也是流亡的:“小女孩被爹爹抛弃,哥哥又被枪毙了,带来包袱和妈妈同住,妈妈又死了,妈妈不在,让她和谁生活呢?”[19]女儿哭了一场之后,只可以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金枝是作为女性命运流亡的形象被叙述的。她与成业在河边相会,在细雨的歌声中开始了自己女性情爱的悲剧命运之途,短暂的爱情体验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业并没有给予金枝想要的安全与稳定,伴随着金枝的则是怀孕的恐惧、母亲的打骂、别人的耻笑,最后孩子也丧生在自己男人的手中。后来为了生存,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对她的凌辱她流亡到都市,但是在那里依旧难逃厄运,不幸遭到了中国男人的欺侮,身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后她不得不转到了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想要去当尼姑,然而庙庵也早已空了,金枝又将能走向哪里去呢?《生死场》中的最后五节,甚至可以说叙述的是所有的人均离开故土流亡的主题:就连思想最保守的二里半也颠簸着瘸腿,投奔革命军去了。
流亡中的萧红渴望有“在家”的感觉,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1934年的时候,萧红与鲁迅一见如故。鲁迅给予的关怀与温暖,使萧红感受到犹如自己祖父般的温暖和爱。然而没过多久,萧红却与萧军出现情感裂痕,陷入新一轮情感的痛苦。心理学认为人类具有“情绪记忆”:“它以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为内容的记忆,引起情绪,情感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却保留在记忆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情绪,情感又会重新被体验到。”面对萧军情感的背叛,少女时代情感受弃的伤痛记忆成为一种激素,加剧了萧红此时内心的痛苦。她常想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理想的爱。“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因此我所想望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萧红无法排除心中的寂寞和伤痛,于是她流亡日本:“从异乡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何况送我的是海上的浪花,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流亡的遭遇,激荡着萧红将自己流亡路上对人生、生命与爱的新的理解再次诉诸文字。所以便产生了萧红堪为经典的小说文本《呼兰河传》等。小说中有如下的叙述:“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多半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景况,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呼兰河人死寂的生活状态,在放河灯的情景里复活了,感到人生漂流的悲凉。”[20]短短数语,萧红内心的流亡者情结尽显。在文本的第四章第二小节,萧红叙述到自家荒凉的院子中所住的一些流浪人物的形象与漂泊的生命形态:“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还住着一个赶车的。……”[21]文本的第六章叙述萧红本族一个特殊的家奴流浪汉“有二伯”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及其生命状态:“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动他的被子就从被角往外流着棉花,一掀动他的褥子,那所铺着的毡片,就一片一片地好像活动地图似的一省省的割据开了;……有二伯没有一定的住处,今天住在那咔咔响着房架子的粉房里,明天住在养猪的那家小猪倌的炕梢上,后天也许就和那后磨房里的冯歪嘴子一条炕上睡了。反正他是什么地方有空他就在什么地方睡。”[22]这些叙述,都毫无例外地描述着流亡的生活情境。由此可见,就是在萧红最为鲜明地彰显出她在流亡生活过程中渴望“原乡”的《呼兰河传》中,萧红的叙述都无法不去触碰“流亡”,毕竟流亡生活、流亡者的身份让萧红感受到了太多宿命般的生命裂变。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是如此的郁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然而啊,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23]然而,萧红注定被“流亡”,她再也无机会回到她那一旦她听到别人说起“家乡”,就立即会让她心慌的呼兰县城了,1941年的冬天已不再属于她,尽管那座小城里埋葬着她的祖父,那个给予她温暖和爱的老人。在1942年1月21日,萧红在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巨大遗憾和悲痛后永远地“流亡”了。
三、结语
萧红的小说话语是个体性的话语,她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乡土的故事。然而无论哪一种故事,都关联着相同的历史情境,呈现着萧红感怀自身命运最基本的心理情结。开始就是结局,结局亦即开始,拼死挣扎的循环是萧红流亡叙事最基本的模式,萧红经年累月的流亡创痛都浓缩其中。
然而,萧红流亡者身份符号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日寇侵占东三省,在异族打压和驱逐下从东北故土逃入关内的难民。这即是说,萧红的流亡亦有着被动的因素。萧红的小说话语是流亡话语,而任何流亡话语都是一种隐含着多维度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话语形式。因此,个体的发声就可以被看作一类人的发声,从而使个体性的话语演变为公共性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萧红在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与文本表现,亦是如此。
注释:
[1][7]单德兴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4-45页。
[2][美]爱德华·W·萨义德:《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3]单德兴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韩震等译,[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5]欧阳景根译,[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6]彭淮栋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8]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9][10][12]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11][13][14][20][21][22]萧红:《呼兰河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17页。
[15]萧红:《失眠之夜》,《萧红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16]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174页。
[17][法]莫洛阿:《人生五大问题》,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7页。
[18][奥地利]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19]萧红:《生死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3]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季红真编:《萧萧落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任晓兵 内蒙古呼和浩特 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010070)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