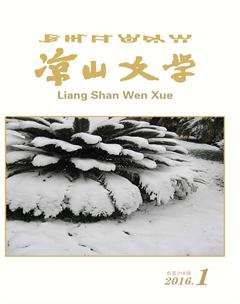抓一把空气揝出鸟声(组诗)
冯笃松
异乡天空下的故乡
望过去——
目力所及,天地之交
远远的,有大山紧锁。
横亘的屏障,冒出了地平线。
转山转水,柳暗花明
视线随道路延伸
延伸的景观,却是
川西坝子一样的沃野
一样的开阔。一马平川
却又百转千回,望不尽的清雅幽深……
金盆地,金盆地
安宁河谷的金盆地
我的日月,我的梦,在此安宁
盆底,盆壁,盆沿——
指着四面环绕的群山
我对素有盆地情结的女儿讲:
我从少壮的盆地走到老来的盆地
岁月的流向没有断脉。
顺流而下,你们
一样生活在盆圈里。
不一样的是,一个大,一个小
大的在望远镜之外
小的在望远镜之内
凉风岗注定替代那个命名者……
他走了。那个命名者
走了。名字却没有走失。
不用置疑,你替他站在
群岭之巅。冥冥中
仿佛是上帝的安排
你注定属于夏天。
风的孕育,风的蓄势
在岗上,不吹自凉
春天在后,秋冬在前
穿越的历史,你忽略不计
不显山,不露水,自己收敛自己。
最终的底线,走轮回之路
追踪自己的季节
风影随形,远方以远
那重新命名的风在吼:
岗上,岗上……
而你在岗上,又漫向四野
远远近近,谁都听见了
你与天与地的对唱:
清凉,清凉……
山鹰
兀立绝顶。世界
在它的俯视之中。
它用翅膀拍打天空
它用飞影抚摸大地
破雾。穿云。黑色的闪电
横空闪过的一瞬——
它劈开了属于它的空间。
张开剑锋一样的利爪
它在捕捉它看准的目标
它叼起了它的捕获……
俯冲,腾跃。它飞出的
那一片蔚蓝,一片云海
一片无尽的苍茫,那巨翅搏击的
剪影,你看见了吗?
有峰岭绵延展开,冲天而起——
鹰魂
离地而起。但它——
不仅仅属于天空。
那高擎着杯子的鹰爪
高举着一个古老的图腾。
在火葬地,火焰的羽毛
更加丰满。那是谁?
乘着升腾的火势
在展开折不断的羽翅。
死亡的影子撒满灰烬
终将被风刮走。
而酒的热度使它再度回暖。
液体的火在杯中
盛满燃烧,不再熄灭
一杯祭天,一杯祭地
神圣的仪式穿越时空
重现着它的飞身——
山的目光
那座山,就在窗外
有时很近
有时很远
我常常看它
它常常看我。
李白“相看两不厌”的吟咏
总是在我的耳边萦绕……
每到夜晚
我在明处,它在暗处
我知道,被夜色包围着的它
仍然默默地在看我。
对于它,我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藏
从内到外,我通透地
敞开胸怀——
如今,那间屋,那道窗
早已碎为烟尘。唯有它
依旧伫立原处,归然不动。
而我,无论走向何方,它的目光
那沉甸甸的目光,没有一丝游移
就像星星的闪烁,高高的
亮亮的,千里万里
投向我。正如我的回顾
那屋,那窗,在不断的对视中
现身……
那一双双灵魂的眼睛
选择沉默。一辈又一辈的亲人始终沉默
沉默在这片抓一把空气都能揝出鸟声的土地。
正如他们的影子,爬在时间的脊背
没有被吹过来又吹过去的风吹走。
暮色合围之前,他们的面影,隐隐约约
浮现于漫天的光影……
之后,一把硕大的金锁垂落
垂下重重的夜幕,他们的身影
融入暗黑,被簇拥,被勾勒
再次显形的不是流萤,不是电闪
更不是人世间的灯火
那一闪一闪的亮色,浮游而来
穿过夜的重门,穿过阴阳的疆界
直向远方的黎明伸延……
我看清了,那是那边的亲人
从未间断的目光,疼爱的目光
在把我照耀——
那树在走……
——写给一位年轻的朋友
起风的时候
那树身不由己。或者说禁不住
被挑起一种欲望,按捺不住地
激动。树体狂扭起来
远远看去,一枝一叶都在狂跳狂舞
欲罢不能的嘶吼,已分不清
发自树声,还是风声……
谁在说:树欲静风不止。
其实,它并不愿意悄无声息地矮化
更不愿意呆立一处
像过往的老树被囚禁一样
寂寞地了却残生。它想出走
内心的绿意在枝叶上迈步
凭借风力向上,踏一片青云
我看见——
它踏出了一条伸向高空的路……
老小孩
一些东西在进入
一些东西在出走
时间夺走了记忆
留在空白处的上下左右
成为风无孔不入的通道
一次次把春夏秋冬的
足迹,一扫而净
不见草,不见花,不见雨,不见雪
这世界似乎不曾来过。
我像一个走失的孩子
跌倒,爬起,跌倒,无助地
陷入空旷的迷茫。
走到梦中多次徘徊的十字路口
我终于想到了母亲,想起姐姐的
那双温暖的手,她们牵着我
走过一座桥一座庙一座山。
此时此刻,我因此被唤醒
找到还未走失的一座灯塔
的光芒,一下子刷亮了还未走远的
那一朵云,那一片天空……
那年的那把万能钥匙
不知是天意的安排
还是谁的捉弄,在十八岁
在一块泥泞的荒草坡
我重重地跌了一跤,却
拾到一把万能钥匙
一个污泥粘糊的金属体
看似一个微型的十字架
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光
不知深浅,对什么都好奇的
十八岁,我试着打开了
各式各样的锁,甚至
打开了姐姐锁着秘密的
那个好看的金匣子
我害怕了
不敢对姐姐说
更不敢对任何人说。
面对姐姐,不敢眼与眼对视
总是绕着走
生怕她看穿我的秘密。
直到姐姐临走的那天我也没有说
悲痛哽咽了我的嘴舌
那个十字架,从此由小变大
覆压在我的心上,常常
绑架我于噩梦中,无以脱身。
看来,姐姐在那边知道了
——这个劳什子。
那日,天气晴好
我专程走向大海,走向海心
面对海与天遥远的衔接处
大声呼喊:姐姐,你放心吧
我已将这贼物连同一块捆绑它的石头
抛入了深深的海底——
位置
祖传的那把雕花太师椅
世世代代摆在正堂屋
神圣的位置,没有挪动过
爷爷常常坐在上面发话,直到
临终,那椅子完好无损
最后成为父亲日常的位置
有时候,背着父亲
叫弟弟俯首下跪,我正襟危坐
于那个位置,装模作样
如今,父亲走了。家规传长
太师椅自然归了我
但我不再愿意就此上座
让它闲在了一间闲屋……
揖别,或者候鸟
鸟声被那只鸟渐渐飞远
留下的一片天空,高而空
他知道,明年,甚至后年
那只鸟还会回来
但他瘦如枯枝,心间
还能筑巢以待吗
仰首向天。寒风中
他呆立了很久。夕阳下
路口拖着他的双影
其一:是他细细的竹杖……
那株盆栽的幸福树
那株被冠名的幸福树
来我家一年多,昨天所有的
叶片,枝条,挂着一脸的晦暗
手臂下垂,头埋得很低
失去了往日碧绿的表情
妻子说:“它死了,死定了。”
一年多的日子,它安身立命于
那盆圈的一小团土块
上不吸天露,下不接地气
阳光隔在窗外,可望不可及
它却将越长越大的“幸福”
负于自己的脊背
一开始就头重脚轻,但
人们的欲念有谁愿意放弃?
它只得认命,以自己的微躯
硬撑着,挣扎到底……
我对妻子说:“现在好了。好了的它
重负卸下,终于可以
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