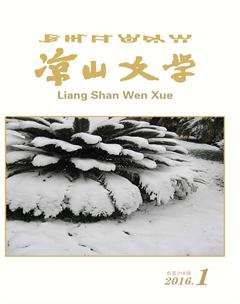我喜爱散文
喻泽先
变化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人的喜爱也在这法则之中。
我喜爱散文,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我爱读散文,特别钟爱古今的好散文;另是我学写散文。
爱读散文,是在我中年以后读书习惯变化所形成的。进入老年,我基本上不读小说,名家名著,偶尔看看。当今当红的“网络小说”,更不屑一顾,不是我轻慢这些作者,是他们的作品,不适合我的胃口。
我青少年时候还是读小说的,而且特别“上瘾”,苏联的、国内的中长篇小说,一卷在握,读完撒手。走路时在读,赤足经常踢在石头上;睡在床上也在读,备受父母的喝斥。上自己不喜欢的课,埋头桌下悄悄读,记得上地理课时读《牛虻》这本书,还被老师收缴过。什么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战争题材小说、爱情题材小说、传记体小说、全塞进自己的脑子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繁荣时期的许多长篇名著,我几乎都读过。我不爱读日本小说,被诩为日本名著的《源氏物语》,闲翻几页便成了摆设。欧、美小说,因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涉猎得很少。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学大量涌入,然而,我的读书爱好已转移。
进入青年时代,“青春期”萌动,我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读诗歌。诗有美的语言,美的意境,诗中有高尚的情操,有爱憎分明的情感,就是说句我爱你,也来得很含蓄,这是我爱读诗、写诗的真实原因。那时候,陆綮、李瑛、严阵等许多诗人的诗集,常是我案桌、枕边的书。青春冲动让我读诗近于“疯”,无钱就卖新衣服,宁可穿旧衣,也要买他们的诗集。
“文革”的阴霾,窒息了我人生最旺盛的求知欲,让我少读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感到为文的底气不足,应是“文革后遗症”吧。
我开始喜爱读散文,是中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那是八十年代的后期,有一天,我去西昌市图书馆阅览室读书,在一本期刊上,读到一篇名叫《夜籁》的散文,文章简约的语言吸引了我,深刻的内涵震撼了我。作品的大意是说:作者在社会闯荡多年,一事无成,决定乘木船去汉江上走走看看,以解烦忧。一天,船停在汉江边一个小山村,作者去山村借宿。在一户烟薰火燎的农屋里,他咽不下老汉苦涩的老梗茶,闻着土菸叶味,呛得他不停地咳嗽。入夜,在这偏僻穷困的小山村,作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子夜后,朦胧的月光穿过土窗射进屋,他忽然听到一个老大娘不断的唤魂声,“儿子啊——回来!”。读完这篇散文,我掩卷沉思,作者之所以一事无成,是他脱离了人民大众,民众在呼唤作家回归,作家只有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中,才能有所作为。就是这篇短文,点燃了我内心情趣的火苗,从此,我见到好的散文书便买来读,越读越喜欢,越喜欢越读,觉得散文太好了,世间万事万物万象皆可写入文中。慢慢地,小说、诗歌与我渐行渐远。每天要读一两篇散文,成了我的日常功课,好似和尚每天必念的经文。人到晚年后,倍感精力日削,读小说犹如水洗沙盘,转瞬就了无刻痕;我读诗,也像老太婆跳舞,念半天也蹦不出半点激情。还是读散文来得痛快,十多二十分钟就读完一篇。
散文是有感而发的文章,读者会随作者情感的起伏而律动。虽然文章不长,但能叫人咀嚼出个中滋味,如含橄榄,满嘴甘甜。如果说小说是大餐,满桌美味佳肴,使人大快朵颐,饱享口福;那么,散文则是一杯醇香的酒,慢斟浅酌,品那回味无穷。为什么青年人爱看小说,中老年人爱读散文,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散文读多了,我的“胃口”也大起来了,余秋雨、宗璞、刘亮锃、熊召政、伍立扬等一大批散文大家的作品,都是我精神上的“盘中美味”。
近几年,我对中国古代散文和赋的兴趣特浓,吟诵这些美文,琅琅上口,心总在微醺中。把古代散文和当今一些散文来比照着读,文章的优劣,立意的高低,立见分晓。对赋这种文体也说几句,我认为赋是中国真正的美文,有韵有节奏,抑扬顿挫中,妙不可言。中国的古诗词、现代诗、小说、散文,书如瀚海,为什么没有人把古今的优秀赋文收集、整理、出版?令人难以理解。谁人来做这件事,真是功德无量。若有出版,我一定要买,精神食粮也要有多口味,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新文化运动(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的散文,如朱自清、周作人、徐自摩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在书店柜台上到处可见,这很时尚,我也凑热闹地买了一些来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只有少数文章被奉为精典,入选中学的课本。读其他名家的作品,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大饱眼福之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读着这些名篇,我常闭目暗想: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单从文字上说,能写出很美的文章,而现在的一些作家,遣词造句是那样的平庸,文字的组合是那样的失血。想来想去,这恐怕与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现代作家,尤其是散文作家,应认真研读古文来充实自己的“语言库藏”。不妨,可以试试。
一个人总有自己的偏好,我喜爱散文,那么,买书也侧重于此,在新华书店、古旧书店,我的目光总是专注这方面的书籍。我藏书五、六千册,从广义的散文说,其量占了藏书的三分之一。现在,我虽然是读日不多慎买书的老而未朽之人,但一看到好散文书,总控制不住购买的冲动,积习已久,难以去除。
再简短地说一说我学写散文。散文读起来容易,短时间就能读完一篇;但要写出好散文,就不那么容易了。有的人能急就成章,怕也是厚积薄发。写散文不需要写小说那样多的结构安排,然而,散文不仅要求情真,也很重视文字的“火候”,“火候”不到位,炼不出好文章。譬如一块好铁,任多长时间的低温,始终不能成为好钢。就是说,真情只有通过美的文字表达,才算得上情文并茂的好作品。
我说自己是学写散文,就是深感自己的“仓库”里,语言的子弹不多,不能供我组合和使用。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也未曾写出满意的文章。我写散文是在学中写、写中学。季羡林大师说得好:“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一位大作家真正靠什么秘诀成名成家的”,“想要写好文章,只能从多读多念中来”。我的体会还得从多写中来。我用此种方法修炼,看能否成为“正果”,不敢断言。对此,我没抱多大希望,不能成“佛”没关系,只要念过阿弥陀佛就很快乐。
众人都说,写散文要真,真人真事、真情感、真感受。此话我完全赞同。虚构的东西,总是虚情,虚情连自己都是言不由衷,焉能动人。
要写出好散文,我觉得还应有一个新,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察、新感觉,旁人笔下无,自己笔下有,以新意满足人的猎奇心理。为什么同游一景点,写同一题材的文章,每一个人的笔下,总是不尽相同,这就是各人的观察、感觉不同的缘故。为什么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人能出新,也是这个原因。
不同就是新。在新字上再融入自己的真情,这样写出的散文,再孬也有三分感人。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人的思维有一种“循旧”的惯性,这惯性束缚了思想的放飞。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大概是酒精挣脱了思想的束缚力,而使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地写出了传唱千古的诗文。
要写出好散文,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如练字练句都是必不可少的功夫。有新发现不能流畅地描述,有好心情不能很好地表达,这就是遣词造句的功力不够,如前所说,仓库里的“子弹”不多。
季老羡林大师,一辈子写了六、七十年的散文。我的后半生与散文结了缘,喜爱上散文,就以读和写散文终其余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