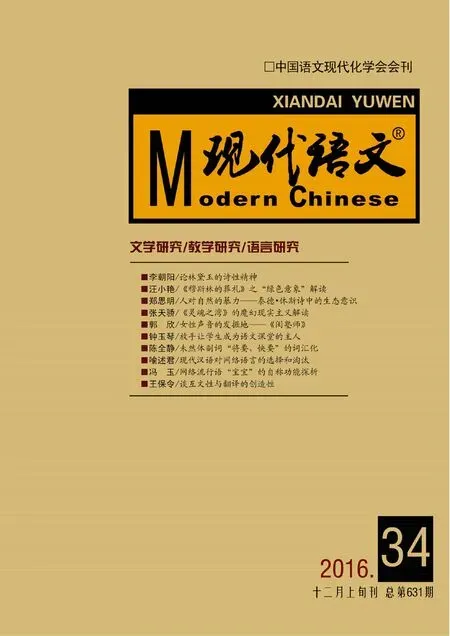论林黛玉的诗性精神
○李朝阳
论林黛玉的诗性精神
○李朝阳
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仿佛就是一个整日流眼泪、爱耍小性的气量狭小的小女子,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林黛玉绝不是小心眼、爱哭闹、不识大体的寻常小女子,而是一位情趣高雅、志节不凡、重情轻物、热爱自由、敢于反抗的具有诗性精神的大家闺秀与绝代佳丽!
《红楼梦》 林黛玉 诗性精神
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仿佛就是一个整日流眼泪、爱耍小性的气量狭小的小女子,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绝不能代表林黛玉性格特征的主要方面,林黛玉的精神实质是中华传统诗性文化的代表,是具有诗性精神的绝代佳丽。
一、林黛玉诗性精神的渊源
“诗性”一词出自维柯的《新科学》,是指原始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惊人的文化创造能力,它具有诗的精神。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认为:“所谓‘诗性精神’,就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1]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就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其内涵不仅仅指作诗的才能,更应该是一种审美的能力、高尚的人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
这种诗性精神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又因中国北方儒家文化繁盛,世俗功利文化更易于在北方流行,而边远地区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小,中华文化中的诗性文化更易于流行,特别是在富足的南方,人们在消除了贫困之忧后,诗性文化更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刘士林先生即云:“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2]林黛玉就是在江南诗性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浓厚诗性精神的奇女子。
首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是以南方女子为原型塑造的。第三十七回探春云:“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潇湘妃子”是探春送给林黛玉的雅号,从中可以看出娥皇、女英是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之一。
《红楼梦》第三回中又有黛玉容貌的描写:“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贾宝玉据此又送给黛玉一个“颦颦”的雅号,是说黛玉病如西施,则西施亦是黛玉形象的原型之一。
《红楼梦》第一回又云林黛玉的前身是一株绛珠仙草,而据专家考证,绛珠仙草和《楚辞•山鬼》中的女神所采之“三秀”实为一物——灵芝,黛玉也和《山鬼》中的女神一样多情善感……则《楚辞•山鬼》中的女神也是黛玉形象的原型之一,故解庵居士在《石头臆说》中云:“《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离骚》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3]
其次,林黛玉的出生地正是最具诗性精神的江南名城——姑苏,这块热土培养了中国人文精神中最具浪漫特质和审美情趣的诗性精神,刘士林先生云:“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或者说江南文化的最高本质恰在于要比齐鲁的‘礼乐’多了些什么。在我看来,与人文积淀深厚悠久、‘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礼乐之邦相比,它多出的正是几分‘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文化实用主义、代表着生命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在中国区域文化传统中,正是由于充分关注到人的审美需要,才使得江南文化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诗性与审美代表着个体生命更高层次上的自我实现,所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文化中才实现了它最高的逻辑环节,以及在现实中获得了最全面的发展。”[4]张兴龙先生亦云:“在历史上的审美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只有江南文化是最名副其实的审美,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同为南国的巴蜀、荆楚、闽粤,演绎出了宗白华先生所说的‘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5]地域环境无疑对林黛玉的诗性精神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也是黛玉诗性精神形成的原因之一。
再次,林黛玉出生名门,《红楼梦》第二回云:“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已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女如珍;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黛玉出生高贵,又是书香门第,从小被当男孩儿抚养,饱读诗书,气质自然高华,这是其诗性精神养成的又一因素。
二、林黛玉诗性精神的具体表现
具体说来,林黛玉的诗性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情趣高雅,志节不凡。《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有一段描写:“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进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里,又有一小门,出去却是后园,有大株梨花,阔叶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面对如此幽静之处,贾政忍不住说道:“这一处倒还好,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而在众女儿搬进大观园时,林黛玉欣赏的就是这一幽静的处所,《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道:“黛玉正盘算这事,忽见宝玉一问,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幽静些。”而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品节的象征,故黛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不仅仅反映了林黛玉的审美情趣,也象征着林黛玉的品行如竹子一样有节。
林黛玉又有芙蓉花之称,而芙蓉又名莲花,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由此可知,莲花又象征了黛玉高洁的品行,其清高孤傲的性格也最适合做芙蓉花神了。黛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行在“黛玉葬花”一节里表现无遗,《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有这样的描写:“宝玉笑道:‘来的正好,你把这些花瓣儿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了。’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落花是女子的象征,更是黛玉自己的象征,其葬花即是表明其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趣,故其《葬花吟》云:“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
在林黛玉的诗词中有《咏菊》《问菊》《菊梦》三首吟咏菊花的诗,在这几首诗中,林黛玉不仅表达自己孤标傲世的情怀,还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倾慕之情,如《咏菊》中的“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菊梦》中的“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花傲霜不凋,是黛玉气节的象征,而对陶渊明的倾慕,表明林黛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竹子、莲花、菊花都是品行高洁的象征,林黛玉对竹子、莲花、菊花的喜爱,既是其高雅情趣的表现,也是其志节不凡的象征。
2.重情轻物,情如生命。林黛玉对情的珍重,一方面表现在其对人情冷暖的重视,如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时,当林黛玉得知最后两朵是别人挑剩下的时候,她当即说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以往的评论家大都认为这一段表现的是黛玉的小性儿,其实,这其中何尝不蕴含着黛玉的自尊,更蕴含着人情的冷暖,说明黛玉渴盼着人间的温暖与关爱。
另一方面,林黛玉对情的重视还表现在其对亲情的渴盼上。林家人丁稀少,黛玉又自幼丧母,父亲也中道离世,黛玉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生活,这使其内心特别容易产生对亲情的渴盼之情,《红楼梦》中就多次提到黛玉自怨自艾其“无父无母,无兄无弟”,当黛玉看到宝钗有母疼爱、有兄照顾时,只能自叹不如,内心不由自己地产生一股悲凉的感情;而当黛玉和宝钗尽释前嫌时,又非常温馨地叫薛姨妈为娘,其对温暖亲情的渴盼显露无遗。
当然,林黛玉最珍视的还是她视如生命的爱情。王昆仑在《林黛玉的恋爱》一文中云:“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恋爱以外,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生活内容,也看不到恋爱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咀嚼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她自己的性灵、嗜好、妒恨,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幽美的诗歌;以后,就在这里面消灭了她自己。”[6]蒋和森《林黛玉论》也云:“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7]李辰冬在《林黛玉》一文中亦云:“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黛玉的恋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其和宝玉自小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两小无猜、自然而然培养出来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一经产生,对于孤苦无依、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来说就是生命中的唯一,让其难以割舍,使其不得不在任何场合维护自己的感情,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
黛玉在重情的同时,她对物却表现出了极大的轻视。如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宫花是皇宫所赐,应该是极为珍贵的,即使不那么精美,也是荣誉的象征,黛玉却对其十分轻视:“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却问是否单独送给她的,以此来探询其在贾府的地位,是否受到别人的尊重,这说明其看重的是人情的冷暖,而不是物质的享受。又如第十六回写道:“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黛玉对感情坚贞,不愿为物欲所玷污,既不管此物是什么贵人的,也不管此物有多么珍贵。而在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赠送给黛玉两条旧手帕,黛玉却十分珍重:“这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道:‘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黛玉还在这块旧手帕上题写了三首饱蘸血泪的诗歌: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这说明黛玉明白虽然手帕的价值不高,于中却蕴含着宝玉的深情,这两条旧手帕见证了他们的爱情,黛玉对手帕的珍惜就是对她和宝玉之间爱情的珍惜。对此,王昆仑先生在《黛玉之死》一文中即云:“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9]在宝钗的现实精神的比较之下,黛玉的诗性精神更加鲜明生动。
3.热爱自由,具有反抗精神。明清是理学统治的时期,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被视为洪水猛兽,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作为贾府的最高统治者的贾母就曾借对才子佳人戏剧的评论发表自己对自由恋爱的鄙视:“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的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林黛玉作为贵族小姐,却对这些清规戒律视而不见,一任自己的情感自由发展,显示出了强大的反抗精神。在第二十三回,黛玉和宝玉共读《西厢》,“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可以说《西厢记》《牡丹亭》等传情作品是宝黛爱情的启蒙老师,正是在王实甫、汤显祖等人“以情反理”观念的影响下,宝玉和黛玉走上了自由恋爱的道路,显示了他们对个性解放的渴盼,也彰显了他们热爱自由的天性。
但这条自由恋爱的道路并非金光大道,也不是毫无阻碍的坦途,其中充满了荆棘和艰难,没有抗争的勇气就很难到达光明的目的地。首先,黛玉要和天定的“金玉良缘”相抗争,虽然她和宝玉前生也有“木石前盟”,但海誓山盟毕竟是私定终身,难以和众人心目中完美无缺的“金玉良缘”相媲美。黛玉却不顾世俗的偏见,以其瘦弱的身躯、敏感的心灵对抗着来自宝钗和湘云的压力……其次,黛玉要和封建家长们相抗争,当贾府上层决定先给宝玉完婚,再给黛玉找人家时,按照常理,如果黛玉服从家长们的安排,心安理得地嫁入一个平常的人家,也许黛玉会过上如常人一样的生活,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但那就是一个寻常的女子,而不是视爱情如生命的黛玉了。当她听到宝玉结婚的消息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的道路,以此来殉自己纯洁无暇的爱情,以此实现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生理想。
尽管黛玉生活的环境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但黛玉却从不屈己从人,仍然是我行我素,洁身自好。其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对封建家长的反抗,表明了黛玉对自由的热爱,彰显了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三、结语
脂砚斋在《红楼梦》第八回回评中评黛玉云:“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裙钗矣!”[10]足见黛玉兰心蕙质、冰心玉洁的诗性精神早已为人所知。而现代人常以庸人的现实的角度去曲解林黛玉,误把林黛玉日常生活中的敏感气质当作其性格的主要特征。总之,林黛玉的个性特征不是小心眼、爱哭闹、不识大体,她绝不是寻常人家的小女子,而是一位情趣高雅、志节不凡、重情轻物、热爱自由、敢于反抗的具有诗性精神的大家闺秀与绝代佳丽!
注释:
[1]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一粟编:《红楼梦研究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4页。
[4]廖明君,刘士林:《在江南探寻中国民族的诗性精神——刘士林教授访谈录》,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第30页。
[5]张兴龙:《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的维度》,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第75页。
[6]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蒋和森:《红楼梦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8]李辰冬:《知味红楼》,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9]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10]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李朝阳 贵州都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红楼梦》研究所 5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