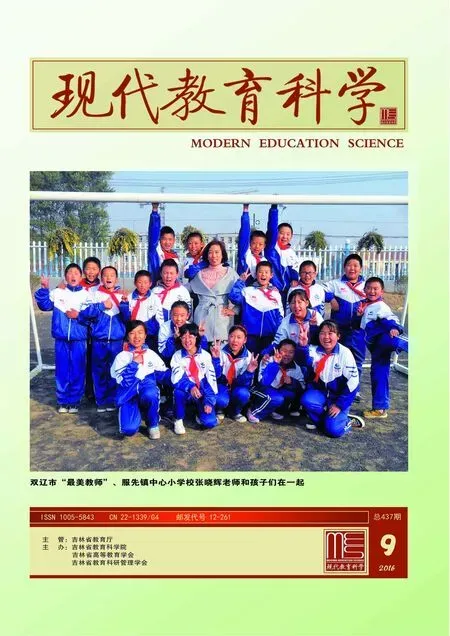卢梭身体教育思想的内在张力
曹晓婷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卢梭身体教育思想的内在张力
曹晓婷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身体教育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是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卢梭作为第一场另类“哥白尼革命”的发起者,在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卢梭而言,身体涵盖了科学意义上的物体论的身体主张,即“我有一个身体”,以及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的身体的主张,即“我是我的身体”两个方面。卢梭的身体哲学启示我们教育要重视培养儿童身心全面发展,重视情境教学,重视知行合一。
身体身体哲学情境教学知行合一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身体性哲学,那么西方传统哲学乃为意识性哲学。以意识性哲学为奠基的理性主义高扬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之旗,欲摆脱一切,主宰万物,使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为破除意识哲学,西方哲学开始重视人的情感、直觉和意志等,并将生命形态的身体作为人们重新理解生活世界的坐标。
一、卢梭的身体哲学思想
卢梭的著作中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自我对抗的论调,以至于后来出现“一个卢梭,还是两个卢梭”的争论[1]。作为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过渡的重要人物,卢梭的身体哲学思想也充满了矛盾性,涵括了科学意义上物体论的身体的主张。受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卢梭的身体观中依然带有“形神二分”的痕迹,但整体来看,他更倾向于形神一体的身体观。
(一)我有一个身体
西方传统的身体观是一种“形神二分”的身体观,其最早起源于古希腊从心灵本体出发的观念主义。随后,柏拉图“两个世界”的理论导致了人的灵肉二分:作为理念的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作为现象之物的人的肉体则为可死灭之物,欲保持灵魂的不朽,就必须摆脱肉体的纠缠[2]。后来西方基督教思想和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形神二分”思想的泛滥。卢梭的身体思想也受到一定影响,他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不过是活了他生命的一半,要等到肉体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过灵魂的生活。他说“当肉体和灵魂的结合形式瓦解之后,肉体就消灭了,而灵魂则能保存”[3]。“那时候,由于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我将成为一个不自相冲突和分裂的“我”。那时候,我只需依靠我自己就能取得我的幸福”[4]。因此,他才认为我们应该保护自己不受情欲的蹂躏,防止我们变成它们的奴隶,要做自己的主人,不服从感官而服从自己的理性。在以上叙述中,一个基本的构架就是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身体是短暂的而灵魂则是不朽的;身体是贪欲的而灵魂则是圣洁的。
(二)我是我的身体
卢梭关于“我是我的身体”的身体观认为:身体意味着身之体,它是灵肉的本原统一体,结构化的经验和意义的整体,人理解和领会世界和自我的中介。
首先,身体作为灵肉的本源统一体是物性和灵性的交织或融合,是涵盖和包容肉体与灵魂二者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始源性存在,富有容纳而又超越肉体性和精神性、情感和理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诸多意蕴和内涵[5]。他认为若身体虚弱,那它将永远不能培养有活力的灵魂和智慧 ,一个人的身体必须强健而充满活力,才能听从灵魂的支配。其次,他认为“理性能教导我们认识善和恶。使我们明白喜善恨恶的良心,尽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没有理性,良心就不能得到发展”[6]。但他又说:“我总觉得用我的良心进行启示,比用我的理智的光辉来解决好,道德的本能从来没有骗过我;一直到现在,它在我心中还保持着它的纯洁,我可以信任它。”[7]在卢梭看来即使是理性有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只有良心才是人类真正的向导,它从来不会欺骗我们。可见,卢梭身体观中的身体既蕴含着内在于人的肉体性、自然性又包含着人的精神性和神圣性,呈现出可见与不可见相互交织、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得益彰的复杂格局。
其次,身体感觉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行为,而是一种身体活动,和感觉是相互伴随的,它实现了特定存在经验和意义的结构化,并将之组合成一个整体。意义作为肉体和情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个体对情境的建构和投入中,其可能性得以实现,以直觉的方式发挥作用。卢梭提出要培养儿童的第六个感觉,也即共通的感觉,它能通过事物的种种外形的综合而使我们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所谓的第六个感觉和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场”非常类似,正是因为身体有知觉场的存在,我们对刺激的感觉才不会只是反映的、呆板接受的,而一定是有格局的、有结构的、有事态的,而且还是有时机的、有脾气的[8]。当我们置身于某个特定情境时,知觉场会使身体拥有一个“身体图式”使得我们的身体不是各种器官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场域式的“共有”也即梅洛庞蒂所说的“我在一个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9]。因此,我们才能对事物有整体的感知和把握。
再次,身体是使人理解和领会世界和自我的中介。梅洛庞蒂的互体性身体观也认为,我们通过身体去理解他人就像我们通过身体去感知世界一样,在身体的意向性活动中我与他人融洽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是通过身体在世界上存在,通过身体介入世界并与世界形成结构关系。与梅洛-庞蒂的互体性身体观一致,卢梭认为人具有两种先于理性的原动力,一是自爱,它推动我们关心自己的幸福,并保存自身;另一是同情,它将使我们在看见一些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看见我们的同类遭受痛苦或死亡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人之所以具有同情之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感觉和体验具有不附带条件的相通性。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具有相同的身体体验原型作为对话的基础,我们才会对他人的痛苦遭遇和悲惨境况产生恻隐之心,从而实现卢梭所谓的从自爱到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乃至爱全人类。这与舒斯特曼所说的身体自我意识的训练将导致自我是特定情景中与他物共关联的共生性自我,而非独立自主的、根植于个体的、单独的、牢不可破的、不变的灵魂的思想殊途而同归。
最后,身体意味着体之于身,以“身”体之,身体力行。个人是在介入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体验到自我的存在的,身体既是感性存在,又是感性活动,是经由感性活动生成的感性存在,这一点在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中尤为凸显。他说“要以行动而不以言辞去教育青年,他们在书本中是学不到他们从经验中学到的那些东西的”[10]。卢梭认为作为教师要言传身教,谨言慎行,在儿童阶段教学方法应尽量采用直观教学,让学生有一种体验式的学习过程。在道德教育方面,他认为最高的道德是消极的,通常也是最难以实践的,所以就不能光谈它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践行。概言之,卢梭的这种身体观强调体验式的行为,注重行为的体验性。
二、卢梭身体哲学思想蕴含的教育启示
卢梭作为身体教育学复兴的第一场哥白尼革命的发起者,对传统教育破坏人的自然本性,忽视人的身体感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和打击,不仅轰动了当时的西欧教育,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我们今天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既然身体是灵肉的本源统一体,富有容纳而又超越肉体性和精神性、情感和理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诸多意蕴和内涵,那么教育就应该注重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不仅重视智力教育更要重视健康教育和情感道德教育。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学生身体的敏感性和灵敏性,激发学生身体对某种教育情境中的原初意义的感受,从而使学生获得整体的知识和意义。通过道德教育,引导学生以理智去认识善,以良心去爱善,以自由去选择善。理性能让我们习得正确的道德知识,学会进行道德判断,能在拥有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去追寻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但仅仅有理性是不行的,因为理性必须依赖于情感,情感传达和反应着人的需要。而且理性只能约束一个人的行为,但情感却能激励人去行动,甚至有的时候,情感可以支配和决定人的行动。诚如卢梭所言“单单凭理性,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它有时候可以约束一个人,但很少能够鼓励人,它不能培养任何伟大的心灵”[11]。在具有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基础上,还要教育学生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善。
第二,既然身体是结构化的经验和意义的整体,而意义作为肉体和情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个体对情境的建构和投入之中,其可能性得以现实化,是以直觉的方式发挥作用的。那么,教育就应该重视情境教学,重视学生的情境化学习。以布朗、杜吉德和柯林斯为代表的心理学视角以及以温格、莱夫为代表的人类学视角都突出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其中,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情景学习理论认为,知识通常是个人和社会与物理情境之间互动的产物。他们提出了“合法的边缘参与”的概念,旨在让隐含在人的行动模式和处理事件的情感中的默会知识在与人与情境的互动中发挥作用,并使得默会知识的复杂性与有用性随着实践者经验的日益丰富而增加[12]。为激发学生积极地建构自己的知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采取以音乐渲染情境、以图画再现情境、以语言描绘情景、以表演体会情境、以实物演示情境和以生活展现情境等多种多样的途径为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创设生动的形象,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第三,既然身体意味着“体之于身,以身体之,身体力行,是经由感性活动生成的感性存在。而意义作为一种存在经验,是身体在实践之中生成或转变的特定经验的总体。意义生产实践,并通过实践得以生产和再生产”[13]。在教育中,要做到“知行合一”和“教学做合一”。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将“学”与“行”结合起来,“学”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学”是“行”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知识的意义往往是在与现实相遇的直接性中作为实践关系的可能性而得以具体化的,学生只有通过这种知行互动的认知方式,才能使各种本然之“知”通过指导“行”而进一步获得明觉之“知”。其次,“行”是“知”的归宿,一切的学习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落实到实践,都是为了通过实践改造我们的生存世界,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活动中使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在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过程中更要强调“行”的重要性,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将德性转化为德行。
作为身体教育学复兴的第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卢梭的身体教育思想惊动了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受到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的影响,他的身体观中有“神形二分”的痕迹,使得身体的含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矛盾性,但他始终认为身体作为人现实的感性活动过程,充盈着目的和工具的和谐共生、主动和被动的相互渗透、能动和受动的交互引发、体用动静的默契交会、内在修养与外在表达的协调一致,成为人真切理解和领会世界与自我的中介。他那注重儿童的感觉教育,注重人的身心全面发展,注重整体性的身体与环境、社会的互动等身体教育思想,给当时以理性为支撑的“知识教育学”构成了强有力的回击。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反观我们自身的身体,重新反思意向性的身体在教育乃至整个生活中的意义。
[1]刘良华.”身体教育学”的沦陷与复兴[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6).
[2]张再林.我有一个身体与我是身体——中西身体观之比较[J].哲学研究,2015(6).
[3][4]卢梭.爱弥儿:下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446,464.
[5]郭祥超.教师专业发展:身体哲学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6][10][11]卢梭.爱弥儿:上卷[M]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3.
[7]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A]卢梭全集:第三卷[C].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8.
[8]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出发阐述原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莱夫.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郑震.作为存在的身体:一项社会本体论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爽)
On the Intrinsic Tension of Rousseau’s Physical Education Philosophy
CAO Xiaoting
(ShanxiNormal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2,China)
The symbolic events of the reviv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ree alternative “Copernican Revolution”, as the first alternative initiator of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the consciousness philosoph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philosophy of the , Roussea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Rousseau, the body covering th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objects on the body claims that “I have a body” and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ontology body claims that “I am my body”. Rousseau’s body philosophical enlightened us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ivat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ircumstances teaching and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ody; body philosophy; circumstances teaching;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05-14
曹晓婷(1992-),女,山西晋中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
G640
A
1005-5843(2016)09-0115-03
10.13980/j.cnki.xdjykx.2016.09.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