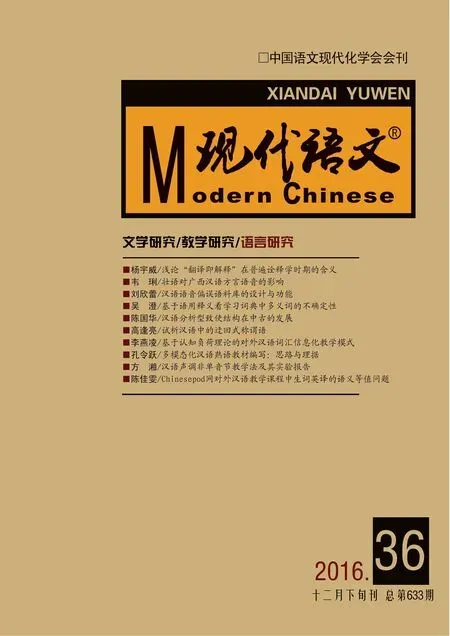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关系探析
□赵 鸣
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关系探析
□赵 鸣
句法和语义是语言理解的重要组块,但学界对于句法和语义在语言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较多争议。本文从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着手,对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句法 语义 关系
王维贤(1991)指出,“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结合的问题是永恒的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句法和语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讨论和思考。本文从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着手,对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理论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的不同时期,对于句法和语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从中也反映出理论语言学者们对于汉语句法和语义间关系问题的思考。
(一)早期的语法研究以语义分析为重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不能同印欧语法一样按照形态对词类进行划分,所以在1898年《马氏文通》中转为以意义作为划分词类和句子成分的标准。认为“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同时根据语义进行句子成分的分析,划分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等。正如朱德熙所说,早期的语法学著作难免要以印欧语法为蓝本,“但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区别,这种不适当的比附也确实给当时以及以后的语法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朱德熙,1980)
(二)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
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这种研究态度的转变主要受到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倡语言的科学描述,主张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汉语语言研究者开始注重结构形式分析,“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方光焘,1958)。在词类划分上,有的学者注重从词形形态变化、形态标记等“狭义形态”上着手进行词类划分。这样的狭义形态在汉语中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与汉语语法特点是不相符合的,由此总结出的语法规律必定缺乏概括性、强制性,最后导致得出汉语没有词类的错误结论。在句法分析上,有的研究者从句法结构形式入手进行语法研究,如邢公畹(1955)认为“主语就是一句话里在前头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宾语是谓语中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吕叔湘(1979)指出,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干脆倒是干脆,只是有一个缺点:‘主语’和‘宾语’成了两个毫无意义的名称,稍微给点意义就要出问题”。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语义研究多是在对句子主语、宾语语义类型的讨论上才被提及,语义研究成为句法研究的附庸。
(三)语法分析中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
由于语法研究的外因和内因两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歧义结构的研究,逐渐暴露了单纯依靠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变换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弊端。例如:层次分析法只能揭示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线性语法结构关系,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所隐含的语义结构关系,所以对于“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这种由于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造成的歧义句,就不能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另外,变换分析虽是用以分化歧义句式的有效手段,但是却不能用来解释歧义形成的原因。上述因素是影响语法分析的内因。
外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语言学开始了对语义研究的重视。这表现在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关系语法、功能语法、蒙太古语法等重视语义研究的学说相继出现。此外,对于推崇句法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生成语法理论也由最初的完全排斥语义,转变为在“标准理论时期”将语义引入并定义为投射规则,把深层结构里各个成分的语义信息按结构关系逐步合并,最后形成全句的语义。“修正后扩充标准理论时期”进一步提高语义的地位,语义表达式不再同深层结构有任何直接关系,改为由表层结构导出,导出过程必须通过语义规则的运用得以完成,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句法结构的投射直接获取,发展至“支配和约束理论时期”及“最简方案”时期更是专门提出与语义相关的格理论和题元理论,足以可见对语义在语法中重要性的肯定。二是计算机语言学的发展提醒语言研究者对于汉语研究不能仅仅着手于形式,还要关注语义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自然语言的发展中,格语法理论对许多系统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相关的研究在汉语理论学界并未受到重视,从而延误了语义组合关系理论在大规模自然语言系统中的应用。也有学者表示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或翻译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是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的中心,因此对动词与其周围的名词性成分发生的语义组合关系做出具体详尽的描写就可以大大提高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或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语言学者在句法结构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语义的关注。朱德熙(1980)提出区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指出两者不是一回事,并在《语法答问》中强调“要使形式和意义相互渗透。讲形式的时候能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陆俭明(1990)指出,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即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吕叔湘(1984)再次强调要区分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分别。”胡明扬(1994)、邵敬敏(1997)、马庆株(1998)等提出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和“语义语法”概念,希望通过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更为抽象的语义范畴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至此,学者们开始重视语义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并展开研究,利用语义特征分析、配价、语义指向等不同的语义分析手段使汉语的语法研究逐步深化。
(四)句法、语义关系的争议
回顾理论语言学对于句法、语义方面的研究历程,可以明确理论语言学领域逐渐明晰了句法和语义在句子中都承担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对于句法和语义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仍然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如例(1)~(3)所示,在汉语中同是“动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的词类序列,却可以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
(1)打算回家(述补结构) 研究结束(主谓结构)唱歌跳舞(联合结构) 挖掘出来(述补结构) 访问回来(连谓结构) 生产管理(“定—中”结构) (他)讽刺说(“状—中”结构)
(2)祖籍安徽(主谓结构) 北京上海(联合结构)首都北京(同位结构) 北京胡同(偏正结构)
(3)训练工作(定中结构) 训练队员(动宾结构)
按照一般语法教科书的解释,不同的语义关系由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是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句法结构的不同(史锡尧,1995;邵敬敏,1995;张黎,1996;陆俭明,2001、2004),有些学者提出“语义决定性原则”,即汉语语法的决定性因素是语义,而不是形式(邵敬敏,1997),“语法是意义之法,……句法形式上的规则只不过是意义的组合之法的表现形式,”(张黎,1996),“语义关系制约着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构造层次的不同只是不同语义关系在句法结构的线性层面上的反映”(何洪峰,2003)。当然,也有些学者表示“我们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凭的不是严密的规则,而是综合了语义理解、自己的经验和部分句法规则”(陆俭明、郭锐,1998),是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心理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心理语言学认为句子的理解是一个包含了多个层级结构(句法、语义、语用)的复杂加工过程,但针对各个层级在加工中如何运作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句法自主理论
句法自主理论又称模块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句子加工中句子不同层级的信息是由大脑的不同功能性模块完成的。句法加工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只受到句法结构信息的影响。语义、语用信息的加工位于句法加工之后,处于第二个加工阶段,根据语义和语用信息可以对句法分析结果做出评价,如果句法分析结果与语义分析结果有矛盾,将重新进行一次句法加工过程(Frazier&Rayner,1982)。由于这种理论认为句法和语义加工阶段有先后之分,因而又称为序列加工理论。
花园路径模型(The Garden Path Model)是最为典型的句法自主理论的模型,由于强调句法结构的作用,又称为结构驱动模型(Phrase Structure-Driven Models)。模型的构建来源于对花园路径句子的研究。所谓的“花园路径句子”是对将读者的理解引向暂时性错误的一种句子的隐喻性说法。当我们对这些句子进行加工时,可能会按照通常情况下句子的理解策略,无意识地形成暂时性的理解错误,直至句子后面相关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现理解错误,然后再重新找回正确的理解方式。例如:
(4)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在例(4)中,当读到“李经理”时,通常会将“李经理”作为动词“解雇”的直接宾语先进行加工,认为“董事长”解雇的是“李经理”,但当“李经理”之后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觉“李经理”实际上是“工人”的修饰限定性成分,“董事长”真正解雇的是“工人”。是什么样的加工机制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方式呢?
花园路径模型认为,在句法加工的早期,读(听)者的句子理解策略是使用词类范畴信息,根据构建短语结构的相关原则,将句子中的词语指派为短语结构成分,这是对句子进行初始化的加工。语义信息在句子结构构建的基础上产生作用,对初步结构构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当句子包含歧义时,读者会放弃最初的分析结果,重新开始构建句子的结构。(Frazier&Rayner,1982)
Friederici(2002)在总结了相关实验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句法、语义加工时间进程上分化出句子加工理解的三个阶段:1.基于词类范畴信息的初始句法结构的构建阶段;2.词汇—语义和句法形态加工以及题元角色的安排阶段;3.不同信息的整合加工阶段。
(二)交互作用理论
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在句子的加工中,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词汇、语义和语用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始的句法分析判断和句法结构构建。
Marslen·Wilson&Tyler(1980)在实验中分别给被试朗读了四个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例(5)~(8),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听到句中“guitar”这个单词时作出反应,这些句子的后续句都是“The crowd was waiting eagerly”,句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谓语动词的语义合适度作了改动,实验结果是当动词结构中动词语义上由合理向不合理转化时,句子加工时间是相应增加的。
(5)The young man grabbed the guitar.
(6)The young man buried the guitar.
(7)The young man drank the guitar.
(8)The young man slept the guitar.
由此,他们提出了限制满足模型(Constraint Satisfac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句法分析不需要任何策略性的加工原则,只要符合语义、句法规则的分析都可以同时得到激活进行并行加工,直至最后判断出正确的理解方式。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句子所有的理解方式都可以被激活,每种理解方式的激活强度受到频率、语境、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形成的理解方式必须满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限制要求。词汇信息在对被激活的各种可能句法结构的判断、评价、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
Trueswell(1996)的实验说明了动词在语义上限制了与它共现的名词时,句子更易于加工,可见语义即时参与到句子的加工中来。实验设计了两种句子。例如:
(9)The witness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10)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如果按照花园路径模型的推测,根据最小附加的原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应该使用相同的加工方式,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对例(10)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例(9)。Trueswell认为,只有限制满足模型可以给予合理的解释。根据限制满足模型,动词识别后将同时激活与动词有关的论元结构,各个结构的激活强度则取决于其不同的使用频率,句法信息限制论元结构的选择,而论元结构又随动词的识别影响句子结构的构建。在例(9)和例(10)中,“witness”本身在句中既可以作为施事出现,也可以作为受事出现,所以在例(9)中,“examine”不能即时地对题元角色起到限制作用。但在例(10)中,“evidence”只能作为受事存在,“examine”可以直接对题元角色起限制作用。正是这种语义的限制作用使例(10)较例(9)更便于加工,加工难易的不同并不是由句法结构分析的不同造成的。
以上两种理论和模型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句法的早期加工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语义信息是否会对句法分析产生即时的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产生了很大分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议,理论语言学在经历了以意义研究为重和以结构形式的句法研究为重的两个时期之后,逐渐明确了语义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汉语语法研究在重视句法研究的同时,语义研究不容忽视。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分歧,并且对于句法和语义信息究竟在句子理解的过程中如何即时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争议,这是理论语言学依靠静态思辨论证的研究方法不能解释的。心理语言学理论更注重从人类认知规律出发探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加工的认知机制,是未来厘清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C740122];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YYC01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2014SJD415]。)
[1]方光焘.体系和方法[A].中国文法革新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何洪峰.句法结构歧义成因的思考[J].语言研究,2003,(4):26-31.
[3]胡明扬.语义语法范畴[J].汉语学习,1994,(1):2-4.
[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版)[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陆俭明.“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J].汉语学习,1990,(1):1-6.
[7]陆俭明.关于句处理中所要考虑的语义问题[J].语言研究,2001,(1):1-12.
[8]陆俭明.词的具体意义对句子意思理解的影响[J].汉语学习,2004,(2):1-5.
[9]陆俭明,郭锐.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J].世界汉语教学,1998,(1):3-21.
[10]马庆株.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J].中国语文,1998,(3):173-180.
[11]邵敬敏.“双音节V+N”结构的配价分析[A].沈阳,郑定欧.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2]邵敬敏.句法语义的双向选择性原则[C].中国语言学报(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史锡尧.论句义的表达和理解[J].汉语学习,1995,(6):13-17.
[14]王维贤.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论纲)[A].语法修辞方法论[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15]邢公畹.论汉语造句法上的主语和宾语[J].语文学习,1955,(9):25-27.
[16]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张黎.语义搭配律刍议[J].汉语学习,1996,(2):41-44.
[18]Frazier,L.,Rayner,K.Making and Correcting Errors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Eye Move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ly Ambiguous Sentence[J]. Cognitive Psychology,1982,(14):178-210.
[19]Friederici,A.D.Towards a Neural Basis of Auditory Sentence Processing[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2002,(6):78-84.
[20]Marslen-Wilson WD,Tyler LK.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J].Cognition,1980,(1):1-71.
[21]Truswell,J.C.The Role of Lexical Frequency in Syntactic Ambiguity Resolution[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6,(35):566-585.
(赵鸣 江苏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