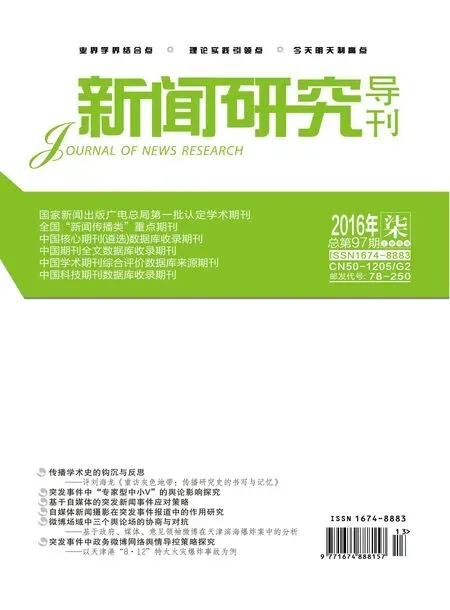从《悲情城市》看侯孝贤电影的艺术特色
吴 双
(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 南昌 330000)
从《悲情城市》看侯孝贤电影的艺术特色
吴双
(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 南昌 330000)
本文将重点分析侯孝贤电影代表作《悲情城市》,从电影视角、电影画面、电影叙事三个方面层层剖析侯孝贤电影的艺术特色,感受侯孝贤“冷眼看生死”的人生态度,走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
侯孝贤;《悲情城市》;台湾新电影;长镜头
一、《悲情城市》体现“关注人”的电影视角
《悲情城市》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最辉煌且最广为人知的电影,曾获国内外各项大奖。侯孝贤刻意淡化了电影的历史背景,用人的遭遇来反映历史的波涛汹涌,讲述个体与大时代抗争的悲情岁月。同时,他没有走很多导演的老路子,将把电影主人公设计为《勇敢的心》《圣女贞德》中那种极具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人物,用英勇无畏的人物来衬托历史的无奈和悲情,而是依旧回归到“用自己的经验,讲述每一个不一样的小人物”的创作起点。
《悲情城市》用宽美的画外音开启序幕,依旧延续了侯孝贤局外人的态度。剧中主角林氏三兄弟,一个是哑巴,一个是黑帮老大,一个是流氓。三兄弟性格各异,文雄重感情,文良狡猾,文清老实,但都是社会底层最常见的小人物。而这三个小人物却无奈地卷进历史的漩涡里,在“二·二八”时期,三人命运都被改变。文良因严刑拷打而发疯,文雄与黑社会斗殴而惨死,文清援助爱国青年而被捕,而文清这一哑巴形象则更是表达了当时台湾本土人“有苦不能说、有怒不敢言”,隐喻了台湾人在光复初期民族身份认同的困难。影片用一个小镇家族的命运,影射当时社会的黑暗,尽管描写的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都是彻彻底底存在于台湾。也正因如此,影片才让人唏嘘,才引发了经历过这段历史人的共鸣。
侯孝贤曾多次在媒体面前表示,自己最喜爱的导演是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因为小津的电影是极度克制,他的摄影机位永远摆放在日式榻榻米同样的高度,他总是运用缓慢悠长的长镜头,连镜头剪切都是极少的。他最喜欢用原节子、笠智众两位演员,而这两位演员也常常在不同的电影里饰演父亲和女儿这两个相同的角色。无论是在描述因为城市发展,儿女与父母感情逐渐变冷的《东京物语》,还是老父亲因为独生女儿出嫁,而暗自悲伤的《秋刀鱼之味》,他要讲述的电影故事始终是二战之后日本大众一种生活状态,讲述一种家庭的故事,讲述一个个家庭因为老人过世、女儿出嫁而走向分离的过程。[1]
小津安二郎克制的电影气质给予侯孝贤深刻的启示,使得侯孝贤的电影以个体生命经验为主要题材,以“关注人”为电影主题,运用固定机位,运用非专业演员。侯孝贤曾说:“人的生命本质,就是每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这样的电影切入点,所以在侯孝贤导演的21部作品里,无论是早期讲述侯孝贤童年人生经历的《童年往事》,或讲述叛逆少年成长为有担当军人的《小毕的故事》,还是到后来把视角放到讲述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的《好男好女》《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电影,侯孝贤始终把自己的电影集中在“关注人”这一角度上,讲述生命的本质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同于别人的独特存在。
侯孝贤的电影,始终用一种真诚的人文关怀,来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苦难命运,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从更深层次体现他对于人生和历史的思考,同时又将他的冷静思考集中于影片的叙事和视听语言中。正是因为这样的视点和主题,所以他的作品总能展现出浓浓的生活气息、隽永的人文关怀,使得看过侯孝贤电影的人或多或少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内地电影导演贾樟柯曾说:“《风柜来的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1995年我在电影学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因为我觉得很亲切,不知道为什么像拍我老家的朋友一样,但它却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
二、《悲情城市》镜头语言的真切
1983年,侯孝贤迎来其导演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完成了电影《风柜来的人》。从这部电影开始,侯孝贤彻底抛弃了前期的商业化风格,开始了用镜头还原现实生活的创作之路。从这以后,还原生活的真实便成侯孝贤作品永恒的追求。
为了追求电影画面的真实感,侯孝贤常常使用静止长镜头。他仿佛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别人的悲欢离合,有淡淡的关怀却保持绝对的冷静。侯孝贤曾经表示,自己电影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沈从文自传》,沈从文那种看待人世间的态度深深影响了他。无论生活多么悲伤,生活中有多少磨难,沈从文却总可以用佛家“冷眼看生死”的态度去面对,活得格外超然。侯孝贤便把这种人生态度运用“静止长镜头”传达给观众。
作为侯孝贤电影的代表作,《悲情城市》这部电影中长镜头的使用更为巧妙,一方面揭示了当时人物的复杂心境,另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大背景。而片中大量长镜头的使用,更使观众对这部电影叙事有一种延伸联想。好的电影应包括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延续。《悲情城市》中出现多达十次对林家饭厅这一场景的刻画,无论是影片开场,一家人在饭厅吃饭,还是到影片最后,几个人在饭桌上聊天,摄影机始终是不动的,这样的镜头语言不但展示了导演构思的巧妙,而且展现了侯孝贤冷静克制的特质。电影人物在固定的镜头里走来走去,无论是平静,还是哭闹,导演始终让自己保持一颗旁观者的心。特别要说的是,侯孝贤在这些场景中,将林家饭厅的门框作为一贯的镜头范围,使画面中的人都停留在这样一扇门里,但观众的视野却可以完全摆脱镜头的范围,观众可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段悲伤的历史。在这部影片中,导演不断运用视听语言来描写门,这有突出纵向景深的作用,加强了电影的空间感,从而使静止中的移动更为受到关注。侯孝贤如此鲜明的个人风格,正是由于他巧妙地使用了静止长镜头。[2]
侯孝贤曾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回顾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如《恋恋风尘》《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都像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理智的侯孝贤通过电影来回忆自己那段迷茫却又难忘的青春岁月。而这些故事之所以总能打动人,就在于侯孝贤的那种缓慢的镜头和淡淡的年代气息,总能让观众到达侯孝贤创造的那个时空,在时空中与导演产生共鸣。
三、《悲情城市》的诗化叙事风格
侯孝贤的电影除了真实的电影画面之外,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他电影中散发出的那浓浓的诗般气息。无论是早期的《童年往事》《悲情城市》,还是近期的《咖啡时
光》《聂隐娘》,都展现出侯孝贤统一文字与影像的导演功力。他的电影几乎没高潮和戏剧冲突,一切都是淡淡的,他用镜头的力量,使观众走进一个又一个“候氏意境”。
《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对于这一点便有很好的体现。首先便是宽美出场,轻缓的音乐响起,山间青雾弥漫,没有拍摄近景,只有几个人走在山上。而后,宽美的画外音随着镜头一直远去,九份这个小镇便在雾气的忽隐忽现中出现在大家眼前。侯孝贤就如同诗人一样,在电影开始叙事之前,便已经给观众描绘出一个淡淡的意境。
《悲情城市》最诗意的部分,是在日本童谣响起的时候。即将离开台湾的日本少女静子与宽美话别,两人相对无言,淡淡的童谣声响起,静子望着窗外,镜头出现了穿着和服在樱花树下跳舞的静子,宽荣在一旁弹奏乐器。镜头一转,宽荣看着静子送给自己的书上的题诗——《同运的樱花》: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宽荣和宽美讲起这首诗的背景:“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随着宽荣的声音,字幕再次出现《同运的樱花》诗句,配合日本特色民谣,如诗如画。而在影片快要结束的部分,文清知道自己即将被捕,一家三口站在海边的火车站。伴随着悲凉的长笛声和火车轰轰隆隆的声音,夫妇二人迷茫地望着远去的列车,没有一句台词,便已经透露出无法与命运抗争的无奈。[3]
电影创作这一点上,侯孝贤与内地导演霍建起十分类似。两人的御用编剧,一个朱天文,一个思芜,都不是专业编剧科班出身,所以她们创作出来的剧本往往不受传统剧本格式的限制。然而相比之下,霍建起导演更追求电影画面的唯美感。《那山、那人、那狗》《暖》《秋之白华》《台北飘雪》等一系列霍建起导演的作品,电影叙事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但是其在电影画面上追求如同山水画般的优美,给观众仿佛徘徊在画中的美感。而侯孝贤的电影不单单在叙事上做减法,对于电影画面,侯孝贤也力求还原真实,使得其电影有一种粗糙的生命质感。
侯孝贤用其眼中富于深意的吉田光羽,逐渐拼接成一个广大的影像世界。起初看起来并不相关,人们往往要到故事的结尾才明白他要讲些什么,出现的部分可以体会,未出现的部分可以想象。侯孝贤的电影平平淡淡,但是电影发生了,如同一首好诗一般,让你久久停留在那个美好的意境里。
根据对侯孝贤电影视角、画面、叙事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品味到侯孝贤电影中那浓浓的生活气息,体会到侯孝贤电影中所传达出“冷眼看生死”的人生态度,更感受到侯孝贤对于生命的尊重。
[1] 唐纳德·里.小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8-19.
[2] 张心侃.论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运用[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05):39-41.
[3] 苏牧.荣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42-443.
J905
A
1674-8883(2016)13-01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