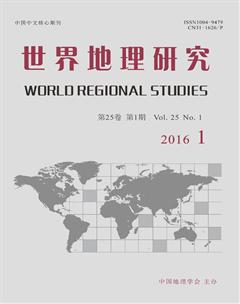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
宋涛 李玏 胡志丁



摘 要: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关键词:地缘合作;东南亚;合作机制;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
中图分类号:K119 文献标识码:A
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世界已步入新的地缘经济大时代[1]。东南亚位于亚洲的东南部,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自古既为贸易往来和文明交互的前缘,又是世界大国势力角逐的“战场”。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成为东南亚地区政府间、区域性、一般性的国家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东盟南增长三角等不同尺度的多元合作成为推动复杂地缘环境下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由“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部分组成,分别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东盟是中国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区域,尤其是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合作不断加深。在上述地缘发展态势下,科学和系统地判读东南亚地缘合作的类型、形式与机制,探索中国与东南亚地缘合作的潜力,是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合作、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支撑。
地缘合作理论源自于地缘政治学,现代地缘政治学由19世纪的拉采尔、麦金德、契伦、鲍曼和马汉等学者共同推动下确立[2,3],其核心思想是探讨地理对国家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影响[4]。地缘政治学中存在着辩证的博弈关系:地缘对抗与地缘合作。前者是早期地缘政治学争夺帝国霸权及冷战阶段的主题;后者则是后冷战时代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5],也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直接结果[6]。就地缘合作而言,跨境区域(cross-border regions)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是研究的重点[7-9]。Grundy等[10]对亚洲的增长三角进行了研究,认为其缺乏自下而上的市场合作机制,在一体化程度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和北美。李铁力[11]重点对边境地区贸易、商品和投资的一体化经济空间进行了研究。胡志丁等[12]亦对地缘次区域合作的战略作用进行了阐述:地缘次区域具有区域经贸文化合作、民生安全保障等多重功能。综上所述,已有学者对地缘次区域合作的具体案例进行了探讨。但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对地缘合作理论框架的探讨,对该问题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案例支撑。因此,本文在系统提出地缘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东南亚区域地缘合作的类型与机制,从而为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争取与周边国家深入地缘合作提供地理学角度的理论依据。
1 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
1.1 地缘合作的概念
地缘指的是两个国家或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上接近而产生的政治关系,其常用语境来自于“地缘政治”[13]。区域合作是某一地理范围内的国家或区域为谋求共同目标,而调整本方行为,形成区域间集体行动,以适应区域当前及未来的需求[14]。结合以上概念,地缘合作指的是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在战略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所进行的区域合作。
1.2 地缘合作的空间层次
地缘合作按照空间层次,可分为地缘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个层次(图1):
1) 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理板块的地理单元划分,主要是针对具有社会普适性的社会经济问题,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为目标,通过国家共同体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就是地缘区域合作的典型代表。
2) 地缘次区域合作指的是若干邻近国家和地区间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以流域、湖泊等空间要素等为合作空间域,为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信息等安全需要而开展的经济、设施、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15],如澜沧江-湄公河、图们江等次区域合作。
3) 地缘经济区合作则以地缘区位为基础,由邻近的两国或多国划定区域[16],在区域内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贸易联合,给予特殊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赛[17]对经济一体化类型的划分(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以生产要素流动为尺度,尺度越小,实现更高级别一体化的可行性越强,如地缘经济区合作达到了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甚至更高层次的合作程度。东南亚在地缘经济区领域的实践形式丰富,包括“新柔廖增长三角”、巴淡工业园等。
1.3 地缘合作的机制
基于不同空间层次的三种地缘合作模式在合作原则、运作方式与合作领域方面表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图2):
1) 地缘区域合作的主体为基于地缘的多国联合体,成立中央协调联络机构来处理多国的经济、社会协调事物。从性质来说,地缘区域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的,多国的联合协调组织,强调国家层次上多国政府的区域合作平台搭建,坚持各国主权的独立,非强制性、开放性和协商一致,反对权力让渡。从功能来看,地缘区域合作对外强调同大国的地缘博弈,及自身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对内则在贸易、关税、安全等领域进行同盟化合作。
2) 地缘次区域合作模式中,围绕着某些地缘要素(如湄公河),建立起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NGO)、私营企业和学术专家等多方参与的多元伙伴关系[18]。主导部门多元化,可以由某些国家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主导或地方政府主导。在多元利益的参与监督下,达成合作共识并被广泛接受,通过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实施,提升次区域合作的时效性。
3) 地缘经济合作区聚焦于经贸、产业合作,其可行性在于跨国相邻区域在垂直分工与合作、规模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运作方式包括跨国的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开发区等。涉及的产业包括农业、机械制造、金属工业、化工、电子、贸易、服务业等。
2 研究区地缘合作的类型
2.1 研究区概况
东南亚地区共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11国,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1亿。东南亚地处热带,具有热带季风和热带雨林气候,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多民族地区之一。早期的东南亚依托其丰富的粮食作物、热带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形成了种植业和初级产品开采为主的结构单一的地域类型。20世纪下半页,东南亚各国逐渐转向了国家干预下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日益扩大,2010年人均GDP最高的新加坡达到了近5万美元,而缅甸的人均GDP则仅仅为831美元(表1)。
2.2 地缘合作的空间层次
2.2.1地缘区域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或“ASEAN”),成立于1967年,成员包括东南亚地区除东帝汶以外的其他10个国家。东盟成立初期,侧重于对区域内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较多,90年代后逐渐开始转向区域内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2003年,东盟领导人提出东盟的目标为“东盟共同体”,旨在达到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一体化。
(1) 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旨在形成单一市场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具体包括产业方面优先在汽车、电子等行业实现一体化。货物贸易方面的目标是到2015年东盟十国实现取消除敏感产品之外的其他所有产品的关税。截至2014年,东盟在开放货物贸易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加坡和文莱已经完全实现了东盟内部关税保护。2010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也取消了大部分《东盟商品贸易协定(ATIGA)》框架下从其他成员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除了部分敏感的农业商品和其他物品之外。2010年以来,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个东盟新成员国家也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但要达到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年的目标,柬埔寨还必须加快降税进度(表2)。
(2) 东盟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旨在促进东盟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方面的协商与合作。针对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与地区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卖、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东盟安全共同体构建出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安全防务对话、磋商和决策机制框架,提出了东盟各国在防务方面的优先实施的合作项目等。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关爱社会共同体、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基地和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合作项目包括贯彻“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关注弱势群体,推动对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关爱,为脆弱群体提供受教育机会,使其获得技术和知识,加强社会福利机制,共同保护地区文化遗产等。
2.2.2 地缘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或“ADB”)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简称GMS)机制,旨在以务实的、注重结果的方式强化次区域优先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这些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电信、旅游、农业、环境、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贸易和投资的交叉领域。其中亚行为出资方和组织者,对具体项目的研究和实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1) GMS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主要的成就即为显著增强的物理联通,包括三大GMS走廊:东—西、北—南、南部经济走廊。这些走廊通过二级公路的连接和促进运输、贸易走廊沿线综合方案的制订而加强,综合方案包括交换航权的扩大、边境管理的协调等内容。其中泛亚铁路(昆明至新加坡)和曼昆(曼谷至昆明)公路构筑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联通的交通动脉。GMS次区域交通运输协会已在GMS次区域商业论坛中成立,旨在加强交通运输业的专业化和协调,并给予私营部门在地区运输和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的设计和实施[20]。
(2) GMS能源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联网项目是GMS计划的核心,旨在通过各国基础电网联网和私营部门介入水电项目的建设来形成GMS区域电力贸易系统。GMS国家的能源协作主要体现在电力贸易方面。老挝和缅甸为东南亚的净电力出口国家,电力贸易收入是其国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表3)。2012年,老挝与泰国和越南签署了备忘录,到2015年前向泰国提供7000兆瓦,到2020年前向越南提供5000兆瓦的电力。除了传统能源,GMS开展了更广泛的能源合作,GMS提出促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获取和供应安全;增进能源部门市场整合,并且推进部门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3) GMS资源保护及其它项目。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核心项目包括农产品的次区域贸易、使用气候友好和促进两性平等的生物能源技术、农业信息网络服务、健康和安全的食品交易平台建设、生物多样性走廊规划等项目。此外,GMS的重点合作领域还包括边境和重点地域的水供给,其他市政设施和服务、教育、健康和社会安全及产业和贸易方面。这些领域既有亚行直接贷款的项目,亦有政策、技术支持的非贷款项目。截至2011年,GMS已动员超过15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贷款资助的项目,也包括ADB和政府所提供的技术援助、其他能力建设和知识创造活动的关键支持[22](表4、表5)。
2.2.3地缘经济区合作—东盟南增长三角
“增长三角”是指由地理上接近的多国部分地区组成的小范围的跨国(境)经济区[24]。东盟南增长三角是东盟最早出现的地缘经济区,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于1990年成立,因此又被称为“新柔廖增长三角”(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其基本概况如表6所示。
(1) 东盟南增长三角的经济双边合作
东盟增长三角通过双边及多边的开发区、免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载体,实现了有重点、重实效的地缘经济合作[25]。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协商决定成立联合开发委员会,通过一系列进出关手续简化等优惠政策,来共同发展廖内群岛(主要是巴淡和宾坦岛)。廖内群岛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巴淡工业园占地500公顷,自成立以来即吸引了索尼、菲利浦、东芝等大型企业入驻。巴淡岛作为免税出口区,吸引的新加坡投资领域包括机械制造、金属工业、化工、电子、贸易、服务业和涉农产业。同时亦是国际门户港,与爪哇机场构成印尼两大空中枢纽。2012年1月,就有约6.2万新加坡人到访巴淡岛。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经济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柔佛州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通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22],吸引了大批新加坡企业入驻该区域。新加坡依赖于柔佛州和廖内群岛来满足国内淡水的需求。新加坡也为柔佛州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促使其成为马来西亚工业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2) 东盟南增长三角的地缘分工
南增长三角参与各方存在着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地缘关联性。三国区域地缘相近,新加坡距巴淡岛20公里,距柔佛州2公里。三国文化背景相近,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属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以转口贸易为主,与柔佛和廖内的经济往来原本就比较频繁。各个国家地区在产业链分工方面具有较好的互补性。新加坡结合印尼廖内省和马来西亚柔佛州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扩展经济活动空间,尤其是从柔佛州获取水等战略性资源。柔佛州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得到新加坡和印尼的帮助。而印尼则依托于廖内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通过参与增长三角,形成了巴淡岛引领下的全方位开发。总之,南增长三角依托于地缘优势和经济垂直分工体系(图3),充分利用新加坡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发展迅速,是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较为成功的范例。
2.3 合作机制
(1) 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侧重于经济、政治、安全一体化的国家联盟多边合作组织,已形成了包括领导人会议、工作层对话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该种合作机制由各国中央政府协商形成共识和行动计划,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发起合作,在关税、贸易、设施建设等方面这种合作机制使沟通和协调定期化,有效地保证了双方合作的顺利开展。企业与社会在协商一致后参与到决策中,非政府部门(NGO)、私营部门和学术精英等也参与到方案的制定当中。
(2)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是非正式多边合作的典范,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灵活性。从性质来说,次区域合作的形成主体包括了区域性合作组织、银行、政府下派机构等。GMS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为亚洲开发银行(ADB)主导,各国中央政府参与下的多层次多元合作,包括部长级会议、司局级高官会议和各领域的论坛和工作组会议,该种模式强调国际援助下的项目推动发展,涉及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和农业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GMS次区域合作依托地缘政治,推进经贸领域的深入合作[26]及禁毒、疾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等非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27]。
(3) 东盟南增长三角侧重于经贸、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合作。合作机制包括部长和较低层次的官员会议,并在各相关合作领域成立了部门工作组,针对特殊政策区域,如工业园区,则成立管理委员会来统筹该区域的综合发展(图4)。然而整体来看,东盟南增长三角以新加坡与柔佛州、廖内群岛的双边合作为主,缺乏多边的协调组织机制。
3 中国—东南亚地缘合作展望
东南亚地区是我国地缘合作的重点区域,包括了地缘合作区—东盟;地缘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边境合作区等。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中国与东盟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边境安全等领域的地缘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由对话关系已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起日益完备的合作机制。未来双方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政策,重点提升各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自贸区的利用率。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升交通、人员、信息、货币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水平。目前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产业链上都位于中下游,双方应充分挖掘比较优势,共同推动区域产业链的升级。此外,在反恐维和、防灾救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跨国人才交流、扶贫等领域应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
中国与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方面,GMS次区域合作是其重要抓手。泛亚铁路、昆曼公路、瑞丽江电站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是GMS次区域合作的重点,也是我国西南边境开放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建立区域铁路联盟为契机的基础设施互通外,推进体系和制度的互联互通,加强产业、金融和民生领域合作,将有助于打造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利益共同体。此外,中国还应与GMS国家中的老挝、缅甸、泰国在湄公河流域开展联合执法,深化安全合作,为湄公河航运提供安全保障。
东盟南增长三角的地缘合作集中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主要载体为巴淡工业园等特殊政策区域。借鉴南增长三角模式,我国应积极开拓与推进跨境合作区建设,尤其是推进瑞丽、景洪、河口、腾冲等重点门户边境城市跨境合作区的先行先试。鉴于东盟内部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多种地缘合作模式应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推进。
4 结论
地缘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促进国家和地区在战略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区域合作的有力抓手。本研究从地缘合作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东南亚地缘合作的模式、成效与机制。通过对三种不同模式地缘合作的比较研究,本文有如下理论发现:
地缘合作依据空间尺度可分为三种类型:地缘区域合作、地域次区域合作和地域经济区合作。在较大空间尺度,某一地缘范围内以国家为单位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国家联盟体为地缘区域合作,强调通过国家共同体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以流域、湖泊等空间要素等为合作空间域,若干国家和地区接壤地区之间的跨国界区域,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所形成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是以地缘区位为基础,两国或多国划定部分区域,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或组成区域性经济团体,从而推进经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就地缘合作的内容和机制而言,以国家为单位的地缘区域合作旨在通过国家联盟的形式,强调高层次领导共同参与国家联盟政策的制定及中央协调联络机构的建立,就某种秩序的权威性及约束力达成共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行动力,在关税、贸易、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效益显著。地缘次区域合作则是利益主体多方参与的非正式合作,强调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信息等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具体项目合作。地缘经济区的机制在于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或组成区域性经济团体,从而推进经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产业开发、贸易协作方面的潜力巨大。
本研究有助于我国多种地缘合作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将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经验与借鉴。诚然,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合作案例分析,跨境合作区等重点空间载体的政策机制等,以验证本研究的理论探索。
参考文献:
[1] 陆大道,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 2013,68(6):723-727.
[2] 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M]. 林尔蔚, 陈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3-17.
[3]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34-51.
[4] 乔纳森·哈斯拉姆.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M]. 张振江,卢明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7-22.
[5] Luttwak E N.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20(3):17-23.
[6] 卢光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3):11-16.
[7] Bunnell T, Muzaini H, Sidaway J D. Global city frontiers: Singapores hinterland and the contested socio-political geographies of Bintan, Indone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6,31(1):3-22.
[8] Perkmann M. Cross-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significance and drivers of region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3,10:153-171.
[9] Shen J.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C]. In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ng Kongs role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2011.
[10] Grundy W C, Peachey K, Perry M. Fragmented integration in the Singapore Indonesian border zone: Southeast Asias “growth triangl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2):304-328.
[11] 李铁立.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4.
[12] 胡志丁,骆华松,李灿松,等. 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J]. 人文地理, 2012, 27(3):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