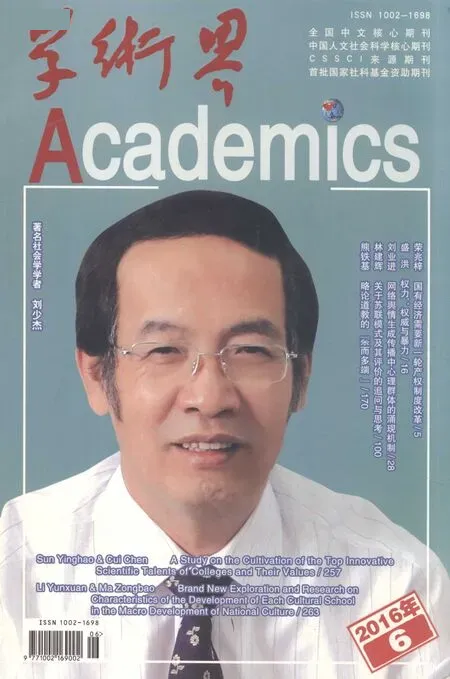从“制度红利”到“制度陷阱”〔*〕
——嘉庆十四年的漕务改革与制度困境
○ 袁 飞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学术史谭·
从“制度红利”到“制度陷阱”〔*〕
——嘉庆十四年的漕务改革与制度困境
○袁飞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蚌埠233030)
嘉庆初政,统治者想通过“咸与维新”,试图整顿当时严峻的漕运,然这一期望随着嘉庆十四年(1809)各省漕弊的大量揭露而破产。面对日益严重的漕运困境,嘉庆帝再一次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治漕运动。然而因为制度的路径依赖、帝王品行等因素,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根本无法跳出旧制度的束缚。此外,因为没有培育出一种认同制度、敬畏制度的文化生态,让制度和人形成良性互动,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漕务;积弊;制度;改革;困境
有清一代作为关乎国家经济命脉、赖以定国安邦的漕运,经清前中期几位统治者一个半世纪的励精图治,无论是从组织机构、典章制度还是人事安排上都趋于完善。〔1〕泰极否来,乾隆晚期以降,漕运开始呈现衰落状态,〔2〕漕运中长期积累的弊端全面暴露。1799年刚刚亲政的嘉庆帝面对日益陷入困境的漕务开始有所作为,试图彻底整饬积重难返的漕运。但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并没有使漕运状况得到改善,反而愈加严峻。至嘉庆十四年(1809)随着各省大量漕弊被揭露,嘉庆帝意识到他前期所作的努力皆徒劳无功。面对日益严峻的现状,统治者不得不再筹除弊治漕之法,于是又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治漕运动。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文献,拟就这一年嘉庆君臣治理漕务的努力作一探讨,以管窥帝制晚期面对危机时的路径选择及制度困境。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引 言
嘉庆十四年(1809)二月初五日,镶白旗都统率领下属赴北新仓领取当年的兵米,却发现所发放的仓米都霉烂了。在拒绝支领后,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上奏报。接到奏报的嘉庆帝十分震惊,立即派大学士禄康、费淳二人前往北新仓会同查仓御史清泰详查。结果非常严重,“该仓稄米六万余石,分贮十四廒,米色俱属霉黑。”〔3〕如此堪忧的状况之前竟然没有一点风闻,在天子脚下的京师真会出现这种贪腐吗?为了进一步确证,嘉庆帝又派户部尚书德瑛等六人急赴北新仓进一步调查,此外还要对禄米、南新、海运、富新、兴平等另外五仓进行彻底查验。
不久,德瑛等人的调查结果与前次无异:“霉湿米石多系受潮蒸变,各仓米色皆不纯净,而北新一仓尤甚”,并当即将米样包封与各仓米色、数目开单呈览。〔4〕显然,情况要比上次更严重。为了慎重起见,嘉庆帝再派军机大臣庆桂等三人进行第三次详查,结果依然与前两次如出一辙,“廒座多有霉变气息。迨验看米色,有甫经发变尚分颗粒者,亦有霉烂太甚现已结块者”,“将各仓米色与前日德瑛等进呈米样详悉对比,均属相符。”〔5〕面对确凿的事实,负有管理责任的仓场侍郎和各仓监督一致声称原因不在于管理和看护的不当,而是因为交上来的漕米就是潮湿的,所以入仓后很快霉变。这一理由很快得到有力的佐证。漕督萨彬图和巡漕御史喜敬在盘验过淮帮船时发现,有很多帮船装载了米色不纯的漕粮,其中“江淮三六两帮兑运漂阳县米石,色黯者居多,缘该县米质本属潮嫩,又经由大小汛湖适值阴雨连绵,起剥时稍有湿润,未及风晾,以致色有不纯。”既然漕粮潮湿,这些入仓的漕米怎么能逃过监兑官弁的检查,又怎么能避开漕粮过淮漕督的盘验,最终交仓时又怎么能避开仓场和坐粮厅的检查?面对事实,嘉庆帝确信“其弊不在粮户而在州县旗丁”,且在“盘验过淮之时,如果该漕督等认真抽查,则旗丁亦岂能朦混?”〔6〕如何解决?嘉庆帝没有一个成熟可行的办法,只能暂时一如既往地警告官员们:“如又有此等弊窦,一经查出,更当加倍惩处”。然而,这样的警告不知传谕了多少次,漕务困境依然如故。
二、积重难返:漕运制度红利的终结
虽然经过清前几朝的改革和发展不管是从组织机构、典章制度还是人事安排上,漕运制度在这一时期内都趋于完善。〔7〕然而,这种状况从乾隆中晚期开始便出现转变,漕运制度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弊端开始爆发,至嘉庆时期已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至嘉庆十四年时,嘉庆帝在这一问题上清醒了。京通仓米霉烂之事还没结束,山东道监察御史李鸿宾就把他家乡江西省存在的漕弊统统揭露出来,漕运黑幕从这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李鸿宾指出“南省各漕情形或亦相类”,〔8〕也是积弊相因。嘉庆帝同意李鸿宾的看法,“所奏情形均属切中时弊”,“江西如此,恐他省亦复不免。”而仓场中的漕米霉变正因为“南省有漕各州县及旗丁等于收兑时相率舞弊,遂致运通米石一经入仓即有霉变等事”,遂强令有漕各省督抚必须认真剔除各种积弊,确保征收的漕粮符合规定。〔9〕然而,漕运中的弊端何止李鸿宾所奏!从南到北,从收漕到交仓,弊端无处不在。官员们的奏报让嘉庆帝真正认识到漕运的真实状况。巡视天津漕务御史吴荣光指出,在北运途中漕弊比比皆是,特别是粮艘经过山东、天津、通州等地时运丁经常盗卖漕米。〔10〕此外,交兑漕粮时也会出现种种弊端:
“南粮抵通停泊,未经起卸之先,每帮有验费,有窝子钱;起卸之始,除照例个儿钱外复有后手钱。每帮每项约制钱一百串或数十串不等,皆由帮丁凑敛(交)坐粮厅号房书役及经纪得受,……该经纪等得有陋规,遂与旗丁通同舞弊,搀灰使水,种种可虑。”〔11〕
针对吴荣光所奏,嘉庆帝特别传旨给仓场侍郎,要求他于当年“新粮抵通时,设法严密稽查,将从前索取陋规种种各情弊一律剔除。”〔12〕然而,仓场也是处处弊端重重。不久,京通各仓又被查出问题。京城太平仓中有四廒被查出粮米霉变,通州中、西二仓所贮“白米尚未完竣,已亏短至十数万石之多。”〔13〕在查办过程中,嘉庆帝对南粮北来途中的一些弊端也有所掌握:“南粮在途往往盗卖米石,并于亏短之后有用药发涨情弊”,而“粮米用药多在天津一代地方所为,其药名为五虎下四川”。〔14〕统治者通过自己掌握的情况隐隐约约地感到漕弊可能有着惊人程度,并要求有漕各省督抚“将一切弊端和盘托出,不可稍涉狥循”。〔15〕
浙江巡抚阮元却报喜不报忧,他表示:“(浙省)漕白正米俱系慎选足额,责令道厅监兑,向无亏短折交情事”,〔16〕漕米也没有中途上岸,“各水口亦无囤粮铺户”。嘉庆帝则明确表示其“所言殊不可信”,并责问他如果“该军船于未经开行之先,其米石早有亏短,又何待沿途盗卖乎?”〔17〕在嘉庆帝的一再督促下,各省漕弊纷纷被揭露。
江西巡抚先福指出,江西漕运的问题:一是各州县原收米色本非一律干洁,此外还用银赴省“向米铺买凑低潮之米充数,其帮船伍丁多所熟识,索得兑费,通同一气,即为上兑。迨至贮舱日久湿热霉坏,抵通虑难交卸,则又先期赴通贿商经胥人等”。二是向漕米中灌水,其手法花样百出,让人骇异。根据向漕粮中灌水方法的不同,旗丁们冠以夹沙糕、打针、开天舱、自来润、发汗、大翻方等称谓。〔18〕之后,署江西巡抚袁秉直除了证实上述漕弊外,还查出尚有一种武生衿监“专藉包漕渔利,揽收别户额粮,折钱入己”,用次米抵漕,“挜交不遂,阻扰滋事,最为漕务之害。”特别是那些没有领过牙帖的米局和奸牙,“平日藉买民间仓米为名囤积丑米,待至漕仓开兑之先广设栈房,结联衿蠹,遍事招徕”。〔19〕
湖北、湖南两省的漕弊经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汪志伊和署理湖南巡抚朱绍曾调查,两省的漕弊颇为相似。湖北省的漕弊有:劣衿包漕,以次充好,胥吏舞弊,私收折色,倒卖漕粮,发水搀糠等。〔20〕湖南省漕弊有:胥吏舞弊,劣衿铺户包揽代纳,以次充好,私收折色,偷盗漕粮,州县浮收,旗丁勒索,向漕粮中搀糠、发水、用药等,无所不至。〔21〕
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浙地区,一直是“最困者莫甚于漕”,〔22〕漕弊重重。虽然浙抚阮元表示浙省漕运状况很好,但嘉庆帝并不相信。而继任浙抚蒋攸铦虽然也没有完全揭露浙江的漕弊,但他对嘉兴府漕弊的调查至少证明了嘉庆帝对阮元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蒋攸铦在奏报中指出:嘉兴府的“刁生劣监包揽好米价值,另买丑米挜交,所在多有州县受其挟制,隐忍滥收,实所不免”,而且“各帮丁力疲乏,积渐已深。”〔23〕至于江南的漕弊,两江总督阿林保指出:“州县以旗丁需费借口任意浮收,旗丁以长途用度不敷肆行横索,竟致有加无已”。〔24〕阿林保认为漕弊产生的根源是旗丁用费不够。之后不久,常熟县生员沈旭向都察院呈递的条陈却推翻了阿林保的说辞。沈旭在条陈中痛述了江苏“吏治日益废弛,即如收漕一项,官吏多通同舞弊,任意浮收,甚至差提锁押,乡民不胜扰累。”〔25〕沈旭的条陈证明了阿林保的敷衍和避重就轻。
江浙的奏报情况让嘉庆帝开始疑惑督抚们的汇报可信度到底有多少。随后,太常寺少卿马履泰详细地奏报了每帮漕船完成一次漕粮任务需要承担的各种陋规,〔26〕揭露了漕运过程中的一大黑幕,进一步证实了嘉庆帝的疑惑。根据马履泰的奏报,就一帮50只漕船而言,一帮一年为应付陋规就要多花去白银7400余两,平均每只漕船每年多付出白银约148两。若除去养家之月粮,以及“沿途遇浅起剥,杨村至通起剥,加以本船头舵、水手、人工、本丁、副丁、人口盘费,沿途盐、菜、柴、煤,又有艌船工料、修理篷桅、铺舱席竹、锚缆器具,尚有琐碎不敢尽开者,所费实多,应得之项委不敷用。”〔27〕很快,马履泰所报得到了巡漕御史程国仁印证。
很显然,督抚们向嘉庆帝奏报的种种漕弊是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并十分默契地选择了对最大的漕弊——“陋规”保持缄默不语。究其原因,他们或多或少是受益者。但无论是选择性的奏报还是主动性的揭露毫无疑问地展现了整个漕政体系的实际状况,最大限度地暴露了漕运中的各种漕弊,让嘉庆帝在这一问题上开始清醒。清前几朝通过有效的漕运制度变迁,极大地减少了漕运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漕运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漕政也发挥了最大的制度红利。然而当漕政的制度红利达到其边际时,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完全改革或创新,仅靠旧制度的修补是无法维持原有的制度红利。嘉庆时的漕运制度在积重难返的弊端影响下,制度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其所发挥的积极效果最终被消极作用所代替,漕运制度的“辉煌时代”已经终结。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皇上亲政之初,于漕务严加整顿,外省知所凛承,虽未能彻底澄清,亦不至若今日之甚。……今已阅多年,各省未免心存懈弛,漕弊又当厘剔。”〔28〕
三、“政出多门”:漕运治理的制度陷阱
大量弊端被揭露后,嘉庆帝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随后的十天内连发两个上谕,斥责大多数督抚之前的做法“未得要领”,指出:“各督抚总以旗丁苦累需索帮费,遂致各州县藉端浮收为词,而剔弊厘奸之要全未筹及。”〔29〕对统治者来说,当务之急不仅要发现漕运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而且还必须具有针对性,并能够上升为一种制度,通行全国。循着这一思路,督抚们开始筹划治漕之策。
巡漕御史虽为临时派差,却代表最高统治者和朝廷,系天子耳目,对于涉漕事务均有巡视、查察、纠劾、章奏等职权。作为巡漕御史的程国仁首先提出办法,他认为:“州县之弊在于折色浮收,旗丁之弊在于勒索帮费”,所以“欲杜受弊之实,必先清致弊之源”,提出八条除弊治漕的办法:1.佥丁宜慎重核实也;2.运丁宜禁止浮费也;3.巡漕衙门宜先肃清也;4.领运员弁宜防需索也;5.漕标委员宜遵例禁也;6.抵通交卸宜防掯勒也;7.开行停泊雇夫起载宜禁把持也;8.粮头伍长等宜选派妥实也。除此之外,重运不得携带多于规定的土宜,回空不许夹带私盐。〔30〕清仁宗颁布谕旨,“着将该御史条奏各款交有漕督抚、漕运总督、仓场侍郎分别查照,妥议办理,不得视为具文,致不肖旗丁有所借口。”〔31〕
不久,兵科给事中史祐提出几条“查禁之方”,立足点是从革除陋规入手,减少漕运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和人员。他建议:1.为了避免勒索克扣,所有旗丁运费应由州县扣解,就近封贴印花,按船给领;2.交纳给厅仓的茶果等银,在旗丁本地所领银两内由粮道库扣发,同经费银两一并解交通济库。三升八合余米收买价银由州县应解轻赍银内扣留,照数给领;3.大加裁省各种委派的催儧漕委;4.漕运总督、巡漕御史及各粮道所带书役应该确定额数,不得多派。另外,裁革各督抚大员随身不必要的杂役;5.旗丁到通交完漕米后,仓收回照请设限期。如果迟延,即行参办;6.通州巡漕御史不得仍用坐粮厅书吏,应从通州水道衙门委派;7.漕粮运京后应请分派一人立即驻扎大通桥,每日率同监督监视掣斛,防范讹索之事。〔32〕虽然史祐的立足点也是革除陋规,但革除的对象要比程国仁更具体,更具针对性。虽然规定越细,可操作性越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多,灵活性也越差,实际操作中就会遇到更多问题和障碍。
江西道监察御史汪彦博则从“民情、丁力、官廉”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1.根据监兑官、巡抚、运官、漕督、粮道、押领等官各自的责任和管辖范围划清界限,分别考成;2.运丁应领各项银钱改交兑米州县临时按数发给,无庸解交道库,其有藩库具领之项亦照此办理。凡粮艘经过的地方负责查禁各种涉漕违法行为;3.外省各属养廉应禁止摊扣,并不得有捐廉名目;4.各州县必须遵守(嘉庆)四五年间收漕之法。〔33〕
此外,礼科掌印给事中赵佩湘也从漕运体系外进一步揭露漕弊发生的缘由,他认为“各省亏空,辗转清查”,而各州县为了弥补库项亏空,“各上司计无所出,又巧增漕余名目”,〔34〕以致各州县任意浮收,浮收不已,从而折色。不肖州县既囊橐私肥,其上司需索漕规,运弁旗丁需索兑费,刁生劣监乘机挟制。因此,要革除漕弊,必须永远革除各省清查名目,严饬各州县不许借漕余之名浮收漕粮。〔35〕
官员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既有制度执行的问题,也涉及到相应的制度建设,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然如果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相沿日久,制度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制度不仅不能得到改善,反而变成了病上加病。〔36〕而这种制度累积,常造成机构重叠、前后矛盾,扯皮推诿、效率缺失,陷入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制度陷阱”。从清朝入关到乾隆鼎盛,漕运的发展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漕运制度建设却是日渐繁密,涉漕机构重叠建设,且多头管理,权责不分,模糊不清。因其时漕运制度的绩效仍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虽有弊端却能呈现出利处,保障对整个清王朝政治经济的贡献率。当漕运的制度红利从乾隆中晚期开始消减直至耗竭时,嘉庆时陷入危机的漕运制度更是积重难返。面对这种窘境,各地官员们提出的种种办法,从漕政体系来看无非是针对弊端或问题而欲建立的种种制度,姑且不论其“本”的治理之法是否有效,单从各种各样日益繁密的制度来看,问题也是非常大的。大量制度的设立,造成制度越来越复杂,制度越复杂,越容易交叉、虚置甚至前后矛盾,相互“打架”,执行成本就越高,甚至是无法执行,况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些办法还是一种倒退。在这种情况下,用一种有问题的新制度去弥补、调整和规范前一种有问题制度所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不但不能解决漕运困境,还会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从而加重漕运危机。没有制度上的真正变革,使得为了漕运能够勉强支撑而设计出的种种规章制度成了国家、社会发展的陷阱,这是嘉庆朝最大的悲剧。
四、无奈结局:制度改革的困境
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五年(1810)的上半年。正当嘉庆君臣还在继续苦寻良策之际,运河又传来了坏消息:山阳县境内运河大堤出现漫塌,塌陷决口宽至三十余丈,运道严重受阻,直接威胁漕运。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朝廷被迫立即将重点转移到河工治理上,有关漕运治理的这场讨论也被戛然中止。在这场讨论中,清仁宗不但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督抚们各不相同的意见反而使他更加不知所措。他只能寄希望于地方督抚的努力,“惟在该抚等严饬各地方员弁随时实力查禁,庶漕务日有起色,于恤丁爱民之道两有裨益。勿徒托之空言,视为具文也。”〔37〕清仁宗又回到了原点。这是这场讨论的最后结局,也是整个漕运治理的无奈选择,更是嘉庆一朝所有弊政改革和治理的最终归宿。
对清仁宗来说,他实在无法也不可能突破旧制度的限制。因为漕运制度经过前四朝的发展已牢牢地确立起来,而这种制度一旦确立,继任者不会轻易改变,这是制度的惯性所导致的,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嘉庆朝漕运陷入危机后,最高统治者仍然在传统的漕运制度内苦苦地寻求治理的办法。对清仁宗来说,只能通过“先存的心智构念”来处理和辨识漕运问题,并解决所面对的困境。而这种“先存的心智构念”则来源于其父、祖们所创造的“康乾盛世”及其之下的制度“报酬递增”。因此,清仁宗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的这种“心智构念”不仅要型塑他在漕政治理上的决策选择,而且还将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能为他所处的社会结构辩护,还能为诸如已经陷入危机的漕运制度这样的绩效找到理由。〔40〕于是,面对漕运危机,“政府行政的程式化、表面化,沉湎于驾轻就熟的经验方法,在碰到前所未遇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不是束手无策,就是套用旧法予以处理。”最终,王朝政府、统治者及其封建官僚阶层“越来越丧失一种制度创新的精神”。〔41〕因此,一种制度一旦确立,继任者不会轻易地去改变,“一朝之内的每一位登基皇帝都必须恪守开国皇帝定下的典章制度”。〔42〕
更准确地说,至嘉庆朝时,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漕运制度已经“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从而使这一制度进入了锁入(lock-in)状态,更加难以打破。〔43〕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让统治者明白改变一种制度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更加巨大,而这些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现实世界中都是无法承担的。更何况,对统治者来说一种新制度或方式给王朝能否带来好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是不可预测的。清仁宗至少明白,以当时蹩脚的漕运还可以将漕粮运到目的地,虽然效率非常低下,危机重重。而一旦改变这一漕运制度,所产生的巨大代价和成本未必比保持蹩脚的漕运要少,或许还会危及到他的统治。职是之故,清朝统治者往往会对制度经常进行边际修补,决不会动其根本。就像清仁宗治理漕运那样,总是在制度内提出各种办法对其进行修补,却没有采用动其根本的办法。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清代政治“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44〕当这种解决问题的统治法术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无法抵消制度所带来的弊端时,矛盾的爆发和危机的呈现是不可避免的。清朝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路前进的,而且越到后来,统治法术的效果越来越难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仁宗始终跳不出原来漕运制度的旧框框,面对日益严重的漕运危机,他千方百计在漕运制度内寻找解决的办法,结果还是令他非常失望,无法解决面临的困境。最终,延续的制度消磨了统治法术的有效性,在解决问题时只能“治标”,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久,弊端又会重现。
其实,制度能否发挥功效,还得看人的作用。制度由人设计,但制度设计的目的不会自动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实践。历代后继者改变或发展前人的政策、措施,屡见不鲜,一句话,没有一成不变的!继承与改变(革)相辅相成,关键在继任者其人的眼光、胸怀、才略。从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这几朝,都是在不断继承与改变的过程中,把清朝推向前进。但乾隆的后继者清仁宗与前几朝帝王相比,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平庸”两个字,是嘉庆皇帝的主要性格特点。〔45〕这就决定了清仁宗不可能有所创新,只能沿着原来的统治轨迹按部就班地走下去。由于缺乏统治“大才”,清仁宗在统治过程中总是犹犹豫豫、摇摆不定,在应对困境时更是缺少果敢的勇气、坚定的决心和恰到好处的治术。因此,即使漕运弊端已远远大于制度收益,清仁宗不会、不愿、不敢也不可能打破旧制度的框框,只能依靠官员们的实力效忠这样一个老套路。然而,乾隆晚年以后官僚制度越来越腐败不堪,“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46〕特别是和珅专权之后,腐败之风更盛,所以乾隆留给嘉庆的决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盛世,而是一个内创累累、积重难返的疲败之局。〔47〕等到嘉庆即位后,官员腐败的“积习已成,不可挽救”,宦途蒙蔽失实,请谒公行之风盛行。〔48〕试问,嘉庆将漕运治理的重任寄于这一群人能行得通吗?
对于漕务,清仁宗是想通过各有漕省份的整治来达到彻底治理漕务的目的,即通过局部的解决达到整体的和谐。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确保每一个局部都不能出问题。清仁宗治漕思想是把重心下移到有漕各省,因此史祐、汪彦博和程国仁三人就通漕而言的办法必须放在有漕各省的具体环境中考量,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个方面又陷入到“法多必乱”的繁杂窘境中。面对漕运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议论,清仁宗并没有找到一个妥当的办法,只能一再希望大臣们能够“忠心体国”,“尽心除弊,有犯必惩”,“实心办理,不在空言”等等。而这种将漕务治理寄托于官员们的主动性和他们所谓的“忠君爱国”之心的无奈选择,却在日益腐败的官僚制度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此,从深层次上说,如果没有培育一种认同制度、敬畏制度的文化生态,让制度和人形成良性互动,到头来制度也只是在文字中落实、在实际中落空。正如秉持“有治人无治法”统治原则的清仁宗那样无法跳出旧制度的束缚,只能在制度窠臼中拼命挣扎。
注释:
〔1〕韩书瑞、罗友枝:《18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2〕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296页。
〔3〕〔8〕〔11〕〔13〕〔15〕〔16〕〔18〕〔19〕〔20〕〔25〕〔26〕〔28〕〔32〕〔33〕〔34〕《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胶片》,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1844-004、03-1751-026、03-1751-044、03-2359-006、03-1845-046、03-1751-099、03-1751-105、03-1752-019、03-1845-046、03-1752-042、03-1752-014、03-1752-025、03-1752-020、03-1752-025、03-1820-007。
〔4〕〔6〕〔9〕〔10〕〔12〕〔14〕〔17〕〔29〕〔31〕〔35〕〔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卷207、207、211、212、212、214、217、219、220、220、229。
〔5〕《清仁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7〕吴琦、肖丽红:《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1〕〔23〕〔24〕〔27〕〔30〕《宫中档嘉庆朝朱批奏折胶片》,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208-071、04-01-35-0208-063、04-01-35-0208-043、04-01-35-0191-027、04-01-35-0208-041。
〔22〕魏源:《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卷46。
〔36〕〔4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74、127页。
〔40〕〔4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131-137、136页。
〔41〕李宝臣:《文化冲突中的制度惯性》,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281、284页。
〔42〕罗茲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45〕稻叶君山:《清朝全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6页。
〔46〕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322。
〔47〕关文发:《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43页。
〔48〕印鸾章:《清鉴》,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539页。
〔责任编辑:陶然〕
袁飞(1980—),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漕运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14FZS025)后续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10XNL01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05),安徽省宣传文化领域(社科理论类)青年英才基金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