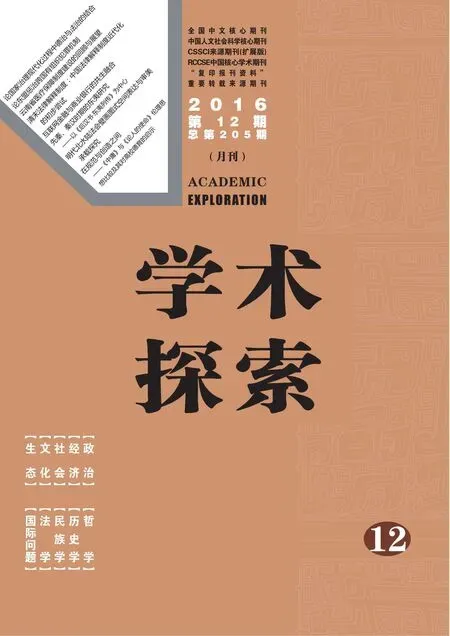在规范与创造之间
——《中庸》与《论人的使命》伦理思想比较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董云川,王 颖
(1.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2.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在规范与创造之间
——《中庸》与《论人的使命》伦理思想比较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董云川1,王 颖2
(1.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2.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庸》的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是社会性存在的假设上,《论人的使命》则通过强调人个性的至高地位,建立了创造伦理学。比较两者异同,对我国当代高校德育有如下启示:(1)在社会规范引入与道德创造能力激发间实现平衡;(2)重视德育中学生的主体地位;(3)让超越性道德标准和具体道德原则结合,探索高校道德教育的新生存样式。
社会性;个性;规范;创造;德育
伦理学是离不开人的学说,对人性的假设是伦理思想立论的基础。《中庸》是中国儒家道德伦理经典,它通过论述天与人性的内外贯通来建立伦理思想,对后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论人的使命》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Н.А)的伦理学著作,它通过对人至高地位的肯定,开创性地提出了创造伦理学,对一直以来居于强势地位的规范伦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立足于不同的时代及社会背景,两部著作在人性论及其伦理思想上都有很大差异。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可以对不同伦理思想传统有所窥见,亦对我国当代高校德育有启示价值。
一、天与人性的合一及规范伦理思想
纵观中国儒家思想,其倡导的均为社会规范伦理,即将人的社会化作为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认为社会规范具有最高的伦理价值。无论是孔子及其之前所推崇的“事亲”的人伦规范,还是董仲舒之后强调的“事君”的原则,都属于实现人的社会化所应遵守的规范。然而,社会规范和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冲突,直到《中庸》才在理论上联通了规范与人性,这使“道”内化为“德”成为可能。因为在中国古代,道德的实现被看成“道”内化为“德”的过程,如“中国最早典籍中‘道’表示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规则,‘德’则强调人对‘道’的认识、践履而后有所得”。[1](P3)又如朱子认为“道”是普遍规律和必然要求,“德”反映了主体对规律和原则的把握。“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2]
《中庸》这一过程的实现,是建立在前世对人性与规范关系认识的基础上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讲述了我国自古对人性的认识的发展过程。[3](P10~16)西周之前,人的地位是不如神秘力量的。那时普遍认为道德规范是由外在的神秘力量决定的,而神秘力量的至高地位要求人无条件地遵从规范。但这不等于规范真正内化为了人的德,因为此时人们并没有搭建任何联通神秘规范和人内心的理论通道,只是迫于压力表面服从着至高的规范。直到周人通过反思“小邦周”灭“大邦殷”的历史,悟到“人”对国家政权更迭的重要性,逐渐才开始重视人的地位。到了春秋时期,规范的内容从“敬神”变为了处理人伦关系,即“崇礼”。“礼”的内容涉及了“人”,但其来源并不是人心,准确地说并非遵从民众之心,而是来自于统治阶级,渐渐被僵化为教条,无法获得广泛人心的追从。后来,孔子提出了“仁”。相比“礼”,“仁”是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存在,不需外求,反求诸己就可以得到。但是,孔子对人内心的过分重视,以至于外在规范与“仁”无法实现完全融通。“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孔孟并不是从 ‘天’‘天命’所标识的外在客观必然处,而是以人之主观面,从主观情感处引申出道”[5](P23),即认为仁是内心道德,反求诸己可以得到,不用向外求。“孔子撇开客观面的帝、天、天命而不言(但不是否定),而自主观面开启道德价值之源、德性生命之门以言仁。”[6](P18)孔子后学则致力于弥补内外的间隙,使外在规范与人心内在依据实现联通。《中庸》就是很好的代表,它将外在规范内收于人心,使得道德准则与人性得到贯通,道有了内化为德的基础。
《中庸》中的“天”相当于道德规范,它是被“人性”赋予意义后的天,但又规范着人。“天命之谓性,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具体来说,首先,“天”是被人赋予了意义的天。“人”之所以能赋予“天”意义,是因为“人性”本来有道德意义,“天”是道德自觉的“主体向外的价值投射的结果”;[8](P17)其次,人又被“天”所规定着,即受到自己投射出的“天”的道德约束。“天”与“人性”仿佛胡塞尔所述的先验意识与意识对象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义投射的关系。[9](P60~61)“道德自觉的人,赋予天价值意义,又从自己创造的价值天中获得道德修养的动力,确保道德的至上与超越性。”[10](P17)这个内外贯通的过程,起点和终点都是人内在的道德性。在人性与天联通关系的认识基础上,演化出《中庸》的两条主要的伦理原则:第一,道德规范的特性与人性是一致的,如“诚”既是“天道”又是“人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1]“诚乃是人作为人即必须首先完成的具体天命,或是人作为人为完成其纯粹天命而必须完成的第一天命。”[12](P168)第二,人性本真不会因为顺从规范而被淹没,反而是会因依托社会秩序而得到肯定。“君子力求不断深化其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不但不与其社会责任冲突,反而必须体现在其社会活动中。”[13]这就倡导人对外化的秩序、规则天然地顺服,如素位安分——“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14]“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4]等思想,又如对“五达道”“三达德”必须遵守。“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15]
“天”和“人性”为什么能够同一?《中庸》中的“天”是关于社会的规范,它有两个最高标准“中和”和“诚”,具体就是一些道德规则,比如五达道、三达德。而人,我们知道,是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三重属性的存在。《中庸》之所以认为人性和社会规范完全同一,是因为它所看到的人,仅仅只有社会属性,即将人假设为社会人。关于人的地位,在论述中虽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其最终目的不是将人地位提到最高,而是以此作为规范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支撑。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人,而没有看到人的创造性。如举了孔子和颜回等圣贤的例子,期望所有人都向他们学习,但是却没有提到人与人间的差异。这就说明《中庸》倡导的是社会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关注大众、普通人,强调人的社会性。
二、人的至高地位及创造伦理思想
与《中庸》形成极大反差的是《论人的使命》,其中对人的个性、自由、精神性和创造性的高扬以及创造伦理学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开辟了更宽广的伦理学视野。
《论人的使命》是基督教倡导者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其伦理思想的提出建立在其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书中包含了作者对宗教虔诚的态度,但却反对旧约中将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君王的形象,认为面向上帝所要寻找的是人的地位。“人与上帝的交往既是人的精神自由的体现和人的独立个性的证明,同时也是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16](P19)这种思想体系的建立和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自身的思想倾向分不开。从社会宏观背景来说,俄罗斯文化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Н.А)著作中对上帝的热切追慕就带有这一社会文化的烙印。从个人思想倾向而言,别尔嘉耶夫一生都十分关注人的个性价值。所以,他的学说就在承认上帝的基础上,赋予拥有个性的人至高无上的地位。
别尔嘉耶夫论述人的本质是从人的两个来源谈起的。他认为一方面,人是上帝在虚无中创造的;另一方面,人又从虚无中被赋予了自由。所以人的本性,既要体现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即上帝的创造性,又要体现自由的特性。在自由面前,人甚至可以摆脱造物主的统治——“造物主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并要求他进行自由的创造,而不是要求他表面服从自己。自由的创造是被造物对造物主伟大呼喊的答复。”[17](P45)“我的哲学类型的独特之处在于,我的哲学根基是自由,而不是存在。”[18](P82)既然,在人与上帝间,人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那么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如何呢?别尔嘉耶夫提出了与社会性相对的个性的概念。他认为个性与个体不同,它属于精神范畴,个性的价值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价值。“个性是别尔嘉耶夫精神哲学的主体,是他心中的理想人格,因而个性是实现精神的自由创造的载体。”[19](P48)人的个性独立于种族,独立于社会。个性价值的发挥依赖于创造。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个性的和创造的。
在对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其伦理思想逐渐凸现出来。别尔嘉耶夫认为个性的价值高于国家、社会、阶层、阶级,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精神的复兴来解决,而不是靠法律、惩罚等。对于人性,“人走向外部,就永远搞不清事物的含义,因为含义的谜底就隐藏在人本身中”[20]“道德现象的原初没有社会来源,道德行为首先是精神行为和有着精神来源的道德的原初现象”,[21](78~79)所以不能用社会压制个性。他反对社会道德,“伦理学的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和社会舆论对个性的精神生命和个性道德评价的自由的残暴统治。”[21](P79)反对规范伦理学、法律伦理学,他认为这些伦理学否定了个性,忽视活生生的人,将社会日常性加给所有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沉沦在了“常人”[22](P20)中,这将使得人的道德水平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别尔嘉耶夫提到了三种伦理学:法律伦理学、救赎伦理学和创造论理学。法律伦理学是社会规范伦理学,他认为这种伦理学以人的社会化为目的,使个性服从社会确定的禁忌。并认为法律规范主义只适用于道德低级的情况,无力改变人的内在精神。救赎伦理学将人从规范中解放,引入内心深处,认为救赎和爱是最高的善。创造伦理学是别尔嘉耶夫提出的开创性思想,它不同于规范伦理学注重规范,而是注重人的个性、精神和自由;也不同于救赎伦理学所认为的生命的道德目的是自我拯救和赎罪,而认为道德应该是创造性地实现真理、创造价值。这里的创造是指心灵向另一种存在过渡,精神性克服肉体性。“个性通过自己的良心自由而与聚合性的精神相连,而不是通过社会强迫和社会权威。”[21](P180)“个性道德责任的觉醒是人类基本道德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好把道德现象从社会的统治下,从社会学的范围内解放出来。”[21](P81)“真正的自由不是执行法律的自由,而是创造新事物的自由,创造价值的自由。作为自由的存在物,人不仅是善的法律的体现者,而且是新价值的创造者。人的使命不仅是遵循善,而且还要创造善。”[24](P59)他认为应该改善大众的生活,将他们引到自由的精神创造中,从而使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他提出了伦理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创造、自由和同情,在爱中实现道德。
综上,《论人的使命》和《中庸》因对人假设的不同,其伦理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庸》只是将对人的重视作为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论述规范的权威性。这里说的人性是只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因此人性与社会规范可以完全合一,人面对社会规范应该全然接受。而《论人的使命》则将人的地位提到了至高,高于社会、国家、阶级、阶层。用人的创造性去否定规范的权威性。甚至认为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也不应该让人绝对服从上帝,而是要面向上帝去寻找人独立的位置。别尔嘉耶夫还认为人的个性高于社会性,作为精神、自由、个性存在的人高于作为肉体、受压迫、社会化的人。个性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生存中心,是独特的生命,遵守社会规范只是关注了社会日常性,或者只关注了如海德格尔所述的“常人”,忽略个性。为获得个性就要反对规范对人的奴役,人要努力创造,在创造中使个性得到展现和丰富。这就是他提出的创造伦理学,在乎的是人有创造道德价值的自由,人能对道德进行自由的评判,而不是遵守国家法律或社会规范、与其他人一致。
三、对当代高校德育的启示
《中庸》和《论人的使命》通过对人性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伦理思想,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有着启示作用。
首先,在引入社会规范和激发道德创造能力之间获得平衡。
《中庸》所看到的人仅仅只有社会性的特征,其肯定人性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赋予社会规范权威性,使得规范对人的限制成为合理。而《论人的使命》则认为人的个性是高于社会性的,认为人的创造高于规范,不应该受到规范的限制。事实上,无论是用社会性忽视个性,认为规范高于人的创造,还是用个性驳斥社会性,认为人的创造高于规范,这两种思想都是有失偏颇的。
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统一的存在,个性与社会性不是完全对立的。“独立的个人是在经验中不存在的抽象物,同样,脱离个人的社会也是如此,只有这样的人类生活才是真实的:它既可以从个人方面考虑,也可以从社会,即普遍的方面考虑;而且,事实上它永远包含着个人的和普遍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23](P27)因此,社会规范与人的创造间应该是相互限制的。斯腾伯格在其学说中就为我们提出了解决之道。他通过讨论“规范”和“高校教育”与创造性的关系,认为它们对创造性有影响。他认为,一方面应该用规范去限制创造力。“限制不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很有价值的。创造力本身就需要限制和规范,因为创造力的行为来自人类与限制人的那些人抗争的结果。”[24](P308)另一方面,也要对规范进行创造性的思考,看这些规范的本质是什么,受限者的年龄如何,规范不能限制创造者的自由,不能阻碍创造力。
我国当前高校道德教育过分重视国家意志、社会规范,而忽视了人道德创造的自由。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的道德发展水平最多仅能达到柯尔伯格所述的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阶段,而无法达到普遍道德原则取向阶段。教育应当领先于当前的社会,引领社会发展,而不仅仅是再现当前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古代的道德教育是着眼于过去、近现代的道德教育是着眼于现在,那么当代国际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则是着眼于未来的。……这种道德教育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培养道德创造和道德选择能力为核心,将品德培养与个性发展相统一作为基本原则。”[25](P372~373)当前高校德育应该借鉴《论人的使命》中创造伦理学的内容,肯定人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对规范和规则进行价值重估,对于阻碍人长远发展的规范应该进行批判,重建道德价值,使道德水平得到发展。对于一些限制性的处理社会关系型规范,应该重新进行思考,因为“人接受道德不仅是为了协调与他者的关系,同时也是为确认自己的存在,协调自己内心世界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达致内心的和谐。……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拥有对自身的德性判断,是自身道德的发起者和创造者。”[26](P128)如果说曾经的社会要求“德育在继承和传播文化,维持和保存既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人们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促进人的社会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7](P109)那么随着社会运行方式从控制式改为民主式,“现代德育功能也表现为由再生性、维持性功能向超越性功能发展”。“所谓德育的超越性功能,是指德育的先导性、前瞻性、创造性和发展性功能”,[27](P109)即对现有规范的价值重估和超越。
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像《论人的使命》那样完全否定人的社会化,因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8](P87)。更不能拒绝社会规范,如涂尔干所说“设想道德是个人的创造物,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因为那样,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让道德完全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29](P14)人与社会间的矛盾必须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实现,德育应该要为人实现社会化助力。其实,应该承认符合人发展、本体意义上具有真理性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存在的。对于这类规范,可以引导学生用道德自觉的方法来遵从,如《中庸》所述用自明、择善、固执和慎独的方法。总而言之,就是在高校德育中应该合理平衡规范引入和创造激发间的关系。
其次,从《中庸》《论人的使命》可看出二者均注重人的主体地位,这值得我国高校德育借鉴。
《中庸》所述的人虽然还仅仅停留在社会性的层面,没有获得个性的觉醒,然而,比起此前“敬神”的社会和完全不考虑外在行为规范的内心依据就强加规范于人的社会来说,它是具有进步性的。将“天命”与“人性”联通起来,一定程度上使人减少了对外在规范的畏惧,人屹立在了天地之间,体现出对人地位的重视。它蕴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前提:规范只有具有人性,人才会遵守。其所倡导的对规范遵守的方法,也不是惩罚和训诫的外在方法,而是立足于人自身、体现主体性的修身方法,比如自明——从自身找原因,择善固执——坚守先验的善根和先验善决定的具体规则,慎独——有专注内心、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等等。杜维明认为这些方法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自觉,“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主体性的深度上,他才算是‘慎独’了”。[30](P26)而《论人的使命》则完全高扬了人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自由不应该受上帝、国家、社会、阶级和他人的限制,人实现精神上的创造就是最高的道德。
道德是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实现道德修养的决定性因素是道德主体自身。“道德活动主体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成为道德活动的主体。否定了人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就否定了人的道德活动的主体地位,就取消了道德活动本身”[31]。只有经过主体内心的思考、判断、省察,道德认知才能转化为自主的道德情感、意志和行为,道德主体也才会对自身的道德行为负责。“作为道德律令的实践理性主要是主观精神,或者说首先是主观精神,因为是主体自觉、自愿的行动”[32]。然而,我国当前高校德育却往往忽视人的主体价值,德育内容过多地注重社会规范,甚至将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德育的主要内容;德育方法偏重外在灌输,不关注学生自我的道德评价能力的提高。学生是教育的主体,道德教育尤其如此,我国当前德育应该借鉴《中庸》和《论人的使命》中对人重视的思想,强调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性地位。具体而言,德育内容、过程、方法和目标都应该从学生出发,考虑学生的特点,让学生通过道德自觉来提高道德境界。
再次,超越性道德标准和具体性道德原则相结合。
两部著作在人性论和伦理思想上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它们都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论述伦理问题,这对于现代高校德育非常有借鉴价值。事实上,超越性的标准与具体性原则往往能相互促进,具体原则是超越标准脚踏实地地支撑,超越标准是反思和批判具体原则的依据。
《中庸》中关于道德规范的论述有两个层面,一是超越性目标,即诚与中和;一是具体原则,即五达道、三达德。在宏观目标上,《中庸》中的“诚”是一个超越性的标准,普通人必须下功夫和努力才能达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33]它保证了道德的神圣和庄严性,为人的道德发展提供了一个终极的追求,有利于促进人的道德境界不断提升。此外,《中庸》还提出了“中和”的概念,作为道德自觉的另一最高标准。“中和”代表的是一种和谐的思想,要达到的就是个人素位安分、心平气和地遵守规则,这样社会才能井然有序。为道德建立了超越性价值,充分保证了道德神圣性和至上性。这是对人主观能动性的无限肯定,依此鼓励道德主体尽其所能去实现道德自觉。当然,《中庸》还不忘提出具体可行的道德要求,即要处理好的五种伦常关系,遵循知、仁、勇三种道德原则。这使超越标准落在实处,具有操作性,更容易被人理解和实施。不仅如此,还多次举出道德榜样的例子,如颜回、孔子、舜等,虽然仅是普遍参照系而没有关于人与人间个性差异的相关论述是不足的,但客观上这些具体的道德形象还是使道德行为有了参照和可操作性。
《论人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完全不逊色。除了在宏观上提出创造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创造、自由和同情,作为伦理的最高标准,还依据这些原则对具体的诸如谎言与真理、良心和自由、国家、革命和战争等十个伦理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例如提出了关于劳动的原则,即应该追求创造性的劳动,不是使个性在劳动中社会化而是个性更大的个体化;又如在关于婚姻和爱情的问题上,别尔嘉耶夫认为婚姻不能仅作为一种社会日常性事实,而忽视了以其最终的意义爱情为基础;又如关于人的理想问题,他认为“应该为人的理想形象斗争,为作为自由的和本真性,即与原初性相关的存在物的个性而斗争,反对任何从社会日常性里确定这个形象。人的理想首先是个性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则是来自于个性的理想”。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论述,使得完善的伦理体系得以建立。
我国当前高校德育在宏观层面,可以借鉴《中庸》前瞻性地提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超越性道德目标,从高度上引领学生道德发展,为其追寻人的至高价值提供导航;也可以借鉴《论人的使命》提出德育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学生处理所有道德问题的标杆。同时,在具体层面上,可以提出不同阶段高校德育的标准,让形而上的追求有立地之处,使学生在追求高远目标时,不至迷茫和自卑;也可以针对一些热点道德问题进行引导,既有榜样和案例,又分析不同学生的特点。另外,高校德育中不但要有处理社会、国家、阶级问题的相关讨论,还要讨论与学生个性发展相关的问题,关心活生生的每一个人。还应该促使大学生用终极追求去反思具体规则,推动社会道德的发展,这个过程将更充分地激发主体性的发挥。
总之,通过对《中庸》与《论人的使命》中伦理思想的研读与比较,能够对我国当代高校德育发展有所启示。我们应该在规范与人的创造性间做到良好平衡,既强调学生的道德义务,还应赋予其道德判断、创造的权利,维持自由、个性与规范、社会性等价值在高校道德教育中的张力结构,拓展创造性规范,探索当代高校道德教育的新生存样式。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朱子语类》卷6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论语·述而》
[5]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6]牟宗三.心性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中庸·第一章》
[8]崔秀军.中庸人性论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1.
[9]涂成林.现象学运动的历史使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0]崔秀军.《中庸》人性论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1.
[11]《中庸·第二十章》
[12]武晓明.“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李广良.“中庸”的智慧深度——中庸和中庸研究的新动向[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
[14]《中庸·第十四章》
[14]《中庸·第十四章》
[15]《中庸·第二十章》
[16]陈红.别尔嘉耶夫人学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4.
[17]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8]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M].雷永生,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9]郭丽双.对客体化世界的反抗——别尔嘉耶夫思想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20]БердяевН.А.Смыслтворчество.М.,2002,С.55.
[21]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2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4]罗伯·史登堡,特德·鲁巴特.不同凡响的创造力[M].洪兰,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
[25]钟启泉,黄志成.西方德育原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6]孙其华.创新精神的培养与高校道德教育改革[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27]李康平.德育发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约翰·马丁·里奇等.道德发展的理论[M].姜飞月,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0]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1]JamesArthur,EdueationwithCharacte,rLondonAndNewYork[J].RoutledgeFelme, 2003,26.
[32]Kennon M Sheldon,Lauar King,Why Positivepysehology 15 Neeessyar,Ameriena Psyehologist,2001,56(3).
[33]《中庸·第二十章》
〔责任编辑:李 官〕
Norm and Cre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Ethical Though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On Human’s Miss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NG Yun-chuan1, WANG Ying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2.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e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human beings are social existence, while On Human’s Mission established creative ethics by emphasizing the supremacy of personality. A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eping balance between norm and creation;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subject status; combin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moral standards with specific moral principles.
sociality; personality; norm; creation; moral education
董云川(1963— ),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王 颖(1982— ),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G410
A
1006-723X(2016)12-01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