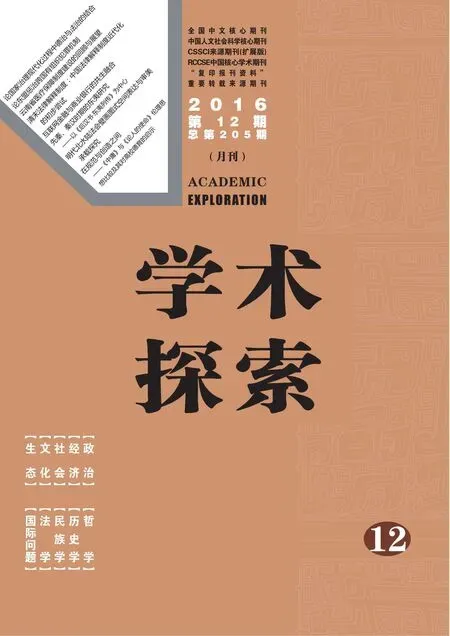法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动物保护立法困境
付 琳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333)
法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动物保护立法困境
付 琳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333)
中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与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全然不符的滞后,法律缺位造成无法可依的困扰,致使业已存在的冲突无法得到依法有序的解决。本文从“效率-公平”从法经济学视角入手分析我国“动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实对立关系,研究法律需求与立法困境的矛盾对立点,提出我国动物保护立法路径。
法经济学;动物保护;法律需求与法律市场
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早已完成,并于2009 年 9 月18 日正式公示征集意见,但时隔多年仍未实施。2015、2016连续两年的全国两会中,都有与会代表提报出台《禁止虐待动物法》、禁止猫狗肉制品流入餐饮市场,网络总支持率和每日支持率均排名第一,但仍旧无法将立法纳入日程。两会议题的网络投票数量及排名可以说明,中国的法律缺失状态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动物保护立法需求。中国的动物保护现状及存在法律需求的层面,以及立法保护的障碍和阻滞等便纳入本研究视野,希望可以从“效率-公平”法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通过揭示我国动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实对立关系,研究法律需求与立法困境的矛盾对立点,达到析出我国动物保护立法路径的目的。
一、动物保护与法经济学理论上的动态互构
动物保护与经济学二者之间有着历史上的渊源,而新教伦理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动物保护获得观念认同和立法结果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与其他理论相较,法经济学分析框架有着不可替代的适用性。
(一)法经济学与动物保护在理论和效用上的同源性
人与动物的关系在“经济”一词未产生时已经存在,总体看是产生于畜牧、养殖,而后根据动物各自不同的本性,发展为经济动物和伴侣动物等不同种类的用途。基于主体论中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中“用”的主体是人,动物是用的“对象”,[1]因此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一命题产生于如何更好地对动物进行“利用”使之服务于人的经济学思索中。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学问题一直可以追溯至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及阿道夫·瓦格纳甚至更早。[2]而边沁正是动物权利保护理论的开创者,边沁1800年将“动物应该有权利”提至英国国会探讨时遭到哄笑,但随后边沁以强大的逻辑能力说服大量国会议员。边沁在其哲学论述中提出动物能够感知痛苦,他同时注意到了“感知痛苦”是理性思维的基础,而对痛苦本能的逃避是所有生物的共性,包括不同肤色的人种。“仁慈”应当具有可观察到的方式才令人信服,人若处于价值核心中,应当充分地通过减少其他生命的痛苦来显示人性。就此,以反对残酷对待动物为主旨的“仁慈主义运动”[3]成为现代动物保护伦理的开端,随后英国出台了《牛尔法案》旨在禁止虐待农场动物,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印证了人对动物的保护可以给人性的良善方面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效用之后,英国于1911年正式出台动物保护法并沿用至今。
在动物福利议题上展开的博弈,促进了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并且,以功利主义视角审度,对动物实施必要的保护为英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福祉,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事实上的促进作用,现在英国高度现代化的、符合绿色环保指标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均得益于二百多年前提出的提高农场动物福利的要求。
(二)新教伦理对经济与动物保护的同期促进
当“天职”(Beruf)一词被转化为“上帝赋予人的职责”,这种“职责”就被代之以“现世的工作”。新教伦理提倡荣耀自身以彰显上帝的荣光,旨在敦促新教徒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为上帝服务。[4](P47~48)既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对动物的保护获得宗教伦理上的支持。笛卡尔的二元论将动物视作没有本能的机器早已饱受诟病,但其狂热追随者尼古拉·马勒布朗士却认为动物没有痛感、恐惧、欲望、智力,所以上帝要保护它们,而人类要做到上帝的要求。正是基于当时的英国社会逐渐认同了动物没有吃禁果、犯原罪的情况下就让它们感知痛苦是不公平的,进而才逐渐认同了应当对动物实施保护的观点。
阿奎那在论述“理性生物与无理性生物的差别”问题时曾经指出:无理性的生物不能主宰自己的行为因而没有自由,应该受奴役,它们存在是为了理性生物的利益,但人不能残忍地对待动物,不过这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对动物残忍也会将这种思维转移到对待其他人的方式上。[5](P7)人们从“神造”到“进化”的认知过程所激发的理性思索能力开始使人类的智识水平真正从唯心主义窠臼中剥离,而作为地球生命物种之一的理念也逐渐生成,直到发展出伦理学的对生命的敬畏。阿尔伯特·施韦泽提出只有当一个人自我约束、遵守帮助一切他能够救助的生命的原则,只有当他摆脱了伤害任何生命的方式,才是真正具有伦理观念的人,自此,“理性”的内容中除了利益衡量、刺激经济发展之外,终于囊括了对其他物种的责任。
(三)动物客体论下的法学分类与立法成就
而基于人本主体对其他客观存在物的可长期利用,以及人类对生态伦理上的责任,爱尔兰政治家马丁1822年说服了英国的下议院,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动物福利保护的《马丁法案》,随后,保护动物的相关法案在欧美国家迅速开展,如1850年法国的《格拉蒙法案》、1866年美国的《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1876年英国颁布《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以禁止虐待作为立法切口,经历百余年时间后,欧洲大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与最早问世的动物保护法典一脉相承,各自在不同国家的公法和私法领域受到保护。
如今对“动物”已经形成了标准的法学分类并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即:实验动物、经济动物、工作动物、陪伴动物、野生动物、用于体育、娱乐和展览的动物,分类说明不同类别下的动物“用途”和对待方式均受到法律约束,超出法定“用途”和运用不恰当的方式对待动物,即将被视为不法、不道德的行为而遭到严惩。《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提出对“动物”法律中含义的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许多动物权利论者将其视为动物权利获得主体性的一个胜利性标志,但基于传统法理对权利的概念建立于法律对人类利益的保护上,国际上仍然存在包括环境法、民法在内的许多部门法学对动物主体地位的“存在”以及实现方式有着颇多尖锐争议,甚至在居于客体地位时权利位阶上亦存在着解释学上的分歧。[6]但动物保护理论在法理学上拓展了“虐待”的客体对象和“权利”主体多样化的可能性,并且在西方神学式微的社会环境下,因由“权利”的生长与包容和经济实践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法律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具有力量的信仰,动物保护立法亦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与文明发展的写照。
(四)全球化条件下动物保护法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发展较早,同时又是WTO现有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这使环境保护、动物福利上的约章与产品贸易产生连带关系,也为WTO协定的起草或者修订中制造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力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的壁垒条款创造了条件。动物保护相关的法案不仅在各自属地被有效地运用,还在国际贸易之间被约定遵循,如果某项产品不符合动物福利的规定,且被该产品在此国家的客户抵制,则该项贸易势必受到影响。如2002年,乌克兰向法国出口一批生猪,经过60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到达目的地之后,却被法方拒绝入境,理由是这批生猪在途中没有得到充分休息,违反欧盟和法国有关动物运输途中福利的规定。[7](P41)
对我国而言,如果进口产品的市场环节中出现了不符合条例的现象而被禁止进口,将是进出口贸易中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并且,这种合法性抵制和禁止可以名正言顺地被作为贸易的条件标准和准入限制。由于在我国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立法方面的阻滞,不仅我国大陆地区的肉制品出口遭遇困境,海外华人所出售的食品安全也常受到质疑。除不符合条例的对外贸易经常受到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起的抵制外,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也曾有人将源自我国的虐待虐杀动物的图片制作成大型标牌高高举起以示抗议。我国动物保护方面的落后,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形象。
二、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理论迟滞与机制匮乏
立法与法律实施条件及保障机制,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畜牧业比重、食品卫生监管等存在复杂的交叉性关联。中国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需求与法律缺位,主要在理论停滞、官方机制匮乏、文化陋习与经济结构、黑色产业链与隐性经济损失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立法阻滞。
(一)理论迟滞与立法需求的对立
没有一个严肃的法律的肇端,动物保护连发展的空间都不存在,动物保护相关立法缺位使社会乱象不得定纷止争。从清华学生硫酸泼熊,到贵州民族节日虐杀水牛,这些残忍行为在法律所保护的价值对象上,无论民法还是刑法的可介入性都是有限的。动物保护的问题目前仍只停留在社会层面,以网络骂战或人肉搜索闹剧的形式,进行着无法控制走向、无法定量,只能以一种模糊的道德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不具有确定性的私力来取代本该是公权力进行的社会控制。
其一,我国学界在动物保护性立法上忽视使理论发展落后而迟滞,无法作为立法支持。相较于以对人的权利进行维护为主旨的传统法学领域而言,对动物进行法律保护显得无足轻重,更遑论权利地位等探讨。为数不多的进行动物保护方面法学研究的学者也受制于无休止的“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主体还是客体”等争论缠杂中,我国的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的困境很大一部分缘于理论场域内主观忽视与客观的发展迟滞。在“是”与“应当”的问题上,国际上集中于动物的权利主体资格上的争论,即无论基于主体论上作为客体上的被保护对象,还是权利论中作为主体享有基本权利,“应当对其保护”的一致性的目的认同早已跨越。而我国动物在客体地位上应当被保护的理念尚未获得共识,这应当视为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国法学理论上的巨大落后,且基于这一落后的相对性,客观上致使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在意识层面和社会认知的立法前期建构中,被动地处于过于超前的状态。
其二,已立法国家的理念超前性使法律移植和借鉴缺乏在我国社会层面的可接受性。我国民众对动物保护的认知形成了极严重的两极分化,即先进者与发达国家理念同步,乃至更先进;落后者尚处于对“动物权利”全然不知,停留在笛卡尔时代的将动物物化的阶段。[8]这种差异在城乡之间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也存在着东西部地区的显著差别。我国的《动物保护法(草案)》根据已有的动物保护立法经验进行了部分的法律移植,但在一些处置方式上存在着理论与我国现实上可接受度的对立。例如,对不能查明的无主犬猫以及流浪犬猫进行“人道处理”,此种“人道处理”包括安乐死和无害化尸体处理,而在立法国家和地区,执行安乐死的法条是建立在有权机构对社会公众进行长久而充分的告知义务,并且在以绝育方式控制流浪动物数量方面,进行过长期的有效努力的基础上的,但假使我国在官方组织并未进行过此方面的救助努力前提下,就将“安乐死”纳入动物权利法条,则处理方式过于轻率;再例如,对流浪犬猫的医疗与绝育,在科学饲养方式以及社会层面的认知、接受和动员条件未进行系统普及和立法先导性培植就进入立法实施阶段,则一方面还未能获得广泛的纳税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会使爱护动物但对科学饲养方式不甚了解的社会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
其三,理论迟滞使道德规范远超越法律规范发展。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同步性,既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又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法治化程度,“一些具体的规范,它们可被确证具有普适的,一致的或相似的内容,且决定了我们对该社会印象的规范、价值及秩序的差异。”[9](P35~37)在动物保护方面,社会对于虐待虐杀动物行为与道德性、正义性的关联程度普遍提高,不仅限于“动物是否有生命权”的动物权利论探讨,而是进入了西方动物保护立法路径中业已经历过的阶段——虐杀动物是对人性的亵渎。然而,在反对虐待虐杀的社会认同已经具有普遍性时,法律规范还未确立,法律理论还在权利主客体关系中纠结,致使私力救济优先于公力救济被公众选择。高速拦车救狗事件与虐杀动物引发人肉搜索事件每年数起,特别是虐杀动物几乎全部引发人肉搜索行为和网络暴力行为,由此引发的道德伦理与立法争论也极为频繁。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这一规则在虐杀者、偷盗者、捕捉流浪动物运输贩卖者眼中被偷换为法不禁止即自由。这种态势下产生了一道巨大的沟渠,分割两种极端:一边是呼吁动物保护的人们不得不采取甚至可能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私力救济方式,在法律的边缘游走;另一边是为恶者和旁观者对法律的嘲弄与漠然。
(二)法律运行需求与官方机制匮乏的对立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在救助金额总量固定的情况下,有组织统筹的资源调配较之单打独斗的救助行为将更为节约、有效。与客观存在的现实法律需求相比,我国不仅在动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缺位,还一直未建立官方组织机构运行的动物保护机制,这意味着即使《动物保护法》颁布,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实施效果,势必导致立法后出现的法律资源不均衡、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情况。以城市流浪动物为例,我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与立法配套的流浪动物救助与领养机制,正确对待流浪动物的方式得不到行之有效的宣传,而正确的认知,即对正当性的普遍、广泛的认同,才是立法、守法最直接的基础。在动物保护立法后的法律运行需求方面,由于缺乏有权机构的先导性的组织为法律运行进行预调过程,可能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无效投入。
尽管民间组织在动物权利保护方面发挥着微薄的效用,但我国各地民间动物保护组织,不仅在职能上无法代替公权力的机制效用,且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其一,经费不足,缺乏统筹。流浪动物救助、医疗、绝育和免疫注射等完全依靠志愿者有限的集资,不能有效维持城市流浪动物基本生存,更无法控制流浪动物数量。其二,组织结构松散,力量微薄。由于民间组织“民间”的弊端,在我国体制下无法发挥同等参与人数所可以发挥的最大作用,在与地方政府部门、机构协调时受到忽视,在跨地区救助合作方面行动力有限,对虐待虐杀行为无权实施合法控制。其三,由于缺乏法定保护依据,只能采取没有合法权利代表依据的私力救济。例如,在遇到偷盗犬猫、违法贩运等特殊情况下被迫盲目冒进,为了维护动物的生命权、人类的健康权而参与高速拦截等极端动物保护行为。其四,技术不足,缺乏保障。在自发实施救助动物的行为时,由于缺乏支援条件和救助技术,志愿者容易造成对自身的伤害,也不存在针对此种行为的鼓励性表彰或安抚政策。其五,存续艰难,后继乏力。由于法律依据和人员不足,许多民间动物保护组织生命周期很短,并且在自发组织的救助行动中锻炼出的具备一定救助能力的人员,出于不被认可、生活入不敷出等因素退出民间动物保护组织,造成大量人员流失和技术资源浪费。
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偷盗、虐杀、虐待、遗弃等理论上应当受到公法制裁的行为却缺乏处置机制,此种情况下空谈立法也是对立法的可执行性的否定。有权机构的制度性缺失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意味着权利主体缺失,这使得立法目的具有先天的残缺。因此,对我国现实存在的法律需求而言,需要设立官方组织机构,实施监督权和诉讼权。
三、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对立法进路的阻滞
(一)区域经济结构与不均衡发展限制立法实施条件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着眼点,而我国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习惯等影响,经济结构各不相同,与动物产业相关的经济结构在部分地区占有非常庞大的比重,而地区经济结构与该地区传统行业、饮食习俗等又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第一,地域自然条件、文化习俗与区域传统经济模式上造成动物保护立法的实施条件不足。我国西北地区,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自然条件干旱少雨,所饲养的多为牛羊等耐寒冷、耐饥渴的经济动物,而饲养环境、生存必备条件的提供与世贸组织所规定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相去甚远。我国西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地区,民族习惯、地方文化中原本就存在着丧葬习俗砍杀水牛、猎杀野生动物、吃猫狗肉等习俗,以贵州都匀水族、广西玉林“狗肉节”为代表。由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地方政府为提升地方经济发展并获得相应的政绩,采取以经济发展为绝对先导的态度,对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陋习、弊端,以尊重民族自治为原则,以鼓励旅游经济为噱头,采取放任态度。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省、黑龙江省,受到延边朝鲜族聚居区域长久的文化习惯、饮食结构的影响,是狗肉黑色产业链最活跃的区域,每年食用无安全来源的狗肉逾1000万只。
第二,作为支柱性产业的部分经济动物养殖与国际环境保护趋势构成天然抵触。我国是世界皮草大国,河北省、山东省是养殖貂、狐狸、浣熊等皮草型经济动物的大省,特别是河北省自古以皮毛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然而,活剥动物皮毛是皮毛产业中最省时省力、资金投入最小的方式,但在央视记者和海外媒体调查中显示,断手断脚、失去皮毛后的动物仍然存活且有知觉即被扔在货车中,仍然可以用失去了眼睑的眼睛回头看着自己的身体——没有毛皮的血肉在冷空气中散发着热气。*详见我国纪录片《奢华美丽背后的残忍》《三花》等,这些纪录片获得了冯小刚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影评及与网友共同对皮草行业的抵制。随着全球化的环保理论及实践推进,各国动物保护及环境保护志愿者着手大力宣传拒绝使用动物制品、拒绝穿着皮草,进而造成了国际性的皮草价格下跌。从2013年开始,丹麦、芬兰、美国等进口水貂皮价格走低,同时,国产貂皮大衣价格也出现了下滑,幅度在15%~20%左右。2014年价格略有下降,2015年貂皮大衣的价格下降了30%到50%,即使是进口貂皮大衣的价格也不超过两万元,比2012年时动辄四五万元的价格已不可同日而语。皮草市场遭受的重创值得引起重视,在需求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无论是延续传统的低成本活剥还是引进先进的瞬时致死性宰杀技术,都不可能扭转皮草行业世界性的死局,对我国而言,帮助皮草行业从业者主动转型谋求新的出路好过于对行业趋势的悖逆独行。
第三,粗放型传统经济模式监管治理不当带来的卫生及人身安全隐患。在河北大营皮草市场上,除了供给高端市场的水貂、狐狸等皮草原料外,猫皮拼接地毯“三花”“狸花”随处可见,狗皮褥子、坐垫甚至整张的宠物狗皮也比比皆是,售价低廉。这种廉价皮草除了来源不合法之外,也存在着简易硝制过程中病毒细菌不达标的检疫隐患。城市无人照顾的流浪猫、狗频频遭遇偷捕猎杀,家养犬被毒狗针、麻醉针射伤偷盗,城市中非法销售并持有的弩、弹弓被用于射杀城市动物,例证不胜枚举。不仅猫、狗因来源于非法途径而无本万利,也造成了未进行检验检疫的廉价毛皮制品损害人类的健康,更严重的还导致了药用胶囊外皮的违法生产牟取不当暴利。根据2014年12月18日大连市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宠爱天下论坛”拦截的偷捕流浪及家养宠物猫的事件来看,猫肉或流往广东餐桌用于食用,或被贩卖于小作坊用于制作火腿肠、羊肉串及其他假冒伪劣肉制品,猫皮即流向河北、河南两省,用于制作廉价毛皮产品甚至药用胶囊。[10]
第四,“特殊性”以自由为名倒逼“普遍性”立法需求不能获得普遍适用。食用猫狗肉的文化与习俗并非是我国具有一般性的传统,而是个别地区、个别嗜好者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被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利用,以自由为名,以“地域文化与民族习俗”为指代,与其他地区进行文化割裂并试图阻止立法。一些省份的部分地区,吃猫狗肉是当地的历史传统和节日习俗,但并非这些省份所有人口日常的主要食物需求,但被以此牟获不法利益的人煽动挑衅,将“特殊性”的需求偷换为普遍性的自由,从而伤害了普遍性的权利,也伤害了地域联结与民族融合的客观条件。广州一地,每天就有多至10000只猫被活活剥皮烹煮;“广西玉林狗肉节”虽然因全国性广泛抵制而被当地政府象征性地禁止,但2015、2016连续两年的夏至显示狗肉节仍然如火如荼,动物保护志愿宣传员也被不明身份的人非法驱逐。吉林省延边地区曾出现狗肉爱好者聚集市政府门前抗议声称如果不允许食用狗肉是伤害我国朝鲜族的民族感情的行为,这正是少部分人的特殊性正在以自由、权利为名倒逼公权力不能实施普遍性的禁止法令。
(二)食品安全与黑色产业链的根本对立——以“鲁P17460”参与式观察为例
猫、狗在西方对动物的法学分类中是归结于“陪伴动物”之列的,而在我国则出现了归类于“经济动物”的实际情况。这不仅造成了动物保护立法在我国的法学分类困境,也生成了食品安全与黑色产业链的监管难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农业部颁布的相应规定,动物运输必须开具制式打印检验检疫证明,猫、犬检验检疫务必施行逐只检验检疫,一猫一证、一犬一证。任何拦截现场没有一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食品检验检疫的要求,且患病犬只亦不可能通过正规检疫。食用猫狗肉的黑色产业链的存在不具备食品安全上的合法性,原因如下:
其一,检疫方面,食用猫狗肉具有特殊的不安全性。如果一只猫、犬从未注射过狂犬疫苗则可能为病犬或病毒携带猫、犬,但任何疫苗都是毒株,即若注射过狂犬疫苗则成为终身的病毒携带猫、犬。这就意味着食用任何一只猫、犬,都有感染狂犬病的可能。“世界卫生组织”在其2015年9月的“第99号实况报道”中,提出消除狂犬病唯有通过为猫、犬只和人类接种预防性疫苗,但并没有给出病犬和病毒携带犬在食用方面的安全评测或安全建议。且犬类所患有的犬瘟热、犬细小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车内一只患犬可于途中使所有犬只患病;而外观显见肿瘤的患犬显然是癌细胞的携带体,不具备可食用性。
其二,成本与价格推断未检疫及来源非法。除上述的猫狗不可能通过食用性质检疫外,食用猫狗的低廉售价也可以推断其未经检疫——猫狗的检验检疫费用远远高于它们在肉用市场上的价格。
其三,法不禁止放纵下的非法逐利。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且曾被报警拦截,仍要继续伪造证件铤而走险,根据鲁P17460车主自述数据计算,揭示了黑色产业链谋取非法暴利的冰山一角。
车辆改装为四层专门运狗,单次纯利润8万元人民币及最低32万元年收入,这在二、三线城市已属于高收入,更何况对比车辆归属地山东聊城十倍有余,且因规范养殖及合法交易的不存在,收购、贩运、所得均无需缴税。黑色产业链的存在充分体现了销售与食用猫狗肉方面的法不禁止即放纵。
其四,非法盗抢造成的隐性经济损失与无法律保护的权利侵害。宠物犬被盗被食用带来的隐性经济损失此前是被动物保护志愿者和社会关注者忽略的部分,由于没有立法、权利所有人不明确、“食用”既成事实无法追查等种种原因,构成了事实上的数额巨大的非法侵害,却没有责任人承担赔偿性的或制裁性的法律责任。鲁P17460贩运中的名贵犬种在宠物市场上价格高昂,其所贩运的25只名贵犬一旦被食用,则会造成隐性经济损失42万余元。车主只负责犬的收购和贩运,并非真正的犬主,否则不可能不清楚这些宠物犬的市场价值;而将犬只卖给车主的人显然也并非真正的犬主,否则不可能将品种犬廉价销售。这种不进行待价而沽,只求迅速出手的行为,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销售行为,却符合销赃行为。
从法律责任要件构成方面分析黑色产业链数据,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十分明确,依照现行法律侵害对象是权利人财物且“涉案金额”数十万元,但权利人因为无法及时获悉所有物下落,故而无法主张自身权利,即便是个别受到侵害的权利人携带犬证到拦截现场指认并证明该犬只是其合法所有,现实中也往往没有使责任主体承担赔偿或者得到制裁。从宠物狗到肉用狗的价值落差所造成的隐性经济损失完全由宠物实际拥有者承担,而食用者也受到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威胁,食用猫狗肉黑色产业链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是公平之殇。
三、中国动物保护立法与经济效率及公平的关系
法经济学着重于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进而为提高经济效率、稳定经济秩序服务的科学。用经济学的方法作为工具和视角分析法律制度,其目的是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原则与经济效率及公平的关系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运行的内生要素。[2]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视角出发,我国动物保护是否有立法必要,可以用效率、效益为主要目标考察。
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主要是确定法律原则,而不单纯是修正具体的法律条款。[11]用法律移植的方法,借鉴国际认可的动物保护、动物福利法律法规,将这些法律标准拿来反观我国农业、畜牧业的经济结构和现实状况时,悖论立显:按照这些标准执行,我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将产生重大改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符合社会基础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的运作,出现了成本高昂、效果很差的“法律失效”现象。[12]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亟待需要从法经济学范式中,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结构进行思索,以确定立法按照何种标准与程度进行,才能既符合社会基础又保障实施效果。
第一,动物保护立法是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而效率就是经济意义上最大的公平,效率还可以丰富经济社会生产中公平的含义。我国的宠物繁殖驯养、动物医疗、民间救助方式中,也存在着丰富而巨大的商机,对此部分权利构成进行明确并予以必要的立法保护是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不仅符合法律追求正义、公平的目标,又将动物保护立法赋予了效率与效益的内涵。当国家在法律层面纵容虐待虐杀动物、纵容非法贩运屠宰危害食品卫生安全时,就意味着法律或法律原则失去正义与公平,与此部分相关的效率便失去意义与基础,效益也不复存在。因此,动物保护立法是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
第二,动物保护立法提升效率与效益。虽然从部分地区的经济情况看来,动物保护立法势必损害旧有的经济结构,但对于提高效率、效益而言,有着长远意义上的促进作用。对我国的动物保护现状而言,进行动物立法保护,可以促进动物相关产业集约化发展,并且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广泛的关注和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伴侣动物的参展、赛事、繁育相关产业发展与伴侣动物保护理念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对皮草产品的需求也逐步降低,皮草行业将走向滑坡,影响有此传统的地方经济发展,在经济阻滞到来之前预见性地立法即是对效率与效益的提升。
第三,动物保护立法提高效率的目的还是为了公平。效率一旦失去公平的社会标准必然走上歧途,滑向效率的反面。在新中国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最初,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水平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并未包括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方面的内容,未能准确地预见匮乏科学技术、法律约制的后果。二十年前小型宠物犬无论品种多么杂乱也是天价难求,利益驱动下不分品种、不加节制地繁殖,造成现今流浪动物的泛滥以及盗抢贩售的犯罪成本低廉。民间发起的对流浪动物的救助与流浪动物本身的市场价格已构成显著的不公平,缺失法律及政府政策的引导,也大大降低了同样的支出所能达到的能动效应最大化。农场动物也是如此,由于贸易壁垒的出现,我国对畜牧业的投入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投入已不能获得同样的产出,这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正在面对的不公平。追求效率时不能失去正义与公平的社会准则。只有在这个准则的前提下才能持续地发展效率,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四,动物保护立法符合理性本质在经济社会的逻辑。所谓人的理性,简单地说,是指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13]出台动物保护方面相关的立法,是我国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必要手段;并可以为社会定纷止争创造有法可依的选择方式,当理性人在面对法律条框约束时自然会选择合法方式以趋利避害;可以使法律的引导作用大大提高,使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选择符合法律要求的动物产业生产方式。这与合理合法地利用动物为人类谋求福利更加契合。
四、法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动物保护立法路径
法经济学的完整范式应当包括形而上学范式即理性选择、社会学范式即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构造范式即谈判理论三个层次。[14]在剖析与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相关的效益与公平问题之后,以法经济学视阈中的立法与法律修订的方式深入思考,可得出如下三种动物保护立法的可能性进路。
(一)理性选择将禁止虐待虐杀动物优先纳入公法保护范畴
“对于中国的动物保护立法,法律过于超前是有害的。”这是《中国动物权利保护法(草案)》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的表述,这同时也隐含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看法,这种看法并非赞许。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即经济基础的发展,即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而我国目前已确立国际政治、经济大国地位,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法律的缺失也拥有了补足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法治国家的顶层设计中应当且必须包含与动物保护相关的立法内容。尽管社会和学界在动物保护、动物权利、动物福利等方面研究都停留在初级水平,但是立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业已完成。
虽然“动物受法律保护”和“动物享有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动物在法律中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客体,只体现立法技术不同,而无本质差别。[15]对于虐待、虐杀动物的行为,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此种行为是对人性的亵渎与对“恶”的激发,构成对人性的冒犯甚至伤害。而基于对人的普遍性的权利维护,对虐待虐杀动物进行公法体系下的禁止性限定,并非是对动物权利的实现,而是对人权的实现。因此,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方式,应当从现实急需的层次脉络出发,搁置“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在我国法学界理论辨析中的争论,以对“虐待虐杀动物”行为的禁止性立法为切入点,在“动物客体论”[16]的理论层面上,从公法体系下实现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开端,改变动物保护立法中的教条主义态度,以顶层设计引导社会向与大国形象吻合的文明进程迈进。
(二)根据交易成本分级逐步培育立法环境
波斯纳探讨法律的市场、供给、需求与价格问题时特别强调,法制是需要成本的。[11]这些成本不仅包括产权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权利交易的成本。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交易费用,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从我国的动物保护方面的现状来看,对西方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直接进行法律移植,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执法成本,也使现有的经济组织与法人因为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完成,因此,为了效率与公平在长远考虑中的理性实现,需要国家进行有效的立法环境培育。
第一,可考虑动物福利性立法的地方化运行。提高动物福利将同时使许多行业投入高额成本以确保不违法,例如:屠宰场,建设封闭隔离屠宰区域、引进电击设备等,与此相应需要企业的融合兼并甚至借助国有资本的力量才能完成。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各地区不平衡的现实情况而言,用短期的、地方性的“不公平”立法与执法,换取短期的法律实现带来的效率,以及对“长期的公平”培育皿与试验田。即在经济发达地区执行符合本地区法律意识、法律需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以验证动物保护性立法所带来的效率与公平,对我国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由当地根据本地区可承受的实施成本分级逐步制定与推进。
第二,对动物进行法学分类并按类别实行分类保护。法律制度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方法的成本和收益后做出。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以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为目的,一切法律制度和原则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努力。[17]因此中国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也仍遵循符合科斯定理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以反对虐待虐杀为立法着力点,颁布《反虐待动物法》,并且通过法律实施逐渐培养更加良好的立法环境。应当纳入公法体系下的除禁止对动物进行虐待虐杀外,还应当包括将杜绝黑色产业链的社会危害,即将猫、犬定义为伴侣动物并禁止食用。同时,只有进行伴侣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分类,才能使“高速拦截运狗车、猫车”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私力救济性质的行为彻底消失。实验动物在国际动物保护方面的争议,但对实验动物利用后的人道处理应当有明确的、接受监督的公开操作流程;经济动物、工作动物类别方面,根据各自的地方性条例,逐步与国际化的环境法、动物福利法接轨。
第三,确立以生命为基础的稀缺性权利在法律框架下的归属权。在法律世界里,权利是稀缺的,特别是那些排他性权利(如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尤为稀缺,因此人们争“权”夺“利”。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在法益中的争夺焦点主要集中于“以动物的生命获取经济利益”与“以生命权、生存权为贵”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是“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之间的博弈。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法律应通过清晰界定权利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理论被称为“波斯纳定理”。[11](P52)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之后,效率远超于公平的发展,也势必将会阻滞效率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我国动物保护理念越发展,影响力越广泛,受到的质疑和抵制也会更加迅猛,利益是牵涉一切抵制的根本原因。对动物进行保护性立法的法律需求体现着良法的法律价值理念从“以效率为轴心的价值理念模式”向“以正义为轴心的价值理念模式”[18](P74)的过渡。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选择,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影响。[17]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动物保护志愿者都对动物保护立法提出了需求,非法贩运、虐杀爱好者等势必对此提出激烈的反对,现今情势表现出的冲突,恰恰证明了立法进行行为调整的需求存在,而将权利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才是法律最应当实现的权利保护。
结 语
尽管从表面上,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法规,制度创新并不困难,经验借鉴和法律移植也很容易,但是法律制定并实施的条件和成本却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空间,甚至扭曲了政府的理性行为。在我国动物保护立法问题长久被忽视的原因不外乎利益的不统一与对动物保护立法的需求表面上看不迫切,抵制与争辩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空间与设计决断能力。但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关涉到社会长远利益,特别是对反对虐待虐杀的相关法律的需求已然迫在眉睫。因此,从反对虐待虐杀动物入手,更符合我国当下对动物保护立法的需求,而其他的如对农场动物、表演动物等的立法保护,需要更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培养。尊重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选择,并加以最低限度的反虐待虐杀的约制,逐步建立起与国际社会接轨、与自然世界共荣的和谐局面。
朱全景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几乎没有经济学的内容,“这种状况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19]而中国的动物保护立法可能也是如此,每一次当人类为某一种文明进步的形式感到骄傲或羞愧时,都不能忽视以争论为表现方式的演进让道德、法治、理念前行,在争论中给予社会整体一个接受、认可的时间,它通常十分漫长。
[1]孙江.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看动物权利的理论基础[J].河北法学,2009,(4).
[2]曲振涛.论法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基础及其基本理论[J].经济研究,2005,(9).
[3]雷根.动物权利论争[M].杨通往,江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彼得·辛格.[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M].曾建平,代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巩固.环境法解释的价值目标与规范制约[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1).
[7]常纪文.动物福利法——中国与欧盟之比较[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06.
[8]刘荪悦,姜文超.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意见[J].法学研究,2012,(12).
[9]托马斯·莱赛尔.法社会学基本问题[M].王亚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0]7个偷猫贼被抓住 志愿者救出千余只猫[N].大连晚报,2014-12-19.
[1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2]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
[13]李树.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0,(8).
[14]魏建.法经济学基础与比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周训芳.动物保护立法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8,(4).
[16]崔拴林.论动物福利概念的内涵——动物客体论语境下的分析[J].河北法学,2012,(2).
[17]魏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J].学术月刊,2006,(7).
[18]李龙.良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9]朱全景.法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J].法学杂志,2007,(3).
〔责任编辑:黎 玫〕
The Plight of Legislation on Chinese Anim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of Law
FU L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333, China)
In the aspect of anim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i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he absence of related laws leads to the plight of lawlessness and the failure to handle the existing conflicts according to law. Meanwhile, the legislation which is far ahead of the reality is harmful too. Thus it becomes urgent to analyz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the level and extent in anim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s of law. To start wi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protec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urrent China; the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egal requirements and difficulty in legislation, aiming at finding the legislation path for Chinese animal protection.
economics of law; animal protection; the demand and market for law
付 琳(1982—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研究。
D922.68
A
1006-723X(2016)12-007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