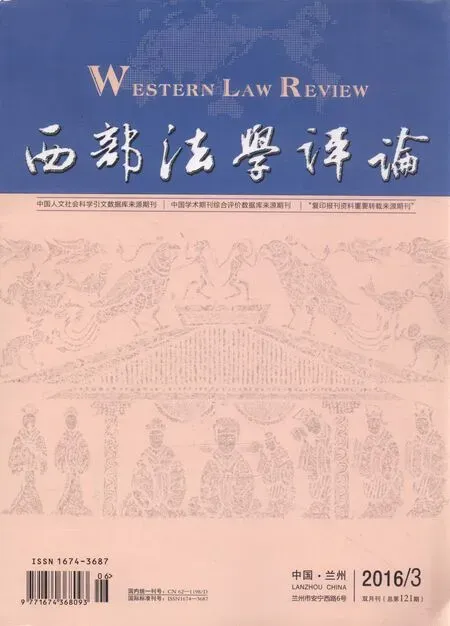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与归责
李开春
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与归责
李开春
摘要:本文通过司法实践中的两个判例,引出共犯脱离的问题,并对共犯脱离的发生阶段、体系地位、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关系、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以及脱离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论述。共犯脱离是共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应与共犯中止区别开来,在我国刑法中应赋予其独立的体系地位。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有共犯关系脱离的空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既遂之前的状态。关于脱离者的责任,其对后续行为和结果自然不需负责,只针对脱离前的行为单独评价,就不同的阶段,负担不同的责任。
关键词:共犯关系脱离;体系地位;判断标准;责任认定
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源自日本刑法理论,英美国家刑法中也有关于共犯退出的类似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有一定研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也有论及。然而对于共犯关系脱离的体系地位和判断标准以及脱离共犯关系者的责任认定,尚有争议。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对脱离者的责任认定,是参照共犯中止解决,还是对其单独评价?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地研究。笔者拟立足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和借鉴域外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社会现实和理论背景,对确立共犯关系脱离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地位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缘起
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实行犯中“一人既遂全体均为既遂”。而在个别情况下,犯罪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如强奸和脱逃等,只有每个人完成了本人的行为才能视为既遂。如果没有完成本人行为,即使其他共同犯罪人既遂,也不能认为他是既遂。*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笔者认为陈兴良教授的主张,意图冲破“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固有藩篱,给予共同实行犯以区别对待,贯彻个人责任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这一主张虽然只是针对共同实行犯亦即共同正犯和部分“亲手犯”而言,然推而广之,在广义的共犯角度上,也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当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下,当共犯中有一人既遂时,其他共犯人都要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很难有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也有可能导致个案处理上的不当。
(一) 判例引发的问题思考
判例1:2007年7月期间,张某、王某因赌博输钱而预谋实施抢劫,并准备了作案工具,由王某选择了周某作为实施抢劫的对象,两人制定了详细的抢劫计划。2007年8月上旬的一天,张某、王某伙同他人携带作案工具至周某家附近欲实施抢劫,因见周某家附近有警车巡逻而感到心里害怕,未能着手实施。后张某多次向王某提出实施抢劫,王某因心中害怕以拖延打发。张某因急需用钱,表示无法再等下去,向王某索要作案工具,王某提供了作案工具。8月下旬,张某伙同左某(在逃)经事先预谋,携带王某提供的作案工具和其他工具至周某家,实施了抢劫,劫得财物若干。对于王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刑事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页。
判例2:2006年初,刘某被免去某集团总经理职务,由朱某接任。同年6月上旬,黄某找到刘某商量,提出利用女色教训朱某。随后,黄某找到洪某,由洪某负责具体实施。洪某利用女色引诱朱某,但未能成功。于是,洪某打电话给黄某,提出改为找人打朱某一顿,黄某表示同意。之后,洪某又雇佣林某,后黄某因害怕打伤朱某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两次打电话给洪某,明确要求洪某取消殴打朱某的计划,但洪某应承后却并未及时通知林某停止伤人计划。随后,林某找来谢某、庞某等将朱某砍至重伤。对于黄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参见:《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8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分析以上两个判例,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共同犯罪中的部分行为人,在犯罪完成之前,退出当前的共犯关系,而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并引起了犯罪结果。关于共犯人的责任认定,对于完成犯罪的共犯人而言,认定他们成立抢劫罪或故意伤害罪的既遂应无疑义,问题是对于并未实际实施犯罪的王某和教唆者黄某(黄某同意洪某负责组织对被害人实施伤害的犯罪行为,应视为教唆行为已经实行完毕)应该如何认定其刑事责任呢?根据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判例1中的王某和判例2中的黄某不能被认定为共犯中止。因为共同正犯中的一部分正犯要成立共犯中止,既需切断主观上的犯意联络并告知其他共犯人,还需客观上积极阻止其他共犯的行为以及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于教唆者而言,虽意图放弃犯罪,并积极实施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但未能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也不能成立犯罪中止。王某和黄某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中止的有效性要件,不能成立犯罪中止。事实上,法院也是这样认定的。法院认为判例1中的王某提供作案工具给被告人张某,其虽辩解当时心中害怕不想参与,但主观上应明知张某拿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抢劫,其未予以阻止,放任张某继续实施抢劫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的共犯。王某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承担责任,还要对共犯张某的行为及结果负责,构成抢劫罪既遂。对于判例2中的张某,法院认为,黄某为帮人泄私愤,雇佣被告人洪某组织实施伤害犯罪,虽然其最终已打消犯意,但未能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其他被告人实施犯罪,导致犯罪结果发生。考虑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地位和作用,其单个人放弃犯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成立故意伤害罪。
虽然案件审理的结局已经盖棺定论,但是司法实践中的这种认定,往往让人感觉对二人的处断过于严苛,量刑过重,没能准确揭示二人与其他共犯人之间行为性质的差别,有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王某和张某退出了之前的共犯关系,是否还要对之后由其他共犯人引起的犯罪结果承担责任,以及应在什么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目前大陆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刑法有关单独犯罪中止的规定出发,强调犯罪中止的有效性要件,认为只要犯罪结果发生了,就不成立犯罪中止;二是对单独犯和共犯的中止作了不同理解,扩充了共犯中止的有效性要件,把共犯脱离纳入其中;三是借鉴德、日刑法中共犯脱离的见解,脱离者和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仅就其脱离前的行为承担中止犯的刑事责任。*黎宏:《共犯脱离论文评议》,载林维主编《共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将单独犯罪中止适用于共同犯罪中,实际上是一种团体主义的共犯观,得出的处理结果过于严苛。按照通说的个人主义的共犯观,共犯也是因自己的行为被追究责任,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是共犯归责的界限。第二种意见缓和了共犯中止的有效性要件,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既然最后发生了犯罪结果,就与我国刑法中止犯的规定不相符合,这样也会破坏中止犯理论的一致性。为了妥当解决此类案件,国内很多学者另辟蹊径,受国外特别是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引进了共犯脱离的第三条处理路径。
(二)国内共犯关系脱离的研究简述
在共同犯罪中,其中的部分共犯人中途放弃犯罪,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来,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而对于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造成的结果,脱离者的责任如何认定,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鲜有论及,新近的理论研究颇有成果。*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刘雪梅:《共犯中止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黄丽勤、周铭川:《共同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王昭武:《我国“共犯关系的脱离”研究述评》,载《刑法论丛》,第12卷;冯晓娜:《论共犯关系的脱离》,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俊华:《论共犯关系的脱离》,吉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共犯脱离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问题,虽然我国不少学者引进了这一概念,但是认识却不一致。张明楷教授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人的中止相关联,但不是相同问题;黎宏教授则认为,共同犯罪的脱离人和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对于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不能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而仅就其脱离前的行为,承担中止犯的刑事责任;林亚刚教授认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事实上就是共同犯罪参与者能否成立中止的问题;陈家林教授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认为没有必要采用着手前的脱离概念;刘雪梅教授则认为,共犯中止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实质上就是共犯脱离的一种特殊形式,共犯脱离是共犯中止的前提。*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543页;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刘雪梅:《共犯中止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这些著述的介绍使我们对共犯脱离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学界的争议还是很大,对于一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分析以上学者们的讨论,笔者认为还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共犯关系脱离的发生阶段。从以上学者的著述可知,共犯关系的脱离发生在共犯关系成立之后、犯罪既遂之前是主流见解,还有学者认为发生在着手实行之后。二是共犯脱离和共犯中止的关系。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明确区分的观点,也有共犯脱离是共犯中止前提的主张。三是脱离者的责任认定,有力见解是判断脱离者能否成立犯罪中止。
(三)共犯关系脱离的发生阶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内涵,笔者认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包括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和共犯(狭义)关系的脱离,而后者又包括帮助犯的脱离和教唆犯的脱离。本文所讲的共犯脱离是广义上的共犯关系脱离。
对于共犯脱离的含义,国内学者的见解比较一致。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共同犯罪的脱离,是指共犯关系成立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其中的部分参与人切断其与其他共犯人的关系而从该共犯整体中解脱出来,其他参与者基于重新成立的犯罪关系继续实施行为,引起了犯罪结果的场合”*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有学者主张,“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关系成立后,犯罪完成之前,部分参与者切断与其他参与者的联系,从共同犯罪关系中得以解脱的情况”*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页。;还有学者仅论述了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是指共同正犯人在犯罪完成之前自动表示不再继续参与该犯罪并得到其他人的认可,而其他人继续实行该犯罪的情况”*曲新久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从上述的界定可知,我国学者关于共犯脱离的时间认定很宽松,从共犯关系形成之后,到犯罪完成之前,行为人都可以脱离共同犯罪。
在日本刑法学界,对于脱离的发生阶段尚有分歧。大塚仁教授认为,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发生在共同正犯的实行着手之后,还未达于既遂的阶段;教唆犯的脱离也是在教唆行为使正犯者作出了实行行为后,在其终了前的阶段;帮助犯亦同。而大谷实教授则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发生在共犯关系成立之后,完成犯罪之前;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包括着手前的脱离和着手后的中止。*[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344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页;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4页。由此可见,前者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发生在着手实行之后,到犯罪既遂前的阶段;而后二者则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发生在既遂前的任何阶段。尽管对于着手实行之前能否发生共犯关系的脱离尚有争议,但是日本刑法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一样,一般都认为共犯关系脱离应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
笔者认为,共犯关系的脱离也可以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后。对于一些犯罪而言,例如结果加重犯和继续犯等,犯罪既遂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的结束,共犯关系仍可能存在。正如承继的共同犯罪可以存在于继续犯中,与其相对的共犯脱离发生在继续犯中也是没有问题的。行为人甲非法拘禁被害人两天后,知道真相的乙参与拘禁的,乙成立非法拘禁罪。同样,在行为人非法拘禁他人后,犯罪已经既遂,这时的共犯关系依然存在,如果部分共犯人脱离当前的共犯关系,那么对于其后的加重结果,仍然存在适用共犯关系脱离的空间。所以,共犯关系成立之后,共犯关系结束之前的任何阶段,都有发生共犯关系脱离的可能,而不应该局限于犯罪的具体形态。共犯关系的脱离与承继的共同犯罪、共犯中止和共犯既遂一样都是共犯论的固有问题。
二、共犯关系脱离的体系地位
借域外理论之长,补我国理论之短,是提高我国刑法理论水平的一条捷径。英美刑法理论虽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其共犯退出制度,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大有裨益。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是双层体系,即犯罪本体要件(刑事责任基础)和责任充足要件(排除合法辩护)。共犯退出制度就是责任充足要件中的一种特殊的辩护事由。
(一)英美刑法中的共犯退出
1.美国刑法上的放弃犯罪
美国刑法上没有犯罪中止这个术语,但有些州的法典上规定的放弃犯罪(renunciation)其实就是中止犯罪的意思。有些州把放弃犯罪放在免罪辩护章节里作为一种免罪辩护的理由,如纽约州刑法典。*储槐植、江溯:《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为了鼓励已经参加犯罪共谋的人退出犯罪,行为人可以援引中止共谋作为辩护理由为自己脱罪。对于中止共谋情况下的责任认定,联邦法院的判例是中止共谋并不免除全部共谋罪责,而是免除退出共谋活动以后的其他共谋者所实行的犯罪的责任。
除了一般辩护事由(缺少犯罪行为或犯罪心态)外,关于共犯的辩护事由还有一种特别的规定。《模范刑法典》第2.06条第6款C项规定,在犯罪既遂之前,行为人中止了共犯关系,且完全消除了该共犯关系对犯罪实行的效力或者给予执法机关及时的警告或者以其他方法为阻止犯罪的实行作出了适当的努力。在《模范刑法典》的影响之下,美国大多数州的刑法典中规定了“中止”这种共犯的辩护事由。*同前引〔11〕,第150页。
2.英国刑法中的共犯退出
英国刑法理论中没有共犯中止的概念,只有共犯退出的概念(withdrawal from participation),其内涵与共犯脱离类似。英国刑法中的共犯退出制度是指共犯如果在实行犯着手实行某项犯罪之前明确地表示退出,那么对于该犯罪他将不承担共犯参与的刑事责任。*英国刑法中的共犯是狭义上的共犯,其实行犯即德日刑法理论的正犯。所以,英国刑法中的共犯退出指的是非实行犯的退出。而本文要论述的共犯脱离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共犯,即帮助犯和教唆犯,而且包括部分共同正犯退出共犯关系的行为。从这一点上看,大陆法系的共犯脱离要比英美法系的共犯退出成立空间更为广泛。在英国刑法理论中,关于共犯的责任有共犯派生责任和共犯独立责任之别(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共犯派生责任是指,共犯本质上具有派生性,其责任派生于与之相联系的主犯。共犯独立责任是指,从犯的协助或者唆使行为对社会产生了独立于主犯的危害性,因而他们的责任独立于主犯。特别是在唆使的情况下,即使被唆使人没有犯唆使的罪,对唆使犯也不能免除处罚。两种共犯责任依据,有不同的目的和价值。派生责任理论倾向通过限制犯罪圈和刑事责任范围来保护个人,独立责任理论倾向通过扩大犯罪圈和刑事责任范围来保护社会。*袁益波:《英国刑法的犯罪论纲》,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共犯派生理论在英国刑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无法证明他人事实上实行了犯罪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一个被指控为帮助或教唆他人实行该犯罪的人定罪处罚。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行为人与其他人的特殊关系而自动产生,其所实施行为的性质使得他被认为与某一犯罪的实行犯具有同一性,所以行为人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共犯归罪根据的派生性。例如谋杀罪的共犯责任是派生责任,它并不要求共犯人具有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图,也不要求行为人造成了死亡结果。它仅仅要求行为人通过鼓励或帮助行为,有意地将自己与他所明知的将要或可能杀人的他人联系起来。虽然这种派生责任有时并不稳定,在某些判例中不能完全适用,然而它催生了共犯退出理论,共犯退出就是在共犯派生责任理论支撑下共犯参与责任的特殊辩护事由。
(二)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共犯脱离
1.德国的共犯脱离
德国实务与学界并没有把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作为中止犯的一个主要的成立条件。*徐育安:《共同犯罪关系之脱离——兼论共同犯罪参与之中止》,载林维主编《共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德国刑法学者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共犯脱离的理论,但是在其实务中,共犯脱离的现象还是客观存在的。严格地讲,关于共犯脱离制度,《德国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未完成罪的规定中可以找到相关的法律根据。如《德国刑法典》第24条第2款规定:“数人共同实施同一行为的,其中主动阻止行为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第31条第2款规定:“如没有中止犯的中止行为,犯罪行为也会停止的,或没有中止犯中止以前的行为、行为也会实施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行为实施的,即不予处罚。”*《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这两个条款就中止和脱离的关系规定了三种类型:一是,阻止了犯罪既遂;二是,犯罪未遂但与中止行为无关的;三是,犯罪已经既遂但与中止之前的行为无关的。其中第一种类型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中止一样,即都阻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行为人负中止的刑事责任。第三种类型一般被认为是对第一种类型的补充,即使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但只要与行为人中止之前的行为无关的,也有成立中止犯的可能。这种类型的共犯中止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共犯关系的脱离,只不过其成立要件非常严格。因为德国刑法中对于此类行为是不予处罚的,所以要求中止者必须为阻止犯罪作出积极的努力,消除之前对犯罪的贡献。正因为德国刑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德国刑法学者也是依此进行解释的,因而也就不像日本那样发展出了独立的共犯脱离理论。
2.日本的共犯脱离
在日本刑法学界,共犯脱离在共犯中止之后产生。大塚仁先生首先提出并确立了共犯脱离的概念。他认为,共同正犯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任意并且真挚地实施了中止行为,但是其他共同者仍然完成犯罪,如果将中止行为者和其他共同者一样作为正犯进行处罚,则未免显得过于苛酷,因此提出将中止行为者当作从共同正犯关系脱离了出来,其到中止行为之前的共同行为,和其他的共同者一起承担共同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虽然都不能成为共同正犯的中止犯,但是,可以对其为中止作出的认真努力予以评价,认为是脱离。”*[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之所以会产生共犯脱离,是因为日本刑法中的犯罪中止不能完全涵盖共犯关系的脱离。根据日本刑法第43条的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刑罚,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可见,日本刑法中的中止未遂发生在着手实行之后,而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可以发生共犯关系的脱离。对于着手实行之前的脱离,犯罪中止无法评价,共犯脱离就有了存在的必要。
大塚仁教授最初提出共犯脱离理论意在弥补共犯中止未遂所不能救济之处,属于中止未遂的救济对策,但是最近的发展已将该理论作为共犯论的固有问题对待。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变化,对于共犯脱离的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界定。首先,对共犯关系脱离的发生阶段有不同的理解。大塚仁教授认为,只能是在着手之后、既遂之前才存在共犯脱离的问题,大谷实教授认为,在共犯关系成立之后、犯罪完成之前,都存在共犯关系的脱离,而西田典之教授则认为着手之前是脱离,着手之后是中止。其次,对于共犯脱离的判断标准,存在“因果关系切断说”和“共犯关系解消说”之争。
(三)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关系
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共犯脱离理论是共犯中止理论的“救济措施”,即“救济说”,具有弥补共犯中止之不足的机能。有学者主张,“应提倡共犯脱离作为中止理论‘救济对策’的肯定说”。*刘艳红:《共犯脱离判断基准: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还有学者认为,“共犯关系脱离在我国刑法中仅具有弥补着手后共犯中止之机能”。*赵慧:《论共犯关系的脱离》,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然而对于“救济说”也有否定的观点存在,有学者认为,“脱离理论虽始于中止犯的救济措施这一理念,但历经发展完善,虽不能说已完全不具有此机能,但其法律性格不再是所谓救济措施,而是与中止犯理论处于不同层面的独立理论。”*王昭武:《我国“共犯关系的脱离”研究述评》,载《刑法论丛》第12卷,第132页。笔者亦持相同立场。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的时间性,虽不像日本刑法那样要求在实行着手之后,但关于中止的有效性和自动性要求都很严格,这无异于限缩了中止犯的成立空间。“如果严格按照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来限制共犯脱离的要件,这样必然导致共犯脱离理论无存在之必要,且不利于鼓励脱离者从共犯关系中脱逸,不利于瓦解犯罪集团。”*姚万勤、陈立毅:《论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中止区分为视角》,载《政法学刊》2013年第1期。因此,对于共犯脱离和共犯中止需要区别对待,在肯定它们之间有联系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们并非同一问题。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所言,“脱离者之罪责、脱离之要件等,并非纯属于中止犯之一个适用事例,宜自共犯论本身予以检讨,始为妥当”。*甘添贵:《刑法之重要理念》,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2页。
在日本刑法中也是如此。日本刑法中中止未遂成立的前提是犯罪结果并未发生,而共犯脱离“原本只有在基于共犯关系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之时才会成为问题”。*[日]大谷实:《刑法总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262页。转引自王昭武:《我国“共犯关系的脱离”研究述评》,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按照日本刑法的规定,既然犯罪结果已经发生,自然不能成立中止犯,而脱离是在犯罪结果已然出现的情况下,讨论脱离者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共犯脱离和共犯中止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它们处于不同的理论层面。共犯关系的脱离本质上是结果归责的问题,它要解决的是如何认定脱离者脱离了与其他共犯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认定脱离者的责任问题;而共犯中止则是属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区分共犯中止与共犯既遂、未遂的界限问题。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应该区分开来。与其说共犯脱离是弥补共犯中止的不足,不如说共犯中止对于此问题是鞭长莫及。
三、共犯关系脱离的判断标准
(一)因果关系切断说
1.因果关系切断说的内容
因果关系切断说是由平野龙一教授最先提倡,经由西田典之教授、山口厚教授等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刘雪梅:《共犯中止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目前在日本刑法理论界占据通说地位。该说着眼于共犯的处罚根据,将脱离者是否切断了自己行为对最后犯罪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作为共犯关系脱离的判断标准。行为人要想脱离共犯关系,必须切断与其他共犯者之间物理的和心理的因果关系。对于脱离者的责任认定:第一,如果脱离发生在着手实行之前,则脱离者一般不承担任何罪责(但可能成立预备犯);第二,如果脱离发生在着手实行之后、既遂之前,则对脱离之前的部分承担未遂罪责(如具备任意性要件,则成立中止犯),而对其他共犯在其脱离之后所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既遂结果并不承担罪责。*[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下册)》,有斐阁2002年版,第1426页。松原芳博进一步指出,“在实施继续犯或者包括的一罪的途中脱离的,仅就脱离之前的部分成立共犯,即便由脱离之后的其他共犯的行为引起了加重结果,也不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犯。”*[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页。因果关系切断说也得到了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支持,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能以真挚的意思切断心理及物理上的联系,则共同正犯的关系即从切断联系的时点起消失,切断关系者只就切断前的行为负责。”*李茂生:《共犯关系之脱离》,载台湾《月旦法学杂志》第21期。
2.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评析
因果关系切断说立足于因果共犯论的视角,对于共犯关系脱离的判断是较为妥当的做法。虽然这一学说能够统一实行着手前后的脱离问题,但是也招致了学者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物理性因果关系和心理性因果关系的切断标准判断不明以及因果关系能否真正切断。有学者指出,“如不存在因果关系,当然应免受刑责,完全没有必要将其设定在共犯关系的脱离这一框架之内”。*[日]香川达夫:《共犯处罚的根据》,成文堂1988年版,第166页。转引自金泽刚:《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而且心理性的因果关系一旦形成,要完全切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案例:甲、乙、丙共同商议入室抢劫丁,甲在实施抢劫计划的三周前事先踩好点,并将丁的住处和其出行规律、作息时间告诉了乙、丙,在抢劫前一周,甲想到自己正处于缓刑期,于是对乙、丙说,自己不干了,还劝说二人也不要去抢劫。但之后,乙、丙利用甲提供的信息实施了抢劫。该案中,甲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乙、丙利用该信息实施了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否定因果关系的延续。该案中由于甲不可能消除已提供给乙、丙的被害人的住址和出行规律等信息,因而严格意义上,只要没有阻止犯行,“因果性的切断”就是不可能的。虽未阻止犯行,但尽可能地消除已经产生的影响,就应承认共犯的脱离。“在此,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因果的思考,而是规范、评价的思考”。*[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所以,该说有不当缩小共犯脱离的成立范围之嫌。
(二) 共犯关系解消说
1.共犯关系解消说的内容
大谷实教授以因果关系切断说为基础,着眼于脱离前后的共犯关系是否是同一共犯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共犯关系解消说”。他认为,脱离,必须是解除已经成立的共犯关系。“为了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或者解除,必须是在具有共犯关系的人脱离之后,脱离人的影响力消除,而形成了新的共犯关系或者犯意。”*[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其脱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脱离者必须表达脱离的意思;其次,其他具有共犯关系的人必须知道脱离者的脱离,剩下的人实施犯罪的时候是基于新的犯意实施的行为,形成了新的共犯关系。
2.共犯关系解消说的评析
共犯关系解消说,是针对因果关系切断说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其脱离的判断标准是共犯关系是否已被解消。在共犯关系脱离的问题中,关键是判断是否建立了除脱离者以外的新的共犯关系,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日本很多判例都是以解消共犯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该说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支持,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学说。但是笔者认为,该说对于着手之后的脱离要求过于严格。按照大谷实教授的观点,着手之后的脱离必须满足:(1)实行行为的途中,共谋人中的某人对其他共谋人表明了脱离的意思,其他共谋人也了解这一点;(2)脱离人采取积极的防止结果行为来阻止其他的人实施实行行为,使当初共谋实施的实行行为未能得以实现。*同前引〔31〕,第428页。这样的要求甚至比共犯中止还要严格,毕竟共犯中止只要自愿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即可。再者,按照此说的逻辑推理,这里的共同犯罪必须是两人以上(不包括两人),因为若是两人实施的共同犯罪,其中一人脱离之后,剩余的一个人无法建立新的共犯关系,自然不可能存在共犯关系的脱离。
(三) 否定共同犯罪关系成立的判断标准
因果关系切断说和共犯关系解消说,都是围绕着物理性和心理性的因果关系是否切断展开论述,实质上都是判断脱离者与其他共犯者之间的共犯关系是否归于消灭,也就是共同犯罪关系不再成立的判断。既然如此,可以借助共同犯罪关系成立的反向进行判断,当否定了共犯关系成立的时候,自然是解消了脱离者和其他共犯者之间的共犯关系,也就是认定脱离了共犯关系。
按照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成立共同犯罪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二人以上。第二,必须有共同的故意。这里的共同故意不要求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只要求行为人具有和他人共同实施行为的意思。第三,必须有共同的行为。共同行为包括实行行为、帮助行为和教唆行为。既然成立共同犯罪需要这些条件,那么如果撤销这些条件,共同犯罪就不成立,自然可以认定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
1.否定共犯关系之客观要件的脱离
成立共同犯罪,客观上要求二人以上要有共同实行的行为。因此,否定了共同实行的行为,就可以认定共犯关系的脱离。当然这一否定性要件的判断,视行为人在共犯关系的地位和作用而定。就共同正犯而言,共同正犯者分担实行行为,相互利用、相互补充对方的行为,使各行为人的行为成为一个整体而实现犯罪。对于共同正犯中的一般参与者,只要客观上不再实施共同行为,就可以认定为脱离;对于其中的主犯和组织者而言,仅客观上不再实施共同行为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其他共犯者的行为。例如,甲、乙、丙三人入室盗窃,甲给了乙一把刀子,用来排除阻碍。当丁来阻止他们的盗窃行为时,甲说:“走吧,我们赶快走!”然后甲就逃离了犯罪现场。这里甲不能成立脱离,理由是:在这种犯罪共同体中,甲乙丙都是“平行”的共犯参与者,要想脱离共犯关系,需要更加有效的行为表现。该案中,甲不仅和乙、丙共同商议实施盗窃并且还为乙提供了犯罪工具,因此要想脱离共犯关系,至少需要收回乙的作案工具。
按照因果共犯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通过正犯者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即处罚共犯者,是因为其诱使、促成了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行为。因此,当共犯的客观行为被否定时,就表示正是由于脱离行为使得对正犯者的帮助和教唆不能成立。具体来说,当共犯者的脱离行为消除了自己先前行为对正犯行为的影响力,就不具备共犯成立的客观要件,因而也就判定行为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对于帮助犯而言,在提供物理性帮助的场合,需要撤回这种物理性的帮助或者这种物理性的帮助客观上没有起到因果力的作用。例如,提供作案工具的人,需要收回提供的作案工具或者提供的作案工具客观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在判例1中,8月上旬,王某和张某基于一致的意思表示放弃了犯罪。而在8月下旬,张某又伙同左某基于新的犯意实施了犯罪,笔者认为王某已经从之前的共犯关系中脱离,其对之后的抢劫罪不应当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即使是持“因果关系中断说”的学者也否定了这种物理性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共犯基于全体一致的真挚合意而中止(放弃)了犯罪之后,过几天,部分共犯基于新的犯意而重新实施了犯罪的,即便犯罪实行者使用了脱离者所准备的手枪等工具,仍应肯定物理因果性的切断。”*[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所以,认定王某脱离了共犯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教唆犯而言,在被教唆者着手实行犯罪之后,教唆者需要采取积极行动阻止被教唆者的行为,消除自己的教唆影响力,可以认定为脱离。
2.否定共犯关系之主观要件的脱离
成立共同犯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有共同实行的意思。因此,否定了共同实行的意思,就可以认定共犯关系的脱离。脱离者主观上需要表达脱离的意思,且为其他共犯所知晓。脱离的表达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明示的脱离指脱离者明确地告诉其他共犯者,自己不再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施,如果其他共犯者一意孤行,那么之后的行为的结果和自己无关。行为人虽没有明确告知,但是通过警告被害人、向警察报案等方式意图阻止犯罪行为实施的,可视为以默示的方式表达了脱离的意思。其他共犯者知晓了脱离者的脱离意思后,那么脱离者之前的心理因果力影响就消灭了。
就共同正犯中的一般参与者而言,表达了不愿再参加犯罪的意思,其他共犯者也知晓了这一点,就可以认定脱离;就其中的主犯和组织者而言,不仅需要明确表达脱离的意思,而且还要积极劝说其他共犯者打消犯罪意图,消除自己的心理因果力。例如,甲、乙、丙三人共同商议意图强奸被害人丁,当他们将丁挟持到宾馆以后,甲发现丁下体不适,并告诉了乙、丙,丙立刻表示自己不干了,还劝说甲和乙,说“这样干会倒霉的”,但丙的劝说无效。甲乙在丙离开后,还是强奸了被害人。本案中,应当认定丙脱离了共同犯罪,丙对他们的强奸行为不应负既遂的刑事责任。
对于帮助犯而言,在提供心理性帮助的场合,需要劝说其他共犯者不再实行犯罪,消除心理性帮助的因果力。在提供决定性信息的情况下,要完全消除这种心理因果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求脱离者警告被害人或者向执法机关报告。对于教唆者而言,在被教唆者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劝说被教唆者放弃犯罪意图,得到其应承后就视为消除了影响。即使,被教唆者之后实施了教唆者之前教唆的犯罪,脱离者也不需承担责任,视为被教唆者基于自己的犯罪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判例2中,黄某因害怕打伤朱某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两次打电话给洪某,明确要求洪某取消殴打朱某的计划,洪某也应承了。洪某尚未着手实行犯罪,黄某就劝说其放弃犯罪意图,应认定黄某消除了自己教唆行为的影响力,脱离了共犯关系。
四、共犯关系脱离者的归责
(一)脱离的效果
以“双重否定”的判断标准,若是认定行为人脱离了共犯关系,那么脱离者对之后其他共犯者实施的行为和引起的结果不需承担刑事责任。脱离者既然脱离了共犯关系,共同实行的事实就不存在了,脱离之前的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因果力就消失了,从客观上看,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脱离者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从刑事政策上考虑,脱离者行为的违法性和个人的社会危险性都大大降低,给予刑法的宽宥是应有之义。但是,脱离者对于脱离之前的行为仍需负责,具体的责任认定将视情况而定。
(二)脱离者的责任认定
对于脱离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尚无统一的定论。在日本刑法理论界,大塚仁教授主张“障碍未遂准用说”,对于共同正犯的脱离者较既遂犯的罪责要轻,较中止犯的罪责要重,准用障碍未遂,就可以与中止犯保持量刑上的均衡,在处断上更加合理。同样,对于脱离了共犯关系的教唆者追究其准教唆犯的障碍未遂的罪责,对于帮助犯应该追究其准帮助犯的障碍未遂的刑事责任。*同前引〔17〕,第341—344页。笔者认为,由于共犯关系的脱离可以发生在共犯关系存续的任何阶段,对于着手之前脱离者责任的认定,大塚仁教授没有论及,这并不周全。再者在某些情况下,脱离者的罪责并不比中止犯更重,应该在具体的案件中分别对待,而不一定要考虑脱离者的责任是否与中止犯相协调。
山口厚教授认为,“若脱离是在正犯或其他的共同者‘实行的着手’之前的话,则脱离者不产生刑事责任(预备罪的场合除外);即便脱离是在这些人‘实行的着手’后但只要是在既遂之前的话,脱离者就仅在未遂的限度内产生共犯的责任。当脱离是‘出于自己的意思’的场合则成立中止犯。*[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由此可见,对于脱离者的责任认定,山口厚教授实际上是作为单独犯进行处断的,行为人在不同的阶段脱离了犯罪,分别可以成立预备、中止或者未遂。但是,“在肯定了正犯或是其他的共同者的‘实行的着手’的场合,有时候会独立于行为人的行为而设定了直至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因果经过,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只要行为人的犯罪促进效果没有解消,就不能肯定共犯关系的脱离。即便是努力去消除犯罪促进效果但却失败的场合,仍不免既遂的共犯的罪责”*同前引〔35〕,第358页。例如日本非常著名的“九百日元案”:M和N一起到K家实施入室抢劫,用刀逼迫对方交出钱财。K的妻子L对M、N说,“我们家那位是学校教师,家里没有钱,只有学校的公款7000日元左右”,对此M说“这种钱不要!”,然后L又从柜子里拿出了900日元,M一边说“我不要这种钱!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这么做,如果你们家没钱,这钱我也不要了(你就只当被人抢了,用这钱去给小孩买点衣服什么的)”,一边对N说,“回去吧!”,便走出了房门。大约3分钟以后,N从里面出来,对M说,“你这种菩萨心肠不行,我把900日元钱拿来了。像你这样做不成事情!”对此,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定M构成抢劫既遂的共同正犯。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脱离者的责任认定,一些学者试图在犯罪的中止、未遂和既遂之间寻找其准确地位置。如有学者主张,“着手前的脱离,如自动脱离,则是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如果不处罚预备,该脱离者就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脱离者在正犯着手之后结果发生之前脱离,则仅在未遂的限度内承担共犯的责任,如果是自动脱离,则成立中止犯”。*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可见,张明楷教授的主张和山口厚教授如出一辙,并无二致。有学者认为,“着手前脱离的场合,就已经成立的预备罪成立共同正犯,如果脱离人具有自动性要件的话,就成立该预备罪的中止犯;在着手后的脱离的场合,有可能发生了犯罪结果。这时候,只要脱离人具有自愿脱离的意思,仍然可以成立中止犯”*同前引〔7〕,第306页。。黎宏教授也是师承大谷实教授的见解。
笔者对以上见解,基本赞同。但是,笔者认为,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可以发生共犯关系的脱离。因此,对于脱离者的责任认定,应不局限于上述见解。在一些结果加重犯和继续犯中,共犯者完成了犯罪,达到既遂状态,此时由于共犯关系仍然存续,部分行为人若脱离了共犯关系,对于既遂之后的行为和结果不需承担责任,只需负基本犯罪的既遂刑事责任。例如,张三、李四、王五一起非法拘禁赵六,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一旦被剥夺,犯罪即达到既遂,但共犯关系仍继续存在,张三退出了犯罪,脱离了共犯关系,若李四和王五将被害人打成重伤或导致其死亡,那么张三对加重结果是不需要负责的。
综上,共犯关系脱离的判断和共犯脱离者责任的认定,应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要分开考量。共犯脱离是一种客观的犯罪现象,是共同犯罪发展形态中的一部分,既然有承继的共同犯罪,自然不能否定脱离共同犯罪的存在。判断共犯关系是否脱离,是为了解决脱离者对其他人的行为和结果需不需要再加以负责的问题,而脱离者的责任认定是对脱离者本身的单独评价,是犯罪停止形态本身的问题。具体而论,行为人在预备阶段脱离的,应承担犯罪预备的责任,如果刑法不处罚犯罪预备则不负责任;如果脱离者具备“自动性”和“有效性”的要件,则可以发生中止犯的法律效果,在我国预备阶段的中止,是刑事处罚中例外的例外,应该免予处罚。行为人在实行阶段脱离的,应该成立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同样若是具备自动性”和“有效性”的要件,则成立实行阶段的中止,可以得到刑法的宽宥,得以减免处罚。行为人在既遂之后脱离的,则只成立基本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对加重结果无需承担责任。
五、结语
共犯脱离问题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对于共犯脱离的判断标准和脱离者的责任认定,尚无定论。司法实践中存在众多共犯脱离的案例,大都以犯罪既遂加以处理,这自然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权利。本文通过实践中的具体判例引出对共犯脱离的探讨,从比较法的角度明确了共犯脱离的体系地位、共犯脱离的判断标准以及脱离者的责任认定。在我国刑法中确立和完善共犯脱离,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共犯形态,丰富我国的共犯理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局,还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和个人责任主义的刑法观。
作者简介:李开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