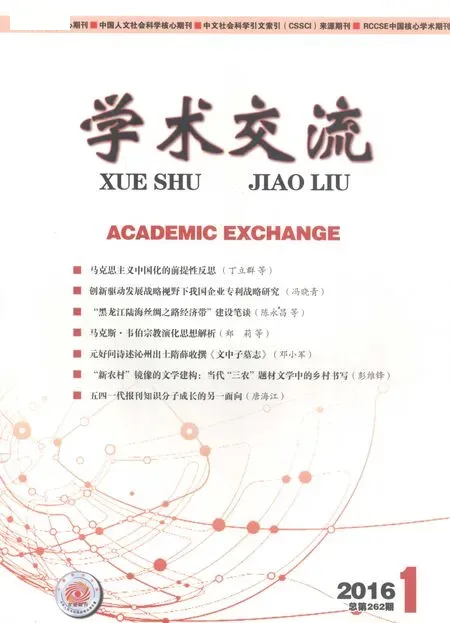贾平凹《老生》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
陆 欣,孙胜杰
(1.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00; 2.黑龙江东方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哈尔滨 150086)
贾平凹《老生》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
陆欣1,孙胜杰2
(1.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00; 2.黑龙江东方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哈尔滨 150086)
[摘要]贾平凹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和突破从未间断,和他以往的作品相比,新作《老生》是一部集作家近年来对创新文学历史叙事形式的思考与历史中融入个体生命记忆为一体的作品。文本通过唱师的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和空间“并置”的民间历史叙事策略,使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历史小说呈现出空间叙事的特征,并且在民间历史叙事中演绎了个体记忆的生命感悟。
[关键词]贾平凹;《老生》;民间视角;历史叙事;空间“并置”
贾平凹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和突破从未间断,对于其新作《老生》,很多评论家都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小说就像“一个老人家在不急不慢地一边抽着烟,一边对读者讲当年的故事”。的确,贾平凹创作《老生》试图尝试的就是一种民间写史的叙事方式,他对于历史的表述,不仅是用语言,更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追忆,所以《老生》是一部集作家近年来对创新文学历史叙事形式的思考与历史中融入个体生命记忆为一体的作品。
一、唱师:民间历史叙事的叙事视角
陈思和先生提出“民间”的概念,为远离“庙堂”与“广场”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与价值立场。“民间”是相对于主流话语的一个空间,“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1]①。而民间视角通俗地讲,就是知识分子站在民间立场运用民间思维方式进行文本叙事,在创作中以民间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时代、反映历史,把自己隐藏在民间,来表达知识分子本身对时代难以言说的认知,这种认知“渗透进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1],所以,民间视角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和创作手法,它更是作家进行创作时秉持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立场。在民间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一般可以理解为“在”而非“属于”,是知识分子的“下放”或“流落”,但还有特殊的时候,比如贾平凹这一类作家,他们出生或成长于农村,切身经历过民间生活,精神上真正属于“民间”,所以这种民间立场与生俱来,虽然后来居于城市,但乡村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立场”几乎不会改变,就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在漫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童年时代带给我们的诗意的理解周围一切的信念的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2]。
文学和历史的关系由来已久,也难分彼此,人类的一切历史都可以作为文学的叙事文本,但其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要看叙事者的身份、叙事的内容以及方式。贾平凹出生并成长在农村,民间文化根深蒂固是不容质疑的,以至后来虽在城市生活,创作的每部作品也总离不开对民间文化的搜寻和利用。贾平凹说他每次回到家乡,一定要做的事情是翻阅县志、看戏曲演出、搜集民间歌谣和传说、参加当地的红白喜事、还有寻访小吃等,因为这民间所渗透的都是一种文化,如果一部作品能够表达、描绘这一切,应该不是作为作品的装饰或附加,应该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3]。作品中的民间文化、民间体验随处可见,但在《老生》这一表现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小说中,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他没有越俎代庖地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代为叙述,而是在主体故事叙述过程中以一个活了百年的民间丧葬仪式的唱师的立场和视角,以他回忆自身的经历为支撑来讲述百年中国人的生存本相和文化历史变迁。唱师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最底层的一类人,以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百年历史发展进程,显然这段历史是民间的,这样的叙事暗含着一种民间视角。
所以,贾平凹选择唱师作为讲述者,其实质是确定民间立场,把话语权交给民间。唱师一生亲历和见证了中国近百年历史,作品中他是回记的主体,更是故事的讲述者,这几重关系的融合决定了以唱师为视角叙事的多重功用。首先,这种视角使故事的叙事者和普通民众之间保持了一种对等的姿态。作品的主体内容是唱师在讲述有关自己经历的故事,因而在“讲”和“听”之间会涉及讲述者和倾听者的身份、姿态问题。唱师在民间的身份属于非社会性,既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者,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权威者,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是自主对等的,不存在强制、灌输式的布道。唱师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或者最多是个被动的参与者,他在普通民众中的神秘和民间敬畏感是民间对带有救赎意义的另类他者文化的期待与信仰,这种文化期待与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
其次,从作品的整体结构布局来看,这是一个流淌着回忆的作品,采用现实—过去—现实的叙事模式。对于这样的叙事结构,陈平原先生这样阐释,“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过去的故事能够融入现在的故事的原因“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于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4]。所以,唱师作为叙事主体,他的情绪心境是整部作品的关键所在。类似于神的存在的唱师在作品中有着普通人的善良坚韧与纯朴自然,远离凡俗世故,保持着原始初心,经过百年的时光沉淀,他对这个民族的历史了如指掌,对后世子孙的种种心态更是能够深刻洞察,以局外人的客观视角来讲述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唱师这个民间的“巫”,在作品中不仅起到作品内外线索的联结作用,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唱师对历史的讲述其实是他自身个体生命的叙事话语,在对过去百年历史的追忆中,对于过往的一切都怀有一份冲淡与平和,对历史与人事的回忆也多了些宽容与温情。
二、空间“并置”:民间历史叙事的叙事策略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讲究时空合构,时间“体现物质运动的顺序性、持续性”,空间“体现物质存在的伸展性、广延性”[5],小说的叙事是在时空合构的结构中运行的。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大多遵循历史时间展开循序式、头尾俱全的线性叙事。也正因如此,历史小说力求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和现实性。而贾平凹在《老生》中的叙述时间是模糊的,读者也只是根据掌握的历史知识来推断故事发生的时间,可见,作者叙事不拘泥于真实的时间年代,而是从大处着眼,注重作品呈现出大的时间结构,而不在意具体时间的真实。通过阅读作品,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正阳镇、老城村、过风楼镇、当归村四个乡镇空间以及在其中演绎着人们日常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生存状态。而使文本叙事时间突破传统线性时间观发生变形的关键,在于故事的叙事主体是一位有着超越族群、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神秘的丧歌唱师,整部作品的叙事就像一位神秘老者在弥留之际淡定地给后人讲述那些当年他经历或听说的故事,在他的跳跃思维和强大主体意识的不自觉渗透下,“将叙事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6]179,整部作品可以明显地分为现实和回忆两个部分。现实的结构是老师给孩子教授《山海经》的文本释读,唱师弥留之际听着《山海经》回忆发生在秦岭中的沧桑历史,是包容回忆的框架,而回忆部分所叙述的是唱师对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回忆,与过往的内容有关,而且在叙事方法上运用的是倒叙。对一个民族百年历史的追忆纳入短暂的一天回忆中,这是对传统小说习以为常的时间蕴含空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颠覆,在时空合构的历史叙事中突出的是一种以空间含纳时间的叙事方式,作者的用意是在“压缩时间的长度来追求空间的宽度”,使小说在空间表现上“获得一种多维立体的空间容量”[6]179。
在《老生》主体故事的讲述中,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把叙事建立在空间地域之上,这四个故事发生的空间地域是一条河——倒流河。作为地理坐标的倒流河是有范围的,人们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地域内进行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的叙事也在其中进行。带有神秘色彩的唱师穿行在围绕着倒流河的乡镇空间中,作为听闻者、亲历者和讲述者,回忆从20世纪30年代陕北闹红军到21世纪初非典横行,回忆终结之时也就是唱师去世之时。开头与结尾由唱师联结起来,形成了“讲故事”的闭合叙事结构,故事在这个闭合结构中展开,其内容不可能突破这种闭合,我们可以试着思考,闭塞的乡镇空间中表现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使宏大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反右”、“文革”等各种形式的暴力逻辑得到认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的双重视野下来寻求。贾平凹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对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简单的谴责,而是能够以民间的视角切入时代。
“并置”作为小说空间形式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指在“文本中把游离于叙事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与暗示、象征与联系等并列地置放,使其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以此形成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置’其实就是‘词的组合’,就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7]。如果延伸一下“并置”的概念,还可以包括“结构性并置,如不同叙事者讲述的并置,多重故事的并置等”[8]。《老生》在空间形式上可以看成是并置结构。贾平凹借助秦岭倒流河这个地域空间形态,依靠唱师的行踪串联起四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但故事彼此之间没有情节联系,其共同点是由唱师来讲述。相对于传统小说,“并置”理论的核心是“加强空间形态而削弱线性时间形式”,在《老生》中通过另外一个并置结构体现,就是唱师弥留之际,听着老师给孩子教授《山海经》的文本释读,《山海经》的内容并列穿插在唱师回忆的四个故事中,作者借助重复的《山海经》内容阻断了主体故事叙事的时间顺序,而且这一重复情节把相对有时间意义的所谓中国百年历史在结构形式上分成四个片断,与其说这四个历史时段叙事缺乏明显的时间标识,不如说作者实际的意图并不是表现时间以及时间的延续,而是在展示一种同时性,即在记忆的一幅立体画面中,把存在于记忆里的一些印迹在时间以及时间的延续中表达出来,这种表述其实质是小说空间性的别一种表述。
另外,《老生》于主体故事中大段直引《山海经》,本身也是一种“并置”结构的叙事方式。《山海经》是一部空间地理之书,这个空间意象的出现表示了时间的永恒。而永恒时间,情节重复是“并置”的具体表现形式,作者通过“并置”的叙事技巧使《老生》产生了形式空间化。通过空间“并置”的叙事策略,使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历史小说呈现出空间叙事的特征,拓宽了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表现形式。另外,作者在民间历史叙事中演绎了个体记忆的生命感悟,使民间历史叙事的空间化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特征。
三、民间历史叙事的个体记忆呈现
《老生》通过唱丧歌唱师回忆的四个故事来呈现中国百年历史变迁与人事变革。文本中呈现的四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可以大概推算:第一个故事发生于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着重叙写陕南游击队的革命历史。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讲述的是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段历史。第三个故事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讲述的是“文革”的历史悲剧。第四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事件。由此,一部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被模糊地呈现出来了。这样的历史叙事让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何谓历史?
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事实上曾经发生过的一种原生态的存在事情,而这种原生态的历史如果要在现世人面前呈现又必须经过讲述或者记录,所谓“没有叙述就没有历史”[9],也正是由于历史的这种被叙述性,所以在历史叙事过程中,叙述者主观因素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会受叙述者的视角、立场和喜好的影响,因此历史叙事的主观化是必然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就更是主观色彩浓重。贾平凹在以民间视角来思考历史,他努力的方向是要逐渐实现作为知识分子俯瞰式的为普通民众写作向民间立场上的作为普通民众写作的价值立场的转换。首先作家自身要持有民间立场,其次是文本中叙事主体要持有民间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民间视角下的历史叙事无论怎样都必然会带有表达作家主体自我意识的话语。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民间视角的选择并不是对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放弃,所谓作家立场的转换,是指作家或知识分子“放弃在话语权上居高临下的霸权态度”,从对民间的排斥、批判到对民间的宽容与尊重的态度转换,并且与民间“形成平等对话的良性关系”[10]。在《老生》中,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设置主要体现在唱师和匡三两个线索人物所形成的民间史和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正史复调式的文本结构中。如果说《老生》的主体叙事是一种民间史的叙事,叙事的承担者是唱师。文本中还存在着一条忽隐忽现的正史叙事线索,那就是以匡三这个人物为主导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这个人物活着的时间以及后来人对他的传说的神秘性不逊于唱师,只不过匡三的存在是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中,作品中这两种叙事并不是对等出现,而是突出以唱师为主的“民间”,“民间”对言说历史权力的获得,其实质也暗含了一种正史与民间史的建构与解构、消解与重构,构成了民间史与正史的对话结构。
贾平凹创作《老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虽然小说的四个故事中有明显的时间暗示和历史事实,但这些并不是作者叙事的重点。一般来说,文学没有能力去呈现整个历史,用文学叙述历史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的,文学自身有其特殊的表现领域,即便是历史小说,它的目的也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呈现,不过是将历史作为文学表现的一种方式。贾平凹在《老生》中所呈现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境界中融入自己独特的个人体验,是被集体意识掩盖而遗忘的个人的历史,“文学即使面对历史也只能呈现个人记忆——这是它的性质,也是它的意义与存在的理由”[11]297。所以,《老生》中表现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
贾平凹曾说过,“在我的意识里,这一历史通过平庸的琐碎的日子才能真实地呈现,而呈现得越沉稳、越详尽,理念的东西就愈坚定突出。”[12]《老生》中所呈现就是平庸的琐碎的日子,“表达的是生活”还有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13]293。历史是日常的,是“底层民众日常的历史”,贾平凹把近百年的历史时间放置在四个村镇空间进行叙述,而且把从民国到当代的时间放到阴歌唱师平静的一天的回忆中,就像一个老人悠闲平淡地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对这个古老故事的讲述中,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还原为个体叙事,各个历史时期的动荡历史事实被排挤在记忆的边缘,因为唱师本身的角色就是一个超越社会、民族的“巫神”,唱师在文本中只是在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所以,作家所持的历史的民间叙事关注的不是在历史动荡冲突年代获得胜利者的历史,而是在历史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情感与矛盾的书写。作为一部叙写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文学作品,贾平凹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对宏观历史准确完整的记录,最根本的是他要通过这部作品表达自己进入花甲之年对经历的历史做出负责任的审视思考和反思感悟,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对新历史小说评论中所说的,“新历史小说讲的不是历史,作家不过是在一个非现实的语境里有所寄托而已”[14],这样的叙事直逼对生活本体价值意义的追问。
贾平凹在历史回忆叙事中又有怎样的寄托呢?这可能就要从作家对自己的年龄和生命状态的真切陈述来看,“50岁以后感到周围的熟人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并且自己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瞌睡也日渐减少,便知道是老了”,关于人世的贪恋、拒绝、偏执、嫉妒都可以做到,可最不可控的是记忆,“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15]。“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该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岁了呢?……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转化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16],“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13]289从贾平凹的《古炉》到《带灯》再到《老生》的后记文字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在生命渐入老年阶段后欲罢不能的是对生命的记忆,生存的生命状态使他在回味生命的记忆中,回溯历史与倾心古典。所以,《老生》是烟熏出来的,是进入花甲之年的他在烟雾吞吐间对历史与生命的沉思。以此我们可以将唱师追忆的历史归结为作者本人的基本生命状态: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无论是叱咤风云还是平平庸庸,无论社会动荡还是和平安详,人世间的许多东西和事情都可能会有选择的机会,可唯有生与死是无法选择也不可避免的。而构成这人类历史长河的正是绵延不断的生生死死,有如亘古不变的倒流河,而不断交替变化着的则是社会、时代、人事、国事。就此来看,《老生》的民间叙事是将社会时代变迁、人世与人事的推演还原到人生存最为本体的生命状态,而恰恰在这还原的过程中,超越了现实,走向了永恒境界。
四、结语
民间写史和正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史是以报告、全纪实为核心的严肃事情,而贾平凹在创作时想的历史是荒唐事情的历史,他“不仅要讲山海纵横与客观事件,更要讲每一种人群在跌宕历史中的浮沉辗转”[17],是历史背后对人的命运、人生、时空问题的思考。倒流河的地域空间“是与天道人事联结在一起,其间隐含着文化与生命的密码”[18]162,河流比喻时间的流逝,并从中体验人事变幻和生命短促,即所谓“临水感逝川之叹”,已经成为中国人时或悲悯、时或旷达、时或感伤的潜在思维模式。似水年华,既映衬着生命的短促,也映衬着历史的荒凉,增加了人生与宇宙相交流的无限感慨。这条河流也超越地理风貌的意义而具有了一种“象征隐喻,成为一种浸透着主体意识与文化观念的意象空间”[18]162。
具体来讲,《老生》中所呈现的陕西南部的乡村里,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历史生活,构成这近百年历史进程的活动主体是“寓社会时代之风云变幻于日常生活的苍茫涌动”,所以,作家在作品中的叙事意图是明确的,那就是以民间视角,带着人文情怀来叙写历史,以期在解构宏大历史的叙事中返归民间生活的本真存在状态,用还原日常生活化的叙事方式来呈现中国百年历史的社会风云变幻。
历史不需要深度,它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最常态,“是生活空间之下的一切,是无序的排列,是非逻辑的生生灭灭。”[11]281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事件在这样日常生活的历史叙事中会变得轻如鸿毛,在民间化的想象中突出的是人性与人情味。贾平凹在《老生》中叙述的四个历史故事既叙述了20世纪中国百年的革命史,更叙写了在百年历史变革中民间底层百姓的世故人情,历史不再仅仅是历史,记忆也不再是个人执著于现实的记忆,这大概就是《老生》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1999,(5).
[2][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2.
[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求缺卷)[M].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334.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4.
[5]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5.
[6]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7][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芬,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1:译序.
[8]吴晓东.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J].天涯,2002,(5):176-183.
[9][美]海登·怀特.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M]//陈启能.书写历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68.
[10]王玉珠.民间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话语的建构[J].人文杂志,2013,(8):63-69.
[11]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12]贾平凹.在《秦腔》首发式上的发言[EB/OL](2005-04-12).http://neus.xaual.edu.cn/searchread.php?dossid=40&newsid=2088&mainbey=首发.
[13]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4]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9.
[15]贾平凹.古炉后记[M]//前言与后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26.
[16]贾平凹.带灯后记[M]//前言与后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6.
[17]吴波.贾平凹“老生”长谈百年风云[N].广州日报,2014-11-01.
[18]韩鲁华.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193-05
[作者简介]陆欣(197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项目“中美生态文学的审丑意识比较研究”(13D074);黑龙江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培养对象专项资金项目
[收稿日期]2015-02-28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另有一些关于“民间”的言说,主要是指那些在官方的文学体制之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在这样的意义上,甚至韩东与朱文这样更多地带有前卫或另类色彩的作家,也都自称为“民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