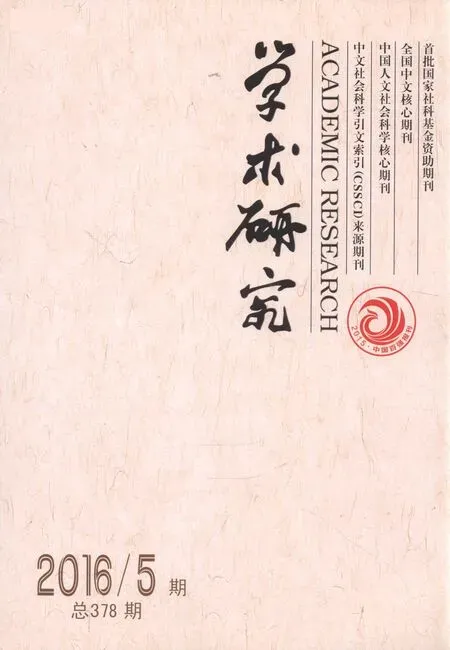微观权力、自我技术与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管理的后现代分析*
胡国栋
微观权力、自我技术与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管理的后现代分析*
胡国栋
[摘要]福柯提出的基于知识的微观权力观,为我们透视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选拔、招聘、培训、控制与激励等一系列精巧设计都被一种基于理性的知识话语体系所左右,其实质是在“宏观叙事”下预设了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通过各种或显或隐的统治技术将员工规训为一个个温顺而有用的身体。基于此,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应该从统治技术转向自我技术。伦理作为连接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桥梁,它一方面通过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按照个人目标去行动,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行动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从而使两类目标实现共时性聚合。基于目标聚合的人力资源管理,一要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以实施自我管理,二要实施以伦理为核心,以心理契约为中介,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德性领导方式。
[关键词]微观权力自我技术组织公民行为人力资源管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与本土化研究”(14FGL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组织理论和组织治理研究”(11&ZD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范式转换研究”(13AGL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层管理者战略性意义生成——给赋行为对组织变革压力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71472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中差序式领导对员工及团队创造力的影响”(71402019)的阶段性成果。
人力资源管理围绕两个核心主题展开:其一是招聘、监督、考核等控制机制,目的是保证员工的目标行为与组织的目标行为的一致性,尽可能地使个体理性符合组织理性;其二是培训、薪酬、奖惩等激励机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潜力与创造性,尽可能地增加组织的活力和能量。无论控制还是激励,其焦点都是员工行为的矫正或改变。对此,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与方法多奠基于固定化、显性化的宏观权力架构,确定每一个员工在组织中的具体位置,并通过权力的意义指向弱化或强化员工的某种行为。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嵌入在一个庞大的、机械化的权力体系及其话语产生的宏观叙事之中。宏观权力天然地具有统治性与压迫性,由其主导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可能真正导向人本主义者对员工自我实现的关注,更不可能使未来的组织成为德鲁克所说的由“有责任的工人”主导的“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Drucker,1946)。[1]
后现代主义者对压迫性权力与宏观叙事提出激烈批评(Drucker,1959;Foucault,1975;Lyotard,1979)。[2] [3] [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规训技术把人变成温顺而有用的身体(Michel Foucault,1975)。[5]规训是一种特殊的干预、监视与训诫肉体的权力技术,它与局部领域的微观权力及其运作息息相关。福柯的相关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两大主题密切相关,而其出发点却是与宏观权力迥异的微观权力观。我们需要这种基于知识的微观权力视角,来系统思考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如何从强加的统治技术转向诱发自觉、自愿行为的自我技术。
一、微观权力:人力资源管理考察的后现代主义视角
权力分析是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为反对启蒙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构筑的宏观叙事模式,福柯从发生学的视角发展出一种微观视域中的新权力观。微观权力与具有占有性、实体性、结构性、总体性与压迫性的传统经典权力模式不同,是一种被传统研究忽略的,地方性、差异性的生物性权力。传统的权力理论大都从宏观的技术或经济角度对组织中的权力现象进行总体性描述,并试图找出具有普遍性和总体性的解释原则,其目的是通过宏观权力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统制原则,通过强制途径迫使权力客体做出权力主体的期望性行为,否则便会遭到报复性打击或被社会边缘化为“异端”。福柯(2003)认为,这种压迫性权力在现代文明的粉饰下日益削弱其惩戒作用,暴力性的惩罚逐渐转向一种规训技术,使“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习惯性的动作”。[6]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在微观权力的视域中去透视。
在现代社会,真正对个体行为发挥主要规范作用的权力不是嵌入在法律、规则与制度中的普遍威权,而是一种微观的、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关系性与策略性的,而非一种可以被占有的所有权,如福柯所说,“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7]微观权力具有流动性和无中心性,“各种力量是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的场(field)”,“除了不断地向别处扩散,快感和权力绝不可能在某个权力中心点、某个循环节点或联接点、某个场址中……凝结或驻留”(Foucault,1980)。[8]正是这种渗透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微观权力而非结构化的宏观权力在现代社会构筑了个体的躯体和认同。
微观权力的发生及其运行与知识密切相关。微观权力之所以具有以上特征就在于它本身是一种“权力—知识”体系。在审视人口管理技术中,福柯提出了“管制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即“管辖、政治”(government)与“合理性”(rationality)两词的组合(Burchell,1991)。[9]“管制”是一种塑造、指导与影响人的行为的活动,“合理性”是事物被管制之前必须被知晓的观念,“管制”天然地依赖于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可认知的才是可管制的。也就是说,权力与知识相互纠缠,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权力的实践生产知识,知识持续地产生权力效果,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实践,没有权力也没有知识”(Foucault,1980)。[10]权力的产生及运行与知识的形成及积累具有共时性,两者紧密结合并拥有共同的作用范围。在微观领域,任何不对称的信息与关系都能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因为这种信息与关系本身是一种知识。在现实中,具体的不确定性因素事实上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如果不确定性存在,那么能够控制不确定性的行动者,即使仅能对不确定性部分地加以控制,即可利用不确定性,将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那些依存于不确定性的人们。就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从行动者的观点看,不确定性意味着权力”(费埃德伯格,2005)。[11]
微观权力观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权力思想,而且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模式。福柯认为权力和理性嵌刻于各种话语和制度性场址中,因而他支持一种多元的、片段性的和不确定的,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分析模式。这对于我们认知和观察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实践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运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关注组织中员工行动的具体领域,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整体性、一致性的行动场所。员工的行为主要不是基于组织的宏观命令与控制体系,而是基于不确定性知识在微观领域中的协商性交换,因此是一种微观权力博弈行为。这启发我们在审视人力资源管理时,必须关注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而不应将组织与所有员工的行为假象为铁板一块式的可控整体。另外,从微观权力的视角,我们发现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选拔、招聘、培训、控制与激励等一系列精巧设计都被一种基于理性的知识话语体系所左右。这使我们可以深入到组织的内部,探究人力资源管理中权力运行的具体路径及员工行为发生的具体、直接的原因,对我们系统思考现有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实质,并探寻与知识经济时代更为切合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与方法有重要意义。
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统治技术与人员规训
个体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分析的基本单位,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分析,组织中个体的主体性不是先天具备的,而是在一系列制度与规则的精巧安排下,通过规训技术被历史性生产出来的。无论是招聘、挑选、评价、培训,还是开发与补偿,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个架构都基于一种理性的设计,尽可能地增加决策与控制的精确性并减少员工的主观性,由此生产出一种科学知识的“宏观叙事”(grand narratives)并形成一种话语霸权,使组织中的每一个员工都被固定在某个具体位置上,并在预设的美好前景的召唤或惩罚机制的恐吓下,自觉或被迫地做出管理者的预期行为。这种知识话语构造的权力无处不在,在各种精细的架构与设计中使员工的自主性消失。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是,在“宏观叙事”下预设了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通过各种或显或隐的统治技术将员工规训为一个个温顺而有用的身体。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出发点是站在掌握资本或知识的具有优势地位的管理者的立场,而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立场,更没有顾及人力资源作为人在组织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如何实现人的本质。以福柯对权力所进行的“微观物理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个流程中的一切精细安排与设计,都是“具有很大扩散力的狡猾伎俩……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观安排……羞于承认屈从于经济要求的机制或使用卑劣的强制方式的机制”(凯尔纳、贝斯特,1999)。[12]在古代对人的管理,由于缺乏资本概念,个体在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主要被视为一种占有物而非一种独立的资源,那时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主要基于赤裸裸的暴力和具有普遍主义的绝对性伦理,由此构筑的宏观权力对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控制与支配过程残酷而野蛮。近现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人在组织中逐渐被视为一种资源,并且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是为获得利润或绩效而做出的最重要投入之一,人的尊严和地位不断提升,对人力资源的控制也不像古代那样明显、直接和残暴,而是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规则中嵌入了一种知识,形成了一种科学理性的话语霸权,使控制变得文明而精细。但是两者的实质与目的都是一种人员规训技术,只不过后者变得更加含蓄了。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方法,不管是基于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是基于理性的绩效考评与职位升降还是基于人性的激励与领导,实质上都是一种控制员工的规训技术。由于不确定性无法规避,员工在进入企业之时与雇主签订的雇佣合同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种不完全契约(Baldamus,1961),[13]员工本应在这种契约之下享有部分剩余控制权,但这种控制权事实上湮没在被社会与组织共同建构的话语霸权之中。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职位归类、职责划分和等级设计,事实上是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编码和归类,都有其明确而理性的指向与暗示,使员工的行为不得不按照其预期进行。正如Barbara Townley(1993)所说,“人力资源管理的工具——对技能的目录编纂、绩效评价体系、评测方法和态度测试——都是通过分化、分类确立等级序列的安排,以促进员工个体行为的秩序化”。[14]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规则生产了一种有所指向的知识,它不间断地对员工进行强制,监督着员工活动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其结果,它尽可能地严密而明确地划分员工在组织中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对各种具体活动进行编码,使员工无形地被套牢在一种功利——驯顺的关系之中,这就是微观权力的运作艺术——规训的力量。正是这种精巧安排所构筑的宏观叙事,使发散性的权力弥漫在组织中的每一个角落,调控着员工的具体行为,事实上剥夺了员工对雇用契约的剩余控制权,而不断地被组织规训为所需要的身体。这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较古代更有效率,因为基于知识的权力能够深入到员工灵魂的深处,并在组织中不断弥散,将单独的个体的力量在功利——驯顺的关系中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更有效率的机制。
以微观权力视角来审视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目的,不仅仅是弄清现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实质,更是为了探讨更加契合人性与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组织中的微观权力及其规训力量虽然也是一种控制技术,但与结构化的宏观权力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一种直接的压迫性力量和单向性的统治行为,而是一种全面调控员工行为的策略技术。由于知识生产的自觉性与传播的双向性,微观权力不但可以成为管理者控制员工的统治性力量,同样也可以成为雇员与雇主以及员工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力量,成为积极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后现代主义者Lyotard(1979)强烈抨击通过工具理性构筑的话语霸权与“宏观叙事”,反对普遍主义的统一性原则,主张一种差异性、多元化的策略。[15]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借助结构化的制度安排及其话语霸权剥夺了员工的自我控制权,成为一种单向性的统治力量。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分析中,需要恢复雇员与雇主的平等地位,兼顾雇员与雇主双方的立场而非仅仅是优势地位者的立场来重新思考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与技术,将人力资源管理分析的焦点从统治技术(个人在话语和实践中受他人统治并被客观化)转向自我技术(个人通过伦理或自我建构方式创造自我认同)。按此路径,微观权力便可能成为员工在组织中追求自我实现的积极力量。
三、自我技术、伦理与组织公民行为
在Greenwood(2002)看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被定义为,“通过人实现组织的商业战略目标,并满足人的个体需要”。[16]人力资源管理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则取决于对“人”的态度及使用途径。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两个目标的分歧,现有的主导逻辑是:通过理性设计控制人的行为,使个人目标尽可能地与组织目标一致,个人目标在组织目标实现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每个员工都有其具体的各异的目标,假如不通过制度与规则把这些分散的目标聚焦于组织目标,组织的商业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个人的薪资与福利等个人目标也就无法保障。基于此逻辑的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的个人目标被压抑或消解为一个假想的统一性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是组织目标达成的附件。这实质上是把员工视为一种简单的并有着相似需求的工具,基于此的人力资源管理事实上也就成为一种统治性技术。
从微观权力视角观察,由于知识的变化与流动,员工的个体目标是分散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并因时因地而变化,其每一个行为都是在其具体目标指导下与其他员工进行权力博弈的结果。为此,我们必须把工作过程本身视为员工的目标行为,员工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得到最后的物质报酬。也就是说,员工在工作过程也有某种追求和满足,这种细微的追求与满足可能是其更为真实的、具体的目标。管理者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应以统治性的宏观权力建构将其忽略或抹煞。但这绝不说明可以降低对组织目标的关注和重视,而是需要将关注的视角扩展到员工的具体目标、微观领域与具体行为这一层面。基于这一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同时实现员工与组织目标,两个目标的统一不再是传统的“先……后……”思路,而是两者可以共时性地兼顾与满足。要做到这点,管理者必须开发与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
福柯(1982)认为个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17]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知识,“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结果”(Peter Dews,1987)。[18]基于对个体自由与非压抑性文明的向往,福柯晚年转向了具有解放性质的自我技术。他将自我技术定义为,“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的实践(Foucault,1988)。[19]福柯赞成个体通过这种自我技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自主的、自我控制的、乐意享有别具一格的新经验、快感和欲望的存在(凯尔纳,1999)。[20]自我技术通过微观权力而实现,它关注员工的自由解放,并与具体、分散的目标紧密相连。
开发并强化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技术,可以减少组织用以制度、规则建设与维护方面的成本,更关键的是自我技术可以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一种自由的体验和某种自我实现的愉悦。这种导向自由与解放的自我技术与伦理息息相关,自由是“伦理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则是“自由所采取的审慎的形式”(Foucault,1988)。[21]如果组织中的员工通过自我控制和伦理规范使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件艺术品,而不再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在雇主的监控下被迫地做不情愿的事情,那么人力资源管理本身也就变成一种令人振奋和富有意义的艺术而不再是冷漠的科学、技术体系。从微观权力视角出发的伦理不应是具有普遍主义、永恒性与绝对性的道德律条,而是每个个体使自己的生活过的优雅、美好与体面的责任,是一种差异化与多样性、包容性的个体伦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中事实上不存在“既是普遍发现的,又是本体论上固定的,而且还是足够确定的和真实的非历史本质,可以只由逻辑推导或经营产生或证明的明确的伦理理论”(舒斯特曼,2002)。[22]导向自我技术的伦理规范更多是一种私人伦理,它指向的问题是“个体应该怎样塑造他的生活去自我实现作为人的目标的问题”。[23]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这种自我技术、伦理规范与员工个体分散的、多样化的具体目标紧密结合为一体。
对于企业来说,利润是其首要目标与生存之基。自我技术主要关注的是员工个体目标的实现,但如果个体目标向多个方向无限分散,组织的商业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从微观权力视角,我们仍然需要深入探究伦理的作用。一方面,在具体行动领域,员工彼此运用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微观权力进行协商性交换,这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权力博弈过程。由于多数员工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场合,因此这种权力交换是重复博弈行为。制度与规范可以外在强加给重复博弈行为一种游戏规则,但这种强加对员工是一种压迫性行为,而且对知识型员工其作用日益有限。而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具有价值规范作用,并能通过构建无形的价值网络广泛覆盖组织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组织中每个员工的内心。加之伦理本身的作用机制是一种自我技术,因此它对微观策略的干预与调适远较硬性的制度与规则强大而有用。另一方面,伦理有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之分。作为自我技术的伦理主要是私人伦理,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实交叉作用,使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两者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当员工认可了公共伦理并将之上升到信念的角度来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时,公共伦理就内化为私人伦理的一部分。因此,伦理能够形成一种“合作性”企业文化,在Miller(1992)看来,在一个合作性的企业文化中,……每个博弈者预期所有其他人合作并实施合作规范。[24]伦理能够强化这种对合作的预期,在对组织员工的行为进行调适和干预时,激发利他动机,诱发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将员工具体行为导向组织目标。
Organ(1998)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没有得到组织中正式报酬系统直接或明确回报的自愿性的个体行为,这些行为从总体上提升了组织的运作效能。[25]组织公民行为超出了组织对员工工作的岗位描述,是员工出于个人意愿而做出的既与正式奖励制度无任何联系又非角色内所要求的利他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对传统组织设计的专业化经典原则的一种扬弃,它基于高度的组织认同,是员工组织生活中建构个人价值的重要表现。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与员工对组织的自我感知息息相关,而这种感知本身是一种自我知识,同时也是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可见,出于自我约束而兼有利他导向的伦理事实上成为沟通和融合员工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桥梁。一方面,它通过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按照个体目标去行动;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行动导向组织公民行为。这样,员工目标与组织目标就自然流畅而又共时地凝聚在一起,而聚合性目标的出现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改进的关键要素。
四、基于目标聚合的人力资源管理改进策略
知识经济时代的员工在价值观、教育与技能方面都与传统操作型员工有很大不同,他们一般具备高层次的教育与培训经历,拥有高水平的技能,更为突出的是,他们要求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参与意识与自主意识都比较强。德鲁克(1999)曾指出,“20世纪的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生产设备。而在21世纪,无论商业结构还是非商业结构,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是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26]德鲁克目标管理的实质就在于承认组织中存在多样性的目标体系,在对组织进行目标体系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协商界定组织与个人均可接受的共同目标,他的出发点是从组织出发来界定员工个体的目标,使无数个体行为聚敛到更为宏大的组织目标之中。但从福柯的微观权力观来看,知识工作者的个人目标对其行为有更强的支配力,他们更多地忠实于自己的职业与信念而不是所服务的组织,在微观权力博弈中更能巧妙并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自我知识,结构化的宏观权力对他们的作用被大幅度消减并遭到极力抵制。为此,组织管理者必须善于干预处于博弈场域的组织局部秩序,改变知识工作者之间权力博弈的游戏规则,利用知识来管理知识工作者。如何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并经由伦理将自我技术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使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呈现内在性聚合,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管理者开发知识工作者劳动效率和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
(一)选择性招聘与培训中的知识传递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目标聚合始于招聘,并在以后的组织生活中逐渐强化。每个组织都有围绕其目标展开的一套价值体系,在招聘环节选择价值观与组织价值体系相似或接近的人员,能够极大地节省目标聚合的成本。如唐斯(2006)所说,“选择性人员招聘对建立高度一致的深层目标,其费用几乎总是比改变组织中现有成员的多样化目标所需的成本低”。[27]因为,这些员工的个人目标经过社会教育与文化侵染已经很容易与组织目标聚合,而这种进入组织之前的目标规范成本由社会垫付。因此,在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招聘主管必须高度重视员工的价值、信念考察,进行价值过滤,筛选出具有与组织使命及价值观相似特征的员工。通过价值筛选的人员,其目标与信念通常已经“凝固”到行为模式之中,并且这些员工的个人目标行为与组织目标接近,因此很容易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但是价值筛选也存在很大困难,主要是价值观本身比较抽象,价值观的边界比较模糊,其具体检测标准很难制定;另外,价值考察很容易受考察者本人的价值观的影响,而考察者本人的价值观未必和组织所要求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为克服这些障碍,领导者除了派人做必要调查,了解考察者以往的道德表现外,还可以聘请专门的中介机构,包括咨询机构和人才测评组织,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直接对应聘员工进行价值测试。
员工进入组织之后,一般需要各种各样的培训。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培训不仅仅是对员工传送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传递知识。员工一般会对组织中的非正式人际网络及其习惯性行为进行接受和模仿,其个人知识会不断地融入到组织知识之中。培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员工的个人知识与规范化的组织知识进行连接,并使隐性的知识显性化。为此,管理者在培训中必须重视的是道德教化与人际关系技能训练。通过伦理营造一种合作性的组织文化,并使之内化到每一个员工内心深处,成为其自我知识的一部分,从而为启动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自我技术奠定知识基础。道德教化的关键就是确立员工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为此,管理者可以尝试在员工培训规划中设立专门的伦理培训班,或在一般的培训中增加伦理培训课程。伦理培训中要强调团队合作精神,鼓励员工做出超越工作职责描述的利他性行为。这样,员工的自我知识与组织知识连接并相互渗透,个人目标也就凝聚在组织目标之中。
(二)自我技术导向的自我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不能仅仅站在组织的立场考虑组织目标的达成,也必须兼顾员工个人目标的实现。目标聚合不是把员工的个体目标消解到组织目标之中,而是从自我技术中导出组织公民行为,兼顾两个目标,实现管理主体与客体双方利益的共赢。因此,管理者需要开发并强化员工的自我技术,使之在个人目标支配下做出自觉性行为。对于即将兴起的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的新型企业,Peter F.Drucker(1954)认为,“必须把工作中的人力当‘人’来看待。换句话说,我们也必须重视‘人性面’,强调人是有道德感和社会性的动物,设法让工作的设计安排符合人的特质。作为一种资源,人力能为企业所‘使用’,然而作为‘人’,唯有这个人本身才能充分自我利用,发挥所长”。[28]实施自我管理对员工具有很强的激励效应。Frederick Herzberg等人(1959)论证了最有力的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即激励因素与工作本身、个人的工作成就、工作责任感、通过工作获得的晋升与承认等都有直接关系。[29]自我管理正是以工作为中心的激励方式的高层实现形式。它消除了结构化的权力对员工的压迫性控制,使员工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由个体目标来决定自己的具体行为,在组织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员工就不再把工作视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一种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这就能极大地激发工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从微观权力视角看,员工都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进行自我管理,基于个人目标,从事过去的习惯性行为或基于不确定性与他者进行权力博弈。欲实施目标聚合的自我管理,管理者应当使员工具有自律精神和追求完美的决心,并为之确立一个朝向组织的方向。从雇主立场看,管理者需要主动开发和强化员工的自我控制技术,引导员工进行自我关注,使其意识到在组织中工作不仅仅是为公司创造利润和获得薪资报酬,更重要的是追求自我实现与人生的意义,获得一种基于工作的内在满足,从而激发其对组织的风险精神和忠诚度。从雇员角度看,员工需要善于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扩大用以博弈的知识权力,同时注意自我修炼,适当地进行意志力训练以节制行为,发展合作意识和非零和博弈思维,争取在与他者的互利中实现个人目标,在对组织奉献才智的同时体验自我实现的快感。
(三)德性领导、心理契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生成
基于目标聚合的自我管理不完全是员工的自发行为,否则组织很容易陷入混乱。因此,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员工不再需要领导,而应该是一种以伦理为核心,以心理契约为中介,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德性领导方式。伦理作为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聚合的桥梁,主要来源于个体的品格、德性和情感等内在性因素。它关注什么是公正、公平、正义或善,思索我们应做什么问题,不应做什么问题。伦理作为人类对自我的规范和约束,通过教育等手段内化、渗透到主体的知、情、意中,并积淀、凝结成为主体性格的一部分,具有非强制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强制性影响力,是对自我的一种内在管理,并能同时产生外部秩序与效能。
德性领导的基础建立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基于伦理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心理契约之上,没有这种基于德性与双方相互承诺的责任或义务的心理契约,德性领导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德性领导是员工对领导者的一种心理认同,通过这种认同,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取得最大程度的一致性,经过目标内在化过程,形成上下一致的合力均衡状态。因此,德性领导是一种自然性影响力,其作用的发挥不经由强制性的权力系统,而是依靠被领导者发自内心的情感,经由双方的心理契约,员工的自我技术自然发展出组织公民行为,组织便能水到渠成地实现其绩效目标。
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的概念最早由Argyris(1960)提出,他认为在工人与工头之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心理的工作契约”。[30]Kotter(1973)将心理契约界定为存在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份内隐协议,协议中指明了双方关系中相互期望的付出与收获。[31]我们认为,心理契约在德性领导中是领导者和员工之间内隐的一种交换关系。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权力以接受者的认同为基础并通过它来发挥作用,其间必然存在一种中介性的东西,即权力从发出到接受者认同有一个转化过程,心理契约便承担了这一功能。
心理契约的起点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互惠,并通过这种互惠将员工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进行融合。德性领导者信任并尊重员工,为其提供资源、场所、权力等支持性资源,员工就会从心理上期望通过提高组织公民行为来寻求与领导者之间的平等互惠。可见,德性领导实质是一种领导与员工的互惠性交换关系。心理契约能否达成以及上下级交换关系能否得以实现,在很多程度上又进一步取决于员工的自我知识。只有在各种微观权力的交互作用中,员工感知到这种交换的必要性,心理契约才可能建立。因此,德性领导的实施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又进一步依赖于员工的自我技术与自我管理能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认知和维持微观权力的良性运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保障员工行动的自由空间及发展自我技术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条件,实施德性领导方式是重要驱动力,缔结心理契约则是关键途径,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组织绩效构成部分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结果。
[参考文献]
[1] Peter F.Drucker,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46.
[2] Peter F.Drucker,Landmarks of Tomorrow:A Report on the New“Post-Modern”Word,New York:Happer and Row,1959.
[3][5]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erson,London:Penguin,1977.
[4][15]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lation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St.Paul,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6][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8、153页。
[8]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0,p.102,p.49.
[9] G.Burchell,C.Gordon,& P.Miller,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73-86.
[10] 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ichel Foucault,1972-77,England:Harvester,1980,p.52.
[11]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2][20]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7、81页。
[13] W.Baldamus,Efficiency and Effort,London:Tavistock,1961,p.2.
[14] Barbara Townley,Foucault,“Power/ Knowledge, and Its Relevanc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no.3,1993,pp.518-545.
[16] Michelle R.Greenwood,“Ethics and HRM:A Review and Conceptual Analysi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no.3,2002,pp.261-278.
[17] Michel 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op.cit,1982,p.208-226.
[18] Peter Dews,Logics of Disintegration,London:Verso,1987,p.65-66.
[19] 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L.Martin,H.Gutman,& P.H.Hutton (eds.),London:Tavistock,1988,p.16-49.
[21] Michel Foucault,“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In James Bernauer and David Rasmussen,The Final Foucaul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p.4.
[22][23]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19、316页。
[24] J.Gary Miller,Managerial Dilemma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5] D.W.Organ,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88.
[26] Peter F.Drucker,Management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Happer Press,1999.
[27]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28] Peter F.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Happer and Row Press,1954,p.20.
[29] Frederick Herzberg,Bernard Mausner,& Barbara Snyderman,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Wiley,1959.
[30] C.Argyris,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Homeword,IL:Dorsey Press,1960.
[31] John .P.Kotter,“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no.15,1973.
责任编辑:张超
历史学
作者简介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5)。
〔中图分类号〕F272.92;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