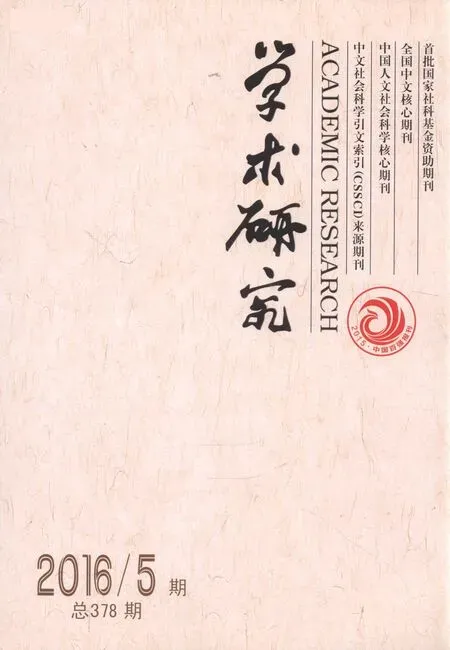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三种经验性批判
——兼谈马克思经验的逻辑*
高惠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三种经验性批判
——兼谈马克思经验的逻辑*
高惠芳
[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直接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作,然而从形式到内容,它更像是《论犹太人问题》的延续和深化。《导言》分别对历史法学派、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整个批判无非是思辨的哲学对市民社会外部关系的批判,尚需从市民社会内部展开经验性的批判,其中内蕴从纯粹哲学的逻辑学向以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的逻辑学批判的方法论转换。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历史法学派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经验批判的逻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15BKS019)、2015年度北京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习近平辩证法思想的总体性研究”、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XJEDU070114A03)的阶段性成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的正本,然后才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副本。从批判的形式到内容,与《导言》更为接近的是《问题》而非《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换句话说,我们能从同时完成于1843年10—12月间的两部著作《问题》和《导言》中发现更多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对《导言》的分析中,我们采取与《问题》结合讨论的方式,当然,我们不会排斥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分析。
马克思给予《导言》的任务可以总结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历史赋予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揭露后宗教时代人的自我异化,展开针对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国家制度而非天国、宗教、神学的批判,因而它具有非神圣性的典型特征。对布鲁诺·鲍威尔宗教批判的批判是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前奏和序曲,《导言》是《问题》的延续和深化。
一、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
我们首先讨论马克思写于1842年7月底—8月6日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因为这篇文章公开地谈到实证与理性的关系。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古·胡果的思维是实证的,因而是非批判的。胡果是自然状态之于人类本性的现实性论点的代言人,马克思称他为“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历史学派的代言人”,并将其著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视为“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2]弗·卡·萨维尼等人就是他的继承人和奴仆。胡果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并被批判,一是因为历史法学派的继承人、奴仆萨维尼在1842年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使得历史法学派的理论、方法成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这是批判历史法学派的世俗原因;二是因为“历史法学派的主张与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3]它具有与黑格尔法哲学的糟粕同类性质的千奇百怪的谬论,唯独没有黑格尔法哲学的“合乎理性”的东西,思辨的意义被历史法学派丢弃到经验阵地的垃圾堆里,故而对历史法学派的彻底批判就要返回到它的哲学,“返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去”。[4]这是批判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因素。不联手黑格尔去打败他的敌人,马克思也就不能完成对黑格尔的彻底批判。在这个战场上,批判的武器一部分是从黑格尔阵地上挖掘出来的,一部分是在反思敌人武器最致命的弱点时收获的。马克思既要批判胡果,同时还要批判黑格尔,并对论战的双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尽管胡果声称自己是康德的弟子,并完全师承了康德哲学,但在马克思看来,胡果曲解了康德,其哲学水平亦低于康德。康德认为,感性的经验事物实在地存在着,但又不为我们完全认识,因而不得不为上帝和信仰置留一块地盘;胡果认为,既然“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承认它完全有效”,进一步,胡果“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事物必然不是实证的(positiv)。①“positiv”既有“实证”的意思,又有“实际的”、“实在的”意思。参见《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编者注。不仅如此,胡果还要证明:“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么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5]前一论断证实了经验和理性的二律背反,不仅没有为康德保留尊严,相反,却极大地倒退到前康德的历史,而且与黑格尔的思辨形成鲜明的对立。后一论断表明胡果在经验和理性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应选择理性还是选择经验,殊不知康德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显然,在这里胡果把自己弄糊涂了。有一点值得注意,胡果无意中探讨了研究的前提、出发点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思维革命中的关键要素。
胡果研究的前提和方法都是非批判、非科学的。阿尔都塞曾将这种非批判、非科学的研究归类为“意识形态”——通常指称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曾把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们视作“意识形态”家,如此说来,胡果、萨维尼之流还不配“意识形态”家的称号,他们的理论仅算作“前意识形态”而已。正因为马克思说:“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是非批判的”。[6]由此可见,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当做批判的武器,并认为胡果的实证主义刚好是思辨理性的批判对象。首先,马克思认为胡果的实证主义充满随意性。“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种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摩西和伏尔泰、理查森和荷马、蒙田和阿蒙”,连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都被他任性、非批判地引用了,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青年黑格尔派。其次,马克思斥责胡果在历史研究时的怠惰,从未打算对经验史实进行仔细的甄别。“这一”实证的事物和“那一”实证的事物在他的眼里都是一样的,甚至没有任何的时间、空间的差别,历史的今天和昨天没有区别,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不合理性的。因此,自然法的研究也就不用在乎这些实证的知识,至少在引用它们时勿以区分。自然,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也就不会成为胡果的研究前提,进一步来说,身为思维前提的实证的知识更不会为思维提供材料和动力。
此时的马克思主要立足于青年黑格尔派去批判胡果,黑格尔为他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正像马克思批判——“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但)他不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所揭露的胡果的“失误之处”一样,这个评价同样也“暴露”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7]马克思认为这句话有着积极的含义。胡果看到了“国民议会的法兰西国家”之于“摄政者的法兰西国家”的合理性;马克思看到了“国民议会的法兰西国家”解体、实现“政治解放”的进步性,他赞扬这一过程是“新精神从旧形式下的解放”,“是新生活对自身力量的感觉,新生活正在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后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犹太人问题》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再褒扬政治社会的“政治解放”,他揭露并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幻象。
我们最终必须承认,1842年马克思写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时,只是单脚站立在黑格尔阵地,另一只脚悬在阵地上空时刻准备寻找新的立足点,一旦发现他就要抽身于德国意识形态之外了。为此,笔者引用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的结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实际上只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8]
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们——胡果的继承者——已用浪漫的幻想或思辨的理性重新诠释了法的思想,使得历史法学派多少带有一些思辨的神秘的色彩,而这里,理性的神秘已不再被马克思所褒扬,毕竟马克思已经或至少准备拔腿站在黑格尔阵营之外了。
二、对理论政治派的批判
1843年底马克思写作《导言》时,再一次批判了历史法学派,批判他们的“前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历史法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posteriori]”;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称他们为“好心的狂热者”、“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斥责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自由历史”无非是“野猪的自由历史”,他们只能在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才可寻找到德国人的自由历史,[9]“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隐喻了理性的纯粹的单一性,德国的现状则直接意味理性的特殊性的现实性。分歧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应对现实性的表象进行批判,从而复归条顿原始森林中的德国精神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已有的对德国现实的经验材料的批判是非批判、非科学的,应对批判展开批判。作为理性的普遍性和单一性的中介,德国的现状就是国家精神的实体性的现实性,对这一中介着的现实性的批判本身就是思辨的逻辑学的必要环节——进一步展开对德国政治的批判。[10]而在马克思看来,“从德国的现状[sts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历史”,依然不能解释、说明德国历史中的1843年。青年黑格尔派视域中的德国现状仍然是观念的历史,国家制度、市民社会无非是德国精神的中介物,“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11]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现状的批判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
“理论政治派可能带有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特征”,[12]青年黑格尔派是理论政治派的主要组成部分。理论政治派从思辨的哲学入手,对德国的政治制度的现实进行批判。他们主要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13]批判的出发点和对象都是自在自为的概念——国家、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14]批判所使用的武器及对象全部是来自黑格尔阵地的。这种批判全然不顾现实的国家和现实的人,即是说,他们并没有完成对德国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是思辨的批判与经验的批判的错位,而且思辨批判的水平远远“高于”经验批判的水平。产生的结果只能是这样:“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15]马克思在《问题》中认为,鲍威尔的宗教批判软弱无力,他仅仅停留在思辨的政治批判而没有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经验中去,并在逻辑上将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类”的解放与每一个“个人”的解放混淆了。事实上,“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6]
理论政治派的缺陷与其思辨的抽象程度成正比。愈是经验贫困之处,理论政治派(或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批判就愈加神秘。依据鲍威尔的思维逻辑,因为犹太人“不用完全地、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马克思立即推论:“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7]也就是说,民主制国家的完成,是政治解放的最终目的而非人的解放的前提。青年黑格尔派坚信,如若不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政治解放。马克思驳斥了这一错误观点:与人的解放的无限性相比,政治解放是有限的,而“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8]由此可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分离的。显然,理论政治派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及其结果,表明他们在市民社会的本质和政治国家的表象的同一性上失足了,他们不仅丢掉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普遍性”的存在,而且把这种普遍性演绎成政治社会的“经验单一性”,哲学的逻辑学颠倒了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真实关系。
三、对实践政治派的批判
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否定德国哲学,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马克思立刻又说,实践政治派与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消灭德国哲学的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因此,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消灭哲学。如果说,理论政治派的错误表现出它的狭隘的眼界,“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19]那么,实践政治派的错误在于,它一面已经认识到“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20]另一面却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现实出路在于它自身,在于用“实践”的方法批判德国的现状。简言之,实践政治派仍然恪守了抽象的思辨的逻辑。抽象的思辨既是实践政治派研究经验的现实生活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国家观、市民社会观的逻辑和结论。较之于青年黑格尔派,实践政治派只不过多说了一句“消灭德国哲学”的话语,其真实现状和思维逻辑与青年黑格尔派无异。无论是理论政治派还是实践政治派,都不能为人的解放找到现实的出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理性的革命的要素——这也注定他们只能以思辨的逻辑统摄一切思维和思维的对象,而且思维世界的产物以概念的抽象存在物的形式出现。为了德国的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它们终究不能提供一点唯物主义的东西,是彻头彻底的唯灵论。
马克思自问自答地解决了德国现实的问题与出路的矛盾。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21]只有彻底的理论才具有现实的说服力,马克思回答:“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2]这一论断是对《问题》论点的持续深化。无论问题的形式还是内容,都表明了《导言》和《问题》的一脉相承的逻辑关联。在《问题》中,马克思对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实现了政治解放的祛魅并发现了人的解放的本质;在《导言》中,马克思实现了由思辨的理论领域向现实的市民社会领域的转换,将人的解放从宗教的政治天国复归为经验的市民社会中去,意味一种对思辨的精神实现经验性的改造的可能性——将思辨的能动性引入感性直观的领地——这是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明确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整阐释了的东西——“纯粹经验”的方法,以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相区别。而一切在这里已经出现了萌芽,这就是马克思的那段经典话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23]
这段论述是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意识形态向科学转变的中间环节,是在纯粹思辨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的思维革命的中介物。它意味着“实践”解决问题存在另辟蹊径的可能性,而这与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的“实践”全然不同,它是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群众”表明,马克思已经发现了神秘的思辨逻辑的秘密——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外部关系中发现的,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市民社会内部,没有深入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这已经超出概念活动的单一领域,抽象的概念运动必须让位于经验世界的目的性,以此发现弃置在概念“容器”中的物质世界的现实存在。我们必须甄别,上述用语是“政治社会”的还是“市民社会”的,是遵循了思辨的逻辑还是“纯粹经验”的方法。笔者的结论是:马克思批判的形式与内容并不同一,他的批判意识业已实现未来完成式,但内容尚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人的解放与类的解放的关系辨析上,批判的对象还没有随着政治经济学一同在市民社会内部建立,即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整体仍是未来完成式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定批判的意识已经实现了它的所有目的。
四、经验的逻辑: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问题》到《导言》
本文开篇有言:第一,我们所采用的论证材料主要来自于《论犹太人问题》而非《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尽管我们不排斥引用它;第二,《导言》是《问题》的延续和深化。读者难免会对上述两点产生异议,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传统书写方式有所不同。笔者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
(一)三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以下时间标注选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1)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它“写于1843年夏—1844年秋”,[24]“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中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主要段落《国内法》第261—313节进行了批判分析”,“标志着马克思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时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25](2)关于《论犹太人问题》。它“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是马克思早期的一篇重要著作”,[26]“文章就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展开论战,从而导致后来对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原则性批判”。[27](3)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它大约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1844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28]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掌握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的原理”,“《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29]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时间在《全集》注释中还有一处标注:“马克思大约于1843年3月中到9月底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30]这与正文文尾处的标注时间是有出入的,注释处标注时间范围远远长于正文处。考证它们的时间顺序,相信已经令我们的文本学专家大伤脑筋,这一点的前后不一致,我们暂且搁置一边。
但我们毕竟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三者的写作时间相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原本是“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似乎应在《导言》之后形成,事实上,我们现在读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极有可能写在《导言》之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说他曾经“加工整理准备付印”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材料,而且材料的内容涉及“法、道德、政治等等”,——这与《法哲学原理》著作的全部章节:“抽象法、道德、伦理”是一一对应的,说明他的确“已经”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全本,马克思对《法哲学原理》进行了“反杜林论”式的批判。[31] [32]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谈到要重新加工整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我们现在整理出版的只有XL印张,且第I印张丢失。批判的内容显然很窄,而且就文章的全部内容来说也不规范,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全本的认知,《导言》的论证基础明显来自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问题》《导言》的批判水平进行评判,《导言》所体现的马克思的思维水平最高、批判力度最大,论题和论点的复杂程度也深,马克思亦最为重视《导言》,并将它寄送给费尔巴哈拜读,此后多次提到《导言》的现实意义,并对法哲学批判本身表示出不满意。①一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下面就会谈到,一次是在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谈及法哲学批判“并非通俗易懂”。
(二)三篇文章的写作风格。《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采用完全评注式的方式,摘抄一段《法哲学原理》中的章节,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写下评语,马克思亦称为格言式的叙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曾抱怨格言式叙述的弊端:不能避免地将“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很多地方,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将经验的材料与思辨的推论混淆了,并一一进行更正,“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制造体系的外观”。[33]这就说明马克思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叙述方式很不满意。《问题》采用半摘引半评注的方式,这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有所区别。马克思抱怨鲍威尔的观点“还是太抽象”,[34]因此,以鲍威尔的两部著作为批判的材料,“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就成了马克思写作《问题》的使命与任务——马克思对宗教国家、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以及政治共同体的解放与人的解放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至于《导言》,应该说呈现了完整思想,文中不仅没有再做任何的摘引,而且确切地表述了哲学与现实、国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作为分析的目的论的需要,笔者认为《导言》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凝练与提升。由此可见,由于写作风格的不同,三篇文章所揭示的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也不同。
(三)三篇文章的逻辑关联。上述两点都将服务于将要进行的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经验观进行了两层含义的批判。一是批判黑格尔对待经验的事实的态度,“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十分尊重,可是,当这些东西以现实的经验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又真的是鄙视它”。譬如,在《法哲学原理》第283—284节里黑格尔描述了大臣的权力及其起源,马克思一边称赞“黑格尔在这里纯经验地描写了大臣的权力”,“思辨的因素在这里是很少的”,然而一边又抱怨黑格尔“把这一‘经验的事实’变成存在,变成‘王权的特殊性环节’的谓语”。[35]二是斥责黑格尔将经验的现实全部纳入思辨的范畴,实体性的经验世界不过是哲学的逻辑学的中介物或手段,是抽象的概念范畴的“容器”。故而,马克思说:“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36]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经验观也蕴含着两个层面:第一,有意识地区分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认为经验世界是研究的出发点,对感性的经验材料需采取批判的态度,批判黑格尔“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作观念的现实真理性”,[37]以及由此造成的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的混乱,同时尖锐地指出“这种混乱表明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38]第二,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对思辨理性的批判与对感性经验的批判是分离的。马克思一方面复归了经验世界的存在并予以保护,一方面又遵循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学”去考察理性世界的概念范畴,“是否合乎理性”成为马克思思维的现实依据、标准。即是说,马克思的思维是在黑格尔哲学内部进行的,所谓思维领域的革命是在黑格尔阵地上发生的。
《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经验观。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表明马克思有意识地区分了经验领域和思维领域,一面还原了经验世界的物质性,一面又应用并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学,并且证明了他的思维方式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那么,《问题》尖锐地指出经验世界和思维世界的冲突、经验事实的感性与纯粹思辨的抽象的矛盾,批判鲍威尔的宗教解放无非是政治解放的幻象,得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的结论。[39]这一结论具有革命性意义:马克思构建了思辨世界通向经验世界的桥梁——国家制度和政治解放,由于人的解放兼具两种属性:市民社会层面的人与人的利己本质相异化的感性直观和政治社会层面的人与政治共同体相异化的抽象理性,马克思也就指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40]马克思分析并肯定了存在着的政治解放的现实性,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的国家制度、政治解放的纯粹思辨性。
《导言》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抽象思辨的全部神秘性,并尝试进行经验世界对理念世界的批判。如果说,《问题》证实了政治解放的两层属性,马克思有限度地承认了政治解放的经验性;那么,在《导言》中马克思则对政治社会与政治解放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指出政治解放并不意味它自身就是人的解放、普遍解放的一部分,相反,必须从经验世界出发全面否定政治解放自身及其幻想。“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41]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国家“以它的一切现代形式包含着理性的要求”,“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42]原因在于“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43]所有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们都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44]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也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现在,“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45]“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46]只有消灭了德国哲学,才能实现德国哲学的现实。至此,马克思提出了将要对整个思辨的德国哲学展开批判、使哲学变成物质的任务。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经验的批判与思辨的批判是分离的,经验的批判还是不完全的。马克思尽管还原了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并未对其做出批判的分析,他的思维依然遵循了黑格尔的哲学的逻辑学,对待现实的感性材料主要还是“经验主义”的,还没有实现经验批判与理性批判的逻辑统一。而在《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朝着经验批判与理性批判内在的同一的路径前进了。
五、结语
无论是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还是对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的批判,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市民社会内部中去,尽管它们理论地阐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作为“市民”的人的解放和作为“公民”的人的解放的关系。直至马克思写作《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才自觉地谈道:“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没有让·巴·萨伊、亚当·斯密、约·拉·麦克库洛赫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有恩格斯的“天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蒙,没有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实践,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性的批判,也就没有历史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1843年的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及“他的困惑”,仅仅针对政治领域的经验性批判仍是不够的,“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惟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47]必须由纯粹的政治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这中间,费尔巴哈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直至“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48]故而,1844年前后,马克思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毫无疑问,这一转变过程是渐进的。
[参考文献]
[1][3][9][11][16][31][39][40][41][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4、5、4-6、46、111、38、28、14、10页。
[2][4][5][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229、230-231、231、238页。
[7][10][1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1页、第251-260页、导论第1页。
[12][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3][35][36][37][38][47][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0、206-207、207、180、170、206、207、207、207-208、207、160、649、198、655、214、658、657、219、47、52、51、48、200、220页。
[3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目录。
[34][42][43][45][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65、64、64、66页。
责任编辑:罗苹
作者简介高惠芳,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北京,100101)。
〔中图分类号〕A119;B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