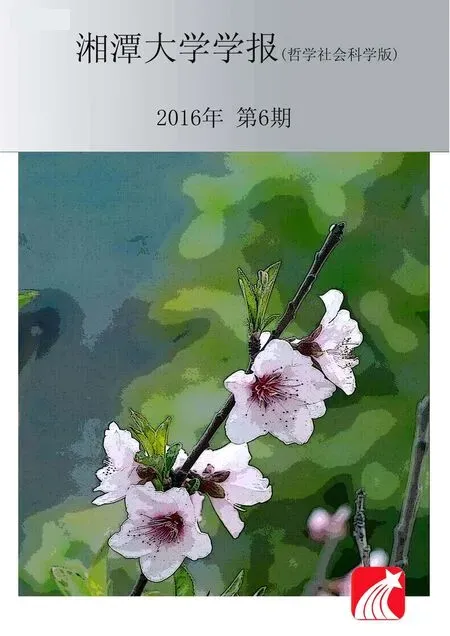文论建设与“中国经验”*
刘淮南
(忻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中国经验与文论建构”专题研究
文论建设与“中国经验”*
刘淮南
(忻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中国当代文论缺少原创性的原因既与中西文化大碰撞中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和根深蒂固的依附性思维方式分不开,也与威权主义相关联,由此也造成了西方话语的大行其道以及不顾国情的强制阐释。今天的建设需要从社会实际和文学实际中蕴含的中国经验出发,以中国立场和人类情怀作为努力的方向。
文论建设;中国经验;人类情怀
一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西方话语的突出无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表现在于: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文学实际,中国原有的“诗文评”无论从形态上还是实用上已经明显不适应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际。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的条分缕析和逻辑思维的严密性以及研究问题的具体性、深刻性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自然,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西方话语的凸显同样难以避免。比如,1920年,梅光迪最早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文学概论”时就是直接采用了英国温采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1]68。同时,在西方话语的使用当中,也确实产生了不少过去难以看到的成果,这些实际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国人对西方话语的推崇。所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已经很难避免西方话语的影响。即使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还是采用了“诗文评”的形态,而且其核心概念“境界”更因为具有独创性,从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其“隔”与“不隔”等术语又同样免不了西方话语的制约。换句话说,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纯粹的传统话语已经很难看到,西方话语在渗入了不少学科和人们思维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成为尤其突出的领域。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文论观点共时性地涌入,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更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成为西方话语的忠实追随者,将西方文论作为圭臬,而并不考虑是否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文学实际,因而也出现了不少词不达意、文不对题的笑话。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西方话语并不就是与中国文学完全隔绝的,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的理论来回答,西方文论只能解释西方文学。但是,所有的西方文论都对中国文学有效吗?或者说,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以西方文论为标准码?特别是,当我们引进了那么多的西方文论、而且多年来的结果又难以使人满意时,对之的反思同样难以避免。在有关的反思中,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威权主义的影响等均为人们所涉及,特别是近两年来对“强制阐释”的强调,可以说,都涉及了制约文论创新的因素。然而,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恐怕还没有很好地为大家所重视,而这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中国文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其实,我们都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个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实际中的操作却又未必始终如此。从西方文论出发衡量中国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很多人的习惯,中国文学的实际以及这种实际中蕴含的理论,往往不被人们关注,或者说,在西方文论的视野中,中国文学的实际和经验并不是人们看重的内容,也不会成为进行总结和提炼的主要对象。也可以说,“拿来主义”成为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比如,王文生曾经提到,在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中,由于受到了反映论的左右,使得“钱钟书选诗的目光,集中于反映宋代重大社会生活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方面。他吃力地维护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这个理论和标准……钱钟书苦心孤诣地从为数不多勉强被解释为反映生活的诗篇里,选出许多被时间所湮没、为读者所遗忘、遭论者所忽视的诗,充其量也不过是符合反映生活标准的诗,而说不上是宋诗的精华。”在举出该选而没有入选的相关例子后,王文生又引用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回忆:“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由此可以说明的是,“钱钟书……错误地片面地接受了以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作为选诗的标准,而在实践中又发现这个标准与宋诗实际扞格不入。”[2]78-88
显然,由模仿说演化而来的反映论是西方文学土壤中的产物,它只能解释部分的中国文学,而不可能概括所有的中国文学。所以,将反映论作为唯一标准的做法,从1980年代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比如,程麻就觉得仅凭反映论难以说明文艺问题。[3]97-113王一川也谈到:“从本体反思出发,艺术不仅仅或不主要是反映,而从根本上说,它是体验,从人的存在这一本根深层生起的体验——这是存在的体验,生命的体验,真正人的体验。它关注的不仅是认识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全面地、深刻地显现生活的本体、奥秘——即体验生活。”[4]
这就导致了一个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有些西方话语可以解释一些中国文学的现象时,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它在客观上也开启了新的感受、理解这些中国文学现象的大门。比如德国美学家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和伊瑟尔提出的“召唤结构”对于阐释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接受而言就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当有些西方文论不足以解释中国文学的事实时,强行使用,只能是文不对题,隔靴搔痒。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以“境界”为核心概念展开评论的,由于这一概念涉及创作主体的属性,“是一个‘生命—主体论’的问题,用于指称诗人时是指诗人生命主体的审美特性”,所以,一百多年来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喜爱。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受到西方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材料共同影响的结果。也可以说,“境界”说虽然流露了“西学义谛”,“但由于与中国固有之材料相融合,达到了理论上的化境,亦西亦中,既非传统之简单的顺承,亦非外来之简单的模仿,完全是一种创新。”[5]89-95尽管如此,我们又看到,同样是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又是一对脱离了中国文学实际而纯粹移植西方话语的概念。我们知道,王国维深受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其“不隔”恰恰是叔本华“直观”影响下的中国翻版。比如,叔本华就明确强调:“每一认识,每一直观,只要仅仅是直观意识到的,还没有在概念上沉淀的,都是人们感到的。”[6]91于是,“不隔”的景物是可以“直观”的景物,“不隔”的感情是可以“直观”的感情。这样,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提出后就成了具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朱光潜、唐圭璋、饶宗颐等学者均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饶宗颐针对王国维“隔雾看花”的说法就指出,“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损其美,反益彰其美。”[7]209而且,中国人习惯以“显”与“隐”来看待文学艺术的效果,所谓“比显而兴隐”(刘勰)、“以隐胜不以显胜”(饶宗颐)等等。
王国维“隔”与“不隔”的例子说明,解释中国文学却离开了相应的土壤,不是从中国文学的事实及其经验出发而是将西方话语作为标准,必然会导致“根基”的失落,乃至于观念和实际相分离,从而出现令人难以认同的事实,这些事实使得一些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也使得另一些人将西方话语作为圭臬,用来衡量一切。由此也使得中国学术界过一段时间就来反思,过一段时间就要调整基本思路,但是调整后的落脚点依然难以回到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和相关经验上面。
二
我们看到,张江教授近年来关于“强制阐释”的文章,对西方当代文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反思,对中国当代文论如何恰当地借鉴西方当代文论具有积极意义,对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联系中国当代文论的实际时,我们又需要关注到中国当代文论之所以受西方话语影响、以致于出现种种脱离中国文学实际的原因。也就是说,看到强制阐释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大行其道对于中国来说只是外因,而其所以存在还有着需要进一步辨析的内因。没有内因,强制阐释在我国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市场。而探讨这种内因,需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二是威权主义对中国文论不可低估的影响。
大家知道,从19世纪中叶开始,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国门后,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自尊心和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逼迫的而非自觉的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导致的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中,“别求新声于异邦”,“破中国之萧条”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然而,在看到这种接受的同时,又应该看到,这种接受的前提中还有着中国人多年来的思维方式,即,长期的集权专制社会使得人们普遍形成的思维上的依附性。尽管说,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对专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触动,但是,这种触动基本上又是在思维内容方面、价值取向上的由中而西遮蔽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而这也导致在1980年代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接受中,不能深入考察这些文论的产生背景,不能结合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生吞活剥、照单全收的情况大量存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事实和经验还没有被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上。
在看到上述原因的同时,还应看到威权主义的影响。就此方面,支宇的意见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反本质主义”对当代文论的反思及其观点,他提出:“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是‘威权主义’知识生产机制。”“文艺理论家们从根本上丧失了设定文艺视角、确立研究立场的个人性和多样性,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政治意识形态身后来辨识早已先行设定了的、唯一的文艺‘本质’。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本质主义’的根源在于‘威权主义’。”[8]15-23确实,就中国当代文论而言,本质主义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本质主义呢?反本质主义的有关学者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而支宇的分析将之继续下去了,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将问题认识得更为清楚。所以,反本质主义简单地套用西方后现代思想,简单地将中国当代文论中的问题归结为“本质主义”,而看不到深层次的威权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强制阐释”。
不管怎么说,建设意识对于广大的文论工作者还是显著的,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探讨,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对中国经验的重视中,又有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现代文论传统的强调。对之,我的看法是,无论是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一样,作为资源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又都不应该成为今天的基本出发点。从古代文论来说,作为文化血脉和营养,今天的文论建设需要它们,但是,今天的生活实际和文学实际毕竟不同于古代,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为大家所认识。再从现代文论来看,虽然与今天距离更近,但同样应该注意的是,从现代开始的文化转型并没有完成,现代文论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形态,用它来阐释今天的文学实际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上面提到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以及在无所适从中所选择的对西方的依附同样体现在现代文论中,而威权主义在现代文论中同样已见端倪,比如对苏联“拉普”某些理论的照搬。这些事实说明,今天的文论建设只能够立足于今天的社会实际和文学实际,只应该从中国的文学经验中予以提炼。
然而,从今天的社会实际和文学实际出发提炼自己的文学经验又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这恐怕才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提出立足于今天的社会实际和文学实际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广泛的社会实际和文学实际中的具体选择。
从近代开始,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转型中,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到1980年代以来,这种并不纯粹尤其令人瞩目。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实际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影响,这也使得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中必然包含着世界性的异质文化因素。也可以说,提炼当代的文学经验应该具有全球视野,也应该具备人类情怀。我们不否认“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依然需要我们的坚持,但是,这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已经不会仅仅局限于“中国”也是肯定的。或者说,中国立场、人类情怀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应有的态度。
这样说的意思是,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对象是中国的生活实际和这种生活实际中的人,是这些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自然,由此出发的中国文论难以离开中国立场,更何况中国文学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所描写的对象,表现的人物,体现的人性,固然应该具备时代的、地域的特征,但是当其达到相当的人学地步,或者说达到相当的成熟程度时,一种人类性同样会蕴含于其中。也可以说,人类心灵的相同之处在这样的文本中可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自然,其人类情怀也同样需要总结。
三
举例来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一句》)作为作者“最成熟、最大气”也受到读者和批评家广泛关注的作品,就是一部具有中国经验、值得好好提炼的文本。从现象层面而言,普通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卑微、底层和阿Q精神,在小说的众生相中表现得可谓丰富多彩、淋漓尽致。以上部“出延津记”的主人公杨百顺来说,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父母的情爱与呵护,13岁时因为丢了一只羊,患着打摆子的他不仅被父亲打得满头血疙瘩,而且还被赶出去找羊而露宿野外、有家难回。后来,得知父亲在他与弟弟杨百利谁去“延津新学”上学一事上做了手脚才使得自己落空后,终于气愤地离开了家庭。离开家庭的杨百顺跟人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但是都没有立住脚。虽然在进入县政府给县长种菜后,算是有了份正经营生,而且又“嫁”给了寡妇吴香香,可是,却因为县长老史的离职而被新任县长老窦赶出了政府。之后,吴香香又因为奸情暴露与奸夫老高双双出走,还给他留下了继女巧玲。而已经更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出于面子和舆论压力只好出门假找私奔的妻子,期间又丢失了继女巧玲,无奈中的他最后到了咸阳才算是娶妻生子立住了脚。小说的下部“回延津记”的主人公牛爱国同样有着类似于非血缘的外祖父杨百顺的遭遇,同样是在妻子与人私奔后出去假找,而真找的却是咸阳“亲人”的几句话。
可以说,就《一句》上部中的芸芸众生而言,虽然彼此之间在伦理上、关系上可能是亲近的,但在心灵上又是疏远的,没有亲情,缺乏信任,只有算计和猜忌,甚至是暴力,尽管如此,他们又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品质恶劣的坏人。所以,鲁迅当年所说的“沙聚之邦”由此也可见一斑。虽然说,这些芸芸众生类似于鲁迅所说的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但是对于刘震云来说,又未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是在强调或者突出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存在和交流的重要。而这种交流又不一定是在亲人之间:杨百顺小时候不是与自己的父母、兄弟亲近(甚至还在心里杀过他们),而是与李占奇要好,要好的原因又是因为共同喜欢罗长礼的喊丧。杨百利与老万这个外地人第一次见面就因为喷空而成了好朋友。因为人与人的隔膜和难以交流,染坊的东家老蒋和下部“回延津记”中汽修厂的老马是喜欢猴子。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作者刘震云在其演讲《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中对“孤独”之于小说和中国人的强调:由于中国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9]92-100虽然他没有更多的说明,而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生态”的特殊性除了宗教维度的缺乏以外,还与集权专制的长期存在关系密切。这也说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养育了中国人的同时,也产生了中国人的隔膜和孤独,因为隔膜和孤独的存在,所以,也显示了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性。而在此方面,刘震云的态度同样十分明确。当他认为《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的“好”是体现在作家的“态度”和“胸襟气度”上时,我以为他本人也在努力开阔自己的胸襟并修炼自己的气度。表现在《一句》中,这种“态度”和“胸襟”就是对孤独的展示和对交流的寻找。从作家来说,当他体验到并且写出了一种经验、尤其是一种中国经验时已经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从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却需要对这种中国经验进行提炼,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而难以上升到理论,将是理论与批评的遗憾。
托尔斯泰关于艺术的一段话是大家熟悉的:“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种感情。”[10]516托翁还说过:“把新的感情(无论多么细微)带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10]518刘震云在《一句》中表现了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还没有为别人表现过的隔膜和孤独,以此与人们来交流,来共同分享,出版方冠之以“千年孤独”,也正是因为小说涉及了中国人心灵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历史来说,小农经济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既培养了中国人的勤劳,也导致了他们的短视,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集权专制下,芸芸众生不仅在地位上是卑微的,心灵上也是隔膜的。自然,心灵安宁成为多少年来的实际问题。
从现实来说,文化转型的社会实际同样带来了人们心灵安宁的问题,物质的富有并不能够解决心灵的迷惘,相反还可能增加这种迷惘,自然,孤独感在今天人们的心灵中依然存在。言说之难、言说之苦依然是今人难以排除的情感实际。
那么,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应该如何关注这种心灵问题呢?如上所述,我们不否认反映论对于中国文学的解释,但是,放弃或者忽视抒情写意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显然又是不应该的。刘震云在演讲中对“表现生活”(我理解就是“反映生活”)的习惯说法不屑一顾,同样启示我们不要忘记文学的根本,不要将文学与其他领域混同起来。正如张江所说:“文学有为时代服务的功能,借古喻今有特殊的历史力量。但是,这不是文学的批评和理论,而是文学以外的批评和理论,譬如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等。”[11]
小说《一句》中传教士老詹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放弃信仰的人物客观上也值得我们尊重。虽然,他在几十年的传教中只是发展了八九个信徒,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努力。虽然,他想给中国的芸芸众生推荐一位新朋友,然而,他推荐的朋友在中国人这里还是水土不服的。所以,老詹给人们的启示同样是重要的。起码,他没有进行“强制阐释”。
可以说,蕴含于《一句》中的中国经验和文学问题是丰富的,不少学者已经对之进行了很好的评价与阐释,如若能够从相似、相同或者相反的例子中引出基本问题、并不断予以提炼的话,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肯定会别开生面。
[1]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王文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下)[J].文艺理论研究,2007(3).
[3]程麻.仅凭反映论难说明文艺问题[J].当代文艺思潮,1986(5).
[4]王一川.本体反思与重建——人类学文艺学论纲[J].当代电影,1987(1).
[5]刘锋杰.王国维“境界”说:一个“生命-主体论”概念[J].河北学刊,2015(6).
[6]饶宗颐.澄心论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7][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 [J].文艺理论研究,2006(6).
[9]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J].名作欣赏,2011(13).
[10]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11]毛莉.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16.
责任编辑:万莲姣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hinese Experience”
LIU Huai-nan
(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XinzhouTeachers’University,Xinzhou,Shanxi034000,China)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origin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deeply dependent way of thinking in the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I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uthoritarianism.This is also resulted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of western discourse and disregard of national conditions.Today’s construction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and literary practice in Chinese experienc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China’ s position and human feelings.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Chinese experience; human feelings
2016-07-08
刘淮南(1958—),男,山西省代县人,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I0-02
A
1001-5981(2016)06-00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