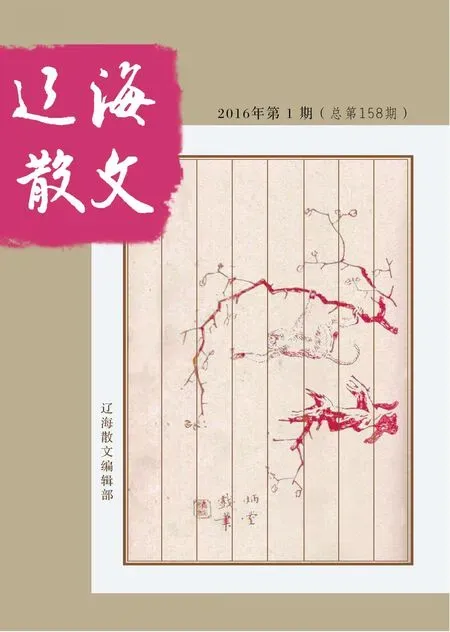先锋散文的真诚性虚构
——读周晓枫散文《禽兽》
林晓波
先锋散文的真诚性虚构
——读周晓枫散文《禽兽》
林晓波

林晓波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四川工商学院。作品载《光明日报》《诗刊》《星星诗刊》《中国诗人》等报刊,有作品获得《人民文学》征文奖等,并多次被收入中国散文诗年选集;公开出版个人作品集3部。
2015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周晓枫的先锋散文《禽兽》。拜读之后,我在追问:先锋散文奇异、精致、鲜活的意象来自哪里?先锋散文作家透彻、犀利、奥妙的感觉又源于哪里?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我注意到冯牧文学奖对周晓枫散文的评语是:“她的作品文体精致、繁复,别出心裁……她对散文艺术的丰富可能性,怀有活跃的探索精神。”再看周晓枫在《虚构者的道德》一文中说,许多人认为写散文必须如实汇报,虚构是被禁用的巫术。但我坚信,无论多么貌似真实的写作都隐藏着对现实的修改——也就是说,一旦落笔,必然伴有虚构……而周晓枫用散文《禽兽》,证明了散文的先锋性,就是对传统散文“真实”的超越——真诚性虚构。
周晓枫的散文《禽兽》以10个片断结构,写了10种动物的本性,实际上揭露了人性本质,其背景深远而意味深长,与一般单纯写动物的散文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禽兽》的真实深刻,到了科学理论的真实程度。文中写了10种动物,用准确的语言写了动物的特性。例如,写蜥蜴的眼球:“厚实、涂满眼影的眼帘,总让人感觉它睡眼惺忪。但有时看到那甲亢患者般半凸出来的眼球——咦?它有三百六十度的双眼皮。环形眼帘,盔状头饰,鹦鹉螺一样盘卷的尾巴。”这样的文字,超越表象而逼近事物的本质,抵达另一种哲学深度。而仔细读仍感觉到是散文,不是一般的科普文章。因为她是用散文家的艺术眼光看那些动物。例如“浓墨重彩的变色龙从着装到表情,戏剧感很强”,其叙述、情绪、感觉、语调、节奏都与充满思辨性逻辑性的科研论文不同。
二是散文的诗性光芒,验证了真诚性虚构的力量。周晓枫擅长在凡俗中发现深刻的美与永恒的诗。在这篇散文中,她将科普语言的说明和诗歌语言的神采组合在一起,还能高度和谐,实属不易。例如,写蜻蜓的眼睛:“它的复眼,是由赛璐珞制成的两个大水泡泡,在凸透镜的效果里,我从中看到密集的黑点,让人昏眩……。”这一段文字有科学的说明,也有诗意的感觉。文字之间自然过渡而不留痕迹。再你看那些小标题,如“复杂的珠宝镶嵌”、“从罐子里倒蜜”、“它被施了魔法”、“他们占据了所有方向”,就是美妙的诗句,弥漫在文中散发出诗的芳香,让散文诗意盎然而更有魅力。在正文中,周晓枫将具体的动物写得很有诗意。如写蝴蝶:“从天下到地上,到处都有无辜的颤抖。蝴蝶不间歇地撞击着玻璃,小而温柔的纯响……他们几乎用一生在酝酿……但现在,飞蛾扑火般稠密而来,忘我地扑向它们的水晶棺——如此汹涌而壮烈的自杀。”这一段文字,分明就是现代的散文诗。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也是真实的。真诚性虚构,让散文有了更大的空间。庄重文文学奖的评语是:“她的贡献在于开辟了散文的另一片天地。”
三是《禽兽》的隐喻性,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也暗喻了背景的真实与生存的虚幻。散文的标题“禽兽”二字十分抢眼。自然让人想到中国民间 “禽兽不如”的俗语和“衣冠禽兽”的成语。这样的标题,在整体上定了散文隐喻的基调,也增加了散文的厚度和重量。在文中,周晓枫采用了多种方式写动物的本性,将人性的本质揭示得很彻底。例如,写骡子:“就像人类美丽的混血儿……作为进化结出的代表,继承了完美的基因,似乎亦无繁殖来更新和提升的必要。然而,隐藏其中是一种残酷的淘汰机制。”写蝴蝶的章节,更是直接描述蝴蝶的生存与灭亡,引申出人性的存在与消亡。这正是越过自恋、唯美和抒情的重重障碍,迫近生存真相。真诚性虚构,让散文的真实进一步拓展延伸,让散文写作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种散文的自由精神,正是中国散文一脉相承的优秀品质。
所以,周晓枫理直气壮地说,我从未改变散文的本质。散文《禽兽》的先锋性,体现了她为探寻和建构充盈、完整的意义世界所做的努力,再次证实了散文真诚性虚构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 孙洪海
老来做书虫
诸葛凹
董桥先生称喜爱读书的人为书虫,尤其人到了老年,能够静静地读书,有自己想读的书,读自己想读的书,或者能够读自己想读的书,实在是人生最后的充实。
什么书可读?董桥先生引用一位书虫的话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读50页才决定看不看下去;过了50岁的人用100减掉读书的年龄就是决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比如一位56岁的人应该读到第44页、63岁的人读到37页,到了100岁,就可以瞄一瞄书的封面断定这本书值不值得看!
身为书虫的人,嗜书上瘾,犹如喝酒贪杯的人一样,对书的不离不弃已成一种依赖,可对书的要求也会日渐苛刻,不好的书、不待看的书绝不会染指,甚至到了一定境界时,会连那些书的封面都懒得看,或许会要求作家写出他们喜爱的那一种。
老来读书,还是喜欢纸本的,有墨香,有回味,一页一页地翻,不用太匆忙,可以从后面看,也可以从中间读,可以翻来覆去地读,可以随意画上标记,做出眉批,而匆忙则是读书的大忌。年轻人或许为了实用,匆忙一些情有可原。可老年了,万事已不必匆忙,况且匆忙了一生也需要缓慢的日子,澄清一下自己的学识,慢慢地读书,读一些纸本书,感觉亲临了书中的场景,聆听了作者的话音,甚至“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董桥语)。
于是,董桥先生的体会是“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董桥先生今年已经七十有四,他经历了太多的文海沧桑,看到了太多的文人浮沉,他对读书的理解既有先哲的睿智,又有入禅的疏淡,如去到英国毛姆家,见到那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的书房,那位写出《人生的枷锁》和《月亮和六便士》的大作家抽着雪茄皱着眉头说自己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却远远地瞄着那一排排书脊在满足地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书虫的执着在于对纸本书的甘心与诗意,“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即使电子狂风吹斜了老屋子,纸本书的墨香会让人一直倔到底。董桥说。